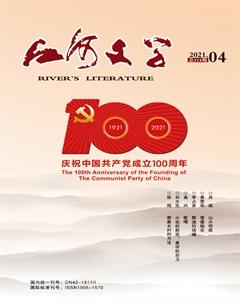疗 心(小小说)
薛培政
住进泛着土腥味儿的祖屋里,睡在父母留下的柴床上,他那顆按捺不住躁动的心,似乎终于找到安放的地方。
他觉得身痛渐渐消失,吃得香睡得甜。睡梦里,他的心被那幅久违的场景暖化了:幼时黄昏里,炊烟袅袅起,娘站在门前台阶上,扯开嗓门儿呼唤贪玩的他,“幺儿——回家吃饭喽——”悠长的喊声在村子里飘得很远。他醒来一摸,眼泪流了满脸。
娘在世时说:“俺幺儿从小不让人省心,这一走心就野了。”
三十年前,那个燥热的夏季,高考落榜的他,在家躺了半月后,起身站到了爹娘跟前,赌气道:“俺要出去闯一闯!”娘被惊得一愣,端在手中的水瓢“啪”地掉在了地上,惶惶地把眼睛转向男人。打过仗的爹心硬,拔出含在嘴里的烟袋,气哼哼地说:“哪里黄土都埋人,你有种就闯出一片天地来!”
他听了爹的话,顿感热血上涌,跪地给娘连磕几个响头后,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他到省城没几天,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就花光了。幸好有家地产公司老板收留了他,让他跟着老员工催收欠款。
他聪慧好学,又有主见,半年后就跑单帮了。为多挣提成,他绞尽脑汁,用尽办法。那年冬天,为按期收回500万元欠款,他在冰天雪地里蹲守半月,终于追到“玩失踪”的老板。那老板漫不经心地瞥他一眼,见是个嘴上没毛的雏儿,当即来个下马威,想打发他走:“小子,你要有本事把我喝倒,我贷款给你结清欠款!”那会儿,他感觉自己的心怦怦跳得厉害,却装作镇定地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接招了,直到把对方喝趴下,自己的胃也大出血住进了医院。
因他骁勇善谋,业绩颇丰,被老板赏识,一步步提拔上来。每次提拔,他的心都狂跳不止。
多年过去,等他做了公司掌门人后,那心便狂跳得按捺不住了。他拼命地融资拿地,扩张开发,直至成为地产界风云人物,过足了站在镁光灯下被媒体簇拥和圈内膜拜的瘾。
其实,他内心的孤独和脆弱,只有自己心里明白。长期超负荷工作,健康过度透支,年前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抢救一夜才醒过来,血管里放入三个支架。
住院的日子,来探望的人络绎不绝,个个来头不凡,他却感觉自己孤单卑小得就像一粒微尘。“23号,量体温!”“23号,打针!”“23号——”两个冰冷的数字成了他住院的代码,护士不时地呼喊着给他做这做那。
药物作用过后,术后痛感上来,闹得他睡意全无,不禁浮想联翩。一想起公司那些事儿,他就觉得心脏碰撞得厉害,想捂也捂不住,生怕放入支架的血管再出意外。说来也怪,只要想起村庄、爹娘、儿时玩耍的镇边小河,还有鸭鹅觅食戏水、牛哞羊咩狗吠声,他的心跳便平缓下来,心情也清爽多了。
出院后,他直奔阔别多年的家乡小镇,想在此疗养一段时间,给心找个安放的地方。
放眼望去,镇内小桥流水,鸡鸣鹅叫。春日暖阳下,徜徉在河边的人们,散步,观鸟,赏景。小广场上,一位老年艺人说着评书,听书的人围了一圈又一圈。
走在老街上,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爹娘去世多年,兄弟散居各地,他不想惊动旁人,便在自家老屋住下。旁边有家心悦茶社,他抬脚走了进去。正和人下棋的店主,斜望他一眼,指着烧得咕嘟咕嘟响的水壶,笑盈盈地打招呼:“茶叶在那儿摆着,想喝啥茶自己沏!”便头也不抬地盯着棋盘。他心生不悦:“哪有这样待客的?”他沏壶当地产的明前毛尖茶,边品边环视左右,伴着袅袅茶香,但见顾客下棋、聊天、阅读,个个从容淡定。他仿佛受到感染,顿觉全身轻松。再看那块“和局道商”的牌匾,他顿觉悟出什么,心底下对店家暗暗赞佩。
离茶社不远,有家“老何理发店”,开店的是其远房三叔,小时候没少光顾。三叔因战伤残,谢绝政府照顾,开起理发店。进店后,见陈设如初,却打理得干净温馨,坐等理发的顾客聊着天南海北的话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俩人打过招呼,三叔也没停下活儿,边忙边与顾客搭话。令他费解的是,虽顾客盈门,却每人只收3元钱。等人散去,他忍不住劝三叔道:“现在理发哪有低于二十元的,您这也太寒碜了吧?”三叔笑了笑道:“世上的钱挣不完,够用就行,再说‘有钱难买乐意,顾客信得过俺,知足了!”这番话犹如醍醐灌顶,他深吸一口气后,对三叔报以一笑。
回乡的这些日子,他仿佛穿越回了童年,故乡的一切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新鲜,行走在蓝天碧水之间,脚踩着祖辈们踩踏过的土地,他感觉到内心从来没有那么平实过,整个人倍感舒服惬意,疾病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要返程了,望着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祖屋和小院,他的心里禁不住涌起一股热流,耳际似乎萦绕着母亲那熟悉的声音:“幺儿,记着回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