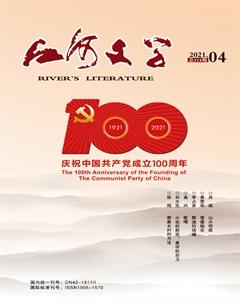河流向东
周火雄
一直不知道如何描述这个春天的遭遇。站在乱石塔前,我仿佛遇见故人,竟然有些激动。那一霎,只差眼泪没有流下来。乱石塔安静地挺立在还有些清冷的风中,日光镀在塔上,一半金黄,一半阴昧。2020年初,在隔离病毒的日子,我常常在心底描画阳光下的砖石,描画石塔上的花草。
阳光渐渐温暖,复苏的脚步愈来愈明晰,满头红的嫩芽已经萌发了,一簇簇,一撮撮,烂漫深沉。
虾哥,噢,我想到了虾哥。
一
二十四岁那年的冬天,我的腿已经彻底废掉了。我常常行走在县河岸边。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行走。内心里,只觉得有一团实物充塞,异常憋闷。我常常要喊出来。有一回我就喊了,不过不是喊,是唱,冲口而出就是样板戏里的唱词,挺英雄气概。这一唱真不是时候,已经是夜静更深。隔日,我的母亲就跟单位的老会计师吵了一架。老会计精于计算,他用一句精短的话语激得我的母亲跳起脚来,接着就是一通臭骂。那句话分明就是坚硬的棍子,指着我的残腿,却恶狠狠地戳在了母亲的心上。从此不唱,从此知道乱唱也是要命的惹祸端的。那个时候我开始了行走。我的行走是乱的,没有规律,白天走,有时候夜晚也走,黑灯瞎火,在河坝上的树林边一通乱走,然后变成一滩泥巴,瘫倒在草地。这时候才觉得胸中的充塞被抽走,块垒没有了,思想轻歌曼舞,我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只飞鸟,扑腾玄色的翅膀,在夜空掠过来掠过去,有了些快乐。这一霎,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的故乡,柳林河边的那个安静的村庄。那些尘封的记忆纷纷复活起来,尤其亲切,尤其透出熟悉的煙火。要命的腿病让我抑郁得不行,白天,我被父母催逼着穿上西装去上班,我坐在电话机旁,忙手边的事情,大半天不挪窝,我怕人,我怕自己走路的样子被人轻慢。我像个逃课的学生等待下课,左顾右盼,然后鸟一样慌不择路扑腾着飞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虾哥还有麻雀。
虾哥是剧团的编剧,那时正为他的剧本的青涩苦恼不堪。“北鲲,说实在的,我已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写作就是这个鸟样,没有丝毫长进,团长说我的作品是死鸟一只,缺少张力,什么是张力你知道吧,譬如有些好作品你看到这里想到了更多的美好的事情,譬如剧本结束了,你久久放不下,还在回味……”虾哥把一大摞稿纸交给我说,你看看,老弟,最好给我提点什么。我知道,虾哥这话是真诚的。这时候我哪里看得懂什么剧本,最多也就是门外汉。但是为了这句真诚的话我真该为他做点什么。我把他的剧本翻过来覆过去地读,先是寻找语病和错误的标点,接着是剧情的合理性,唱词与生活的距离,逐一标记在稿纸上,然后送给他。他挺感动,诚心诚意地说,北鲲你与他们不同,你是真的看了,是用心再看,不像有些人在糊弄。那一天,在虾哥的家里我认识了麻雀。麻雀是不起眼的企业工人,活得不好,自认为有些才华,说话做人吊儿郎当,一双手喜欢斜插在裤子的口袋里,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不止一次跟我说,我麻雀这是龙游浅滩被虾欺,总有一天会飞起来,一定会飞起来。说这话时他抠着鼻涕。于是虾哥笑了,我也笑了。许多年以后我没有见到麻雀,也没有麻雀的消息。后来忽然有一天他在福建打电话给我,才知道他在一家报社干得很有水色。他的文章,尤其是广告软文,点击率到了10万计,真是了得。
遇到虾哥和麻雀,这是我第一次找到文学圈子。我有了自己的快乐。
二
我已经好久不写作了。虾哥说。那就不写吧,生活是第一位的。先有生活再有文学,这是不可逾越的,你如果硬是要触碰,只会头破血流。不知道这是谁说的,这样的场景,竟然依样学样说给虾哥听。我知道虾哥的艰难,搞文化的看似清闲,但是每月拿到手的也就那么一点点,实在养不活婆娘孩子。其实麻雀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个看似活得透彻的人,内心在憋着,不知道为什么而憋,总归是憋着。他的梦也是压抑的,难得伸展。手头的拮据,以高就低娶了媳妇,以为会幸福,以为可以放手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鞋子如何自己的脚知道。那种若有若无的忧愁在麻雀的脸上甚至目光里时常浮现。十之八九不如意,这就是生活。比较起来,麻雀的生活更糟糕。他的方式是冷战。他可以十天半月裹着被子在沙发上熬到天亮。他的老婆受不了这样,不断地委托朋友去说合。她不知道这样的根源不在于此。这就是底层百姓的生活吧,谁知道呢。
我曾经到过麻雀家。麻雀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会去看他。他正倚在沙发上,嘴里叼着烟,一只脚搁在摇篮上,就这么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嘴里哼哼着,没有词。摇篮里的是他的女儿,大约一岁不到。啊哈,你老鳖的北鲲怎么会来了?嘻嘻,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麻雀竟然笑了。我怎么就不知道。路在嘴边。谁说的,孔子说的!啊,孔圣人说过这句话?烟火味太熏人了。看来他也不光是诗句里的蝴蝶,飞在人间之上。麻雀兴致高昂起来。不等我坐下就拿出农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泥娃子乐队》给我看。这是一篇写实的文章,文章反映的是乡村的一帮土音乐家组织在一起,活跃在村头巷尾,闹腾出了小气象。这在九十年代初着实是一件雅致的新闻。
这时候,我收到远秋的来信。信中远秋谈到她对文学的爱,对文学和生活的不理解。又一个对现状的不满。他们仿若纤夫,极尽辛苦地拉着自己的船逆流而上,什么时候能够进入理想的境界?但是,远秋的苦闷与麻雀不同,远秋是快乐的,她的不满足只是理想的船帆过于高远。
虾哥的二胡好极。常常是一个人拉着拉着,眼睛湿漉了。这时候,他是极其投入的,手臂摇动,心绪浮荡,奔流的情感在心之河放逐,流向遥远。促狭的麻雀这时候也不说话,目光游移不定,似有所见,似无所见,一种虚无恍惚的境界。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当我们头发斑白,忆及这段经历,心里还有许多的感慨。清贫、苦难的生活,因了这一缕飞翔的诗意,有了生存的希望,没有让灵魂遽然倒下。
这是虾哥最后一次给我们拉二胡。不久,他去了大都市,去了那所著名的戏剧学院。再不久,他的剧本有了飞跃,他终于忙碌起来……
三
我已有几年没去过虾哥的家。
虾哥打点简单的行囊,一个人走了,在都市,他有了一帮新的文学朋友。
我依旧在江北这座小镇混日子,写写散文,偶尔写写小消息,拉拉广告,换一些铜板回来交给我的母亲,买米,买菜蔬,买日用,把清寒的日子度过。年复一年的坚持,我的散文已经有了很大的起色,在文字的驾驭上,在写景状物上,已经进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境界。我已经摒弃了大量阅读,专门找来一些名家的专著,聂鲁达、郁达夫、朱自清被请到案头,漫长的夜晚,这些文字伴随窗外的虫鸣愉悦了寂寞的心灵。远秋也屡屡推荐一些书给我,但是,都是心灵鸡汤一类,隔几天就被疏离掉。为此她表达了她的不愉快。她喜欢云淡风轻、轻舞飞扬。她跟我不是同一个类型。兴之所至,她会热情奔放。她让你不知所云。常常在行云流水的序曲中,她突然咔的一下,让乐曲中断。你下定决心投入地向着她,她却退却了。是这样吗?我们。她眨着眼睛,画出了疑问。她的目光是一汪水,让你深陷其中,但是,不久她又遽然让你变成一只离开水的虾,在岸上大口喘气。她向往着自己是一只高傲的天鹅,在洁白的云端,霞霓围拥,百花娇艳,天使在曼妙的乐曲中翩翩起舞。
而我,蜗居在另外一个世界。
更加想念虾哥和麻雀。
一个冬日的夜晚,我和几个朋友从酒店出来。朋友兴犹未尽,硬要大家到舞厅消遣消遣。我的腿不好,从来不上那种地方。耐不过朋友的好意,只好答应去坐一坐。
七彩的灯光中,音乐大作。一群男女尽兴地游动在迪斯科当中。我记起一个文学朋友曾经神秘地告诉我,为什么人们喜欢迪斯科?那是性动作的模仿哦。其时,我谙然。我不懂女人。但是,这话我记下了。
又一曲音乐响起,我看到一个女人像鱼一样步着音韵游进舞池。那姣好的身材,美丽的脸庞,使我突然一惊,韵芝!是的,是虾哥的媳妇。
跟她一同游进舞池的男人始终在伴随她,形影不离。这个人就是先倒卖钢材后来开影院,再后来把影院变成养猪场又被村民告发的毛癞痢。
我溜出了舞厅,在寒冷的风中给朋友打电话,编了个离开的理由。
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虾哥?我在冷风中犹豫不决。
事情变得严重了。我给虾哥打了电话,电话中除了问他的学习,还让他回家一趟,大家想他。
虾哥没有回来。也许他早已把那个女人淡忘,也许功课忙顾不上回家。
秋天就这样不依不饶地来了。好几回我走过虾哥的院子。那个矮矮的院墙长满扁豆。阳光热烈地考晒扁豆的藤蔓,紫红的扁豆花儿静静开放……
日子风一样流逝。梅城的四季没有了虾哥,没有了麻雀,唯有我——北鲲,依然在坚持。正如鲁迅在《故乡》里的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样的一天,虾哥忽然打电话邀请我看戏。他说,这是他走出戏剧学院编写的第一部黄梅戏,感觉甚好,嘱我一定要看看。是吗,虾哥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哦,我一定前来学习,一定。虾哥笑了。北鲲,你还是这样,没变,他说。
戏未开演,我绕到虾哥家。依然熟悉的院墙,依然是熟悉的钢材焊制的涂上了银灰油漆的铁门。走进院子,没有人。我叫了一声,再叫了一声。虾哥喝得酩酊大醉,躺在竹床上。我摇晃着催醒他。见我进来,他迷迷糊糊,指着他的媳妇骂起来。他的媳妇愕然一惊,捂着脸,跑了。骂着骂着,他吐了。我为虾哥洗了把冷水脸,然后,掩上门,走进了剧院。
这是一部现代版凄楚而优美的爱情故事。他的大开大合的故事,浓郁的人间真情,超脱世俗的温暖情怀,博得观众一片掌声。就像一粒珠子,久磨终于成器,虾哥的才华终于在高等学府的磨砺中放出了光华。就是这部戏,带着虾哥一路走向更高的境地,先是在市里获奖,继而在省里引起叫好,最后,又走进了全国戏剧大赛圈。
那个下午,他找到我说,你请我喝茶。我们坐在那个有些阴暗的茶楼,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坐下。高挑的玻璃杯,那些好看的茶条在沸水中舞蹈。这是龙井的舞蹈,尤其有魅力。我们说到文学,说到戏剧,说到那些大作家的轶事,安静地度过了一个下午。我说,虾哥给我唱一段曲子。虾哥真就唱起来:
三呀更子里哎正好去贪眠
三更那个蟋蟀子闹呀么三更天
蟋蟀子那厢叫哎奴在这厢眠叫得那个小妹妹伤心痛心
小妹奴的干哥哥哎越叫越伤心娘把女儿问那
什么东西叫沉沉女儿回娘话哎妈妈娘你听清
三更那个蟋蟀子唏唏唏唏唏唏闹呀么三更天。
说到茶,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话题。期间,麻雀从杭州邮来许多茶叶,有我的,有虾哥的。麻雀说,茶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金钱美女也会有的。麻雀混迹江湖,已经染上了浓重的匪气……
我早已跟远秋不来往。在江湖,在乡村,我一个人慢慢行走,在行走中采撷。后来实在累了,就匆匆结婚,安静地过日子。两年后生下了孩子,早晨醒来,孩子已经飞跑着说给你鞋子,啪地丢在被子上……那么一个早晨,打开微信,一个陌生的加入者打着招呼,嗨,北鲲,这竟然是远秋。当初我该跟了你。她说。给她一个笑脸。从此不再联系。一个人的江湖能有多大……
虾哥沉默了。事业的顺利并未挽回婚姻的颓势,相反,促成了他的婚姻的解体。韵芝从此搬出了扁豆花儿静静开放的院落,留下他的老母亲守着院子。那个外表十分漂亮的女人早已离开那个属于舞厅的男人,远嫁了一个不为人记起的地方。
麻雀回来的时候带着夫人,洋娃娃一样精致。举起酒杯,虾哥在怀旧的音乐中流下了眼泪。他已是醉了。在饭桌上,他唏嘘着唱起:同是过路,同做过梦,本应是一对,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那是梅艷芳的《似是故人来》。
秋天,我依然在黄昏走过虾哥的小弄,走过那个扁豆花儿静静开放的院落。只是我没有再见到他。他已然带着他的那些作品,离开了这个世界。那条小巷,已经翻修了道路,平坦规整了好些。一个孩子在小巷走过,留下瘦小的背影。他是虾哥?但是,他是虾哥吗?“长说满庭花色好,一枝红是一枝空”,也许,好些年后,这里还有人在吟咏“门前绿树无啼鸟,庭下窗台有落花。聊与春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也许,岁月更迭,人事轮回,虾哥一样的人儿还在县河边构思最醉人的黄梅风情。
责任编辑:高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