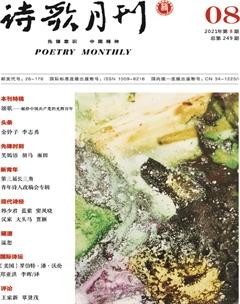关于《告别》一诗的创作
王家新
2018年前后,我母亲、父亲在不到半年内相继去世,这是我于2018年2月7日写《告别》一诗的直接背景。当然,更大的背景,是我对自己故乡和亲人的感情以及对我生命的一次“总结”。
我的家乡湖北省丹江口市,位于鄂西北山区(“机翼下,是故乡贫寒的重重山岭”),更具体一点,是处在武当山下、汉江河畔。我的父母为中小学老师,我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即使在早年贫困、艰难的岁月里,我也在接受故乡最美好、难忘的赠予。
2018年2月初,半身瘫痪的父亲在我母亲去世不到半年内突然“走了”(弟妹们说他“去找我们的妈妈去了”),我从北京匆匆赶回家乡。在父亲的丧事办完后,我没有回北京,而是乘飞机赶到上海给每年一度的“新概念作文大奖赛”做评委。诗中写到“一个新建的航母般大小的机场”,即武当山机场,它处在山脊上,也的确只有航母般大小。当然,用这个比喻,也正和“告别与远行”的主题相吻合。在隐喻的意义上,故乡也正可以看作是我们起飞和归来的“航母”。
而“飞向上海”,即从中国的偏远内地飞向东部沿海,似乎也比飞回北方更切合这首诗的“方向”(纵然我不是为了这首诗才飞向上海的)。
飞机“轰鸣着”起飞,这是一个重要一刻,带着我内心的颤栗。父母相继去世,我和故乡似乎有了一种“了结”之感。父母亲生前患病期间,我经常回去看他们。他们是我生命中最揪心的牵挂。他们一走,似乎也就断了我和故乡最根本的联系。临行前给父母最后一次上坟,并特意去看望二姨,这些都带有与故乡告别的意味:我在心里知道,以后我会很少再回故乡了!
但是,当飞机升空,机翼下展开故乡的山岭,我不仅有了一种最后告别故乡的情感涌动,我也更清晰地看到了从我们生命中如释重负“卸下”的一切。那时,也正值一场冬雪融化之际,诗中的意象和细节,因而也都带上了死亡、创伤(父母的死对我们不能不是一种重创)、忍受、抚慰和复活的意味。“是山体上裸露的采石场(犹如剜出的伤口)”(荣光启博士在评论该诗时就注意到括号里的这个隐喻),而它历历在目。我也不得不忍受着悲痛,尽力去看最后一眼这片我深爱的、埋葬了我的童年和一个个亲人的山川大地。
当然,不仅有远行人的回望,诗中的这些意象,还包含了一种故乡的“送别”:“是青色的水库,好像还带着泪光……”(我的故乡现在成了南水北调的主要库区),而到了“父亲披雪的额头,母亲密密的皱纹”这两个主要意象的出现,这首诗就达到了一个抒情高潮,对父母的感念也变成了对整个故乡的礼赞——他们已和这片山川大地融为了一体,或者说,一切都化为了这两个永恒的意象。说实话,写到这里时,我的泪几乎也要涌出,虽然我一直在“克制陈述”,而只用了像“披雪”“密密”这样的字眼,来传达内心的颤栗。
这是一首远行人献给故乡的“告别之诗”,它必然也包含了我对故乡、对我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望,“但此刻,我是第一次從空中看到它”——过去我们回故乡是坐火车,后来也开车走长途回去,家乡新建的机场开通后,我的确是第一次从空中看到故乡。但在诗中,这样写也具有更多的含义,因为我们只有拉开距离,从一个超越性的俯瞰视角才能达成对生命的“辨认”。“我的飞机在升高,而我还在/向下……”我也只能这样不断地回头“向下辨认”。
诗写到这里,每一句都不可变动,不仅出现了“父亲披雪的额头,母亲密密的皱纹”这样的核心意象,不仅看到了“一个少年上学时的盘山路”,全诗也形成了它自身的意义结构。纵然如此,它仍需要一个能与全诗相称的结尾。因为是在飞机上,是离开故乡的远行,我忽然想到了人们都熟悉的世界名著、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我为此而兴奋,因为那不仅是一个奇异的童话故事,它也暗含了一部一个人的“成长小说”,因此我决定把这种联想用到诗的结尾,同时我用了“但愿……”这样的语气,而“最后一次揉揉带泪的眼睛”这一句,还有意运用了某种孩子气的语言(在故乡和父母的眼里,我们也永远是个孩子),在飞向未知之前对故乡作了最后的道别。
但是,正如全诗和结尾所提示的,这是告别,也是开始,是满怀伤痛的辞行,但也是对“新的生命”的展望和飞越。我庆幸这首诗有了这样一个结尾。
就这样,这首诗在飞机上基本上就完成了,到上海宾馆入住后,当晩我稍加改动,落上了它的写作时间:2018年2月7日。
这是我生命中的一次蜕变和再生,也是我献给故乡的哀歌兼赞歌,它也在广大读者那里唤起了深深的共鸣。我在网上看到过许多让我感动的留言,在“中国诗歌网”2018年度十佳好诗评选中,它有幸被评选为“榜首”。
至于具体的写作,这首诗同我近年来的许多诗一样,我都在用这一句话来要求自己:终其一生,达到质朴。显然,这种质朴不是那种简单的质朴,而是“有难度的质朴”。这种质朴排除了炫技和任何多余的虚饰,它只尽力将生命的本真质地显现出来,但它并不排除精心选择最新鲜、独到、有表现力的隐喻和意象,也不排除独异的心智、哲思和想象力的运作。
正如这首诗所显示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向前走,或在悲痛中展翅(纵然有时还需要以泪水作为“燃料”)。所谓诗的生命,就是这样一个在不断的告别和蜕变中重获再生的永无休止的历程。
附:
告别
昨晚,给在山上合葬的父母
最后一次上了坟
(他们最终又在一起了)
今晨走之前,又去看望了二姨
现在,飞机轰鸣着起飞,从鄂西北山区
一个新建的航母般大小的机场
飞向上海
好像是如释重负
好像真的一下子卸下了很多
机翼下,是故乡贫寒的重重山岭
是沟壑里、背阴处残留的点点积雪
(向阳的一面雪都化了)
是山体上裸露的采石场(犹如剜出的伤口)
是青色的水库,好像还带着泪光……
是我熟悉的山川和炊烟——
父亲披雪的额头,母亲密密的皱纹……
是一个少年上学时的盘山路,
是埋葬了我的童年和一个个亲人的土地……
但此刻,我是第一次从空中看到它
我的飞机在升高,而我还在
向下辨认,辨认……
但愿我像那个骑鹅旅行记中的少年
最后一次揉揉带泪的眼睛
并开始他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