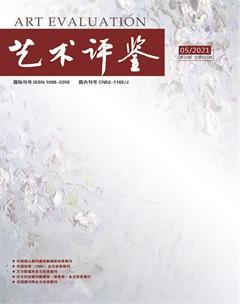民间舞原生态之浅见
王晓雪
摘要:20世纪40年代由戴愛莲先生发起把民间舞蹈搬上舞台,原本流传于各地的民间舞蹈自此之后作为一种元素融入艺术舞蹈走上舞台,在这一过程中,舞台上的民族民间舞蹈越来越和生活中的民间舞没有了可比性,加之近年来“原生态”一词的愈发流行,“原生态民间舞”也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本文重提“原生态舞蹈”这一话题,以藏族舞蹈为例,从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维度分析了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的藏族舞蹈,论述了何为原生态舞蹈、原生态舞蹈的形态应该是怎么样的以及其在当代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传承方式。
关键词:民间舞 原生态 藏族民间舞蹈 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J705
舞台上的民族民间舞以民间舞蹈为元素,将舞者与观众拉开距离,舞蹈追求完美,呈现出一种严谨性和娱人性。而生活中的民间舞供人们自娱自乐,没有地点、服饰、人数的限制,表现出一种随意性和自娱性,因为一直深藏在民间,舞蹈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蕴藏着本地民俗、宗教、道德、审美、文化等诸多元素。
一、“原生态舞蹈”之概念辨析
在谈“原生态舞蹈”一词之前,首先对“民间舞蹈”和“民族舞蹈”进行辨析。“民族”这一概念,并非自古就有,而是19世纪拿破仑发动全面战争之后所引发出的一个概念,它是被创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属于人类学概念;而“民间”则是针对于“城市”这一社区的一个民俗学概念。“民族”和“民间”有着本质不同,“民间舞蹈”和“民族舞蹈”更有着质的差异。民间舞蹈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它离不开民间,而民族舞蹈则是以民间舞蹈为元素、经过整理美化的舞台艺术。
“民族民间舞蹈”一词“将‘民族和‘民间两个词并列放置,其实是一种偏正关系,用‘民族修饰‘民间,是民族化了的民间舞蹈”,其结果仍然是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美学活动。
学科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简而言之,生态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和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基于此,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于1955年提出“生态文化”的概念,意在解释具有地方特色的独特文化形貌。“原生态文化”则是指在一切自然状态下生存下来的文化形态。“原生态舞蹈”作为“原生态文化”之下的子概念,是指在一切自然状态下生存下来的舞蹈形态。资华筠也曾提出关于“原生态舞蹈”的三个“自然”标准,即:自然形态、自然生态、自然传衍。
对于“原生态舞蹈”一词的解读,我们往往陷入以下误解:一方面认为原生态舞蹈是原生形态的舞蹈。一方面认为原生态舞蹈是生态舞蹈的原型。
这两种观点有一个共性,即将原生态舞蹈看成最初某一时期的一种舞蹈形态,且一成不变。但通过上面对“原生态”一词的理解,不难发现,其中并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反而是空间上的强调。故而,我们要认识到,原生态舞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某一舞蹈形态与它所处的生态系统结成的耦合体,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一直在适应它所处的环境,但是它的本质却一直不变——与其生存环境相辅相成,生于民间、长于民间、体现民间的文化以及民间人的思想。
二、藏族原生态舞蹈的形而下分析
这部分以资华筠提出原生态舞蹈的三个“自然”标准为依托,对藏族原生态舞蹈的表现材料、表现形式、舞蹈语言进行了详细论述,分别对应自然生态、自然形态、自然传衍。
(一)表现材料
舞蹈的表现材料是人体,为了使舞者更好地表现舞蹈作品,我们对舞者进行肢体上的训练。而原生态民间舞的舞者既是民间艺人,也是农民,更没有专业的理论和系统的方法进行支撑,人们凭借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无形中建构起一套巧妙而自然的训练体系。其实,与其说是一种训练体系,不如说是一种身体上的肌肉记忆和经验更为准确,而这些,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
在藏族民间舞当中,脚下动作居多,膝盖的屈伸、一顺边的动律成就了藏族舞蹈的特色。这与藏族人民生活的地域不无关系,广袤的青藏高原有草原、有林地,行走在草原上的动律不同于行走于平地,表现在藏舞中,成为双膝的屈伸;生活在林区的人们,为了躲避周围参差的树木,又不得不侧身行进,无形中形成一顺边的体态。原生态舞蹈从人体这一表现材料上说,离不开原生态的训练方式,只有长期沉浸民间的人才会具有,故从本质上说,原生态舞蹈离不开民间这一自然生态。
(二)表现形式
人类学家最初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论及舞蹈,总是会将其与巫术和祭祀仪式联系在一起,舞蹈被当成一种祭祀仪式用来与神灵对话,这个时候的舞蹈对艺术形式有着严格的要求,讲求以严密的形式渗透人的心灵。
但除此之外,人们更多时候以自唱自舞、载歌载舞的形式来自娱自乐,凭借自身独特的肢体动律、得天独厚的嗓音以及毕旺、扎木念等藏民族独有的乐器,呈现出一种独树一帜的民间舞蹈,这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自由进行的舞蹈,没有任何外在的雕琢。
拉萨河下游与雅鲁藏布江交汇的北岸,有一个靠打鱼为生的村落,名为“俊巴”渔村,历史上,这里交通闭塞、耕地稀少、又没有牧场,所以打鱼是唯一的生存方式,牛皮船不但可以帮助人们捕鱼,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在他们的舞蹈里,他们背着牛皮船,顿地为节,哼着或悠长或短促、或舒缓或热烈的船歌,不乏沧桑厚重之感,舞蹈在这样一种最自然的表演形式中诞生。
(三)舞蹈语言
藏族民间舞蹈的手部动作多以甩、扬、撩、盖、绕为主,女子温柔优美,男子粗犷豪迈,这些手部动作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无关联。藏民族地处高原,昼夜温差大,人们穿着宽大的袍子,白天热的时候脱下一只衣袖系在腰间,也是为了劳动方便;夜间寒凉,人们又套上衣袖做保暖之用。袖子一般长于胳膊盖过双手,舞蹈起来飘飘欲仙,极为优美,又可以作为道具延长肢体,充分宣泄情感。也正因为由长袖发展而来的丰富手部动作,藏民族又有“长袖善舞”之称。
基本步伐有拖步、踏步、点步、踢步、跨步、蹉步等,每种步法又在前后左右等各个方位进行发展,千变万化,富有活力,这同样离不开独特的地域环境和生活方式,藏民族是雪域高原上的民族,寒冷的气候促使人们用自己的脚奋力踏向地面,而藏民族又几乎是全民信教的民族,对佛的信仰使人们一直坚持徒步朝拜佛所在的圣地、一遍遍转经祈求众人安康幸福,对他们来说,一步步走出来的路意味着踏实和诚心。所以,在藏族舞蹈当中,脚下的动作极为丰富且变化万千,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舞蹈的独特韵律。
三、藏族原生态舞蹈的形而上分析
在原生态舞蹈自然传衍的过程中,一个民族世代传承下来的审美观念、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等都会被舞蹈这一形式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出来,这种自然传衍下的文化底蕴是原生态舞蹈最大的奥秘。
(一)自然而然的审美意识
藏族民间舞蹈遵循着一个“顺”字,长期的生活方式塑造了民间艺人的体态,比如前文提到的一顺边的基本动律、脚下动作的敏捷迅速、手臂动作的延展绵长,这些都不是刻意编创,而是在长期的生活中逐渐显现,藏族人民以身体最本真的状态和动律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一种舞蹈形态。舞蹈中也并不要求人数的多少,上下场也没有特殊规定,场面的调度从“一”字形到圆形也是在不漏痕迹间进行转换。这一切都是一个“顺”字在起作用,随“意”而不任“意”。舞蹈怎样变化,以什么样的形态发展,都是在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审美意识。
(二)积极乐观的社会意识
藏族歌舞中很少有悲伤之意存在,笔者认为有主观和客观两层面的原因:客观上,如萨迦·班智达的专著《乐论》中说:“那里定没有悲伤,神圣的音乐至高无上”。在藏族人民的心里,歌舞意味着快乐,是喜悦欢欣的代名词,所以不管唱歌或跳舞,人们都必须以热烈的情绪去表达,比如昌都果卓的深沉豪迈、热巴鼓舞的激昂奔放、弦子的柔美绵长、囊玛的优美典雅、堆谐的灵巧欢快等。
主观上,则是人们长期以来的一种处世心态在起作用,这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原因。藏民族自古以来一直生活在广袤的雪域高原上,广阔的天地给了藏族人民广阔的胸怀;在盛行千年而不衰的藏传佛教影响下,人们始终相信神明无边,反馈给自身的同样是无边的心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广阔的胸怀,人们才开始以歌舞的形式缓解着劳动的疲累、消解着偶尔的不快,传达着生活的乐趣。
(三)长歌当空的生命意识
在西藏,人们自古以来信奉万物有灵,寺院当中教徒以舞蹈的形式祭祀日月山川生灵、祈福纳祥、驱鬼禳灾。日常生活中人们又以自唱自舞的形式歌颂着自然万物,歌颂山时,就对着大山;歌颂水时,就对着大江,声音高亢嘹亮,舞蹈热烈酣畅。
不管是高山、长河、密林,还是黎明的宁静、落日的壮丽、暴雨地喧腾,亦或是凯旋的自豪、婚嫁迎请的喜悦,任何细微之物都能将藏族同胞内心深处那种自由自在的冲动牵引出来,人们向往舞蹈,因为舞蹈为人们带来了胜利和生命,人们也用狂热的肢体展现着生命的活力。
(四)由心入境的象征意识
笔者认为,藏民族的原生态舞蹈是抽象的,它不为再现故事情节,不为展现人物形象,甚至也看不出其舞蹈语言所指代的具象意义,它自产生以来就是人们情绪上的一种表达。
藏族人民对孔雀有着特殊的感情,流传在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昌都芒康县、林芝等地的孔雀舞,基本都是以模拟孔雀姿态而舞,但舞蹈风格特点不尽相同,舞者们用人体动作展现着孔雀的美丽和优雅,表达着对孔雀的喜爱,但又各有不同,取其意境而淡化其形象。流传在西藏阿里地区仲吉霞布卓(野牛舞),其中的基本步伐“三步一踮”和手势“前推手”亦是模仿野牛姿态而来,被人们用在举行婚礼、祝福迎祥和送鬼驱邪时而跳的一种舞蹈。这些模拟动物的舞蹈在发展的过程中,技艺和风格也在不断升华,不仅局限于对动物姿态的模拟是否相像,也越来越注重情感和技艺的融合以及舞蹈最终所要表达的意义。
藏戏中,演员们在空旷的场地中表演,仅凭肢体、语言、唱词便营造出宫殿、野外、山间、河边、民宿等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无疑也都是一种由心入境,内心的感受促使身体的舞动,并使这样的舞蹈生动而真切浓烈进而引人入胜,让观者也被不自觉地带入其中。
四、原生态舞蹈在当代的传承方式之我思
对于原生态舞蹈,我们容易陷入一个漩涡,即追求这个“原”字,认为这个“原”才是最正统、最权威的,所以千方百计去触及这个“原”。从另一方面来说,真正的初始形态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形态,我們谁都不清楚,仅仅通过一些考古发现和岩画所了解到的舞蹈能断定就是最初的吗?
文到此处,其实我们对于原生态舞蹈仍旧有许多疑问,比如:原生态舞蹈到底是舞蹈的某种具体形态,还是当今时代我们对于舞蹈文化的一种态度,或是我们用来编创作品的一种手法,又或只是在这个市场经济越来越繁荣的时代,各商家用来炒作而竖起的一杆大旗?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舞蹈在当今社会到底存不存在?我们不能不加思索就一味去利用“原生态舞蹈”这一称谓,这样只会让真正的原生态舞蹈走上一条不归路。
话说回来,当一个局外人意图走进异文化圈,并研究和传播这里的舞蹈,当他踏入这个文化圈的时候,就注定将其破坏。正如我们爬山看云,总感觉云离我们很近,再走几步便触手可及,而当我们真正接触到的时候,我们已经将其破坏却并不自知。
那么,对于原生态舞蹈,我们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或许是保持一种“只远观而不亵玩”的态度,或许是道家的一种“无为而治”,任其自由生长,反而繁茂鼎盛?
但这些都太过于消极,笔者认为,或许我们可以再提习近平主席提的“文化自信”这一理念,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我们才会有意识地去继承和保护,如此,才能塑造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氛围,才能更加带动原生态文化的繁荣发展。
五、结语
本文立足“原生态舞蹈”这一焦点,首先对概念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以藏族民间传统舞蹈为例,从表现材料、表现方式和舞蹈语言等三个方面对藏族原生态舞蹈的自然生态、自然形态和自然传衍进行了勾勒,意欲唤起我们的文化自信,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旭烽.中国生态文明词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资华筠,王宁.舞蹈生态学导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3]强巴曲杰.藏文古籍中对舞蹈的论述[A].西藏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集[C].1989年.
[4]高历霆.藏传佛教寺院舞蹈“羌姆”探源[A].西藏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集[C].1989年.
[5]刘晓真.舞蹈人类学、方法论和中国经验(上)[J].民族艺术研究,2016(06):130-136.
[6]许锐.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认识演变与概念阐释[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