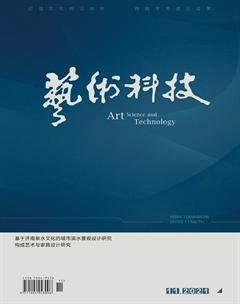《蝇王》中“善”与“恶”的艺术表达
摘要:在20世纪的文学领域中,威廉·戈尔丁盛名在外。他在小说《蝇王》中引入他始终关注的深刻议题:群众文明所推崇的理性同天性中所携带的野蛮成分的抗争。本文选取《蝇王》进行评估,依托善恶观视角,理解故事主角们后期遵循丛林法则,互相残杀的真实诱因,重新剖析此部作品。
关键词:《蝇王》;人性;善恶观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1-0-02
1 《蝇王》中“善”的艺术表达
1.1 人性与文明
威廉·戈尔丁笔下的飞机事故发生于未来的战争中,一群儿童降落至一座没有现代气息的荒岛上。不过,儿童的降临令岛内的生态境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在迎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规律,改造环境,以便于自身发展[1]。
拉尔夫、皮吉两人首先碰面。拉尔夫被视作文明、秩序的继承者,他遭遇事故后仍然有条不紊地行事,并未表露出慌乱情绪,十分刚毅果敢,同时他高大强壮,形貌姣好,又是海军司令的后代,可以说是一位传统的领导人形象[2]。紧接着出现的是杰克带领的合唱团和一群五六岁大的小孩子们,拉尔夫、杰克存在年龄优势,自然会对岛内生态起到决定性作用[3],其余儿童过于年幼,缺乏独立决断力,根本不清楚降临至荒岛的后果。皮吉和拉尔夫相遇时,他强调海螺可以用于传递信号,管理岛屿上的其余儿童。
海螺被赋予权威、民主两重含义,这里塑造了拉尔夫的领导地位[4],拉尔夫凭借年龄、阅历及海螺,成功当选为领袖。儿童们根据综合信息,不断明确自己作为人的身份,小说前半部分频繁出现“我们”这一主观强调和统一的主体也反映了孩子们对于人的身份的早期共识。在角色标签获得共识后,儿童们认同全部行为根据约定条例开展的倡议,这说明秩序得到建立和维护[5]。依托此类身份共性,他们尝试打造以往生活中接触到的秩序结构,树立领导者角色,明晰救助任务,通过设置常规相处事宜等细化秩序框架成为这一儿童群体的重要使命。
拉尔夫和杰克两人引导儿童共同组建了类似成年社会的结构,通过理性管制方案确保既定文明秩序得以留存和保全。此时,孩子们仍然按照伦理操守行事,以善意人性处理彼此关系和日常活动计划[6]。
1.2 理性秩序的建立
第一,拉尔夫意识到荒岛上的一切必须变得井然有序起来,于是他致力于建构合理程序[7]。首先在生活上,拉尔夫指挥大家在沙滩上搭建窝棚遮风避雨,前往淡水区获得水源,食物来自山间水果,如厕活动统一在某处岩石附近进行,这一选址可排除对水源、食物的污染,确保岛内卫生条件符合预期。此外,拉尔夫试图通过皮吉的眼镜聚焦太阳光,实现点火,以引起往来船只的注意,让大家得以获救,他明晰火堆的价值,打算令专人负责保护火堆。
第二,关于各自工作内容的分配。拉尔夫确立大体任务内容后组织儿童们分工完成计划。在该环节中,杰克组织合唱队共同管理火堆,按照轮岗制,确保火堆一直燃烧。除此以外,杰克还自觉负责狩猎任务。截至目前,儿童全部活动皆存在玩耍倾向,这也是他们得以团结的缘由之一。他们难以像成年人一样管控自身举止,始终具有玩乐诉求,但在孩子们看来,这类操作具有创造意义,也是他们主动勾勒小型社会的首次尝试[8]。
第三,关于规章条例的设计及落实。荒岛中存在诸多儿童,意味着秩序管理格外关键,这将是岛上保持和睦的必备因素。儿童所熟悉的秩序在于仅当对方持有海螺时,才能在会议途中讲话,这一规定可令所有群体拥有发声机会,另外的群体不可干扰其言论阐述过程。海螺被赋予象征意义,因此被推向权利代表物的战略高度,所有人都视海螺为命令[9],此外的条例皆围绕日常活动展开,以约束为主要性质。相关秩序存在合理性、目的性,且依托年长儿童的往期阅历而建成,他们尝试重塑以往的社会景象。根据上述内容,可以认识到儿童都了解家庭教育,年长儿童甚至有过校园经历,他们按照社会中人的角色定位自身,彼此互证角色。来自文明社会的教化作用持续了一段时间,令儿童保持了人性,克制了兽性本能[10]。但这时儿童的兽性本能并不清晰,饮食、娱乐诉求得到充分回应,儿童便能安于现状。同时,他们对于回归原本生活的希望并没有磨灭,在相关诉求可被实现,憧憬和冒险精神的指引下,他们构筑了相对秩序井然的局域社会环境。在这一期间内,理性特征更加明显,秩序左右着彼此关系和自身活动,人性、兽性的界限尚未被混淆或打破[11]。
2 《蝇王》中“恶”的艺术表达
2.1 兽性与野蛮
野兽的出现使得祥和的氛围被打破,出于恐惧心理,儿童们拥有了危机感,也对自身定位产生了怀疑。以往,他们始终认为彼此都是英国文明环境培养出来的后代,可以重返家园,然而野兽超过了其承受范围,这让两个大孩子的立场分化,不再继续配合得当。共性认知、目标无法生效,因此群体尝试通过捕猎满足当下诉求,却不曾察觉自身角色已产生动摇,身份的混同造成了秩序不稳的现状[12]。
小说中,最适宜作为兽性标志的人物当属杰克。当他第一次追捕野猪时,他没有将刀插入野猪的身体,这从侧面反映出此时杰克具有善良意识,其道德操守并未完全消失[13],然而事后他感到羞愧难当,并下定决心下次再也不会如此善良了。
后来,伴随着杰克成功猎获野猪,吃肉被视为一种特权。杰克终于将恶视为自身标签,不再惦念原本善的外衣,不再掩饰本能,而其余人也不断表现出兽性特征[14]。出于方便猎取野物这一动机,杰克尝试用泥巴伪装自己,这也不断侵蚀着他的羞耻感,使其丧失自我概念,但涂花脸的行为令其内在兽性得到开发,他的行为越来越血腥暴力[15]。因为打猎山顶上的火堆熄灭了,儿童们在该阶段丧失了被救的可能性。当他们纷纷围坐探究“野兽”存在的真实性时,杰克表示,拉尔夫仅调度其他人行事,自己并没有做出多少实质性努力,并认为规章不应被继续遵守,他以各种形式削减拉尔夫的权威形象,不再履行会议的秩序要求。在这个时候,狩猎的企图心压倒了恐惧意识,杰克诱惑孩子们宰野猪,并借此机会带领儿童们靠拢恶的一面。摆脱了秩序框架的他们,愈发突显出动物性特征,无限自由所导致的景象即是原始和罪恶[16]。在野猪被杀死后,罗杰率先认同由杰克担任新一届首领,他非常果断地接过这一头衔,还主张对拉尔夫队伍进行攻击,从而取得火源,这是两派儿童正式斗争的起点。围绕在杰克身邊的猎手选择趁天黑之际潜入窝棚取得眼镜,杰克此时已经具备主导地位,却依旧期望拉尔夫消失在岛屿,以此免除后患,这一目标最终使其火烧全岛[17]。
在这一环节中,多数儿童显露出兽性大于人性的特质。角色定位失常,人的角色概念逐步模糊,造成秩序不复存在。他们不再维护原有的章程结构,选择以丛林法则谋生,缺乏管制后,他们内在的恶性成分被激发,最终演变为彼此谋害的乱象。当火焰弥漫岛内时他们才终于有所领悟,但此时已无力回天[18]。
2.2 理性秩序的毁灭
岛上关系出现变化后,拉尔夫无法继续获得统治地位。杰克着手规划自己的统治范围,这时拉尔夫仅拥有小部分统治区域,而海螺使其保留再度夺权的可能性。不管这是习惯所致,或是他们知悉海螺的深层含义,海螺印证着他们合力打造秩序社会的时光,能够令其回忆过去的种种经历[19],每个人仍然尊重海螺的权威性,即使是杰克也是如此。杰克的统治地位建立在狩猎技能的基础上,在拉尔夫、皮吉展示海螺,试图重新笼络人心时,有许多孩子都动摇了,这时杰克愤怒了,他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感,这导致他的嫉妒心与日俱增,他的理性同样指出——抢夺海螺才能彻底奠定统治地位[20]。
皮吉原本想要用海螺为自身发声,夺回眼镜,而这触发了战争。杰克派人绑架了拉尔夫一伙中的两人,拉尔夫愤愤咒骂,但此时皮吉一反常态,赌上尊严,用海螺宣告,这让其他人不屑的态度有所收敛。他期望借此引导众人重新恢复理性,他对大家发问:“秩序和得救,狩猎和堕落,两者只能选一个,那么你们选择哪个?”不幸的是,此时各儿童的关注点已经放在更高处的巨石上,无暇剖析这一问题内涵[21],于是所有人都欢呼着看巨石压倒皮吉。皮吉尚未意识到危机,于是被巨石推进海中丧生,海螺也因此碎裂。这一举动完全激发了杰克团伙的兽性,无法忆起人性内容。他们在集体无意识的氛围和状态下,诞生了罪恶事件,却并未予以警醒。皮吉的丧生、海螺的破碎,无疑象征着岛上文明结构已经被摧毁[22]。
杰克看到这一幕时,不由得大叫道“海螺完蛋了,现在我是头领”,兽性彻底覆盖了群体的意识领域,杰克成为仅有的统治者,终于如愿拥有了领导权[23]。
3 结语
《蝇王》描述的是在特定的环境下,为了生存和权利而进行的善恶之争。人性为善还是为恶?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应结合当时的客观环境进行分析,否则难以找到人性善恶的真正答案。
在尾章中,作者选择以荒诞的形式了结此文。军官在意料之外抵达小岛,为儿童提供重返故土的契机,拉尔夫见此场景,号啕大哭。这一幕中,他不仅是在感叹岛内生活中的恶性经历,还对后续生活所要面临的新的恶意感到担忧,战争并未消停,成人世界出于利益的考量所采用的残害方式远胜于儿童群体。他哭泣时,不完全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还从杰克等人的立场出发,为他们向残酷世界妥协、放下人性美好一面而感到难过。拉尔夫明白,假如自己不能得到外界救援,很可能被迫呈现兽性、恶劣的一面,沦落为人性丧失的怪物。这类堕落过程非常隐蔽,更能引起深思。
戈尔丁曾经深陷二战煎熬场景,他不希望看到世界被邪恶和野蛮充斥着,同时也不想再看到战争。在《蝇王》中,孩子们在荒岛上表现出的善与恶的冲突,最终是恶战胜了善,但细读作品,给读者留下的最后印象却是惩恶扬善。作者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恶,使人看清楚真正恶的表现,从而间接阐述善在文明社会中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黄子萱.浅析生态文化的渊薮及发展[J].汉字文化,2018(21):152-153.
[2] 步路瑶.浅析《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J].汉字文化,2020(20):120-121.
[3] 顾晓宇.浅析《寂静的春天》中的生态伦理意蕴[J].汉字文化,2019(22):185-186.
[4] 杨广承,刘中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几点探析[J].戏剧之家,2019(25):156-157.
[5] 代兵.权利、法治与和平:康德国际秩序思想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20(11):71-77.
[6] 何如意.新时代背景下传统孝道伦理的两面性思考[J].漢字文化,2018(17):68-69.
[7] 杨广承.新时代人才思想时代价值探析程[J].汉字文化,2020(11):145-146.
[8] 张美红.认知理论在社会公德建设中的应用[J].大众文艺,2018(14):237-238.
[9] 杨修志,张泽腾.对古希腊罗马史诗作品中荣誉问题的反思[J].汉字文化,2019(14):41-42.
[10] 步路瑶.《变形记》中失衡下的人性探究[J].汉字文化,2020(23):125-126.
[11] 叶朗.对莫泊桑《羊脂球》的现代性解读[J].汉字文化,2020(16):122-123.
[12] 杨修志.浅析杜威对“经验”与“理性”概念的改造[J].汉字文化,2018(18):100-101.
[13] 叶朗.《伊利亚特》中英雄的典型人物形象分析[J].戏剧之家,2019(32):228-229.
[14] 舒婷婷.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真善美[J].汉字文化,2018(22):71-72.
[15] 贾尧天.浅析萨特《恶心》中的荒诞主题及存在主义[J].青年文学家,2018(23):101-103.
[16] 谢蔚晖.荒诞时期的压抑与自由[J].汉字文化,2019(11):27-29.
[17] 何如意.卡夫卡《变形记》中的异化表现[J].青年文学家,2018(23):89-91.
[18] 何如意.彼得·辛格《动物解放》的伦理审视[J].戏剧之家,2019(11):222-224.
[19] 冉聃.浅析赛博朋克科幻小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J].汉字文化,2019(11):71-72.
[20] 莫艺祯.探析《何以为家》主人公性格的变化[J].大众文艺,2019(14):183-184.
[21] 陈崇天.荀子性恶论及其对矫正校园欺凌行为的启示[J].大众文艺,2018(19):211-212.
[22] 魏婕.从人性角度解析东野圭吾作品[J].芒种,2018(14):84-85.
[23] 刘倩如.《动物庄园》的叙事策略分析[J].汉字文化,2020(03):88-89.
作者简介:顾菁(1996—),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