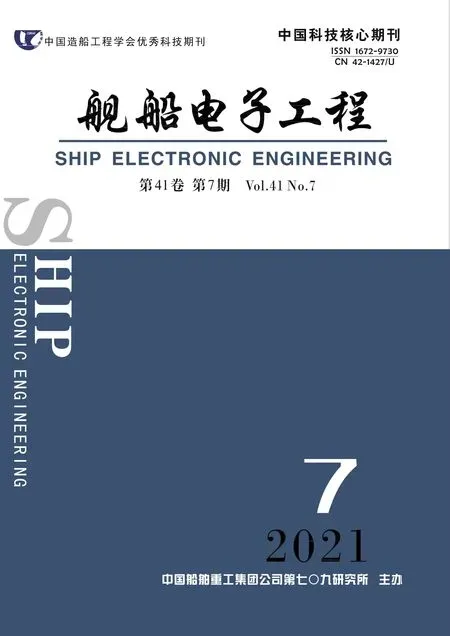高超声速飞行器作战运用探要*
郝晓雪 王 忠 韩光松
(1.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办公室 北京 100144)(2.火箭军工程大学 西安 710025)(3.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石家庄 050084)
1 引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苏两国在高超声速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历了高超声速技术探索、基础理论研究和武器型号研制等阶段,开展了大量试验性项目,为高超声速飞行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高超声速被称为“21世纪的隐身能力”,高超声速飞行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战争的时空观,成为世界强国争夺非对称战略优势的又一制高点,大国之间围绕高超声速技术领域的新一轮持久博弈已开启,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应用前景[1]。
前苏联开展了“银鸟”空天轰炸机、“信天翁”水陆两栖飞机、“4202”等项目研究,在高超声速飞行器领域长期领先。俄罗斯开展了YU-70与YU-71高超声速助推滑翔导弹等项目研究。2001年12月,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大力构建全球反导体系。俄罗斯高超声速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是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在经济寒冬情况下坚持高超声速导弹核常兼备,秉承非对称发展定位,海军、空军和战略火箭军各自保留一个项目,分别是舰载“锆石”、空基“匕首”和陆基“先锋”高超声速导弹[2~3]。
美国的高超声速飞行器计划起步较早,但由于需求不迫切,加之各军种项目纷繁,导致整体进度进展缓慢,长期停留在技术验证和各项目磨合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将高超声速技术视为战略能力转型的关键,战略指导思想是优先研发各种先期部件和高超声速飞行试验平台[4]。从目前的发展进程来看,美国高超声速武器化落后于俄罗斯,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工作缺乏统一规划。各军兵种和研究机构在高超声速武器领域的研发进展未协调一致,部分项目存在重复建设问题,目标高、摊子大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由于高超声速技术不成熟或资金不足,导致很多研究项目终止,如HTV-2、X-43A、X-51A等。二是关键技术缺乏积累继承。美国很多项目仓促下马或结束后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加之各单位技术封锁较为严重,军种、部门、国防承包商之间的利益纷争导致严重的内耗。
俄罗斯“匕首”“先锋”高超声速导弹先后服役,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由于大国竞争的回归以及对“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的担忧,发展高超声速武器的必要性正在凸显。美国为确保高超声速武器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全方位重振高超声速技术发展,调整高超声速武器的发展思路。一是着眼尽快形成作战能力,明确高超声速武器发展目标。二是国防部全方位统一规划,整合高超声速项目资源[5]。三是多部门加大资金投入,推进高超声速武器型号研制[6~7]。美军持续推进“全球快速打击”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战略打击能力,将给对手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本文从高超声速飞行器的能力特点出发,研究高超声速飞行器在未来高端战争中可能的运用方式,分析高超声速导弹对未来战争的影响,为新型武器的研制和作战筹划提供参考借鉴。
2 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路线
高超声速飞行器,是指以5Ma以上的速度在临近空间持久飞行的飞行器,包括高超声速导弹、高超声速飞机等[8]。高超声速导弹包括助推滑翔导弹和巡航导弹。高超声速飞机可在2h内抵达全球任何地点,执行侦察监视、兵力投送、远程打击等任务。根据动力类型,高超声速飞行器分为助推滑翔式与吸气巡航式。
2.1 助推滑翔式飞行器
助推滑翔式飞行器,采用助推火箭发射,通常在距离地面35km以上的高空释放,利用高升阻比气动外形在临近空间以高超声速远距离滑翔。助推滑翔式飞行器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和滑翔效应,通过钱学森弹道或桑格尔弹道滑翔,能够进行大范围横向与纵向机动。

图1 助推滑翔弹道示意图
钱学森弹道也称助推滑翔弹道,于1948年钱学森在美国火箭年会首次提出,由火箭发动机将导弹推进至高超声速;然后弹头在临近空间增程滑翔,进行横向机动与纵向机动;随着弹头在大气层高度不断降低,大气密度增加,弹头速度逐渐降低。这种飞行方式要求飞行器具有更好的升阻比,需要根据飞行器最大航程专门设计气动外形,目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双锥体外形,具有中等升阻比,横向机动能力有限,如AHW;二是乘波体外形,具有高升阻比,如HTV-2[9]。
桑格尔弹道也称滑翔跳跃弹道,通过改变飞行器进入临近空间的姿态、速度和时机,或采用更优化结构的气动外形以提高飞行器的升阻比,实现滑翔跳跃飞行,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用石头打水漂”。桑格尔弹道在航天领域运用较多,登月飞船和深空飞行器的返回舱在大气层“打水漂”,可快速降低自身速度。例如,登月飞船的返回舱采用“桑格尔弹道”进行回收,该过程可以认为是高超声速飞行器。返回舱第一次再入大气层后,在距离地面约60km高空受到强大的弓形激波作用而反弹回宇宙空间,这一过程将消耗返回舱大量再入动能,进而降低其二次再入大气层的速度;多次利用60km~100km空间的低温环境可大幅降低返回舱的温度。
2.2 吸气巡航式飞行器
吸气巡航式飞行器的发动机全程工作,在距离地面20km~30km高空飞行,从大气层中吸入所需的氧气,具有全程动力、全程操控、全程机动等优势。这种飞行器必须解决动力问题,实现大气层内经历不同高度,跨越亚声速、声速、超声速直至高超声速均能有效工作。发动机的工作状态与飞行速度、高度等密切相关,不同发动机都有其最佳的适用范围。例如,涡轮喷气发动机只能在航空空间工作,最大速度3Ma;超燃冲压发动机必须达到4Ma才能有效工作[10]。
目前,吸气巡航式飞行器的动力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采用组合循环发动机,将不同类型的发动机组合在一起,保证高超声速飞行器在宽广的飞行包线范围内高效可靠地工作,因此高超声速飞行器至少装配两套动力系统。二是采用协同吸气式火箭发动机,英国反应发动机公司研发的一种一体发动机,通常具有火箭与吸气两种工作模式。飞行器采用协同吸气式火箭发动机,低空飞行时就像一架喷气式飞机,从大气中吸入氧气燃烧所携带的液氢;高空飞行时,发动机切换到火箭模式,依靠携带的氧气燃烧液氢。
3 高超声速飞行器能力特点
美智库评估认为,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代表了继螺旋桨、喷气式后航空史上的第三次技术革命。高超声速飞行器具备飞行速度快、打击范围广、突防能力强等显著优势[11]。相对于现役的常规导弹,精确打击能力、强毁伤能力并不能作为高超声速导弹的能力特点。
3.1 飞行速度快
按照6Ma~8Ma的速度计算,高超声速导弹的速度是亚音速导弹的10倍,从本土发射一小时可打击全球任何目标。高超声速飞机从机场起飞,两小时能降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机场。亚声速“战斧”巡航导弹打击1000km以外的目标需飞行一个多小时,而高超声速导弹只需约8min,与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一致,具备实时攻击能力,高超声速导弹的打击能力跨入“秒杀”级别。
3.2 打击范围广
高超声速导弹的打击范围包括射程、横向机动范围两个方面。高超声速导弹的气动外形对射程的影响特别大,随着升阻比增大,射程不断增大。助推滑翔式飞行器在临近空间滑翔可使其射程提高一倍,吸气巡航式飞行器依靠动力系统自由加速,使得高超声速导弹具备大范围横向机动能力,从本土陆基或海基平台发射,不需要前沿部队提供支援、后勤补给等,大幅提升发射单元的战场生存能力。
3.3 突防能力强
研究表明,当飞行器的速度从5Ma增加到6Ma时,突防概率从78%增加到89%[12]。高超声速导弹独特的物理特征、飞行轨迹、飞行空间等使其可突破现役所有防空反导体系。

图2 高超声速导弹升阻比-射程关系
一是探测跟踪难导致反应时间短。高超声速导弹的雷达与红外特征明显,但与传统的弹道导弹相比,高超声速导弹的助推时间短、飞行弹道低,导致敌方预警卫星、雷达的探测距离大幅度减少,预警时间缩短。高超声速导弹返回大气层时,激波形成包围导弹的高温等离子鞘套,增大了雷达稳定跟踪的难度,进一步压缩敌方的预警时间和拦截窗口。此外,高超声速导弹还通过释放诱饵干扰、电子干扰等手段,极大地提高了突防概率。
二是大范围机动导致轨迹预测难。高超声速导弹在临近空间飞行时可进行大范围横向机动,纵向采用非弹道机动飞行,其飞行轨迹与瞬时所处空间的大气层密度息息相关,敌方导弹防御系统很难预测其飞行轨迹与攻击方向。
三是直捣敌方防空反导体系间隙。“标准”-3导弹的拦截高度在70km以上,主要在100km的大气层外拦截飞行中段的弹道导弹;“萨德”系统只能拦截40km以上飞行末段的弹道导弹;“爱国者”-3导弹的拦截高度在20km以下。高超声速导弹的飞行高度主要在25km~40km,目前仅“标准”-6导弹的最大拦截高度达33km,可能对其构成一定威胁。
4 高超声速飞行器作战运用
近几年高超声速飞行器迎来了井喷式发展,将形成新的作战威慑力,具备改变未来战争“游戏规则”的潜力,在海上高端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4.1 作为开路先锋遂行攻坚拔点任务
高超声速导弹基本具备“发现即摧毁”的实时攻击能力,可快速精确摧毁敌方预警体系、指挥机构、导弹阵地、军政首脑、预警机、大中型水面舰艇等目标。
一是突防能力强,首轮打击防空反导体系。由于高超声速导弹具备强大的突防能力,通常执行首轮火力打击任务,摧毁敌方防空设备、远程警戒雷达等高价值目标,为后续导弹突击梯队、无人机突击梯队、空中突击梯队的作战行动创造条件。
二是飞行速度快,即时打击时间敏感目标。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联合作战体系中侦察监视、信息传输、导航定位等作战要素的响应时间大幅缩短,能够在有限时间窗口内发现、识别、跟踪时敏目标,并做出攻击决策,为高超声速导弹快速突击提供支撑。而高超声速导弹接收到目标指示信息后,能够在短时间以高超声速飞临时敏目标所在区域,大幅增加了对时敏目标的控制能力。
4.2 强对抗环境集火攻击大范围散布目标
未来高端战争中,针对敌方水面舰艇编队、防空反导系统等具有多个子目标的高价值目标,高超声速导弹采用协同攻击规划、多弹弹目距离协同制导等实现多种样式弹道,多层次、多方向集火对这些目标实施多点同时打击,有助于提高突防能力、目标毁伤效能和作战效费比。
一是大范围机动攻击。高超声速导弹具有良好的气动外形,能够进行横向和纵向大范围机动,采用“直拳式”“勾拳式”等方式攻击高价值目标,不仅可以绕过敌方主要拦截集群,还可以形成较大范围可达区,穿透性打击分布在广阔战场上的超远程固定目标与移动目标。
二是多导弹协同攻击。随着现代导弹技术的快速发展,高超声速导弹可以装配多种智能制导模块,智能感知复杂战场环境的态势与接收各种平台的制导指令,成为一体化联合打击体系的重要节点,弹头在飞行过程中协同完成侦察探测、信息共享,实现协同突防与攻击任务[13]。
4.3 使用门槛低创新了慑战并用作战方式
高超声速导弹将时间、空间、能量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拥有全球快速精确打击能力,成为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战略性手段,可作为核武器的“替代品”。与传统核威慑不同,高超声速导弹采用常规弹头,既具备战略打击能力,又不必承担使用核武器所需付出的高昂代价,基本上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实战。
高超声速导弹具有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势与重要的实战价值,具备比核武器更加可信的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将变革现有作战方式,对敌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从而达到“未战而先胜”的威慑效果。高超声速导弹丰富了常规导弹战略打击的作战概念,主要对敌方要害目标、高价值目标、时敏目标等实施快速、定点、清除式打击,可极大地提高了作战的突然性、隐蔽性和威慑力。
4.4 生存能力强丰富了高空侦察监视配系
高超声速飞机搭载各种情报、侦察、监视载荷,利用飞行高度与突防优势,对敌方进行全天候、全天时高空侦察监视,将实时搜集的战场情报通过C4ISR系统分发至各级指挥单元和作战平台,为实时的临机决策、毁伤评估等提供重要支撑。与有人或无人侦察机相比,高超声速飞机的战场生存能力强,可执行对地、对天双重侦察监视任务,大幅拓展侦察监视范围,情报搜集时效性显著增强。高超声速飞机与预警机、侦察卫星等构成一体情报侦察体系,充分发挥战场情报搜集整体优势,可对己方周边广阔海域实现全域覆盖和全维监视。
5 高超声速导弹对未来战争的影响
5.1 颠覆现有空防规则,实现非对称战略制衡
高超声速导弹具备强大的突防能力,能够刺破敌方现役的防空反导体系,彻底打破现有大国之间相对的军事力量平衡,增大了威慑的可靠性,将对敌方武器装备体系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一是敌方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升级防空反导体系,向更高预警维度、更快反应速度、更大打击力度的陆、海、空、天联合防御体系发展。二是高超声速导弹强大的打击能力,或将使敌方军事造船业发生转折,导致海上作战力量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因此,高超声速导弹可以实现非对称战略制衡,加速瓦解敌方现有作战体系和综合国力。
5.2 战争进程显著缩短,体系对抗更趋激烈
高超声速导弹突破了时间和空间对战争的限制,信息化战争真正进入“秒杀”时代,导致作战节奏显著加快,极大地压缩了“观察-定位-决策-行动”循环周期中行动到观察的时间,在敌方未采取行动之前破坏和削弱其体系作战能力,有利于夺取作战行动主动权,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因此,信息与速度一起成为联合作战制胜的决定性因素,高超声速导弹加速了未来战争制胜机理嬗变,将对信息化战争带来显著影响。一是主动发起战争的风险增大。高超声速导弹高度依赖作战体系,使得信息化作战体系之间的对抗异常激烈,攻击方不断提高自身体系的支撑和对抗能力,受攻击方为应对高超声速导弹的巨大威胁,必然会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破击对手作战体系。在战争主动权巨大红利的诱惑下,可能爆发战争的双方之间更倾向于主动打响战争第一枪。二是战争更加依赖完备的战前预案。由于高超声速导弹打击速度呈几何级提升,一场高端战争或许在数个攻击波次之后就分出胜负。因此,各战略方向需要根据使命任务,提前制定多套详细的作战计划,以应对敌方可能突然发起的高超声速打击行动。
5.3 空天一体攻防作战,催生新型作战样式
高超声速导弹打破了“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策略。基于空基、陆基、海基发射平台,高超声速导弹全面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形成分布式跨域部署能力和全向发射能力,可能催生诸多新型作战样式,如极速点穴战、远域毁瘫战等。一是极速点穴战。海上高端战争中,高超声速导弹可从多维空间发起突袭,对敌方军政首脑、前沿军事基地、大中型水面舰艇、侦察监视平台等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摧毁敌方空海一体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实现非对称战略制衡。二是远域毁瘫战。根据战局发展和作战需要,高超声速导弹作为核武器的战略降级打击替代方案,对敌方战略纵深高价值目标、深埋地下的指挥机构等实施远程精确打击,既能降低引发全面核战争的政治风险,又能起到战略慑止作用。
5.4 核常交缠更加突出,核武化打破战略平衡
2019年,俄罗斯率先部署“先锋”高超声速核导弹,与美国核力量结构形成了新的非对称优势。目前,法国、英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也在加紧发展高超声速导弹。一是核常交织更加突出。当前大国关系发生深度逆转,核力量发展呈现出不平衡、不对称的特征,可能促使高超声速导弹核武化态势进一步扩散,美国、法国、印度都可能将高超声速导弹列入战略武库,使得潜在的核常交缠问题更加突出。二是核误判风险增大。高超声速导弹具备大范围机动能力与核常兼备的双用途特点,敌方难以判明其攻击意图,难以判断来袭导弹的打击目标、弹头类型等,这些复杂情况增加了战略不稳定性,使得战争升级机制更加复杂而危险,可能导致战略误判、风险升级、事态失控。
6 结语
高超声速导弹兼具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传统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缺点,而具备两者的优点。高超声速导弹的广泛运用势必加速战争形态演变,对传统的防御手段、作战样式、抗击方法等带来颠覆性影响,改变现有军事力量体系的发展方向。通过研究高超声速飞行器的作战运用及对未来战争的影响,牵引新型武器装备研发和推动作战理论创新,不断寻求军事实力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