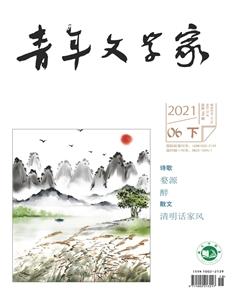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的《倾城之恋》
雷咪咪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代表,具有《叙事分析手册》中所言“无综合”“没有等级分层”“怪异性”的后现代主义叙事学的特征,对原有的结构主义等级分层的摒弃,拒绝服从形式规律,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只关注形式的结构主义研究,将其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起来,探索文本在何处存在模糊性。女性主义在后现代叙述中寻找文本中存在的性别意义,而促成这一转变的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苏珊·兰瑟。1981年,苏珊·兰瑟在她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中,首次提出将文本的叙事形式与社会历史相结合。1986年,苏珊·兰瑟在《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中,提出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概念,阐述了这一学派建立的必要性,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1992年,苏珊·兰瑟在其《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结合文本进行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系统分析,将文本的形式研究中加入政治、历史等因素,拓展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新角度,为叙事学的结构分析加入了新元素,使得叙事学超越了符号和形式的研究,加入了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从而走向叙事学的新方向。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女性作家权威的建立
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兰瑟选择了“叙事声音”作为自己的阐发点,兰瑟认为,“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等存在状况……无论是叙事结构还是女性写作,其决定因素都不是某种本质属性或孤立的美学原则,而是一些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常规。这些社会常规本身也处于社会权力关系之中,由这种权力关系生产出来。”文本的创作本身是结合权力关系生产出来的,叙述声音也是结合形式规范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其中充满意识形态的斗争和矛盾,对于叙述声音的研究还应该包括性别、教育、民族、阶级等社会形态。
女性主义叙述声音在女性文本中的叙述声音也聚集着各种对抗和冲突的形式,这种对立通过文本体现出来,“女性可以通过叙述声音的不同角度在文本中得到话语的权威,获得尊重和认同。每一个叙事学概念都带有着这种语境的痕迹,而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认为,这些痕迹就其表达那一语境之权力关系而言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女性叙述声音同样充满意识形态的斗争,将叙述声音分为了三种类型: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体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来说明文本是通过叙述声音体现性别的权力,将叙述声音性别化。个人型叙述声音是指“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但排除了个人内心独白的形式,说话人是虚构故事的参与者,自身故事中的“我”统筹着其他人物的声音,表明自己的经历和话语的有效性。作者型叙述声音是“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这样一种叙述行为,在其叙述过程中某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被赋予叙事权威;这种叙事权威通过多方位、交互赋权的叙述声音,也通过某个获得群体明显授权的个人的声音在文本中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來”。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认为,女性应该“成为自己”,成为独立自足的个体,有写作的自由和空间,以此来反对男权的文学以及男权文学中对女性的丑化和奴化,女性主义文学必须通过创作建立女性的主体性,争取女性的话语权利,不仅表现在争取实际的、身体的需要,也表现在文本中,争取叙述话语的自主性。
“要真正改变女性边缘化的局面,就需要采取一种激进的立场:既考虑男性的作品,也考虑女性的作品,而且从妇女作品入手来进行叙事学研究”。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文学作品多为男性创作,男性在文学中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力,而文学领域女性作家的不在场形成了女性话语的缺失,当时张爱玲的作品并不入社会主流。《倾城之恋》由女性作家创作,为女性主体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张爱玲生于上海的贵族家庭,使得她对遗老的家庭里的陈腐和压抑有透彻的理解,也使得她对封建大家族中的女性命运有深刻的体会,父母离婚带来家庭破碎的创伤在她早期的生活中投射了阴影,她与胡兰成的婚变也对女性的心理产生了影响,形成了张爱玲对于婚姻和爱情的冷漠和怀疑的态度,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的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为她建构女性意识提供了更可靠的叙述,更便于建构女性的权威。
二、集体型叙述声音中女性自我实现的障碍
集体型叙述声音是在叙述中,群体被赋予叙事的权威,多角度、多方面地传达个人的叙述声音,传达集体的思想。兰瑟将叙事技巧融入社会意识形态的文本表现,分为了三种形式,以某个叙述者代替某个群体发言的“单言”形式,以“我们”作为主语来叙述的“共言”形式,以及群体中每个人轮流表达的“轮言”形式。集体型的叙述声音是边缘人物以及受压制的群体的叙述,这种方式是采取某种策略,将权威隐藏起来的建构方式。
金蝉道:“那范柳原是怎样的一个人?”三奶奶道:“我哪儿知道?统共没听见他说过三句话。”又寻思了一会,道:“跳舞跳得不错罢!”金枝咦了一声道:“他跟谁跳来着?”四奶奶抢先答道:“还有谁,还不是你那六姑!我们诗礼人家,不准学跳舞的,就只她结婚之后跟她那不成材的姑爷学会了这一手!好不害臊,人家问你,说不会跳不就结了?不会也不是丢脸的事。像你三妈,像我,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活过这半辈子了,什么世面没见过?我们就不会跳!”
在《倾城之恋》中,四奶奶和宝络的对话是作为旧时代的大家庭中的女性所言,她们的潜在话语是对白流苏冷嘲热讽,她们认为白流苏不应该离婚和回娘家。徐太太和流苏的对话是讲述流苏寄居白家的处境,两人认为流苏需要寻找男人来离开当时的被人冷落的环境。白家的女性代表旧时代家族的群体,她们身处被压迫和阴冷的环境而不自知,身为女性,是当时男权的附庸。三奶奶、四奶奶对白流苏去见范柳原十分不满,对于她们来说,离过婚的女人是不配得到爱情的,她们对流苏挖苦挤压,把白流苏的相亲也只是当作笑话来看。宝络、金枝、金蝉这些女性之间的勾心斗角,为取悦范柳原作为自己的立足点,以嫁给有背景的人作为目标。通过她们各自的声音传达各自的态度和价值观,形成附庸男性的女性群体。
以白太太为首的女性代表当时旧时代女性对于女性的态度,她们对于流苏的憎恨和鄙视,是主流的依附者女性的普遍看法,她们对于男性保持依附的立场,是女性的自我觉醒道路上的阻碍。与流苏为自身寻找依托之所的主体意识形成了对比,也可窥见张爱玲女性话语建立的艰难和重要性。白家女性已经成为男权的代言人,通过这种轮言的方式,这些群体的不同声音得以吐露,从当时每个人表达自己的声音来看出当时女性在实现自我中的障碍和艰难。
白老太太长叹了一声道:“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罢!”
流苏在和范柳原产生矛盾后,回到家中,白公馆的人认为她很丢脸,她代表传统的女性对女性的态度,女性应该屈从于男性,白流苏认为她自己不应该这样低下,虽然她最后还是迫于家庭的压力去找范柳原。白家的女性群体习惯于被男性奴化。顺从并依赖于男性,这些女性是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一个大群体,对流苏寻找自我的过程形成了干扰,也反映了女性在真正实现自我中遇到的障碍。正如兰瑟所认为的,复调在被支配的女性声音中更为重要。“恰恰是因为女性的和集体的方面,该叙事策略成为抵抗男性和个体的作者式叙述模式的最自然的形式。它有助于‘女性身体政治的构建──对立于个性的男性政治的集体的女性主义政治。”作者以白流苏为代表建立的女性意识对以一个人代表一个群体的声音表现的女性的屈服做出了挣脱的姿态,权威性地建立了女性话语。
三、作者型叙述声音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作者型叙述声音是超出故事之外的,隐藏地指称着自我的叙事状态。作者型的叙述声音不参与虚构的世界,它与虚构的人物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 因此,女性作家通过自己的叙述最大限度地宣称自己叙述的“准确真实性”,与同时代、同背景的男性意识形态文本形成一种对抗,女性作家由此成为其中的对抗者,这在当时女性作家极少的情况下,女性作家的介入带来了一种新姿态,形成了自己的话语权力。
白流苏和范柳原跳舞后:
范柳原真心喜欢她么?那倒也不见得。他对她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
这也是作者所发的议论,作者在对白流苏当时的处境做出判断,凭借自己的经验对范柳原的言行分析,自己是白流苏唯一的依靠,此时作者在宣示着白流苏作为个体的觉醒,她不再作为附庸从属于任何权力,她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这里通过女性作家张爱玲的介入,建构了一种女性作为个体的权威,作家的立场是代表女性的发言,完成了女性对于自我的审视。
流苏的手没有沾过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欢赌的,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家人虎视眈耽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气。
这是作者的声音以一种隐匿性的方式表达着,以一种自由间接的方式描述白流苏的心境,是对以男权代表下的白家人的冷落的反抗,作者也是在表达白流苏最终依靠了自己,这是迂回地表达作者的女性意识,来建立女性声音的权威。
流苏心里想着:你最高明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你自己。如果我是一个彻底的好女人,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
作者以一种介入的姿态进入文本,这是作者对于男女双方在爱情中位置的感悟,这是女性对于自己的理性分析,为寻找心灵的依靠而在内心与对方博弈着,作者为女性的形象在清醒地定位,作者建构的女性形象在成长。
流苏自己忖量着,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白流苏在寻找一个感情的寄托和可以安身的场所,最后寄希望于结婚,并不是对于男权的附和,正在白流苏这里,感情是克制的、理性的,白流苏在寻找着自我的依托,也是女性意识的建立。这是白流苏和范柳原的爱情观,也是张爱玲的爱情观,张爱玲在表达着自己在爱情中的观点和态度,表露了对于男权中心的控诉,作者通过展示女性自身真实地位来反抗男权中心主义,形成了女性在文学中构建的话语。
这三种模式都表达了自己的一套标准和规则,形成了一种类型意识,也构成了类型化的文本的权力关系、规则和可能。作者创作中的叙述声音主要为作者型叙述声音,在文中并不是界限严格的不同声音的叙述,在文中不断变换声音,形成了文本的叙事特色。张爱玲作为女性作家不是纯粹关注于小说故事的内容,也不只是针对小说的叙事结构来进行探索,而是在叙述的形式和内容的表达中找到了平衡点,来思考作家创作对于男性主流的倾覆和女性主体的建构,这是张爱玲对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重要意义。
女性主义叙事学在传统的文本形式中加入意识形态的因素,拓展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新角度,张爱玲的女性作家身份对男性话语权力的主导地位形成冲击,女性的写作和语言具有了合理的存在意义,便于女性权威的建立。同时,在文本中女性的叙述声音显示了女性的境遇和地位,女作家在叙述声音中完成了女性意识的表达。《傾城之恋》将叙述声音与女性意识相融合,主要以两种叙述声音来传递女性色彩。在集体型声音中显示出女性实现自我的障碍和困难,作者型声音中表现出女性的主体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