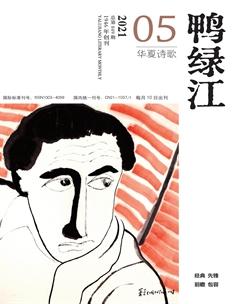缅怀父女诗人李瑛、李小雨


冯永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新诗研究会会长。
2019年3月28日晚,一条微信向我传递了我国新诗泰斗李瑛老师逝世的消息。尽管对此我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心里还是一时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经过电话求证确认之后,我向李家亲属发去唁电,在书房久坐无语,眼噙泪水,心潮难以平静。
我早在1965年就与李瑛老师建立了联系。那时,我在空军航空兵某师服役。当时,李瑛老师还是《解放军文艺》的诗歌编辑。他看了我在《空军报》《解放军报》上发表的一些诗作,托一位离我所在部队驻地不远的作者转告,鼓励我给《解放军文艺》投稿。
我投去几首诗,他就在《解放军文艺》1965年第9期选用了其中的《战斗值班休息室》。之后,她又选发了我的《美国佬,算个啥》等诗。我复员回上海,《解放军文艺》停刊,我们的联系就中断了,很久以后才恢复。
50多年来,除了那段断档期,我和李瑛老师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彼此通过这种古老的方式交流思想,切磋诗艺。
因在上海工作期间我家经历了多次搬迁,从1985年开始我又南下了,许多存放在上海居所的书信和资料大多遗失。
在南方定居后的30多年,我才专门设档收存,珍藏了李瑛老师和他女儿李小雨的亲笔信70多封和他们赠送的一批诗集。
诗心长明,辉映岁月
在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的名单中,写诗历史之久,创作作品数量之多,而且质量始终保持在高水平的诗人,恐怕还没有谁能超过李老。
李老从1942年就开始写诗,那时他还是个16岁的中学生。在长夜难明的苦难岁月,他摸索、倾听、寻找光明,胸中跳荡着一颗能照亮未来美好世界的诗心。这颗诗心蕴涵着他对大美和大爱的强烈向往,对真理和幸福的执著追求,陪伴他一同走完了生命与诗歌共存的漫长岁月。
从1944年开始,李老为我们留下60多部沉甸甸诗歌专著。不管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他的诗心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的温度和亮度,辉映着他无论是匆匆奔走、还是艰难跋涉的脚印。他的诗心能保持长明不熄,关键在于这不是一颗靠刻意模仿用来自我炫耀的诗心,也不是靠封閉自我专事雕琢所谓个人经验的诗心,而是他在2014年10月版的《李瑛诗选》后记里所诠释的那颗诗心:
我的思想和心灵是开放的。我是用思想和血来写作的。我致力于挖掘自己灵魂深层的一面,又希求表现出那些与人类关系最紧密的单纯、本质的共性的一面,使诗既具有美学价值,又具有生命价值;既具有浓郁的情感韵致,又闪烁着灿烂的理性光芒,力求传达出诗的思辨之深、诗艺之美,传达出其所应具有的思想和历史深度。
这是诗坛泰斗对其诗心最完美、最科学的诠释。
在李老消失了六、七年之后,我陆续读到了他别具一格的几本新诗集。1972年出版的《枣林村集》是他以军人目光观察农村的诗,这本集子发行量超过30万册,采用了带谣谚风味的通俗语言,这对他说来无疑是一大尝试。接着我又读到有英、法、朝三种文字译本的《红花满山》(1973年)。
读1975年出版的《北疆红似火》,尤其使我感到亲切,因为我的军旅生涯大部分是在北疆度过的。
1976年,他又接连出版了《站起来的人民》和《进军集》两本诗集,抒发了全国人民对走向新生活的强烈期盼。
历史上有不少流传千古的不朽诗篇,正是诞生于国难深重的时候。
屈原的《离骚》,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不正是写于国家走向衰亡和民不聊生的战乱时期吗?
李老写于特殊期间的诗,丝毫没有离开他多年来信奉的创作思想和美学原则,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许多诗篇,因为情思的深邃和诗性的深厚,至今读来仍具有特殊的魅力。
1976年那首纪念周总理的长诗《一月的哀思》传播之广是空前的,不知感动了多少淳朴的民心;而此后的获奖作品《我骄傲,我是一棵树》中丰满的现实启迪和浓烈的浪漫色彩,则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共同赞赏。
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了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诗歌组的创作活动和辅导工作。受李瑛诗心的熏陶,我结合阅读他的大量诗作,也在诗歌的感性和理性交融,诗的思辨和诗艺之美的糅合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我把几首怀念军营生活的诗和文化宫诗友的作品选出来,寄给他,很快就得到了他的回信。
在1981年11月27日的回信中,他对上海工人文化宫的业余诗歌创作活动给予热情鼓励,告诉我他担任了主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三个编辑部党务和行政的领导工作,不再从事编辑业务,所以把我的来稿转给了《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一年后的11月15日,他又来信感谢我对刊物的支持,更感谢我始终怀念在部队的那些日子。
《解放军文艺》先后发表了我的《怀念军营》和《红花与军被》两首诗。
由于他公务繁忙,此后与我联系更多的是他的女儿李小雨。
李小雨也当过兵,转业后分配到《诗刊》当编辑,从此我们之间书信不断,使我有机会从父女两代诗人的身上,得到非常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诗骨铮铮,傲立毕生
李老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应该受到学院派文风的一些影响。但他大学毕业后就从戎南下,在烽烟炮火中磨砺了一身军旅诗人的风骨,同时也形成了他在创作实践中任何时候都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诗骨。他的诗中既有细腻动人的柔美抒情,又有壮怀激烈的血性喷发。在诗歌主张上他从不随波逐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摸索的正路。由于我一直将他作为学诗的标杆,就有幸得到了他更多的关心和指导。
虽然有他女儿鸿雁传书,但只要我有新的诗集寄给他,都会得到他的亲笔回复。
1995年5月,我给他寄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如火的恋情》,他于6月10日回信致谢,并说:
多年来,不断从报刊上读到你的诗作,从中看出你的成长、成熟,看出你对生活、对艺术的追求。如今得以结集,值得庆贺,容当细读。盼有更多新作问世!
他所指读到的诗作,主要是我从部队复员后写上海工业区生活和特区风情的诗。前者如《我赞美旋转》和组诗《汽笛,呼唤诗歌》《我们拆旧》《黄浦江畔》等;后者如组诗《关于深圳》《一个从海上浮起来的故事》《深圳风》等。发表后获得一些好评,有的还获了奖。我很感谢他对我创作的鼓励。
同年10月,我又给他寄了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关于深圳》,他于11月10日回信致谢,并感慨说:
你过去在部队时,曾经给予我们工作上很大支持,你转业去地方后,则联系不多了,但你的作品风格,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
深圳,多年前曾应邀访问过一次,你写了一册反映这个新城的诗,使我对它有更深的理解了。容当细读。盼读到你更多的新作,谨先致函以释念。
1994年,我向小雨表达了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愿望,想请花城出版社总编、广东老诗人李士非老师和李老两位长辈当介绍人。小雨向父亲转达了我的请求,李老欣然应诺,并亲自出面向中国作协有关部门介绍了我的创作情况。1995年递交申请表之后,到年底还没有消息,我忍不住写信去问李老。他于1996年1月17日回信说:
所说入会事,我已同作协书记处同志谈过,请他们予以关照,他们已答应了。但不知究竟如何?因过去我曾介绍过的同志,后来也未获准。
信发出后我有些后悔,觉得不应该为这件事再去打扰他。其实中国作协已在年底的会议上通过我入会,按一般程序通知了广东作协。广东作协未及时告知我本人,以至造成悬念。但李瑛的回信证实了他为介绍我入会所做出的努力,使我非常感动。
1997年8月6日,李老收到我的散文随笔集《琴弦上的国魂》之后,回信致谢说:
过去读过你不少诗作,这次又可集中读你的随笔。对你的勤奋和多产,表示敬佩!
2003年我当选为深圳新诗研究会会长,创办了《深圳新诗》报,由袁庚同志题写刊名,想请李瑛等几名老诗人当顾问。我致函表达了这个心愿。李瑛于7月23日回信说: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嘱任你们的顾问,愿共勉。为我国诗歌事业的繁荣发展多做工作。嘱写几句鼓励的话见另纸。请正。
题词:希望培养更多的诗人,发表更多的好诗。贺深圳新诗研究会成立暨《深圳新诗》出版。
李瑛
2003年7月
2009年10月12日,在收到我献给新中国六十岁生日的诗集《大地之歌》后,他回信说:
收到你送我的《大地之歌》,谢谢你!
记得多年前你在部队时就写了许多诗,至今坚持下来,且越写越多,越写越好,真不容易。祝你写出更多新作!
当时他已有83岁高龄,仍不断有新作问世,而且诗心不改,诗情更浓,使我敬仰不已。对我的赠书他每次必回信,不断给予鼓励,更令我觉得暖流涌怀。
2014年1月,我偶然得知他出了新诗集《比一滴水更年轻》,急忙到书城去购买,但跑了几家都没有买到。这年李老已经88岁了,新诗集的书名却充满了青春感,对我产生了极大的诱惑。
我听小雨说过:父亲的书出版社给的样书很少,一般不送人。尽管如此,我还是给李老写了封信,在问候和祝福之后,透露了想得到新诗集的愿望。他于2月10日回信说:
收到1月27日大札,谢谢你的问候和祝福。
你想看看我所出的《比一滴水更年轻》,这书出版社送我十本样书,我自己只购存了十本。因为多年来诗界斑驳复杂,诗早就处于边缘状态,像我这样的人更处在边缘的边缘,因此我便很少送人,免被耻笑。这里送你一本四年前印的《河流穿过历史》吧,它收诗稍多,估计你没有读过,欢迎批评指正。
读过你许多诗,祝贺取得的成就!
这封信既使我为意外的收获高兴,因为《河流穿过历史》是一本很厚重的书,是李老的新时期诗歌选;同时又使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听见了他心海深处的潮声:诗的边缘化,诗人的边缘化,这对一颗毕生倾情于诗歌,与之长相守的诗心来说,是不小的打击。我能感觉到他看到的愤懑和无奈。早在1991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瑛《对诗的思考》一书中,我就听见了他对诗界一些不良现状提出的尖锐批评。在一篇随感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近一时期以来,许多诗作在内容和技巧上,明顯地、程度不等地存在着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和西方一些文艺思潮的影响。当然,对此不做分析地全盘肯定或简单化地一概否定都是不对的。但讲诗的力量和价值必然要讲诗的思想性,讲诗的主题、诗的内容。绝不能将这种作法看成是把诗等同于“政治宣传”,认为是“左”的理论,是“践踏艺术”,是“玷污缪斯的圣洁”。那种一味脱离现实、淡化生活、摈弃理想、过分追求“空灵”的诗歌,那种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纯诗”的境地的诗歌,那种流露消沉颓废、表现迷惘失落的诗歌,是心态扭曲的反映,是和我国人民当前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和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壮丽生活毫无相同之处的。诗人毕竟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和对社会的思索。要知道,抒写个人的内心精神对世界的主观感受和个人直觉,与反映时代和现实应该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一个人离开自身历史的发展,离开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连西方的一些美学家也不能不承认的。
作为《诗刊》的编委之一,李老这篇诗论,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诗界问题的本质。并用一双诗人的眼睛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
现在有些诗表达的感情越来越窄,时代的影子和生活的气息越来越淡,题材内容越来越多是宣泄什么社会之外的生命内在状态和生命的瞬间冲动;在技巧上或者则不加选择地采用一个个离奇怪诞的比喻和暗示,来渲染某种读者难解的幻觉、感觉和情绪;或者则毫无节制地罗列一堆无序的“意象群”,进行奇怪的组合和对接;或者则诗句之间、语词之间完全割裂,过大的跳跃使读者难以理解作者感情流动的轨迹,完全阻碍了作品通向读者心灵的道路等等。这些貌似深奥的作品,如分行的巫术,使人如坠入五里雾中,百思莫解。
……我们当今有些诗人所写的一些孤芳自赏的作品,这种游戏人间、充满沙龙气息、贵族气息的作品,对广大人民究竟有多少意义和价值呢?
可叹的是,这样的声音居然被越来越张狂的“颠覆传统”等喧嚣声干扰甚至淹没,久病不治,以致形成顽疾。
李老来信中所言“多年来诗界斑驳复杂”,正是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次原因。在来势凶猛的浑浊诗潮中,李老以接连不断的创作实践和为数不多的犀利评论,显示其铮铮诗骨,傲立毕生。
诗魂永生,美韵长存
2015年2月11日,刚刚卸任《诗刊》常务副主编的诗人李小雨英年早逝。89岁的李瑛痛失爱女,经受了心灵上一次难以弥补的重创。在忍受了一个月老泪纵横、哀伤难抑的精神煎熬之后,他于3月11日通宵达旦写下了《挽歌:哭小雨》这篇160多行的亲情杰作,交给《光明日报》发表。
这首父亲悼念女儿,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诗篇,字字句句令人动容,催人泪下,更使我哽咽不已。
李小雨在《诗刊》当编辑,一干就是近40年。为了诗歌,期间她可谓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复刊后的《诗刊》,百废待兴,且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小雨在父亲的影响下,热爱生活,热爱诗歌,性格善良委婉,待人宽容大度,处世喜欢自然简朴。在创作上她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觉,心灵开放,视野开阔,如果不是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必有更丰硕的成果。在《诗刊》社的漫长岁月里,她忘我的敬业精神,堪称同业的模范。她每天要审读大量自然来稿,在编辑部看不完,又带回家去接着看。发现好诗和有希望的创作苗子,她会兴奋异常,常常和父亲一起分享收获的快感。她和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对我的每一次投稿,都会提出很具体的处理意见,有的稿子即使不用,经她说明缘由,我也感到信服。
1984年《诗刊》为了培养更多的新人,创办了刊授学院,她是具体的组织者。我虽然已不算什么新人,但为了支持她的工作,也报名参加学习,1986年受邀参加了在庐山举办的《诗刊》改稿会,对诗艺的长进确实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对彼此了解的加深,我们的通信已经从一般的编通往来升华到友谊的层次。
小雨去世之后,我一直关心着李瑛老师的健康,祈望他能从失去亲人的阴影中走出来,重新享受明媚的阳光。每看到他继续有新作发表,总是感到十分欣慰,并写信祝贺。
2016年5月30日,我又收到了他寄赠的两本新著,内附一封写满整整两页纸的信。这是一封用颤抖的手写下的心声。信中说:
衷心感谢您对我的敬重和关切。也感谢您在小雨生前给予她工作上的支持和帮助。她过去曾多次和我谈及您的热情和诗作。
我这几年过得很痛苦,因为老伴和唯一的女儿相继去世,使我的身体和心情都很不好。尽管我的思维和记忆,仍然和年轻时一样敏锐,在生活中又常有创作欲望和激情,但这恰恰带给我更大的痛苦。现在每天只有书报能给我带来安慰,当然有些较好的老友和一些真正喜欢诗并严肃追求诗歌的年轻诗人来看我,给了我许多难得的温暖和友情。对社会上一些文学活动的邀请,我是大多谢绝了。您对当前我国诗界的看法,甚得我心:在这个十分浮躁的社会,文学界特别是诗界不健康之处太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弊端的存在已经太久了。我看到诗人黄东成写的一些文章,都是实情,所言极是。你看到了否?
送您两本小书,不知您读过否?我的诗,每首都是探索和尝试。我始终是依了我自己对诗的认识和理解,既具诗性又具智性来指导实践的,不知道像不像样子,请予惠正。我现在仍未断写作,您若见到,请能教我。
这是一封非常珍贵的信。一个年过九旬的诗坛领军人物,前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第一、二届优秀诗集一等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图书奖等殊荣获得者,在生命交响曲接近尾声的旋律中,依然在宣告他的每一首诗都是探索和尝试,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诗界不健康现状和表现在文学上的社会弊端,依然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深重的忧虑。
2017年,他支撑着垂老之躯,应许多读者的呼吁,为女儿亲自编辑了一本有代表性的诗选《红纱巾》,并亲自写了一篇编后记《生活给予的美》,这篇后记以诗性的语言概括了他再也熟悉不过的女儿的一生,相当于一篇文情并茂的墓志铭。她对女儿一生的评价是客观、公正而自豪的,他提到的那些事实和情景,我是亲身见证过的。如: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出出入入总是带着一大袋又一大袋的稿子,每次外出开会,即使只有两三天时间,拉杆箱里装的也不是衣服、化妆品,而是塞满箱子的一件件来稿。
每每看到好的稿子,尤其是新人的稿子,她总是激动不已。在她心里,只有诗,只要诗好,没有其他。
我多次在她住的旅店里亲眼目睹了这种情景。至于培养新人,谁都知道她是《诗刊》“青春诗会”的多次策划者和組织者。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后记中写到的:
在她工作后期,为了进一步办好刊物,她兴致勃勃地走访了许多诗人和读者。
我就是她走访过的对象之一。她担任《诗刊》常务副主编之后,我给她推出一些建设性意见。我认为《诗刊》应该珍惜多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必须保持原有的面向大众的办刊特色,坚定地走与时代同步、为人民抒情的正道,不能走进纯粹西方化、绝对个人化的死胡同。我在给李老的信中也表达了这些意见。小雨听得很认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李瑛老师和李小雨都把诗歌视为生命中的不可分割之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这是非常难得的父女诗人组合。李瑛老师的成就虽然远远大于女儿,但李小雨将毕生事业完全与诗歌融为一体的无私奉献,同样会像她的诗歌一样被众人所传诵。在她以自己的名字为题的《小雨》一诗中,她抒写道:
我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
溅起那么多、那么多的水波。
那涟漪,那枯叶,那古树,
那幽深的青苔,暗淡的磷火,
一种声音说:
不要打搅,不要打搅,
不要扰乱我平静的生活!
我淡淡地一笑,唱我的歌:
一滴雨是一粒种子,
带着空气的潮湿,泥土的热。
我播种生命,播种热情和新鲜,
明天,该清新的世界在这里收获。
一片浮萍或者是几枝莲菏,
哪怕是一个最原始的微生物,
只要是生命的,
那就是创造,
那就是我!……
小雨的诗,继承了父亲诗性和智性精巧糅合的传统,创造和传播了人间的大爱大美。这是伴随父女诗人一生的魂魄。
斯人已去,诗魂永生,美韵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