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创作的一体性
李 明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陕西 西安 710054)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点,古代文论界曾有很多总结。有的学者总结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有方法,如意象批评、人化批评等;有的学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立论,指出古代文学批评思维具有直觉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等特点;有的学者从话语方式上入手,指出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模糊性,以及缺少体系性等特点;有的学者则聚焦文体问题,揭示古代文学批评文体的演变过程和文备众体的特点(1)对古代文学批评的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和批评文体等方面研究的综述,可以参考黄念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研究的现状与反思》(《东方丛刊》2004年第3期)、蒋述卓等《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水云《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术档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论著。。值得注意的是,罗根泽、朱东润、彭玉平等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另外一个本质性特点,即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一体性。他们虽然强调了这一特点的重要性,但未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试图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这一特点的具体内涵和启示意义。
一、批评家与作家身份的一致性
西方一向有独立的批评家职业。罗根泽先生如是总结西方批评史:“他们自罗马的鼎盛时代,以至18世纪以前,盛行着‘判官式的批评’,有一班人专门以批评为业,自己不创作,却根据几条文学公式,挑剔别人的作品。由是为作家憎恶,结下不解的冤仇。19世纪以后,才逐渐客气,由判官的交椅,降为作家与读者的介绍人。”[1]13但罗先生所说并不准确。按照法国批评家蒂博代的判断,西方的职业批评在18、19世纪之后恰恰达到了顶峰,他在其《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即总结了自18世纪伏尔泰以来职业批评的发展史,认为:“就职业批评而言,这个批评如此普及和如此强大的十八世纪,只不过是一个过渡阶段罢了。”[2]“这个伟大的时代,应该等到十九世纪。”[2]总之,西方独立批评家的历史是由来已久了。
与西方极为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批评家往往就是文人。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批评家与作者身份的一致性。如罗根泽先生说:“在中国,从来不把批评视为一种专门事业。”[1]13“所以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1]13朱东润先生也指出:“吾国文学批评家,大抵身为作家,至于批判今古,不过视为余事。”[3]美国学者李又安则从中西方文学批评比较的角度来谈论这种差别:“中国批评家本人是诗人或是散文家,他们有意识地实践着这一艺术,他们针对这一艺术带来自己的批评力量。在西方,我们可以想到诗人批评家如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和艾略特等众多人士,或小说家批评家弗斯特等人。然而我们也对西方这一现象十分熟悉,即批评家并不对他所评论的文类加以实践。而这类人在中国就十分罕见,刘勰即属此类,他仅以《文心雕龙》而著称于世。”[4]如李又安所说,西方批评家除了少数兼任作家外,大部分是属于独立的批评者。而绝大部分的中国古代批评家往往就是作家。李又安举刘勰作为例外,但实际上刘勰并不例外。《梁书·刘勰传》谓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刘勰制文。”[5]又言其有“文集行于世”[5]。可见,刘勰亦非不能文者也。
批评家与作者身份的一致性,是缘于古人的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谙熟创作之甘苦,才有资格评论诗文。如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所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如果文章写得不好,是没有资格评论作者的,所以他反对的是“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6]。对于其中的道理,清人徐增解释得比较清楚:“诗之等级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诗出。学问见识如棋力酒量,不可勉强也。”[7]442又说:“今人好论唐诗,论得着者几个?譬如人立于山之中间,山顶上是一种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种境界,此三种境界个个不同。中间境界人论上境界人之诗,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论最上境界人之诗,直未梦见也。”[7]442对诗文的创作原理有长时间的深切体验,才能达到“一览众山小”的批评家的地位。方孝岳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批评家固然站在旁观的地位,但是天下事往往要身历其境的人才能说得清楚;隔岸观火,终不能得其究竟。我们时常听见人家说‘眼高手低’,又有人说‘眼有神,笔有思’,这就是说只能批评而不能动笔。这种人比较既能评又能作的人,就不免相差一筹了。”[8]写得好才能评得切,这种观点在职业批评家看来,显然是不必要的要求。职业批评家只需要判断作者是否符合自己认为正确的批评观念和理论体系,而古人则认为批评的内容应该是创作上的得失。对“批评”的不同理解也就导致了对批评家资质的不同要求。
中国古代很多诗话的作者在自道写作渊源的时候,都往往强调自己是经过多年学诗而深得其甘苦的。清代黄子云在《野鸿诗的》序言中说:“余经三十年困苦中研出,故不得不以授人。”[7]879又如张谦宜在《茧斋诗谈》卷三中的自叙:“吾尝与高大将军语,嘱曰:‘君辈慎勿谈兵,非身历行伍,九死一生,岂知此中消息。’噫!吾十三学诗,今五十五稔矣,刀痕箭瘢,遍体鳞皴,然后敢为后生言。”[9]809在古人看来,没有扎实的创作经验就率而谈诗,无异于纸上谈兵了。很多人在为他人的诗话作序跋的时候,也往往以作者的诗学创作功夫作为诗话值得信赖的原因。如王铎序李东阳《麓堂诗话》:“先生之诗独步斯世,若杜之在唐,苏之在宋,虞伯生之在元,集诸家之长而大成之。故其评骘折中,如老吏断狱,无不曲当。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予于是亦云。”[9]1399鲍廷博在为《麓堂诗话》所作的跋中亦云:“李文正公以诗鸣成弘间,力追正始,为一代宗匠。所著《怀麓堂集》,至今为大雅所归。诗话一编,折中议论,俱从阅历甘苦中来,非徒游掠光影娱弄笔墨而已。”[9]1400
作为重要批评形式的诗注也是如此。古人认为,必须要对诗学有深厚的体验,才能做好诗的注释。钱大昕序许宝善《杜诗注释》云:“故尝谓注诗者,必深于诗。未达乎诗教之源,未究乎诗律之细,未讨论乎诗人出处本末,性情旨趣之所属,虽日从事于铅,犹无当也。”[10]钱大昕所说的“深于诗”应包括善写诗。当代诗学大家陈永正先生在其《诗注要义》中总结历代注者之擅诗:“古代注家多能文擅诗,《山谷诗集注》作者任渊早年曾受黄庭坚指导诗歌创作,《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作者赵次公曾‘且注且和’苏轼诗,《王荆公诗注》作者李壁‘其绝句有绝似半山’者,现代注诗大家黄节、瞿蜕园、王蘧常、钱仲联、白敦仁等更是杰出的诗人,他们既能诗,又熟悉所注释对象的创作风格,为其诗作注,优自为之。”[11]由陈先生所言可见,创作经验对于注诗之重要。
好的选本也需要选家对诗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理解。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指出:“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12]1376清初人沈荃《莼阁诗藏·序》也认为:“予谓必胸罗万卷,具八叉七步之才,玉衡冰鉴之识,然后扬榷品题,不差累黍。否则蒙瞍之操埏埴耳。”[13]“八叉七步之才”即出色的创作才华。有足够的创作才华才能有李东阳所说的足以选诗的“识”力。
如上所论,批评需要一定的创作能力。但另一方面要说的是,从事创作也需要高超的批评能力。创作是需要建立在对前人作品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尤其对于中国古典诗文来说,模拟前人是一个必经阶段(2)程千帆《文论十笺》卷下《模拟》篇、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第二章第三节“古代文学史上的模拟之风”等文章对古代文学中的模拟之风有详细分析,可以参考。。而以什么样的作品为学习和模拟之对象,乃至如何学习、模拟,都需要对前代诗文的体制和演变进行一番辨体。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14]136关于“家数”,清代何世璂《燃灯记闻》记王士祯语有详细举例:“为诗要穷源流。先辨别诸家之派,如何者为曹刘、何者为沈宋,何者为陶谢,何者为王孟,何者为高岑,何者为李杜,何者为钱刘,何者为元白,何者为昌黎,何者为大历十才子,何者为贾孟,何者为温李,何者为唐,何者为北宋,何者为南宋。”[7]123又曰:“学诗先要辨门径,不可堕入魔道。”[7]123当然,古人学习和模拟前人,最终是希望能够通过模拟达到“脱化”而形成自己的面目。但即便如此,学习和模拟也是达到“脱化”的必要过程。如叶矫然《龙性堂诗话》谢天枢序引叶氏语所言:“诗不能自为我一人之诗,为之何益?然非尽见古人之诗,而溯其源流,折中其是非,必不能自为我一人之诗也。”[9]933可见,识古今体制源流、雅俗的文学批评能力,是创作的前提条件。
这种创作所需的评鉴能力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正法眼”“具眼”或所谓的“识”。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指出以“正法眼”来辨别“第一义”的重要性:“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14]11尽管严羽以魏晋盛唐诗为“悟第一义”的观点可以商榷,但对初学者来说,具有对前代诗史的判断力还是很重要的。又如清代薛雪论“具眼”:“读书先要具眼,然后作得好诗。切不可误认老成为率俗,纤弱为工致,悠扬婉转为浅薄,忠厚恳恻为粗鄙,奇怪险僻为博雅,佶屈荒诞为高古,才是学者。”[15]95在这段话中,薛雪所说的“具眼”则指学诗者应该能够正确把握风格,避免诗病。古人学诗又常常强调“识”的重要性。如吴雷发《说诗菅蒯》:“笔墨之事,俱尚有才,而诗为甚,才与识实相互表里。”[7]933“诗须多做,做多则渐生才识也。然必有才识者方许多做,不然,如不识路者,愈走愈远矣。”[7]933叶燮《原诗·内篇下》中所论才、胆、识、力四种“在我者”的主体要素中,特别突出“识”的重要性:“不知有识以居乎才之先,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15]24“今夫诗,彼无识者既不能知古来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兴感触发而为诗;或亦闻古今诗家之论,所谓体裁格力、声调兴会等语,不过影响于耳,含糊于心,附会于口,而眼光从无着处,即历代之诗陈于前,何所抉择?何所适从?”[15]24“夫人以著作自命,将进退古人,此地前哲,必具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15]24学诗者要学习前人,必须练就能够通古来作者之意和古今诗家之论的“识”力,这也就是要求诗人必须要具备很高的批评能力。
二、批评与创作之循环
批评与创作互为前提,形成一个循环。这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意思。
第一,批评从创作中来。西方文学批评的命题与体系,多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衍生而来。如柏拉图的“模仿说”即从他的“理念”哲学而来,茵加登的文学理论是从现象学而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从索绪尔语言学发展而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以其社会学为基础,等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受到经学思想、道家思想、理学思潮等方面的影响,但主要的源动力则来自于各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如钟嵘所提出的“直寻”命题即是针对当时用典繁缛的文风而言,殷璠的“兴象”和“风骨”论则是对盛唐诗风的总结,江西派诗人的“活法”诗论也是针对江西派末流诗风过于生硬晦涩的弊端而提出。正如罗宗强先生所总结的:“中国古代许多文学批评范畴的出现,都和创作中某种文学思想、文学思潮有关。”[16]
第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创作。对于中国古代的诗文评而言,批评不是为了客观的裁判,也不只是为了促进对作品的理解,而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后进诗人提高写作水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序论诗文评之功能云:“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17]“有裨于文章”正是诗文评的重要意义所在。在这种批评目的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内容以探讨创作技巧得失的“创作论”为主,就不足为奇了。罗根泽先生就曾指出:“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1]12他所讲的“文学理论”不是指作为当代学科的“文学理论”,而是指诗文创作的原则和技巧之类。孙绍振先生也指出:“中国古典诗论与西方之根本差异,在于其基础为创作论。”[18]如《文心雕龙》的主体是“论文叙笔”的20篇文体论和“剖情析采”的19篇创作论,都以指导创作为目的。唐代流行的诗格诗式类著作,也都是以作诗的声律、对仗、句法等法式为主的,备陈法律,目的是以晓初学。从宋代开始大兴的诗话,除了“旁采故实”和“体兼说部”之外,也在于通过技巧的谈论来启发后学。如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点明用意曰:“诗话之作,非为能诗者作也,为不能诗者作,而使之能诗。”[19]683其实,不要说“不能作者”,即使“能作者”,又何尝不能得益。又如清人李沂《秋星阁诗话》张潮跋曰:“有以评古人诗为话者,有以教今人作诗为话者。夫古人之诗,即微我之评,亦复何损?若夫教今人作诗,则其话为有功矣。”[7]943其实张潮所说的“评古人诗为话者”又何尝不是给学诗者以门径呢?
批评从创作中来,又指导创作,由此,批评与创作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略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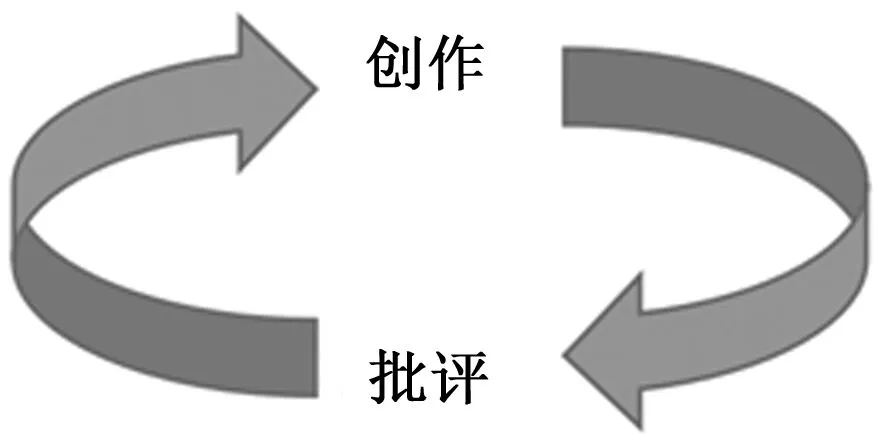
三、创作与批评的文体同一性
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在文体上大多具有各自的独立性。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等古希腊罗马的批评著作开始,西方文学批评的主要文体就是以成体系的理论篇章为主,与文学作品是断然不同的。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却与文学文体紧密交融在一起。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首先,古代文学批评的很多篇章都是以文学的体式存在的。《文心雕龙》是以精美的骈文写成,陆机的《文赋》则是以赋的形式出现。自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解闷五首》等论诗绝句以来,历代的论诗诗又蔚为大观,如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等。这些篇章既是文学创作,也是文学批评,可谓一体而两用。
其次,就言说方式而言,古代文学批评大多不是抽象式、逻辑式的,而是形象的、隐喻的,是诗性的批评。如钟嵘在《诗品》中评价范云和丘迟诗的风格:“范诗轻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19]15《南史·颜延之传》载鲍照评论谢灵运与颜延之诗:“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雕缋满眼。”[20]又如敖陶孙《诗评》用隐喻的方式评论历代二三十位诗人的风格,如评论曹氏父子:“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21]在语言批评的层面,古人也往往用隐喻论之,如唐代诗格中用“芙蓉映水”“龙行虎步”等“势”来言句法,又如金圣叹用“烘云托月法”“草蛇灰线法”等比喻论篇法,等等。这样的意象式批评在古代文学批评的各种文体中俯拾即是。从根本上说,这种话语方式的形成是由古人对“言”“意”关系的看法决定的。《周易·系辞》中说:“言不尽意。”又说:“立象以尽意。”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也进一步发挥,认为:“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22]“尽意莫若象”[22]。同样,文学作品之“意”也是无法用分析性的“言”来论说的,而以“象”来言,更能得之。
四、从“知行合一”到“作评合一”
诗学上创作与批评的合一性正是中国思想“知行合一”的呈现。西方哲学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亚里士多德将理智分为“沉思的理智”和“实践的理智”:“沉思的理智同实践与制作没有关系。它的状态的好坏只在于它获得的东西是真是假。获得真其实是理智的每个部分的活动,但是实践的理智的活动是获得相应于遵循着逻各斯的欲求的真。”[23]可见,西方思想注重追求与“行”无关的纯粹之“知”。而中国传统思想却多认为“知”和“行”是一体的。
中国人秉持着一种“实用理性”,并不以与行动无关的纯粹之“知”为最高追求。中国传统思想认为,相对“知”来说,“行”是最终的目标。《荀子·儒效》篇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24]刘向《说苑·政理》也说:“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25]可见,对于中国思想来说,“知”不是纯粹之知,而是找到“行”的方向和方法。另外,与“行”无关的“言”,古人认为是空说,墨子称为“荡口”:“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尚)之,是谓荡口也。”[26]可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尚用是重于求知的。
“知”离不开“行”,“行”也离不开“知”,由此有宋明儒学所提倡的“知行合一”之说。他们认为,只有“行”了才是真“知”,如《二程遗书》云:“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27]朱熹也主张“知”和“行”是一体的,是互相促进的:“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28]148又云:“知与行,功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28]281在这种思想传统下,才有了王阳明著名的“知行合一”之说。《传习录》云:“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29]19
在“知行合一”的思想传统下,古典诗学中创作与批评合一的特点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尚用重于求知,所以古代的文学批评大多不是为了建立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指导创作。因为“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所以古代诗人初学时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批评鉴别能力和前代批评家的指引;因为“行之愈笃,则知之愈明”,所以文学批评需要批评者具有深厚的创作经验作基础。由此就造成了古代作家与批评家在身份上的合一现象。而西方哲学追求纯粹之“知”的传统,则造成了西方文学批评注重建立独立体系,追求客观裁判,以及身份上职业批评家的流行。
五、古代文学批评“作评一体性”的当代启示
明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创作的一体性,可以给当代的批评史研究以很多启示。
由于古代文学批评的范畴和命题往往从创作潮流中总结而来,因此在研究文学批评的时候,不能忽视对文学创作的考察。正如罗宗强先生所说:“研究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离开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文学思潮,都难以做出更接近历史原貌的解释。”[16]罗先生所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范式,将文学创作与批评结合考察,正是出于对古代文学批评这一特点的认识。因为古代文学批评的内容以创作论为主,因此确切地阐释批评范畴、命题的内涵,需要研究者对创作有一定的体验和心得。古代文学批评往往用点到为止的印象式的批评方法,而不是逻辑式的详尽言说。如果缺少对作品的领悟,是很难确切体会到批评者的用意的。比如古代诗学中所说的“瘦硬”,如果没有对黄庭坚、陈师道等江西诗人作品的研读,是很难领会其意味的。其他如“平淡”“神韵”等范畴皆是如此。所以,程千帆先生说:“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完全没有创作经验是不行的。研究诗最好能够写点诗。”[30]
古代批评家往往就是从事写作的作家,这一事实被彭玉平称为批评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其所著《诗文评的体性》一书中,他指出:“批评家是以作家的身份兼有的。这一基本事实是如此清晰,它不容我们坐视不顾,也当然应该成为批评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31]12因此,他认为批评史研究应该以作家为本位,而非以批评家为本位来建构理论体系:“所谓的‘批评史’并不纯粹是‘批评家’的理论批评的发展历史,原生形态的批评史——也许用‘诗文评’更为恰切,应当以作家的本位为逻辑起点,从中演绎出其学术观念和思维特点。匆匆忙忙去构建什么理论体系,或者以当代的学术意识去框架古代文学的批评文献,也许就显得过于功利了。起码现在是如此。”[31]14彭先生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