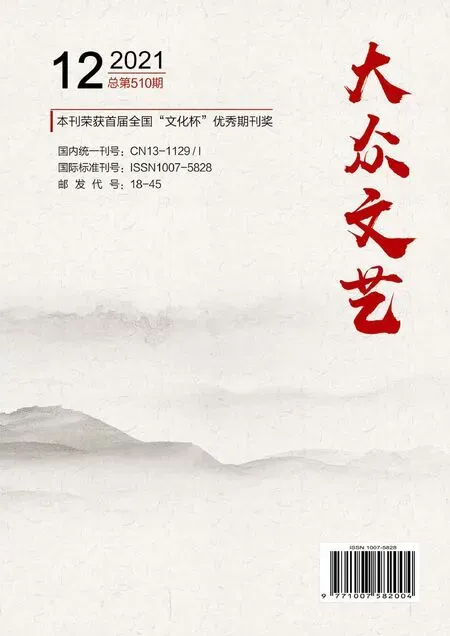接受美学视角下杜牧《秋夕》的四种英译文评析
朱梦伟
(浙江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00)
一、引言
“中国诗词讲究起承转合,头尾呼应,追求一种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浑然一体的艺术审美效果”。然而要真正把诗歌的艺术审美效果完整翻译出来很难,因为诗歌翻译中有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译性。所以说“诗歌翻译是一门有缺憾的艺术。诗歌原作中的美无法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完整地保存下来”。笔者认为,无论诗歌在翻译中是否“丢失”或者“丢失”多少原作的艺术审美效果,诗歌都是可以通过翻译来传达某些效果的。但是翻译中由于译者很难把他所感受到的审美体验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且不同读者所接受的文化程度不同,故而在译作审美期待上有所差异。因此诗歌翻译往往会有所争议。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文艺批评理论,即接受美学理论。这一理论的研究重心不再仅仅停留在作者上,而是把重点关注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和审美期待上。接受美学的出现给诗歌翻译带来了新颖的角度与启示。本文从这一视角出发,评析了杜牧《秋夕》的四种不同英译本,认为: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可以通过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使译文更符合读者审美期待。因此,不同诗歌译本往往各具特色。
二、接受美学理论
“接受美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联邦德国出现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者一作品一读者所形成的总体关系中,读者绝不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因素。相反,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作品是注定为读者而创作的,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这意味着读者由于其所受文化教育及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对源文的理解有所不同,读者作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对译文的审美期待和创造成就了译文要传达给读者的艺术体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同时也是译作的作者。作为读者时,译者得先接受源文所传递的审美体验而形成个人对源文的审美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由于译者个人素质、教育、心理、背景等等因素,译者的审美体验存在差异,所以对原诗的审美判断也会有所不同。而在翻译时,作为译者时,译者希望通过译作来传递给读者他对原文的理解,其翻译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确定性和不可译性。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积极发挥他的主动性,以读者为中心给译文加以创造,以便读者达到他的审美期待。这就导致译文再现源文这个阶段,不同译者传达给读者的审美体验有所差异。其次,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译入语读者与源语言读者的审美期待也不同。因此,评判诗歌翻译时避免不了讨论译者的主体创造性,评析不同译本的空间也相对较大。当然,在诗歌翻译中,译者不能随意发挥其主体性,因为原诗的意象与情感限制了译者创造活动的范围。如果离开这个对象,跳脱了限制,那么就不能称之为诗歌翻译,从而失去了诗歌翻译的意义。
三、《秋夕》赏析
《秋夕》这首诗描写的是身处深宫之中的宫女失意凄凉的生活场景。诗歌第一句“银烛秋光冷画屏”为景物描写,“银烛”“秋光”与“冷画屏”营造了一种幽静、孤冷的氛围。第二句“轻罗小扇扑流萤”描绘了宫女在宫中生活百无聊赖、寂寞孤独的处境,只好拿着小扇扑打萤火虫来消遣娱乐、打发时光。而“流萤”又暗含“腐朽”“荒凉”的意思,暗指宫女生活环境的凄凉。第三句“天阶夜色凉如水”指夜色渐深,深宫的夜晚愈发寒冷。寒气袭人,可是宫女没有回屋入睡,而是“卧看牵牛织女星”,因为她想起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而被他们的美好爱情深深感动,因此对美好真挚的爱情产生了向往和憧憬,从侧面突出了封建时代宫女的悲惨命运。
到目前,已有很多中外译者为此诗做了不同的英译版本。本文将以四个不同版本的译文加以分析。分别是:许渊冲版,Witter Bynner &Kiang Kang-hu版,徐忠杰版和Peter Harris版。许渊冲先生结合诗歌翻译的音、形、意而提出了三美论,认为“译诗不但要传达原诗的意美,还要尽可能传达它的音美和形美”。Witter Bynner“是美国20世纪著名诗人及翻译家,他在‘散体’译诗思想的指导下,以独特的方式传译了唐诗的情感、语言风格和音乐性”。徐忠杰是我国著名的诗词翻译家,在诗词辞藻、韵律上颇有建树。Peter Harris“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并担任南京大学客座教授,他撰写与翻译过多部有关中国及周边国家的著作”。
四、译文比较分析
接受美学提倡以读者为中心,给予译者较高的翻译自由来发挥其主体性以达译入语读者的审美期待。由于译入语读者同源文读者审美期待可能有所差异,因此诗歌翻译很难树立一个绝对的标准。本文四位译者的译作风格迥异,各具特点,原诗内在的情感要素在各自译文中具体化为了不同的表现形式。
从许渊冲先生的译本来看,译本充分体现了许先生“音,形,意”三美原则。诗歌以“ABAB”押韵,句式完整且优美。许先生版的第一句采用了被动语态,“chilled”一词可以带给读者强烈的冲击,从而带给读者孤寂悲凉的感受。但是许渊冲先生在第一句中没有把“秋光”翻译出来,似乎是漏掉了一个意象。其实不然,接受美学强调翻译中要把读者作为中心,译作要符合读者的审美期待。该诗中,“秋光”这一意象在这里同“银烛”一样,为了渲染冷寂的气氛。在中国的古诗词中,“秋”这一意象经常被诗人用来表达惆怅,悲痛的心境或者象征事物衰败荒凉的结局。而从外国读者接受角度分析,一般“秋”并不含中国古诗词中约定俗成的意象,所以如果把“秋光”放入译文,反而不符合读者的审美期待。第二句中的“passing”一语双关,即表达了萤火虫偶然飞过打破宫女无聊生活这一插曲,也暗指了时间的流逝,美好事物的结束。较为贴切地传达了原诗“流萤”的形象。最后一句原诗引用了中国古代“牵牛织女星”的典故。从英语读者接受角度分析,典故翻译所要传达的是其背后所要表达的目的和蕴含的情感。若直译过来,英语读者在没有接受相关中文典故知识的教育背景下,是无法接收到诗歌所表达的情感的。许先生的最后一句通过意译的手法比较直接地表达了宫女触景生情而流泪心碎的情感。虽说没有完全表达出原文宫女命运悲苦的含蓄之感,但从读者接受角度看读者是可以充分接收到诗歌要表达的悲痛之情。
徐忠杰的版本相较于原诗发挥了其译者主体性从而添加了译者创造性的想法。诗歌结构采取了“AABBCCDD”的形式,结构完整,读来朗朗上口。但是诗歌第一句用“throw”这一词描写了烛光跳动的动态感,但是就景物而言,没有把景和情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是通过第二句中旁观者的角度交代了微凉的环境。第四句中译者用“swatting”表现宫女扑打流萤的动作。但是“swatting”表示的是“重拍”,即拍打的程度很重,且拍了一遍又一遍。下文译者给出了解释说明因为黄昏降临的缘故视线不清楚,所以宫女一直拍不着而有丝丝恼火之意。这显然与流萤轻盈灵动的感觉相去甚远,但是译者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给译作增添了新的色彩,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体验,可谓别有一番趣味。最后典故的处理也很巧妙,一方面用“legendary stars”暗示这是一个传奇爱情故事,与牛郎和他的爱人有关。充分激发了读者了解故事具体情节的兴趣,也比较含蓄地表达了宫女对美好爱情向往的情感。
Witter Bynner的诗歌第一句通过形容词“silvery”和“chill”烘托出寒冷,寂寥的氛围。但是译者又用了“bright”来描绘画屏。“bright”在英文中是“明亮、光明的”意义,词语色彩偏褒义。故这里与译者所描绘的氛围有所冲突,从读者审美角度看略有不和谐之感。第二句中没有把宫女拍打流萤的动作描绘出来,只是说给萤火虫准备了小扇,至于是干什么的,没有明说,一定程度上丢失了原诗宫女生活无聊孤单而通过拍打流萤消遣的意味,但是给予了读者一定的想象空间。最后牵牛织女的典故没有直译,而是用“parted”表现分别的惆怅与无奈之感,但是感情的表达没有许先生来得强烈与直接,而是留给读者许多想象与回味的空间。最后是Peter Harris的版本分析。这一版本整体来说比较偏向直译。第一句中的景物描写,Harris版的是这四个版本中唯一把秋光给翻译出来的。表示拍打的词语是“hits”,而“hit”更多是来表示“碰撞和打击”的意思。不过后面用了“swirling”来修饰萤火虫,把流萤灵动纷飞的特点准确地表达出来。后面“天阶”指的其实是“石阶”,这里直译成“Heavenly Steps”,表达略显生硬。最后的牛郎织女星也是用直译地手法表达出来,从读者接受角度看,译文稍微会有生涩之感。
总体来说,这四位译者的版本各有其特色之处。许先生的版本兼顾了音、形、意三美,读起来很有节奏感,朗朗上口。徐先生的版本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并给译文加以创造,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审美期待。Witter Bynner的版本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留白空间,从而扩展了读者的接受限度。最后Harris的版本虽然直译现象较多,但充分尊重原作且极大还原原作带给读者的审美期待。综上分析,我们了解到诗歌翻译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使不同版本的诗歌翻译具有不同审美特质。
五、结语
虽然诗歌翻译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译性,但接受美学给诗歌翻译带来了新的启示。接受美学重新把读者拉到中心地位,同时强调不可忽视译者的主体地位与创造性。故在诗歌翻译中,译者要先理解作者通过诗歌想表达的艺术效果而形成译者的审美体验。翻译中译者要以读者为中心,充分考虑读者的审美期待,可适当发挥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而把原作的魅力和情感体验传达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