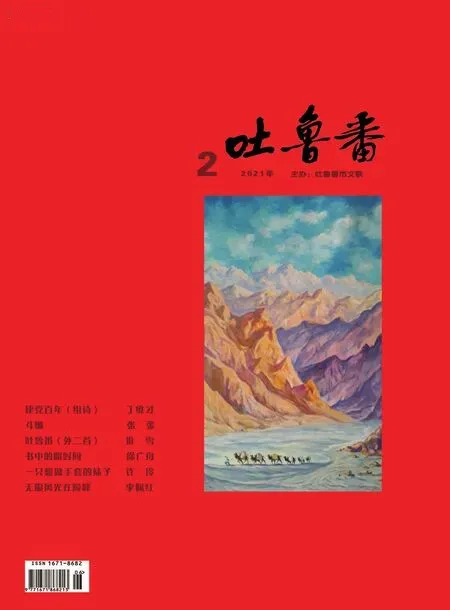艾丁湖的月光(外二章)
张玫

艾丁湖的月光
湖心低落处,长满枯黄的苇草。盐壳微微翘起,剥落岁月的伤痕。偶尔的鸟鸣是心脏微微的起伏、驿动。
在岑寂的地平线上,湖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静静的湖,仿佛一弯残缺的闪着泪光的月,倾听寂静里幽深的寂静。
亿万年的海在哪里?
亿万年的碧波是和蓝天一样的富饶辽阔吧!
身陷沼泽,匍匐黑色淤泥。从高处一次次下沉的样子,没人看得到。
痛被隐匿。被地球深深隐藏。像流星的坠落,被宇宙蕴藏在浩瀚里,划伤水润的眼眸。
那些海水被谁吞噬?
从亿万年前浩渺的海洋里出离,谦卑地渡化成陆地柔软的秘境。
这需要经历多少沧海桑田的变迁,需要练达多少失落后坦然的心魄。
湖还在啊!
只是想起亿万年前的海水吗?会飞的海浪翅翼搁浅在礁石上,龟裂的皮肤逐渐萎缩,丰盛水草间肥沃的鱼族已无踪迹。
心早已将劫难化为一面冰凉的镜子。
清澈,透明,空远。与天空拉开遥远的距离,并不疏远。每个夜晚数着星辰。心依然爱着辽阔。
青色、稚嫩变为金黄的草甸,养育黑白分明、野性自由的鸟。风无可奈何地收敛脚步,放缓呼吸。
穿透地球疲惫的脉搏,将一切沉淀,救赎。
走向属于我的宁静的艾丁湖。
指尖沁入湖水,濯洗高处虚空的自我。
一些热烈在冰凉的湖水里消散。
苇叶裹满泥浆,黑刺扎入湖底。一些不离不弃的植物,艰辛地生长、蓬勃。
所有属于艾丁湖的生命,都不再辩解诉说,只为湖而生。
听说,艾丁湖的前生是一轮满月,有幽蓝神秘的光。
交河落日
陌生而又仓促,虔诚地翻阅一座故城。
无数次的往返,一次次的命中心扉,打开这不掩饰的虚无的城门,走进空旷的街坊、深巷。我仿佛归来的公主,提着白色裙袂,忧伤地徘徊故土,寻找久远的记忆。
交河里的杏花、杨柳,何人所栽?
这可是千年前的杏花?红肥绿瘦的水畔,只记得车水马龙的铃铛脆响。车师古道红霞弥漫,白云缭绕。我只吟得“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饮马的黄昏,交河是甜蜜、羞涩的。
汲水的女子粗布罗裙,婀娜地走出城门。城楼上的士兵迎风瞭望,目送倩影。交河两岸杏花怒放,杨柳依依,引得彩蝶纷飞,鸟语宛转。一年年,一遍遍,杏花开了败、败了开……
交河的杏花,生生不息地爱着、活着。
千年后的黄昏,残垣断壁,镀上金色的光芒,仍然凛然地存在。
月亮还是那个千年前的月亮。交河水千年不息,潺潺向东南奔流,生养一树又一树的繁花。
月光,像千年前,凝视这凄凉的城。
佛音仿若响起,殿宇空寂无人。
这是一个把信仰放在高处的国度。
玄奘法师取经归来,曾于此,高坐佛台,设坛讲经。
梵音似天籁悠扬,开悟如交河水清澈明亮。土塬、丘壑、墙垣,断崖、峭壁,或站立、或躺卧,成慈悲的百佛姿态。
古老的城就要入梦。
落日沿着山边缓慢移动,亚尔乡的村庄接受了这古老的太阳。
杏花,杏花
一
亚尔镇上湖村的杏树林,颠覆了火热的视野。
粉粉的白色,白白的粉色,烂漫了枝头,明亮了世界。一大片一大片的村庄、田野,丰饶出杏花的海洋。
蔚蓝静止,白云隐藏。天空伏下幽蓝的身体,做杏花的天井。
是天空囚禁了杏花,还是杏花绚丽了蓝天?
无数的笑靥,落在树枝、墙头……像一朵朵寒冬腊月暗香浮动的白梅,镌刻在坚褐色的枝杆上。
杏树道上,热瓦普、吉他,弹唱悠长。
缺了牙齿的须髯歌者,一展歌喉,动人的旋律穿透杏花的时光。
一匹堪称“吐鲁番马”的壮硕的马,佩著粉色的马甲。红黄白绿的点缀,丰润这早来的春天。
这属于杏事的温柔啊!
二
托克逊夏乡的杏花村从不甘示弱。
一棵又一棵的杏树牵手走向田野的尽头。一样的姿态,一样的轻灵,通透着辽阔、澄净的灵魂。
没有一片雪花的飘落,没有一滴雨水的注入……这无可逆转的干涸的苍茫命运。
尽情地打开,像遵守诺言,舒展万顷缤纷。
村庄、炊烟、废墟、山坡、牛羊,在怀抱里宠爱,在饥渴中衍生。
不敢超越一朵杏花并不高远的仰望,踟躇在她无限的素净清雅里。
哪怕是一支流落郊野的杏花,也有着独特的锦绣花蕊,让我们停下脚步行注目礼。
无声的触碰里,杏树舒展身体,一树一树的杏花如雪芳菲。
三
雅儿沟里村的夜晚,篝火升起。
粗壮的木头浑厚朴拙,炙烤黑夜的寒冷。
歌者再次用沧桑的嗓音,对着天空、黑夜吟唱对兄弟姐妹的爱。
古老的榆树伸出纤细的枝条,托举着月亮。它担心月亮醉了,会掉进篝火里燃烧。
我们像回到了黑夜里的冬天。
可所有的寒冷都在惧怕歌声、火焰、温柔……
等太阳升起,我们又会循着花香找回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