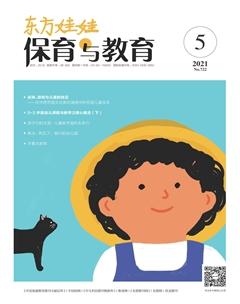反讽、游戏与儿童的自足
陈静
在儿童绘本的世界里,有不少作品充满奇思妙想,令小读者大笑不止、反复阅读,却令成人莫名其妙。它们或是内容离奇,或是反复谈论同一个话题,让成人深感无聊,以致产生隔膜感。这样的绘本可以归入荒诞绘本的范畴。何谓荒诞绘本?其中的“荒诞”所指为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了解具有差异的中西荒诞文化意识,研究这些意识影响下的儿童文学的话语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荒诞绘本的叙事结构要素与价值诉求。
不和谐与“诞兽”:中西荒诞文化意识溯源
“荒诞”是现代社会中一个十分常见的语汇。在文学领域里提到荒诞意识会让人想到“荒诞派文学”。1950年,“荒诞派文学”首先以戏剧形态诞生于法国,随后在欧美各国迅速传播与发展,并产生重要影响。无论中西,人类对荒诞之事的兴趣都由来已久,对“荒诞”的解释也大不相同。从词源意义上说,“在西方语境中诞生的‘荒诞(absurd)一词源于拉丁文absurdus,意为‘不合曲调(out of tune)或‘无意义(senseless)”[1],因此西方词源意义上的“荒诞”具有听觉性和抽象体验感。在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荒诞”一词逐渐获得了“缺乏理性或恰当性的和谐”“与理性相悖”的含义,即欧美荒诞派文学的文化意识——“一种认为我们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里陷入了困境,而且无论是上帝与人类、还是神学与哲学都不能解释人类的这种困境的想法”[2]。与词源意义上的“荒诞”一样,荒诞派文学之“荒诞”关涉的也是人类的本体体验,其中的“无意义”乃是人类个体无法在自身情境中找到和谐、价值与归属感时的心理外化。欧美荒诞派文学谈论的人类境况并非没有意义,而是其中再无确定不疑的现成意义。人类在其中需要面对的始终是自身的虚无与异化——一种如加缪(Albert Camus)所说的人类丧失家园,又与自身生活分离而产生的荒谬感[3]。荒诞派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是加缪重新发掘的神话形象——推着石头上山而石头又滚落下山,乃至终日为此劳碌的西西弗。此外,《變形记》《等待戈多》《百年孤独》等作品中的人物情境与经历亦是荒诞派文学的典型。
中国文化中的“荒诞”文化意识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东方朔在《神异经》中提到一种生活在西南荒的异兽:“其状若菟(作者注:‘菟通‘兔,下文将统一用‘兔),人面能言。常欺人,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4]这就是兔身人面、操持能与人类交流的语言且常欺骗人类的“诞兽”。东方朔的西南荒之“诞”大约就是中国文化中较早出现的东方“荒诞”意象,它依靠奇幻审美构造而来,带有视觉性与叙事感,强调人类体验与现实影响。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随大荒诞兽演变出“荒诞不经”一词。明人张岱在《家传》中所言:“与人言多荒诞不经,人多笑之。”[5]这句话中的“荒诞不经”被继续用来强调真伪之别,有“离奇,古怪,不合常理,不足为信且引人发笑”的意思。
西方荒诞意识指向的是一种异化虚无的人类生活,而中国的诞兽则凭反差性的意象强调谎言迎合人类、借人之口传播的生活表象。中西方荒诞意识各有其文化渊源,其所指与本质大相径庭,但是它们都强调荒诞乃是诉诸人类体验的某一情境,或充满无意义感,或带有奇幻色彩,或欺人却有趣,或引人发笑,等等。正是因为种种情境可供体验,围绕荒诞意识所包含的情境构造文学话语,包括面向儿童读者进行文学创造才成为可能。
奇幻与无意义:从荒诞意识到儿童文学构造
如果把中西荒诞文化意识的构造辐射到文学,那么诞兽式叙事可以构造出意象奇幻(“兔身人面”)、夸张虚构(“常欺人”)而令人沉迷(“其肉美”)的文类。此类文本在成人文学的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是现代儿童文学展开的重要方式。究其原因,或许与现代儿童文学中需包含顺应儿童热爱幻想、拥有假想同伴的自足性有关。在与自身生命内质相符的奇幻叙事中,小读者才可能充分体验他人在不同寻常的境遇中面临的种种状况,探索生活可能的样貌。可以说,奇幻式荒诞儿童文学与儿童的假想同伴作用类似,既可提供陪伴,赋予儿童勇气,给予他们生活策略方面的引导,又能给他们带来审美的情感宣泄与愉悦。
不过,小读者对奇幻故事的热衷并不代表荒诞儿童文学仅仅转化诞兽表征,而排斥不和谐、无意义的荒诞构造。这既是因为充满自由与想象的文学创造绝非遵循一种模式,也在于中西荒诞意识在面向受众时具有融会贯通的内核。诞兽的“言东而西,言恶而善”可以转化为文学中的不可靠叙事,也意味着其中言说脱离了人类行动和追寻意义所依据的现实。因而,所有受诞兽式文学话语影响的读者都需要在现实与虚构关联的基础上,发展经由奇幻之境构造意义的思维能力。西方荒诞派文学在将角色抛入行为脱离现实、既定意义丧失的环境时,其荒诞情境也十分注重给予读者体验感,强调读者经由荒诞文学领悟世界的无意义与荒芜感,重获探索自身的力量。因此,中西荒诞文化意识在文学与读者的互动中殊途同归,在创作中亦可互相融合。在荒诞儿童文学的创作中,融合上述荒诞意识的作品,在叙事上既可侧重充满想象的奇幻虚构,又可以运作为无意义的情节变奏,或两者合一为“无意义的有意思”。
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兼具奇思异想与无意义的荒诞意识在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的《荒诞书全集》(A Book of Nonsense, 1846)中比比皆是,本文略举一例加以说明。《荒诞书全集》中有一首这样的诗:
There was a Young Lady of Troy,
Whom several large flies did annoy;
Some she killed with a thump,
Some she drowned at the pump,
And some she took with her to Troy.[6]
特洛伊有位年轻女郎,
几只大苍蝇惹得她抓狂;
她“啪啪”拍死几只,
用水泵又淹死几只,
剩下的带回了特洛伊家乡。[7]
这首诗的原文和译文都有齐整的韵脚(AABBA)和动感的节奏,也包含一种滑稽的荒诞感 —— 一个人花式打苍蝇的行为,这是人类不胜苍蝇之扰而大动干戈的表现。这种理解越是成立,诗中人类的存在状态就越有违理性,乃至产生一种人类被机械化、变成打苍蝇机器的感觉。这也是女郎行为引人发笑的原因,因为“任何行动和事件,如果会使我们感觉到一个既是活生生的又是机械僵硬的东西,那就是滑稽的”[8]。这首诗具有的轻松活泼、毫无说教气息的特质就是所谓的“无意义的有意思”,其“无意义”表现在人物行为上,“有意思”则与作品的离奇表述不无关联。
利尔的荒诞诗在他生活的时代红极一时,他因此被后人大为赞颂:“而儿童像移民涌向他,他成了乐土。”[9]这一切或许均与“无意义的有意思”息息相关,而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1865)亦有此特质。后世的世界儿童文学创作追随此二人的脚步,“通过‘荒诞的 情节、‘疯狂的人物、‘巧妙的语言等”[10],向儿童展现包括无聊、奇幻、脱离常规、不和谐等在内的种种荒诞可能。与成人的荒诞文学相比,荒诞的儿童文学作品轻逸、活泼,犹如儿戏,仿佛毫无向世界标榜自身重要性的意图,但这正是荒诞儿童文学向成人提出审美挑战的表现。在荒诞文化意识进入儿童绘本领域后,由于需要考虑低幼儿童的接受状况,其中“无意义的有意思”的程度被加强,这更使上述挑战变得严峻起来。
反讽、游戏与儿童的自足:荒诞儿童绘本的结构与价值
世界儿童文学的荒诞文本在诗歌和小说领域的代表——《荒诞书全集》和《爱丽丝漫游奇境》在诞生时就不仅诉诸文字,还配有精彩的插图。这似乎在暗示荒诞文学理应在图像叙事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毕竟图画塑造想象之物的功能与视觉性的荒诞文化意识(“兔身人面”)颇为契合。荒诞儿童绘本满足了荒诞文学以离奇滑稽、富有冲击力的具象图景进行叙事,以更直观的方式影响受众的内在需求,因而在现代社会中颇为常见。
中西荒诞意识都有将受众引入情境的趋向,正是情境的存在为荒诞意识向图文的双向转化提供了动力,而图与文以何种关系创设荒诞情境则是荒诞绘本艺术的核心问题。《荒诞书全集》和《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初始插图都呈现文图一致化的倾向。诞兽“言东而西,言恶而善”的双向性则意味着荒诞情境亦可以图文背离的关系展开。据此,本文将荒诞儿童绘本分为图文非一致的背离关系与图文一致的对位关系两类。绘本作为叙事文体,其荒诞情境既可能在情节突转处发生,进而影响整个叙事的走向与寓意;也可以贯穿于文本始末,以演绎自身的多样化为叙事重点。这意味着,只要绘本的关键情节出现了一处荒诞情境,就有将其归入荒诞绘本之列的可能。下文将就荒诞绘本的两种类型——“图文背离型”与“图文对位型”举例,探讨其各自的叙事结构要素与相关价值。
1.“图文背离型”荒诞绘本的图文反讽与儿童自足
“图文背离型”荒诞绘本是在图文叙事内容相互背离的关系中促成荒诞情境的儿童绘本。这种背离可以表现在绘本的关键性部分,也可以贯穿全书。本文以美国绘本的里程碑之作《100万只猫》(Millions of Cats, 1928)为例,对此加以说明。这部绘本的荒诞情境出现在文本叙事的突转处。书中的老爷爷奉妻命去寻一只猫,却带回了几百万只。书中的荒诞情境在于具有竞争关系的几百万只猫在翻页之间突然消失。虽然文中交代“我想一定是他们互相把对方吞掉了”,但整洁干净的环境怎么也不像是凶案现场。这本书的图文背离大大加强了绘本图文本已存在的“反讽”状态——“图画书中的文字和图画的关系往往是反讽的——其中一个说起的事情,另一个必定保持缄默”[11]。这种反讽性还促使读者对幸存的小猫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一般的看法认为,《100万只猫》是作者婉达·盖格(Wanda Gag)运用民间叙事手法创造的绘本。民间故事的“描述给出的只是纯粹的行动,而放弃了任何细致入微的描述。它提供了情节线,却不让我们体验情节的背景”[12]。可见,民间叙事传统促使盖格省略作為背景的猫咪竞争图景,这一点与提供情节线的文字互动则产生了引人遐思的文本裂痕。在此影响下,有人将注意力放在图画未曾呈现的几百万只猫的消失这一荒诞情境上,认定被选中的小猫是超自然的存在,具有魔鬼一般的狡诈与耐心,它参与了同伴互吞的竞争,作为胜利者笑到了最后。有人则相信图文情境里的正义性,认为藏起来的小猫具有谦卑者的智慧,它对自身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两种观点之所以分歧巨大,完全是因为它们与绘本互动的重心不同:前者利用了图文背离的冲突,后者则选择相信图文表达中的一致性倾向(具有图文背离关系的绘本实际上并不排斥图文一致关系的使用)。由此可知,荒诞意识对真伪与离奇的关注,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受众的力量,加剧了绘本图文背离产生的反讽性。作为符号对象之间的冲突,反讽“充满了表达与解释之间的张力”[13],使绘本的内涵变得异常复杂。但这种局面也令人希冀对《100万只猫》的阐释可以超越善恶价值的评判,获得直面现实的可能。
如果考虑到童书需要关注自身与儿童之间的关系,那么就需要在阐释中把小猫的处境看成契合儿童心理的情境,即“《100万只猫》似乎也是为安慰大家庭中害怕被忽视的儿童读者而创作的,它让小读者去幻想父母亲会拒绝其他所有孩子而去爱自己——这个与所有其他孩子的外表和设想都相反的孩子,并始终都最值得关注”[14]。当阐释面向儿童的内心期望时,回望《100万只猫》的文图背离之处,会发现其中的图文叙事完全是一种对儿童心理的整合表达,是面向儿童心灵化需求的表现,而非对具象现实状况的模拟图景。如果将图文背离关系所引发的反讽贯穿《100万只猫》全书,则会发现以之为代表的“图文背离型”荒诞绘本的叙事结构要素一方面需具有同时包含真伪可能的荒诞的矛盾性,另一方面则应在图文中隐藏走近儿童个体的宣泄式虚构,从而使儿童个体通过奇幻荒诞追寻自足体验,为其内心生活注入希望与活力。
《100万只猫》中的“图文背离型”荒诞情境虽然不多,但对整体叙事而言非常关键。这种图文关系也可贯穿整部绘本,推进荒诞情境的展开。约翰·伯宁罕(John Burningham)充满儿童与成人的冲突、现实与幻想的对立的《莎莉,离水远一点》(Come away from the water, Shirley, 1977),乔恩·克拉森(Jon Klassen)利用双重视角叙述的《这不是我的帽子》(This is Not My Hat, 2012)等绘本作品,都始终贯穿着荒诞情境,将图文反讽与儿童自足之间的关系演绎得十分充分。它们同样具有荒诞的矛盾性与隐形的宣泄式虚构并存的叙事结构要素,同属面向儿童心理言说、帮助他们暂时解除日常规范的限制并给予他们超越现实之快乐的绘本艺术。
2.“图文对位型”荒诞绘本的游戏变奏与儿童自足
“图文对位型”荒诞绘本是在图画叙事与文字叙事互相对应的状态中创设荒诞情境的绘本。由于荒诞情境在图文配合中体现,其中的荒诞性会因图文的一致性得到强化,从而产生需要借助变奏赋予文本多样性的创作需求。关于这一类型的绘本,本文以德国儿童文学家玛加蕾特·克拉拉(Margaret Klare)和瑞士插画家克劳迪娅·施密德(Claudia Schmid)合作的《沙伯纳克》(Schabernack, 2002)为例进行论述。
《沙伯纳克》是一个以“在路上”为主题的绘本,其中的文字具有介绍图画中的人物、人际关系与行为的功能,因而促成了文图叙事的一一对应。书中的两个人类和一只猴子沙伯纳克在路上行走。他们在登上一座巨人山顶时,沙伯纳克为了制止猎狗、公鸡、母鸡和青蛙的争吵,将他们一一装进口袋。下山时,口袋撕裂,所有动物都掉了出来,最后还掉出来一只巨大的蟑螂。蟑螂把所有动物吞入腹中,包括两个人和一只猴子,然后这只蟑螂爆炸了,所有角色又转危为安……
这本书中,除了蟑螂,所有角色音译出来的名字都包含“克”的发音——施尼克、施纳克、沙伯纳克、达克、吉克、伽克、塔克-塔克和克瓦克等。因此,即使朗读译本,这本书也会由于不断出现“克”的发音而形成韵脚跳荡的活泼感。这合乎动物的喧嚣,却被沙伯纳克和蟑螂的两次禁闭打断。两次禁闭显然与动物们的生命节奏不尽相符,充满了不和谐。同时,由于禁闭关押人物的增多,禁闭之所最终自动崩溃。这种充满不和谐和无效性的情节连续发生了两次,使整个故事由偶发性的禁闭悲剧转向情境重复而引发的无端荒诞。两次禁闭紧密相随,使喜剧中常见的荒诞、滑稽动力——“以无情的速度堆砌起来的一场场灾难”[15]随之到来。
对《沙伯纳克》来说,朗读声效是加剧书中情境荒诞性的要素,但促成荒诞感的根源则在于潜在对抗使压制变成了游戏般的无效事件。两次重复的禁闭事件包含着刺激读者的危机,但危机会随时间的推移演变为令人兴奋的破解过程与解放结果,让人觉得全书讲的是一个恶作剧的故事。而在德语中,“沙伯纳克(schabernack)”一词的意思正是“爱搞恶作剧的孩子”。在绘本中,这体现为猴子以禁闭的方式关押了所有动物。但很快就连恶作剧者沙伯纳克也被蟑螂吞入腹中。关人者和被关者此前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完全颠覆,转而变成了引人发笑的共同禁闭状态。
可见,密集的声效、堆积灾难的喜剧性和对抗性的人物关系是使《沙伯纳克》中的荒诞情境成立的变奏性结构要素。同样的叙事要素在长新太(Shinta CHO)强调期望与现实互动的无厘头力作《圆白菜小弟》(KYABETSU-KUN, 1980)以及本尼迪克特·弗洛伊桑(Benedicte Froissart)和皮尔瑞·普拉特(Pierre Pratt)合作的让幻想侵入现实、艺术冲击日常的《亨利叔叔的晚餐客人》(Uncle Henrys Dinner Guests, 1990)中也可寻见。在《圆白菜小弟》中,上述要素表现为书中重复的一声声“嘣咔——”、猪山大哥一再幻视的吞食圆白菜而被异化的动物的灾难性形态,以及他们敌对关系的最终破解。在《亨利叔叔的晚餐客人》中,同样不断出现具有声效的拟声词,颜色爆发、杯盘倾覆等灾难的堆积也隐隐存在着对抗性的人物关系。
在“图文对位型”的荒诞绘本中,故事生动形象且充满喜剧性,内在包含既对抗又和解的人物关系,看似莫名其妙却具有充分的游戏变奏精神。这里面似乎没有什么教益性的内容,一切都只是无厘头,却与儿童期望超越日常、超越现实的非理性精神诉求息息相关,是以游戏变奏顺应儿童发挥想象力的自足精神而诞生的绘本艺术。
结 语
人们在很久之前就对荒诞不经之事充满兴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仅成人可以借助荒诞意识重新感知世界,重启追寻价值和意义的脚步,就连儿童也因追求自足精神的内在需求,希冀与充满奇幻、无厘头、“无意义而有意思”的荒诞叙事相遇。在图文背离与图文对位中,荒诞绘本中荒诞的矛盾性与宣泄式虚构并存,以包含声效、喜剧性与对抗性的叙事结构要素为儿童开启了为日常所遮蔽的见识与想象、欢乐与灵光的大门。日本绘本大师安野光雅(Mitsumasa Anno)有言:“仅仅教孩子们‘正确的概念并不总是好事情。科学的理解很重要,但也应该鼓励发挥想象力。”[16]正因如此,荒诞绘本对儿童才是充满价值的,对成人则意味着需要与之碰撞,从而发现自身与儿童可以共享的审美体验与智性愉悦。
【参考文献】
[1] 吴靖. 荒诞简史. 澎湃新闻.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810064, 2020-11-02.
[2] (美)查爾士·B.·哈里斯. 文学传统的背叛者[M]. 仵从巨、高原,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3] 参见(法)阿尔贝·加缪.《西西弗的神话》[M]. 杜小真,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张华等. 博物志(外四种)[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
[5] 张岱. 琅嬛文集[M]. 云告,点校. 长沙:岳麓书社,2016.
[6] Edward Lear. The Book of Nonsense and Nonsense Songs[M]. London;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s, 1996.
[7] (英)爱德华·利尔. 荒诞书全集[M]. 杨晓波,译.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1.
[8] (法)柏格森. 笑与滑稽[M]. 乐爱国,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9] 卞之琳. 无意义中自有意义——戏译爱德华·里亚谐趣诗随想[J]. 世界文学,1993, (3).
[10] 赵明. 荒诞的儿童文学[J]. 湖南社会科学,2013, (2).
[11] (加)佩里·诺德曼. 说说图画:儿童图画书的叙事艺术[M]. 陈中美,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
[12] (瑞)麦克斯·吕蒂. 欧洲民间童话:形式与本质[M]. 户晓辉,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
[13]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4] (美)克劳迪娅·纳尔森.心理分析对儿童图画书创作的影响——以《一百万只猫》和《逃家小兔》为例[J]. 谈凤霞 , 译.保育与教育 ,2016, (1).
[15]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M]. 黄灿然、李桂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16] (美)伦纳德·S.马库斯. 图画书为什么重要:二十一位世界顶级插画家访谈集[M]. 阿甲等,译. 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