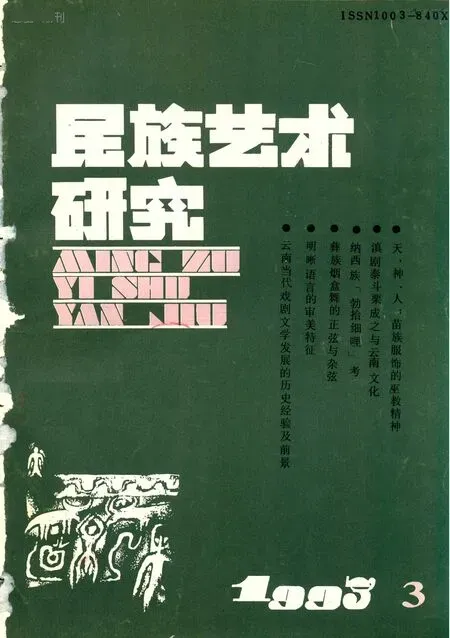柏拉图技艺论与古希腊艺术的传统和革新
——从《法篇》《智者篇》及《政治家篇》中的艺术对话谈起
孙晓霞
探讨柏拉图思想与希腊艺术中的传统和革新问题,不得不从埃及艺术传统说起。埃及艺术只允许摹仿前辈而不可有新发明的宗教禁忌①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The History of Ancient Art I&II,Curtis Bowman ed.Thoemmes Press,2001,p.171.,因此我们看到埃及艺术的特色之一就是所有雕像、绘画及建筑形式都遵循同一种稳定的风格,这套风格有严苛的范式:坐着的雕像必须把双手放在膝盖上,男人的皮肤颜色必须要比女人的深,太阳神赫拉斯必须表现为一只鹰,死神阿努比斯必须表现为一只豹②参考[英]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等等。熟稔艺术的柏拉图③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us,约200—约250年)记载,柏拉图本人可能研习过诗歌、绘画,并热爱体育,他“曾经投入到绘画学习中,他还写诗,起初是写激情狂热的诗歌,后来创作了抒情诗和悲剧”,甚至一度要去争夺巴克斯悲剧奖,因此他对诗歌的论说很有可能是有实践基础的。柏拉图还跟随阿里斯顿(Ariston)摔跤手学习体操运动,身形健硕,甚至还曾在地峡运动会上(每两年一次在科林斯地峡举办仅次于奥林匹克的地峡运动会)参与摔跤。此外,他跟随昔兰尼的赛奥多洛(Theodorus of Cyrene)学习数学。柏拉图将数学知识与绘画等艺术活动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也是有其合理性的。(Diogenes Laërtius,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literally translated by C.D.Yonge,London:George Bell&Sons,1828,p114—116.)不过第欧根尼的这本书附会有很多希腊神话人物与哲学家交流的故事,也使其可信度大打折扣。对此深以为然。他之所以景慕埃及艺术,是因为他相信埃及人严格遵守了艺术中的秩序和尺寸这一传统。在后期的《法篇》④目前学界对柏拉图的对话录分期已基本达成一致,如德国古典学者保罗·纳托尔普和王晓朝译本皆将《智者篇》《政治家篇》《法篇》列为柏拉图的后期著作。不过,保罗·纳托尔普也提醒我们对年代日期的不同意见不应成为人们接受对柏拉图对话内容进行事实性阐明的障碍,见[德]保罗·纳托尔普:《柏拉图的理念学说——理念论导论》,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版前言。中论及音乐的教育功能时,柏拉图以“雅典人”的口吻,援埃及以自警,胪举埃及人在法律中所规定的各类艺术发明,音乐和绘画、雕像三类被划为重点,强调传统和法则在艺术中的重要性:
这个国家(埃及)似乎很久以前就承认了我们现在肯定的真理,如果这些姿势和旋律是年轻一代公民的习惯行为,那么它们必须是好的。所以他们把各种类型的发明集中起来,把样品存放在神庙里。除了按照传统模式创作,禁止画家和其他设计艺术家发明新的模式,这项禁令仍旧存在,适用于这些艺术以及音乐的各个部门。如果你观察他们各处的绘画和雕塑,你会发现一万年前的作品……既不比今天的作品好,也不比今天的作品差,二者表现出同样的风格……这是因为埃及人无比信任他们的立法者和政治家。在埃及的其他制度中无疑也可以找到许多根据,但音乐问题——它至少是个事实,很有说服力的事实——实际上证明了在这样一个范围内用法来规范展示内在永恒正确性的旋律是可能的。(《法篇》656E-657B)①《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404页。
柏拉图认为埃及的这种万年不变的风格之所以能够延续,端赖埃及人始终贯彻一种相同的艺术规则,此规则可以展示一种永恒性和正确性。相反,雅典人的艺术在他看来是屈从于无秩序的愉悦,将艺术委托给感官判断,这是柏拉图所谴责的。而那些在西西里和意大利表演习俗中,通过听众投票来决定胜利者,听众成为裁决者,这种做法既腐蚀了诗人,又腐蚀了听众的品味,故而艺术同样要有“法律”宣布为正确的规矩来约束诗人和艺术家。立法家可以劝告甚至强迫拥有天赋的诗人来创作高尚优美的诗句、适当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法篇》659C-660A)。②《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那么柏拉图对艺术规则的这种严苛要求是否有其现实的艺术实践土壤?
一、有机规则:古希腊艺术的理想主义传统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生活于古希腊历史进程的中晚期,其时的城邦政制、文化、艺术等都刚刚经历过生气勃勃的黄金时代③这被后世称为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年—公元前429年)黄金时代。,处在即将由盛入衰的“后鼎盛”期。一方面出现了各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各类理论经过沉积后极大地丰富起来。作为技艺的一种,各类艺术的经验性知识中获得了一般性的标准和稳定的规则,艺术理论著述颇为丰富④这一时期的艺术理论主要是基于经验的。黑格尔认为艺术是一门从经验出发的科学,其标准和法则也是经过挑选和汇集形成的,然后经过进一步的更侧重形式的概括化,就形成了各门艺术的理论。([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页。)。较为知名的有希兰纳斯的《关于多利安人的对称美》、画家帕哈修斯的《论绘画》、雕塑家波留克列特斯(Polykleitos)的《法则》(kanon)⑤波留克列特斯认为,一件成功的雕塑作品依赖于对抽象法则的准确应用,因此重点不在对立平衡的形式,而是比例和尺寸问题。在论文《法则》(Kanon)中,他提出了关于雕像制作中所遵循的原理和使用的比例,规定身长与头部的标准比例是7∶1。在后世的艺术史学家看来,波留克列特斯制作的《持矛者像》(约公元前5世纪)描绘的是其心目中理想的运动员或武士像,因此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示范,以辅助其论文《法则》,而波留克列特斯给这尊雕像起的名字本是与其论文同名的——“法则”。[英]简·爱伦·哈里森:《希腊艺术导论》,马百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5页;又见弗雷德·S·克雷纳、克里斯汀·J.马米亚《加德纳艺术通史》,李建群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32、133页。;音乐方面有公元前5世纪的达芒(Damon of Athens)关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论文,其中提出特定的旋律与节奏能够模仿特定类型的性格与生活方式,以及索福克勒斯的《论合唱队》,等等。尽管这些著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从佚散后世的片断及引注中可知,一种遵从数的规则的原理性知识在希腊时期的艺术经验知识的总结中是普遍存在的。⑥[美]门罗·比厄斯利:《美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代》,高建平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5页。
事实上,规则、法度、原理等确切的理论表述始终是希腊艺术家孜孜以求的。温克尔曼的艺术史考察发现,古希腊雕塑中,即便是处理衣褶也都在讲究一种规则。他夸赞尼娥柏的衣衫是按照一种规则刻画,使之成为一组组的形式,是古代最优美的衣衫;远古时代的艺术家盖伊(Heioy)的雕刻作品中,狄安娜穿的衣服从鼓起的部位自由地向两旁垂落,这不同于近代艺术品中衣褶的变化多端和错落曲折。①[德]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邵大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同时,希腊人习惯性地将数、线条、几何图形等作为一种能表达普遍性的最优方式,艺术家对抽象的、确切知识的热爱将技艺概念中的知识特性不断具体化。如西西奥尼(Sicyonian)派的雕塑家声称,他们的艺术就是知识;建筑学则遵从静力学规则的知识;绘画家帕姆菲拉斯更宣称,“任何一个缺乏建筑学与几何学知识的人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②[波]沃拉德斯塔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耿幼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3页。。
规则成为希腊人艺术创作的核心:建筑由于其内在秩序和完美结构而成为艺术,画家通过正确再现而创造出美的整体。为达到这种效果,“艺术家必须了解和运用统治世界的永恒法则”③[波]沃拉德斯塔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耿幼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3页。,优秀而真实的艺术的标准就是要与世界法则相一致,并符合道德秩序,“由于艺术的标准存在于恰当之中,其支配原则必然是理智而不是情感”④[波]沃拉德斯塔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耿幼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3、164页。。显然,在当时社会中普遍盛行的艺术标准是法则,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是规则,这并不只是柏拉图一个人的独断,而是当时艺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质。对称、秩序、比例等基于规则的原理性要求,在艺术创作中不仅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得到了理论化的阐述和分析研究,从而将规则问题从经验性的范本生产推向理论化、知识化的原理性分析,一种科学化、普遍化的理论表述在艺术活动中盛行。
若仅就艺术的规则问题而言,柏拉图对城邦中那些不合法度的艺术的反对是合乎其历史逻辑的,但问题是,作为一种完美的、古典化的艺术活动,希腊人的艺术中又处处体现着发明和创造力,这似乎又与稳定少变的规则、法度等要求相悖逆。那么希腊人是如何在一种稳定少变的规则性知识和不断追求完美的好奇心所引发的发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的呢?
过往理论多笼统地将其归因为古希腊艺术的理想主义,认为希腊艺术作品创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应用稳定普遍的知识揭示和支配自然的规则,其间体现着一种理想主义的艺术风格。如温克尔曼相信希腊人是根据理想的观念和严格遵从真理而对待艺术问题的;黑格尔也以古希腊雕像为古典型艺术的代表,认为它体现的是完美理想的艺术创造。对称、比例等规则性的核心理论与希腊人自由想象的艺术创造的平衡和谐,形成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艺术风格等。而现代理论研究就此形成了如下几种新的、更为具体的判断。
第一种是超越民族性。著名古典学家简·爱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在考察了理想主义艺术所具有的形而上特质后,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埃及、亚述和腓尼基皆已消亡的情况下,希腊艺术能独树一帜,永葆青春?答案是,希腊艺术的特殊品质在于其具有“某种广博和普适性,其中的民族可以消亡,但这种品质永存不朽”⑤[英]简·爱伦·哈里森:《希腊艺术导论》,马百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前言第1页。。通过分析希腊的塞利努斯的排档间饰特性,她指出,希腊艺术的独特品质就是“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其艺术中,就是由人神同形同性(神)、英雄崇拜(英雄)、对完美人体的追求(人类)三者组成的。“从特殊的上升到普适的,这种本能最终导致了最高级形式的理想主义。”⑥[英]简·爱伦·哈里森:《希腊艺术导论》,马百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前言第122页。哈里森对希腊艺术的这一判断,洞见到希腊人在艺术创作活动中从民族形式中跳出,形成对特殊形式的普遍化这一特征。在艺术中追求人性化、普适性特质与柏拉图在其技艺概念中所追求的普遍性知识的目标和理想不谋而合①参考孙晓霞:《“技艺”理论研究与西方艺术学科起点》,《文艺争鸣》2020年第2期。。
第二种是有机规则论。塔塔尔凯维奇认为希腊艺术是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完美结合。他认为,与埃及艺术生硬的规则约束不同,在希腊人眼里,规则是重要的,但却不是像埃及一般让标准化的规则僵化不变。希腊艺术中除了对规则性技艺的掌握和遵守,更注重在抽象理论的引导下,探求和发现新规则,因为在他们眼中艺术的“规则是一种发现而不是发明,规则是一种客观真理,而不是人的构造”②[波]沃拉德斯塔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耿幼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3页。。不断发现新的规则,这就令希腊人可以抛开传统禁锢,无须固守旧规则。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突破传统、更新规则,生成有机规则的新可能。
塔塔尔凯维奇认为,只有公元前5—前4世纪的伯利克里时代前后,才是西方文化艺术最完美的顶点时期,才可被称为古典时期,这些作品是其他古典时期的原型和新古典主义的典范和榜样。③相较而言,巴洛克是兼具古典和颓废时期特征的艺术;哥特式和浪漫主义艺术则由于追求的是极端而不是适度,因此不能称为古典的。([波]沃拉德斯塔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耿幼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1—63页)米隆的青铜雕塑善于捕捉运动员努力瞬间的复杂身体姿态;波利克莱图斯用石头刻画运动员身体静止时的完美平衡、对称和比例;菲迪亚斯则在青铜雕塑的作品中将优美和伟大统一起来。这些雕塑作品在对称之外还追求一种更为高妙的、更符合有机的人体规则。塔氏总结的过程是:最初他们大体上遵守规则;然后他们有意识地偏离它们;最后,他们抛弃了传统的程式化模式,转向了有机形式。④[波]沃拉德斯塔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耿幼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9—70页。
第三种是规则矫正论。对于希腊艺术中的规范之改良问题,贡布里希曾探讨过它在知识层面的发展逻辑。贡布里希承认它是一种对概念式艺术的“习惯的突然背离”⑤[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正本、范景中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但他更强调希腊艺术是通过图式和矫正来实现的,它所遵循的规则不是一成不变地复制历史,也不是彻底地抛弃传统程式,而是根据知识的扩展而进行修订、矫正和完善的,这是希腊艺术获得成功的根本。新的变化与其说是偏离规则,不如说是基于完善技艺所诉求的一种新型创作方式。他们的图式是严谨、规范的,是艺术家应首先知道和掌握的规范,同时艺术家们要通过观察现实,并以模仿为手段,根据自然形对比先前的概念式图式进行连续的、系统的矫正,直至运用新的模拟技巧匹配现实取代制作。⑥[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正本、范景中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140—171页。这样的雕塑作品方可既“达到了完美的和谐,又没有带来预料之外的新问题。古典时代就是这样解决了问题”⑦[美]苏珊·伍德福德:《剑桥艺术史——古希腊罗马艺术》,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8页。。在新原则和新技巧的支撑下,希腊艺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再重新组合的实验方式,重新塑造理想化的体格、运动、衣饰等类型,形成了一批新的、较埃及人更为丰富的图式或模型。
上述研究视角不一,但都承认希腊人在理性指引下的思路清晰的选择能力,配合着对理想秩序的追求,创造了艺术的经典。通过有机化处理以寻求新的艺术法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艺术规则随时可以修改和校正;同时它们注重比例且以哲学中的事物的理想比例来规定雕塑。⑧[波]沃拉德斯塔维·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杨力、耿幼壮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9、70页。这一点在数学界也已成常识,希腊人的雕塑“并不注重个别的男人和女人,而是注重理想模式,这种理想化加以扩展后,就导致了身体各部位比例的标准化”⑨[美]莫里斯·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张祖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页。。这构成了古希腊艺术理性知识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典型气质。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不断的改良终究会触发革命性的震荡,这一点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更加彻底地显露出来。
二、革新:来自视错觉手法的理论挑战
阿诺尔德·豪泽尔认为埃及艺术的特点同样是遵循理性主义的造型原则,但它太安于标准化生产,相反,支持标新立异却是希腊艺术的精神特征①[匈牙利]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黄燎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0页。;而贡布里希的看法是希腊艺术并没有比埃及高明多少,之所以能产生这种新变,原因是出现了一个“希腊革新”的时代②事实上,贡布里希并不认为希腊艺术是革新,而只是规则的改良。“希腊雕塑和绘画的各种技能也被证明是惊人地有限,一批数量有限的公式被用来表现站立的、奔跑的、战斗的或跌倒的人物,希腊艺术家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反复使用,只有比较细微的变化而已……希腊的艺术语汇比起埃及的多不了多少”。见[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正本、范景中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171、172页。。对传统习惯的偏离与当时哲学、科学以及“剧场政制”(theatocracy)③“政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术语,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密不可分,如溥林译本中甚至将其名篇《国家篇》译为《政制》,见[德]保罗·纳托尔普:《柏拉图的理念学说:理念论导论》,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19页。“剧场政制”一词还参考孙晓霞:《柏拉图“剧场政制”论与诸艺术的统一性——基于艺术学科视角的历史考察》,《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11期。的发展交相呼应,导致艺术规则突破与范式革新,其直接表现则是艺术中新技艺、新知识的不断涌出。其中,艺术家采用的弥补视错觉方法给哲学家的理性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据维特鲁威《建筑十书》载,在埃斯库罗斯创作悲剧时,阿加萨霍斯(Agatharchus)曾撰写了关于剧场布景的论文,后来德谟克利特和阿那克萨戈拉受他启发,也撰写同一主题的论文,论述在布景绘画中精确再现建筑物的外观时所应用的视觉与光学原理,以及绘画中的透视内容④[古罗马]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美]I.D.罗兰(英)译,陈平(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而塔塔尔凯维奇考证发现,古希腊艺术中允许那种因光学和视角改变而描绘出新的物体外形,“视角”被引入,绘画中加入了“投影术”。假如我们希望看一个圆,艺术家必然会画出一个椭圆。这在古代是艺术家和理论家都熟知的一种图形绘制技艺,不过,现存较早的是一位2世纪的希腊数学家留下的相关论述,“一个圆有时会被画成一个椭圆形,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同样,方形可以被画成长方形,尤其是放在高处的物品的外形与它的实际形象根本不同”。⑤Wladyslaw Tatarkiewicz,Two Philosophies and Classical Art,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2,No.1(Autumn,1963),pp.3-8.也就是说,在当时人们很可能已经意识到需要光学的、透视的、空间几何等知识,来进行三维物体在二维视觉平面的呈现和转换。
建筑方面也大量应用了此类知识。现代艺术史显示,公元前447—前438年建成的帕特农神庙中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都严格遵循了这样一个代数公式:X=2Y+1。从外观看,神庙建筑的长宽比就是这样一个比例关系:短边有8根圆柱,长边有17根圆柱;基座的长宽比是9∶4,同样其内殿的长宽比,两个相邻的柱基的圆心距——轴间距(interaxial)与圆柱本身直径之间的比例也都依据上述公式来计算。但是在这一严格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事实,那就是该建筑有改良规则的诸多特征,例如不符合常规的横平竖直柱梁结构,圆柱均向内微微倾斜等,这些改良在现代学者看来符合“对偶倒列”,会使建筑更富生命力⑥神庙由建筑大师卡利克拉特(Kallikrates)和伊克蒂诺斯(Iktinos)设计建造。其墙面和山形墙的雕塑饰品是菲迪亚斯监督完工。参考[德]达格玛·卢茨:《古希腊艺术如数家珍》,程爽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45—47页。。对此现象更为直接的、不带感性判断的内容最早出现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在关于帕特农神庙的古代论文中⑦[美]弗雷德·S·克雷纳,克里斯汀·J.马米亚:《加德纳艺术通史》,李建群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136、137页。,维特鲁威发现古代建筑的这些调整,是在补偿视错觉(trompe l’oeil),并且这种视错觉弥补要严格根据模数比例的调整来进行。但是,哲学家认为采用这类手法的目的是欺骗眼睛和心灵,因此是不被允许的。
当然,反对视觉形象带来的感官愉悦并不只是柏拉图一个人的固执己见,而是当时社会面对巨型建筑和雕塑中新兴方法的普遍心理。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学者策策斯(Tzetzes)记录了古希腊的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①菲迪亚斯曾于公元前450年前后制作了雕塑作品《穆勒尼亚的雅典娜》,立于雅典卫城的入口处。参考[英]简·爱伦·哈里森:《希腊艺术导论》,马百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5、73页。的著名故事。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菲迪亚斯曾接到任务,要雕刻一个站立在高坛之上的雅典娜。菲迪亚斯将女神的头雕刻得比既有定律要求的大出不少,这遭到了雅典人的反对,因为他们关于艺术的观念是与柏拉图的真实、宇宙中心主义一致的,他们与柏拉图一样,对于创作幻觉变形艺术深恶痛绝。菲迪亚斯很难为自己的雕塑进行辩护,但他说服他们耐心等待,直到作品矗立在指定位置的那一天时,雅典人才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巨型雕塑。②Wladyslaw Tatarkiewicz,Two Philosophies and Classical Art,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2,No.1(Autumn,1963),pp.3-8.困扰菲迪亚斯的问题到下一个世纪时就大大消散了。老普林尼(Pliny)在著作《自然史》中记录了公元前4世纪希腊雕刻家利西波斯(Lysipus)对此种问题的最终定论:“过去的老艺术家展示的人是他们所是的样子,我所展示的是他们看起来是的样子。”③这段话在李铁匠译本中被翻译为“他喜欢说他创作的人,就像他自己看见的人一样。而他的前辈创作的人,则像过去的他们一样”(见[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史》,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39页),但从艺术史的角度来思考,此段表述显然不够明晰,为此本文重新参考了以下两个译本:一是在1961年英译的十卷本《自然史》中,该段话被译为:he used commonly to say that whereas his predecessors had made men as they really were,he made them as they appeared to be(Pliny,Natural history IX(LIBRIⅩⅩⅩⅢ-ⅩⅩⅩⅤ),translated by H.Rackham,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p.166.)二是塔塔尔凯维奇1963年发表在《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上的文章中,将这段话英译为“The artist of old showed people as they were;I show them as they seem to be”(Wladyslaw Tatarkiewicz,Two Philosophies and Classical Art,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22,No.1(Autumn,1963),pp.3—8)。综合以上两个英译本,作如上翻译。显然,新世代的观者对眼中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已经有了充分意识。面对舞台布景、雕塑和绘画等巨型作品时,视觉上的完美性,迫使人们不得不以新的角度重新定义艺术作品的真实性问题,视觉中的形象有了新的技艺法则,感官世界得到理论的观照,对艺术的变形开始有了肯定的声音。那么身处于传统与革新的世纪旋涡中,被认为是艺术保守主义的柏拉图④如贡布里希就认为柏拉图反对绘画等的疾呼与后世“反对‘现代艺术’的疾呼”没什么两样。见[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正本、范景中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要如何处理这些“不利”因素呢?
三、柏拉图技艺理论的张力:与艺术实践平行
面对“礼崩乐坏”的革新时代,柏拉图和当时的知识界一样,一时间无法接受在视觉艺术中采用视错觉弥补法。相比《理想国》中对艺术作为第三类模仿的批判,透视画和戏剧布景绘画,以及建筑和雕塑执着于通过幻象来满足视觉感官的审美需求,这激起了柏拉图更多的不满,自然要对这类制造错觉的把戏大加挞伐。突破法则以满足视觉的愉悦,这从道德伦理的哲学层面与柏拉图对话中所主张的视觉形象的制造之观点正相违背。为此,他指出,那些制作巨大尺寸的雕塑家或画家造出或画出与真实事物有相同名字的事物,是在利用视觉距离欺骗儿童,他们抛弃真相,制造出或大或小的像,只要显得美丽(《智者篇》234B、236A)⑤《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这类制造形象的技艺制造了知识的混乱,迷乱无知者的心灵,与玩弄词藻的智者技艺一样,都是一种不诚实的恣意的模仿(268D)⑥《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艺术的视错觉产生幻象,混淆了真与假的边界,因此作为一种“伪饰”的、不能反映真的知识,被钉在了“伪知识”的“耻辱柱”上①[英]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正本、范景中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152页。。艺术被理性世界所排斥。柏拉图宁愿选择信任人体这个自然物的完美和善。②在《会饮篇》中,柏拉图指出,人体美是趋向理念美的第一步,女人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体美的典型代表。但真正的美既不是一双手、脸或身体的一部分,也不是话语或知识,也不存在于动物、大地、天空等事物上,它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始无终,“它自存自在,是永恒的一,而其他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对它的分有。(《会饮篇》211B)”人们可以从个别的美开始探求一般的美。这里面有美的进阶,个别形体美——所有形体美——体制之美——知识之美——以美本身为对象的学问,则人类可以看到美本身。(《会饮篇》211C),见《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4—255页。
但是,哲学家同时意识到的,绘画、雕像中的这些新手法在提供所谓关于对象的“伪知识”的同时,也围绕绘画、建筑等本体形成了基于感官的新的专业性知识。例如,在实际的神庙建造过程中,建筑师对于视觉效果的追求并非背离理性,相反,他们强调要通过严密的数学推理来进行视错觉弥补,“在产生视错觉的地方,就要用推理来补偿”,也就是通过增加模数的比例来“弥补眼睛失去的东西,并以此满足视觉上的愉悦”③[古罗马]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美]I.D.罗兰 英译,陈平 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9页。。显然,当时的艺术家明确遵循着技艺的数理性规定,对先定规则的改良和变革也是基于严密的数理推理的④详见维特鲁威:《建筑十书》第3书第十章。。尽管十分厌弃这类艺术远离真实世界,批评它们只能通过模仿制造“虚假”形象,但具体到技艺范畴上,柏拉图不得不思考这类知识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后期,柏拉图似乎对艺术问题有一个明显的态度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对视觉艺术“真”的变形表示了默许。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模仿的本质。在《智者篇》中,柏拉图扩展了模仿的含义,将其从《理想国》中的负面定位,提升为一种制造形象的生产和受神性引导的行为。他指出,技艺与模仿归属不同的关联层。自然是技艺的产物,是“神的技艺的生产”(《智者篇》265E)⑤《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其生产是带有理性和先验性知识的(《智者篇》266B-C)⑥《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9页。;人的制作是模仿,其模仿要依赖特定技艺才能完成,因此“模仿确实是一种生产,只不过它生产的是影像,如我们所说,而非各种原物”(《智者篇》265B)⑦《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模仿是人之制造在模仿神性原物,该行为是人类制造不可或缺的一个途径。技艺的根本是神工制造,模仿的根本是人的制造,但模仿不只是简单地被动仿制,其背后的动力是对真理的一种趋同方式⑧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69—270页。。绘画中的形象就是以人的实物制造为前提而存在的一种虚假的东西,但这种虚假的东西并不是毫无地位的,它在存在物中拥有特定位置。因为其中借助了技艺这一途径,艺术的模仿指向了神性的真理性。简言之,艺术模仿幻象的技艺也是拜神所赐,因此艺术的“模仿”同样是在向真理趋同。
其次要解决的是标准和尺度的问题。柏拉图发现,即便是突破规则的事物,只要有衡量标准的存在,也就会存在规则与适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晚期名篇《政治家篇》中,柏拉图通过比较政治技艺与纺织技艺论述了“适度”问题,提出了两个相关联的命题:“第一,技艺存在;第二,过度与不足的可度量性不仅相对于不同事物而言,而且也意味着标准或适度的实现。如果第二种意义上的尺度存在,那么技艺也存在;反之,如果技艺存在,那么第二种意义上的尺度也存在。否定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就否定了二者。⑨《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而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客人又由适度原则对度量的技艺做了区分,一种是要“以相对的标准去测量事物的数目、长度、宽度、厚度的技艺”;另一种是“与特定场所、时间、运作有关的技艺,各种标准在这些时候已经消除了它们极端的边界而趋向于中度”①《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政治家篇》。
在塔塔尔凯维奇看来,柏拉图的技艺标准和适度问题,其实继承自毕达哥拉斯,因其中突出强调以几何和数学为基础的、运用计算和尺度来制作的技艺(与只为经验或直觉所引导的艺术相对照),意在可靠地履行艺术于真善美的功能。而且,这种艺术不只是为数学计算自身而存在,而是考虑到目的的那种计算,有了这种预期的目标与所追求的利益的计算,才是一种卓有成效的艺术,也就与随意的制作之间形成了完全的区分。也就是说,柏拉图在“适度”这个范畴内,既给新技艺知识的不断生成留下了一定空间,又不偏离技艺之数理的、逻各斯的规则性内核。
除此之外,柏拉图还承认技艺自身是不断进步的。在《大希庇亚篇》的对话中,苏格拉底与希庇亚都承认技艺是进步的,包括艺人的技艺和智者的技艺,都在进步,都会超越古代旧制(281D)②《柏拉图全集》(第4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如此,作为技艺之属类的各门艺术,其中对新规则、新技艺的发现和追求就是合理而正当的。
一方面追求一种永恒真理的普遍性,一方面包容新生专业知识的创造力,柏拉图赋予技艺理论的弹性和张力,使得其基于城邦政治和道德理论的艺术定义颇为含混,前后不一。但可明确的是,通过技艺这一概念,柏拉图为艺术规定了一个崇智传统:技艺性知识不仅与道德伦理、政治哲学等实践性知识相关联,而且与纯粹的理性知识相通,具有向真理逼近的驱动力,在其本质上具有自我完善或自我矫正的潜质与能力。因此,尽管柏拉图本人受制于他的完美国家和幸福人生的政治伦理观,对部分形象突破事物原有逻各斯的艺术革新流露出不满情绪,常以悲观色彩的理论阐述排除艺术的创新内容,但最终在后期的论述中,他通过对技艺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其思想体系的不断扩容,使其关于艺术的理论言说与古希腊艺术的发展走向保持了基本的平行,即认可追求新规范的理想主义艺术在突破旧法则的同时,依然沿着技艺所规定的逻各斯道路,不断完成对其自身特殊的专业知识的精进和理论化。
结 语
综上可知,柏拉图并不始终是艺术的否定者或保守主义者,相反,后期的他简直像艺术新秩序、新方法的“护航者”。柏拉图自身从对艺术的反对态度似乎转变为对艺术原理进行推论,艺术在其思想体系中呈现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退一步讲,如果说从哲学层面看,柏拉图后期关于模仿、标准和适度等问题的论述还不能被全然视为对艺术革新事实的妥协或让步,那么此举至少为艺术模仿论在后世的发展铺就了道路。而从艺术思想史角度看,柏拉图通过这些问题所整合扩容的技艺概念进一步强化了艺术对真理的趋同宿命,驱动了艺术知识体系自身的不断更新和创造,形成了一种严正开阔而富有生机的理论特性,同时也令其自身关于艺术的理论言说与古希腊艺术实践的走向保持了基本的平行,彰显出技艺概念中的理论张力。温克尔曼曾感慨:“希腊雕像上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同时也是鼎盛期,亦即苏格拉底学派的希腊著作的真正特征。”③[德]约翰·亚奥希姆·温克尔曼:《希腊美术模仿论》,潘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2页。这一论断对柏拉图的技艺理论同样恰当。
以上提醒我们,理解柏拉图对其时各类艺术的诸多评价时,不能混淆两类知识体系:一类是依据想象所造出的作品意象;一类是技艺自身所引发的艺术原理阐发。前者的叙事基础是对世界的想象和情节充实;后者的制作基础是科学性知识(如对几何、透视光学等知识的掌握或直觉)。前者的价值被柏拉图赋予高度道德伦理和终极秩序的哲学要求,使得柏拉图在早、中期的艺术论述呈现为一种功能性存在;后者的要义在于,它作为一条中间通道,将科学性的知识与技术性操作勾连起来,以证实技艺的道德伦理及终极秩序的可能性,这些理论更多出现在其后期的对话中。二者构成柏拉图艺术理论的完整面相,不可偏废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