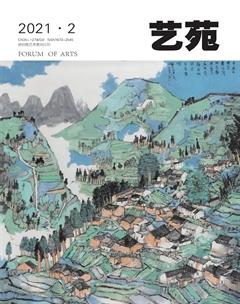以医学影像为媒介的艺术作品研究
林文财 周玉媛
摘 要: 医学成像的发展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审美对象、新的技术、新的展示形式以及新的观念。文章基于医学影像和以医学影像为媒介创作的艺术作品进行整理和分类,运用图像学的分析方法,从成像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医学影像作品中艺术语言的分析、医学影像作品中的艺术观念三个方面对相关艺术作品展开了深入的解读。艺术和医学影像的交叉研究为新媒体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关键词:医学影像;艺术作品;跨学科;创作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医学影像是指运用医学成像技术获得身体内组织的解剖形态、生理信息和病理状态的影像,影像所显示的视觉表像可用于疾病诊断和研究。[1]82医学影像主要包括五大类:医学中光学产生的可视影像,如显微镜和内窥镜等;医学中透射、反射或辐射形成的可视影像,如X射线投影影像、超声扫描影像、热成像影像及核素影像等;医学中由身体数据重建的可视影像和仿真交互影像,如CT、MRI、VE、VR、AR、数字虚拟人等;医学领域中的测量记录的信息图,如脑电图、心电图等;医学动画影片。[2]1-2影像中包含有点、线、面、色调、造型等诸多的审美因素,例如灌注成像将身体的状态显示为线的形象,因此,用医学成像技术来进行艺术创作也受到了艺术家的关注。从医学成像技术在摄影中的运用,再到各类医学影像中形式语言的转化,以及医学影像中的身体意识、文化意识、历史意识、政治意识等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影响着艺术家的艺术实践。
一、医学成像技术在相关艺术作品中的运用
医学成像技术让人类的视觉感知得到了延伸,主客体的审美关系随着透视技术的到来发生了改变。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提到“技术的干预会提出不可见结构这一层次上的测量、实质和构成等问题”[3]189,医学成像技术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深入到原本不可见的视觉领域中进行新的观察和思考。早在20世纪初,抽象派摄影艺术家就将显微镜和X线摄影用于摄影创作,它们的实践不仅在摄影技术上为创作带来了新的可能,同时也为影像注入了新的影像特性,产生了新的审美体验。X线摄影以其透明的特质受到了艺术家的喜爱,例如巴勒斯坦裔的英国艺术家莫娜·哈透姆,英国摄影师Nick Veasey、Hugh Turvey,荷兰艺术家阿里·凡特·里尔特(Arie vant Riet),日本艺术家Saiko Kanda和Mayuka Hayashi,法国艺术家Laurence Pico等都利用医学X线成像技术进行了摄影、影像的艺术创作。医学成像技术是借助某些介质(如X射线、电磁、超声、同位数、温度)与身体相互作用,把身体的内部器官和信息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出来,以供医生诊断使用。除了X线摄影外,还包括内窥镜成像技术、超声成像、热成像、血管造影成像、心电图、脑电图、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随着成像技术的发展,医学成像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和实践路径。例如,莫娜·哈透姆利用内窥镜的漫游检查技术创作了《陌生的身体》,艺术家Laurence Pico利用3D医疗成像技术对奢侈品进行扫描和创作,陈箴创作的装置作品《再生之门》也利用到了CT影像,冯峰利用血管造影成像创作了《内在风景》,胡介鸣利用心电图进行创作等。阿布拉莫维奇 2011创作的作品《相互凝视的魔力》则是通过采集大脑活动的数据进行艺术创作。医学成像技术将我们带入新的影像制造的逻辑之中,它为艺术家提供了新的成像方法、新的认识世界的角度和途径,新的成像媒介使得其工作方法明显区别于录像艺术的创作环境和工作方式。以医学新的成像技术为支撑的影像创作在这里孵化和分离出来。
二、医学影像相关艺术作品中的艺术语言分析
医学影像不仅具有艺术作品的属性,如形态、空间、声音、布局、分辨率、颜色、亮度等形式语言的内容,同时还具有独特的影像语言的特性,如蒙太奇、叙事、记录、时间、透明、序列、可量化、可交互等特征。医学影像背后的文本和意识形态对于艺术语言的实验都有重要价值。
(一)医学影像的透明特征制造了一种多维度、内外展开的多空间关系。医学影像呈现出来的透明特征和内外关系让艺术语言有了内外景象的处理方式,在画面中能够将身体的内部的景象和外表的形象并置在一起,并将艺术家的情感和内在矛盾表现得极为成功。艺术家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Hugh Turvey和Nick Veasey利用X线摄影拍摄着装的身体以及生活中的其他物品。在他们的摄影作品中,物品和身体呈现出影像检查中的透明景象。身体上的着装、佩戴的首饰和随意的身体姿势使得身体摆脱了医院中影像检查室的固定空间。医学影像成了冰冷、理性和死亡的符号,这些冰冷的图像符号不再被束缚于医学知识的解释之中,而是将透明的身体移位到社会生活的空间中,将死亡与鲜活的生命表征联系起来进行探讨。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是事物的外在形象,医学成像的眼睛看到的则是事物的内部景象,医学影像的透视技术将外在的表象全部过滤掉。服饰和外表所代表的华贵和身份都成了一堆白色框架,医学影像成为人们进行自我认识的新的镜像阶段。[4]25-39例如,奥本海姆利用X射线摄影技术拍摄了《我的X光肖像》,她将医学成像技术中透视的视觉经验植入到她的艺术创作,公共空间中穿着大衣和戴着饰品的人物形象变成了透明的框架,物品的身份特征在这里被剥离掉。[5]97大卫·林奇的电影《六个病人》讲述了六个男人生病的全部过程,医学成像下的镜像表现让大众认识到身体内部自成系统的景象,描述了人类的另一种命运。通过上述相关艺术作品的分析,医学成像技术为人类打开了新的观看视角。多层、多角度的成像让人类认识到身体的空间嵌套关系。外表的空间、身体内部的空间、社会公共空间以及精神空间互相嵌套在一起,这样多层、多角度的身体空间描述了身体的多重存在方式。
(二)医学影像中色彩色调、形态、分辨率等属性成了艺术创作中的元素。医学影像和其他影像藝术作品一样具有影像的基本属性,如色彩、分辨率、亮度、饱和度等。马琳·杜马斯在关于疾病的系列创作中主要参考了疾病的相关照片。例如她1985年创作的《白化病》就来自病人病变的照片,身体的疾病特征在失焦、伪影、曝光过度、分辨率不足中变得离奇和不安。影像的属性颠覆了我们对医学插图的视觉体验,影像中的诸多属性成了艺术创作的重要语言。黑白色阶是医学影像的基本色调,例如X线影像、超声影像、CT影像、核磁共振影像都是黑白色阶影像,黑白色阶给人以距离感和陌生感。1986年马琳·杜马斯创作的另一幅《白化病》描绘了一位得了白化病的黑人,黑白在这里一方面呈现的是疾病的颜色、医学的身体;另一方面,黑白又意指黑白种族关系。白色作为疾病的颜色暗示了它在社会中的问题。在这里黑白色阶被巧妙地运用于社会审美批评。吕克·图伊曼斯1992年创作的《诊断视图》系列作品中参照了医疗诊断手册中的诊断照片。作品中的色调比马琳·杜马斯的作品更为冷漠和阴郁。1993年,吕克·图伊曼斯创作的《血迹》描绘的是显微镜下的血液细胞,他并没有去描画显微镜下的奇幻世界,而是在画面中渗透着阴郁的色彩,这是一种医学下的整体色调。危险、隔离、密闭的气息在抽象形态中散发出来,这也许是人对于病患的集体无意识的生动图景。作品中表面的平和透露着离奇和可怕的气氛,疾病事件背后的真实的集体记忆被注入到了画面中。
(三)数字规律一直也是艺术作品中的形式语言,数字规律常以比例、大小、多少、长短的关系在造型和构图中被使用,在这里,数字艺术扩展了数字的审美功能。医学影像中包含着丰富的数据关系,例如CT影像中的黑白色阶都代表着具体的CT值,身体中包含着大量的数据,医学影像学正不遗余力地挖掘其中的信息,并将其进行可视化处理和运用。艺术家丽莎·帕克(Lisa Park)通过脑电波数据来控制48盆水的实时状态,在这里,艺术家对于数据的可视化处理有别于用于疾病诊断的脑电波影像,艺术家将数据以水的状态可视化为人的48种情绪。艺术家熊超的思维艺术项目《Mind Art》是让残疾人通过脑电波控制颜料的爆炸来作画。绘画在艺术策略中改变了绘画中的数字语言,数字不再局限于绘画中的位置安排和比例造型所带来的美感,数字中的节奏、韵律、力量、互动、调节、驱动等审美内容被释放出来。
三、医学影像相关艺术作品中观念的分析
医学影像作为媒介不仅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形式,同时也为艺术家的精神探索开启了新的社会审美路径。医学影像相关艺术作品中凝聚了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意识和批判精神。
(一)医学影像与意识形态的联结。例如在马修·巴尼的电影《悬丝》系列中,虽然形象丰富且复杂,多层叙事相互交叠,多重结构相互嵌套,但在这庞杂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悬丝》系列中医学的参考坐标。从1994年的《悬丝4》至2002年的《悬丝3》,“悬系”影片中贯穿着胚胎孕育的医学叙事,如葡萄与舞蹈演员象征着胚胎的初期形态。玛丽安娜·西姆尼特(Marianna Simnett)同样也是基于医学文本和医学形象进行观念的传达,例如2015年的电影《蓝玫瑰》、2016年的影像《针与喉》。X光外套、超声波以及内窥镜图像等医学影像中的场景成了真实和妄想的场域。医院和手术室是一种隐喻,在控制和安慰的仪式中携带着威胁的力量和人的警觉。此外,冷战时期的骨碟以X光胶片为材质刻录当时西方爵士乐、摇滚乐的唱片,作为意识形态的危险品的骨碟刻录了二战后物质短缺的创伤、后斯大林时代的消费主义的兴起和美国精神荷尔蒙的渗透。意识形态归根于社会存在,医学的发展将社会演进为医学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也受到了医学认知的影响和建构,医学的社会建构了医学的身体。
(二)情感的表达。医学影像一直呈现出冰冷、理性的图像面貌和视觉感受,它那种无情感的状态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死亡的恐惧联系在一起。日本艺术家Saiko Kanda和Mayuka Hayashi共同创作的摄影作品改变了医学影像检查中的姿势。作品中的人物姿态多为拥抱、接吻、蜷缩等形象,这使得冰冷、无情的透明影像呈现出温情、孤独的人类情感。画面中营造的人与人的情感关系消解了医学影像中的恐怖气息,作品流露出作者对于人类生死命运的浪漫情怀。法国艺术家Laurence Pico的影像作品《男人的痕迹》是利用三维医学成像技术扫描奢侈品,作者将医学影像的透明特征和男人的欲望进行了讨论。精致、高贵、华丽、通透、冰冷的奢侈品表征描述了男人欲望的痕迹,作品散发出来的气息正是这种男性欲望的润滑剂和赤裸裸的表象。
(三)女权主义。艺术家莫娜·哈透姆也利用了医学影像中的透明特征来进行创作。1980年,莫娜·哈透姆利用X线透视影像创作了互动影像作品《live show“ Dont smile,You are on camera now”》。在这个作品中,作者身体内部x光影像与现场观众身体外形的影像进行重叠。正如观众的身体成了作者身体的外在表征,而作者的内部的解剖形态则进入了观众的身体内部,作者拥有了观众的外表,观众同时也拥有了作者的内在。作者的身体和观众的身体在这种互动中被移位,性别和身份的思考在这种替换和内外关系的交叠中被引入深处,新的身份幻想在透明的幻想中滋生出来。1994年,莫娜·哈透姆采用内窥镜检查技术显示身体内部的信息,通过女性的生物学特征来认知女性的身份,而不是被描述为男性的参照体。
(四)工业生产与商品内在精神的空虚。医学影像构筑了机器身体的符号美学,这种特殊的身体景观影响着艺术家的艺术思考。例如英国艺术家Nick Veasey利用X线摄影的方式拍摄明星、着装的人物、昆虫、植物、衣物、推土机、飞机等物品。这是一种医学影像的身体符号对外表符号的碾压。服装、肤色、首饰在X线穿过之时,权利、名望、欲望、审美追求、身份都消失了,一切事物成了一种死亡的景观。繁华的景观被无情地碾压而过,X线的透视景观为大众的身体审美堆叠了另一种权威、另一種命运和身份。摄影师Nick Veasey的摄影作品利用医学成像技术中透明的特征将日常物品的外在形象和内部空间一并展示出来,通过他的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工业产品的冰冷和商品内在空无一物的空虚内核。在Nick Veasey的作品中,阶级、肤色、人种、身份在透明影像中被抹去,对外表的覆盖所获得的权利也被一并抹去,消费社会中物质的繁盛和人的物欲追求被赤裸裸地剥掉,只剩下了冰冷、空寂的死亡景象。艺术家Hugh Turvey同样利用了医学影像的透明特征进行创作,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透明的影像与现代主义的理性美学结合起来,影像以点线面的形式构成来组织画面,形成一种比医学影像更为冷酷的视觉感受。点线面的精致提取和安排导向一种脱离物质实体的精致和虚假。
(五)解读和建构存在。医学影像中记录着丰富的身体数据,艺术家通过采集和提取身体的内部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创作,并借此理解意识、记忆、思考等内容或者存在的形式。例如艺术家Lisa Park的作品《精神正常》系列采用身体数据进行艺术创作,通过作品解读了大脑是如何记忆的、大脑是如何加工形象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等问题。艺术家Refik Anadol将大脑工作的数据提取出来,并将这些数据转译为数字绘画、数字雕塑。大脑的工作状态在数据和可视化的结盟中显示出其难以言状的转动、生长过程。艺术家胡介鸣则利用心电图探讨人的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的关系。1998年他创作的《与快乐有关》作品中利用心电图测量生理状态的心率指数,依据这些数据的波形进行谱曲。[6]52乔纳森·济慈(Jonathon Keats)利用脑电仪(EEG)来记录人的脑电波,并通过配套的软件挑选出特定的波形,再将这些脑信号用于控制机器的操作。脑与躯干的想象在这里被延伸到了机器运动。2013年Yukiyasu Kamitani创作的电影短片《人脑解梦》是根据电脑对梦中大脑活动的解码而制作的,电影的一系列图像和文字与受测试者的语言描述密切匹配。比尔·维奥拉于1988年创作的《理性的睡眠》让我们看到透明的身体使得个体的精神世界变得可见和可监控。在艺术家Gary Hill的作品中,基因代码的抽象符号和医学影像的虚拟特质共同构筑了现代身体的认知,医学影像代替了人体的物质实体,成了医生诊断和身体研究的重要媒介。生物学的抽象符号在身体的描述中占据了霸权的位置,一种生物学政治正在被建构,身体的形态影像渐隐于数字抽象模型之中。数字符号力图模拟世界的真实,艺术同样也热衷于去把握世界的真实。
(六)社會疾病。医学影像作为一种镜态的功能投射出社会的状况。社会疾病和身体疾病在这里建构出了一种镜像关系。例如1992陈箴的作品《再生之门》通过容纳废品的通风管道和病人的CT影像建立起关系,通风管是环境污染和呼吸疾病的交通枢纽,大众在生产和消费的颂歌中自食循环的恶果。在这种镜像的循环中,身体与环境的危险关系不断地被确诊。2000年陈箴的作品《水晶体内风景》[7]66-67是在体检床上展示了11个由水晶玻璃制成的内脏气管。晶莹剔透的内脏气管将外部环境直接反射到了器官的内部,在这里镜子的边框消失了,身体与环境直接叠化在一起,身体成为一种风景,风景同时也成为一种身体。作品的镜态幻境叠化了社会与人体的互通作用及生命本身的脆弱。温德尔·沃伊的作品《教堂》从远处观看是静穆、圣洁的光景,近看却是以X光图像为意象。远近的视觉感知将虚伪和真实联系起来,镜像的想象和象征的欺骗在这里起到了作用,以生理的身体形象来攻击基督教的虚假面目。
医学影像携带着人在医疗体验中的视觉感知,有着丰富的感性特征,它呈现出焦虑、恐惧、冰冷、陌生的视觉印象。同时医学影像凝结了医学、生物学、信息学、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内容,形成独特的视觉符号系统。实验艺术创作让医学影像从线性的理性观念中逃逸出来,艺术家能够在医学影像的感性层面和视觉符号的语言系统中进行审美元素的重构和审美批评。
结 论
医学成像技术的发展为新媒体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医学成像技术有着不同于传统艺术的创作手段,除了技术外,医学影像类型中包含有诸多的美学因素,影像中的美学因素使得影像成为新的审美材料,同时也具有社会的审美评判。医学影像中潜隐着改变生存命运的潜能,艺术作为医学影像符号中新一轮的解释物对医学影像进行了新一轮的重构。医学影像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艺术和医学影像的交叉研究使得医学影像重新生成,艺术也重新生成。
参考文献:
[1]祁吉.医学影像学词典[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高上凯.医学成像系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3]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邱志杰.摄影之后的摄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张海涛.未来艺术档案[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7]陈箴.陈箴Chen Zhen[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林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