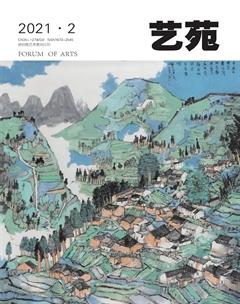丁西林与王尔德喜剧比较论
侯梦汐
摘 要: 丁西林和王尔德各自开辟了中西饶有风情的喜剧乐园,在一片智趣横生和哲理思辨的氤氲下,两人剧作暗合的深层原因在于世态喜剧的“机智”特征,同时这种“机智”又暗藏相异之趣,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貌。如果说王尔德以游戏人间的姿态来张扬早已蠢蠢欲动的玩世不恭与肆意洒脱,尽显风流才子的放荡不羁之美,那么相较而言丁西林的智性书写则在捕捉人心微妙的变化层次上秉持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高度敏感与细腻,蕴蓄着理性温和之美,是区别于王尔德的一种“机智”变奏。在幽默的循环往复和微妙的试探体察中,两位剧作家均完成了本民族喜剧世界的自足,亦在机缘巧合的促成下实现了喜剧盛宴上相映成趣的流动对话。。
关键词:丁西林;王尔德;喜剧;机智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袁牧之曾论及丁西林的作品:“作者的俏皮语句和两性关系的哲学,很有点像王尔德的唯美派,同样地作者戏中的布景,都圈在漂亮的客厅里,作者戏剧中的人物都咬着烟斗埋在舒适的沙发内。”[1]142这段话涉及了丁西林与王尔德的喜剧在题材选取、语言技巧、人物设定等方面的相似性。纵观中西喜剧的发展,丁西林和王尔德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两颗璀璨明珠。中国现代喜剧是在欧洲喜剧的滋润下萌芽成长的,深受英国世态喜剧影响的丁西林回国后登上剧坛,代表了喜剧的自觉;王尔德作为欧洲世态喜剧的最后一位大家,为欧洲的传统世态喜剧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作品经翻译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备受国内知识分子的推崇。尽管丁西林從未表示自己接受过王尔德的直接影响或对其作品情有独钟,但若基于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寻求内在的关联和可比性,会发掘丁西林的创作能与王尔德机智喜剧暗合的深层原因,在于以他者书写的视角洞察世态风俗,以睿智的对话谈锋感知语言魅力,以幽默的两性关系抒发真善美的理想。而同时“机智”又暗藏相异之趣,形成独特的变奏,呈现了不同的审美风貌,在幽默的循环往复和微妙的试探体察中,两位剧作家均完成了本民族喜剧世界的自足,亦在机缘巧合的促成下实现了喜剧盛宴上相映成趣的流动对话。
一、“机智”的相似之缘
丁西林作为开创中国现代戏剧的功臣之一,是唯一一位专门进行喜剧创作的作家,剧中传神的欧化风味与以王尔德为代表的英国世态喜剧存在精神联系。世态者,世俗之常态也。世态喜剧的主要特征在于“机智”,对一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风俗和人情世态加以关注。以下拟从他者的客观视角、睿智的对话谈锋和幽默的两性关系三方面对丁西林与王尔德剧中的异曲同工之妙进行类比和解读。
(一)他者的客观视角
投身于戏剧创作的过程中,丁西林和王尔德不约而同地淡化了重大历史事件,对社会议题持有客观和中立的立场,采用他者的视角叙述较之于暴露剧烈的主观感情要显得更为冷静,形成开放的文本,为读者留出独立思考与评判的自由空间。追根溯源考察两位剧作家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意趣,可细究其中的缘由。
丁西林青年时期在英国留学,主要研究数学和物理学,期间还另外涉猎了诸多英文原著小说和戏剧作品,喜欢欣赏剧院的排练演出,大量积累的阅读经验与剧场体验为日后的戏剧创作实践培植了丰沃的土壤,增添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学成回国后,丁西林被聘为北大物理系教授,日常生活虽以严谨求真的科研实验为主,但他的情调和气质都倾向于喜剧,写戏成为业余爱好,且多是在与朋友打赌的乐趣中即兴所作,以此陶冶情操,自娱自乐,既不用来维持生计,也无需刻意迎合复杂的社会局面和观众的接受视野。与此同时,丁西林作为“现代评论派”的一员,受到欧洲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反对文学具有功利的目的,并不认同“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思想,体现出智者的超脱眼光和对艺术的一种独立、自由的追求。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褪去功利外表的喜剧心性和智性书写使得丁西林的戏剧天分在当时的文坛脱颖而出,孕育着诸多突发的奇思妙想,凝聚为泛着理性光彩的智慧结晶,创作中的束缚和顾虑也随之减少,以轻松的喜剧形式、对光明生活的信心和独立乐观的精神,平中见奇而富有寓意的主题在笔下自然地流泻出来。
《压迫》作为上演次数最多的一部戏,被研究界广泛认为是丁西林最脍炙人口的佳作,纯熟的戏剧技巧与题材的现实性交相融合,取得完美的戏剧效果。租房只提供给有家眷的人这一奇怪荒唐的现象在许多大都市屡见不鲜,类似的题材在陈白尘的喜剧《结婚进行曲》也有深刻展现。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中,漂泊四方的单身群体无不为租房被拒的难堪遭遇而焦头烂额,现实事件透过喜剧性情节不断发酵,作者“自我”的观点和评判未曾着墨,剧作因此具有更强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喜剧情境的留白不只隐含了单纯的一笑而过,更多是引发读者对于当时社会传统的沉思怀疑,对于被压迫者与被欺侮者的同情怜悯,对于剥削压迫者的奋起反抗。
丁西林创作思维中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戏剧观,使得他的作品颇为蕴藉,几分哲学意味的审思与明辨表达得含而不露,但又未脱离现实,而是像一位站在身旁的老友般洞彻人情世故,从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素材进行提炼加工,剧作立意于平凡的市井深处静候发掘,在隐身世外的保护伞下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巧施笔墨,幽默言说。这种独树一帜的实验性和先锋性与王尔德的艺术观念不谋而合,因为王尔德曾在此前表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东西,它和思想一样,有独立的生命,而且纯粹按自己的路线发展。”[2]王尔德所处的19世纪中期正值资本主义矛盾尖锐,维多利亚贵族淫乱奢靡之际,势单力薄的个体难以直接与强大的上层统治阶级相抗衡。王尔德的戏剧创作按照以往写童话的原则,以唯美主义运动所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来回应在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大行其道的“为金钱而艺术”,以客观和疏离的视角记录英国贵族阶级的自私和伪善,选取婚姻、抛弃、私奔和社交圈等话题建构社会剧的线索脉络,写来得心应手,能够灵活自如地反映客观内容,营造出一派置身事外看戏的观感,而心底的愤慨和反叛的思想隐藏于朦胧的面纱背后,“在越轨和循矩之中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3]128-132。
(二)睿智的对话谈锋
剧本的基础是语言,人物之间的对话于无形中促使戏剧情境迎来转机,最能够彰显剧作深厚的语言功底。17世纪的西班牙戏剧家维迦曾说:“双关语和暧昧的措辞在观众里很受欢迎,因为每个看客总以为话里的含意只有自己一个人懂。”[4]186丁西林在喜剧创作中充分重视对话艺术,人物正面交锋,出口成章,鞭辟入里,对话经过独具匠心的安排,往往暗藏玄机,意趣横生,值得推敲寻味。
在四幕喜剧《妙峰山》中,王老虎和华华妙语连珠的对话令读者应接不暇,极尽机智和风趣之能事。剧情发展到第二幕,华华问王老虎是否有太太,王老虎回答说自己有一个昨天刚结婚而明天就要离婚的太太,就在读者和华华一样对此不解而惊诧时,王老虎脑筋急转弯式形象的描述让人忍俊不禁,原来自己的太太正是脚上带的铁镣——“一天到晚不肯让她的丈夫离开一步”[5]220。这句夹带着笑声的俏皮话一语双关,意味深长,既表明了王老虎认为结婚像被扣上铁镣一样束缚于身,又暗含了早日走出黑暗现实的强烈渴望。
俏皮话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妙言慧语,经王尔德从生活中收集后“随便”地应用于剧中各类人物不凡的谈吐,解构原本严肃的婚姻家庭问题,制造层出不穷的笑料,使剧本生色不少。在嬉笑怒骂之余,代言人常常能够一语中的,从反面道出世间真理,折射王尔德对19世纪上流贵族虚伪心态的调侃和价值观扭曲的讽刺。《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的邓比言之有据,“经验是人们为自己的过错取的代名词”[6]59委婉地貶斥了那些自称情场经验丰富的老手,颇具艺术感染力。剧中温德米尔夫人是所谓的好女人,但轻信谗言,失去理智思考,误认为丈夫阿瑟与欧林纳太太有染。而欧林纳太太起初因一段不光彩的过往被认为是 “堕落”的坏女人,后来在紧急关头冒认扇子:“恐怕今晚我离开府上的时候,错拿了您夫人的扇子,真抱歉极了。”[6]62周旋于复杂的人际关系间,欧林纳太太依然能逻辑自洽,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凭借一番机智巧妙的应答实现突围,峰回路转,保护了女儿的人格,挽救了女儿的婚姻,避免重蹈自己的覆辙。
以机智的谈锋化解矛盾,推动情节步步深入,环环相扣,在思维逻辑的转弯处狭路相逢,短兵相接,智者出奇制胜,既洋溢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声东击西之旨趣,又回荡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音绕梁之神韵。在明快有力的对话中喜剧人物持有的观点令读者耳目一新,思辨借助文本介入现实,不断引发耐人寻味的思索,凸显了两位剧作家驾驭语言的高妙手腕与精湛才华。
(三)幽默的两性关系
喜剧如一面镜子,反射出新生的明媚光线以驱散愚昧的尘埃阴霾,是人格品性的自呈,是言行身份和自我意识的审视。丁西林和王尔德的世态喜剧以男女平等和婚恋自由为精神基调,倡导和谐平等的两性关系。对于男女之间存在的固有成见和矛盾,运用机智和幽默的方式迎刃而解,对爱与平等的理想追求贯穿始终。
《妙峰山》中的男女主人公王老虎和华华在抗战时期的妙峰山上相遇,走在时代前沿,引领精神风貌,实现抗日救国的抱负,比丁西林以往独幕剧中塑造的人物更为典型。两人的恋爱观和相处模式,笼罩在一派英伦雾霭中。被官方视为“土匪”首领的王老虎曾在英国留学,还当过大学教授,他公平对待俘虏,具有高雅的绅士风度,主张自由平等,积极响应人民群众的呼声,为抗战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同时他又坚持独身主义,对女性心存偏见。而华华开朗直率、有才干有主见,不卑不亢,大胆地追求自己的所爱,在双方机智诙谐的恋爱攻守战中,王老虎最终为爱缴械投降。这种“女追男”的两性关系设定类似于王尔德《认真的重要》这出爱情喜剧,两位女主角格温德丽和西西丽犹如盛开在异域的“双生花”,她们敢作敢为,善解人意,极有主见,同时爱上了一个名为“Ernest”的男子并紧追不舍,而“Ernest”(与“Earnest”读音相同)其实是被冒充的假名字。当荒诞的把戏被揭穿,顶着假名的两位男子决心为爱受洗,历经有趣的周折,改名后赢回了恋人心,两对情人各遂所愿,皆大欢喜。
此外,太太形象也活跃在喜剧场上,成为世俗社会的缩影。《理想丈夫》里的奇尔顿夫人将对丈夫的爱当作终极的崇拜,不能接受丈夫的任何缺点。《酒后》里的妻子在丈夫主动要求离开时却败下阵来,没有勇气亲吻沙发上熟睡的友人。伯维克公爵夫人在《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中顶着一副伪善的面具挑拨离间,与勇敢的欧林纳太太给读者留下同情敬佩的印象截然不同。《压迫》中的房东太太执意不肯将房子租给单身的男房客,是固执又充满偏见的有产者不断对无产者进行施压的生动写照。《认真的重要》中的布雷克耐尔夫人以明显的贵族偏见作为筛选标准,将死板僵化的婚姻家庭等级理论表述的活色生香。《三块钱国币》中的泼妇吴太太尖酸刻薄,恃势凌人,因女佣打碎了一个花瓶而斤斤计较,资产阶级吃人的本质登时跃然纸上,读来令人忿忿不平。《妙峰山》中的谷师芝泼辣自私,俗不可耐,毫不关心抗战大局,而丈夫郭士宏性格懦弱无能,做事畏畏缩缩,他们之间爆发的争吵不外乎一门心思要抵押对方留在此地,暗自打着自己先下山回家享福的如意算盘,资产阶级夫妇昏庸可笑的关系在剧情的推进中逐渐显形。
某种程度而言,上述所列丰富多元的女性形象具有共性,当理想女性和传统女性的姿态被明镜照见时,不难发现古今中外包含相通之处。无论是王尔德所处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还是丁西林面对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循规蹈矩的传统婚姻价值观仍是社会的主流婚姻观,大部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仍处于从属的位置。而男性身为既得利益者,在习惯性的舒适区里陷入刚愎又不愿反思,需要对自己的潜意识进行剖析和自照。两位剧作家赞赏敢于冲破牢笼、独立自主的理想女性,对于因循守旧、迂腐保守的传统女性则以含蓄的方式揶揄,对于男性寄予了真心改悔的愿望,一条通向真善美与理想乌托邦的蜿蜒小径连接着中西文坛,纵然路途曲折,但人道主义思想随时代演变不断扩充其内涵,两性之间真诚友善关系的确立成功地得到深度扩写。
二、“机智”的相异之趣
艺术家身为创作主体,不同的个性修养和文化品行直接影响了作品风格的走向。丁西林与王尔德两者喜剧的“机智”表现出一系列相似之处的同时,也暗藏相异之趣,呈现了不同的审美风貌。王尔德短暂的一生如戏剧般跌宕起伏,早年大步流星地走上求学写作和娶妻生子的道路,在文学创作正处于如日中天的关键时期,竟因同性恋的罪名锒铛入狱,这种“不敢说出名字的爱”被误解之深,致使王尔德的情思和意志浸润其中又饱受摧残,生命以流亡法国病逝而落下帷幕。他的玩世不恭和狷狂邪魅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留下华丽的身影,尽显风流才子的放蕩不羁之美。在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如果说王尔德以游戏人间的姿态来张扬早已蠢蠢欲动的玩世不恭与肆意洒脱,那么相较而言丁西林则在捕捉人心微妙的变化层次上秉持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高度敏感与细腻,蕴蓄着理性温和之美,形成本民族喜剧世界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因而丁西林的智性书写不妨看作是区别于王尔德的一种“机智”变奏。
无论是写戏的审美风格,还是排演中对于演技的要求,丁西林一贯追求的是自然、平易和亲切,一切如常,不以情节激烈的大起大落来博人眼球,就像物理现象是遵循一定的规律而变化。驻足于寻常巷陌,留意司空见惯的琐碎剪影,在最平淡的小事里以轻盈的笔调和精巧的构思反映出生活的本真。丁西林的六部独幕剧均撷取朴素微渺的一隅,洞观人情世态和社会风气,更重要的是对于英国世态喜剧并非机械式模仿,而是以个人从容淡泊的风度进行本土化重塑,整体氛围如清粥小菜般爽口怡人,又如品一杯古茗,回味在唇齿之间是自在的幽香。丁西林不会为了写戏而刻意做戏,他的喜剧让人心领神会般豁然开朗而不夸张做作,散发着诗意与理趣的光芒,堪称中国现代喜剧的典范,这不仅是清淡之笔体现在技术上的炉火纯青,更是静水流深般的生活态度与世事观照。
对于人物微妙心理的细微体察和细腻刻画,让丁西林作为知识分子所独具的敏锐与严谨得以展现。正如卡西尔所指出:“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7]15《北京的空气》不曾渲染帝都雄伟的气势,转而聚焦于弥漫在京城空气中看不见摸不着的奇异分子,交织为一层覆盖着体面和尊卑的透明膜,人们圆滑世故的内心深处暗流涌动,主仆之间以窃取之道还治窃取之身,围绕着烟一来一回、一“偷”一“借”的趣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戏剧是注重“行动”的艺术,丁西林善于运用戏剧动作外化人物心理,通过安排具有个性特征的戏剧行动,真实贴切地描摹出人物内心波动的层次。《一只马蜂》的背景发生在五四新旧交替时代,吉先生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身处其中,思想难免会比较复杂,一方面迫切希望挣脱封建家庭的管束,另一方面旧有思想又仍徘徊在脑海,因此在追爱之路上彷徨不定,只能采取迂回之术。当向母亲打听余小姐对相亲一事的回应时,吉先生心中既在意余小姐,不想受到母亲对自己感情的摆布,又不能在母亲面前表现出自己对余小姐的关心。穷则变,变则通,针对两难的情形,丁西林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向来不吃糖的吉先生在对话中吃糖的动作,其他元素全部建立在这个动作上,前后产生紧凑的呼应。当吉先生内心对母亲的回答不满或疑惑时,正要送往嘴里的糖便被迅速拿回,而当听到自己满意的答案时才将糖送入口中,该喜剧性场面的细致描绘独出机杼,韵味无穷。
作为科学家,丁西林注重思辨,从理性主义的命题出发,兼具了人文思考和理性诉说,读者通过理性思考由衷地发出会心一笑,精神世界由此得到抚慰。丁西林和王尔德的剧作情节设置中不乏“欺骗”的模式,王尔德所写维多利亚社会的婚姻充满利益纠葛,男女相爱不过是逢场作戏,靠虚假与欺骗维系表面的和谐稳定。而丁西林建构的“二元三人”模式中,两个人物出于各种原因有着同样的目的,需要“强强联手”的默契配合,“心照不宣”地共同欺骗第三个人方能以机智取胜收场,如《一只马蜂》中的吉先生和余小姐因彼此心仪,又不想被父母约束,所以联手欺骗了吉老太太;《瞎了一只眼》中原本毫无大碍的先生故意装作摔伤后瞎眼的模样,和太太合伙欺骗赶来探病的朋友;《压迫》中男房客和萍水相逢的女房客没有不欢而散,而是共谋假扮成夫妻欺骗巡警和房东太太。但仔细品味,会发现这种“欺骗”情有可原,是身陷困境灵机一动时编织出的善意谎言,欺骗他人的同时真情流露,认清了自己内心的真正需求,即便是偶发的“惊人之笔”亦于人无损,合乎情理,顾及他人的体面,也给自己留有余地,没有触碰到道德的底线。就像《一只马蜂》里精心打造的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与封建家长制之间的喜剧纠葛,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谁是谁非之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合理之处。剧末吉先生坦承自己说谎的理由,所隐喻的正是不自然的社会里羁绊在两性关系、长幼尊卑,以及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障碍,不愧是点睛之笔。丁西林将这种“人为障碍”勾勒得妙趣横生、引人开颜,有效地将各种矛盾冲突通过“欺骗”达到相互调和的状态,最后形成相对平衡,从而在总体上呈现出温和隽永的喜剧风格。
结 语
综上,丁西林与王尔德以各自的扎实底蕴和卓绝才智开辟了饶有风情的喜剧乐园,为本国戏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站在平行比较的视角研究丁西林与王尔德的喜剧,在一片智趣横生和哲理思辨的氤氲下分析“机智”本色的异同,在创作视角、对话谈锋和两性关系的探析中窥视作为有志之士的剧作家对于社会弊病陋习的幽默还原和含蓄讽刺,在放荡不羁和理性温和的美学碰撞中不断自我凝视和回望反思,衍生出对于中外戏剧更多元立体的理解,为中西戏剧精髓的继承和再创造开拓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
[1]袁牧之.中国剧作家及其作品.丁西林研究资料[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
[2]王尔德.王尔德全集(4,评论随笔卷)[M].杨东霞,杨烈,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
[3]冯涛.王尔德与丁西林:机智喜剧之比较[J].江苏社会科学,1997(6).
[4]余秋雨.观众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5]丁西林.丁西林剧作全集(上册)[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6]王尔德.王尔德戏剧选[M].钱之德,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7]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万书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