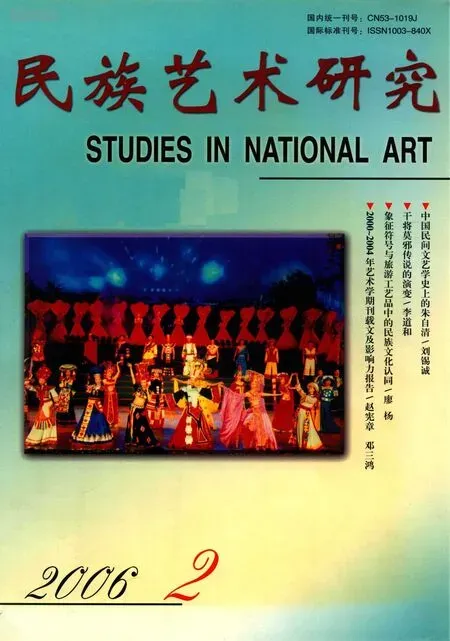多元化进程中探索学科前沿
——学术谱系视域下的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实践回顾
楚高娃
田联韬先生(后文简称田先生)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科奠基人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创性地创建该学科以来,经几代人的辛勤耕耘,田先生的思想观念对该学科的研究队伍构成、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田先生与北方诸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的深厚之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织和参与策划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2001年)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1998年、2007年)两部宏大巨作,对于深入、全面地认识包括蒙古族、满族、朝鲜族、鄂温克族等民族在内的55个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并对之展开微观至宏观的整体研究指明了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其二,在人才培养方面,先生亲自指导培养的二十余名博士中有多位北方少数民族族属的学者。又经第一代学者们的努力,近六十余名第二代博士中,研究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学者人数增至最多,队伍最为庞大。经三代人的努力,已逐步成为较有特色的学术团体,在强调选题的原创性、新颖性的同时借鉴和融合多学科理论,出现了诸多居于学科前沿、创新性强,甚至填补空白的科研成果。
本文以“学术谱系”为视角,梳理和回顾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央民族大学的近二十位博士和博士后所做的蒙古族、满族、朝鲜族、鄂温克族等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课题论文,意图从学科队伍、研究对象、研究理念等方面看三代人的少数民族音乐学学统的代际传承,使学界对当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状况有所了解,以利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及高层次人才培养之未来发展。
一、研究队伍的多元化:“他者”与“我者”共述多彩音乐文化
培养和建设优秀的学者群体和良好的学术梯队是社会科学事业不断发展的基础。相较于汉族传统音乐研究的情况而言,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更多了一层难度和挑战。尤其对于无文字传统的少数民族,语言即是历史,音乐即是文化。如果想要推进学科发展和深化研究领域,需着重培养在掌握语言文字和民族文化方面占有优势的少数民族族属的理论人才。田先生是较早认识到这个关键要素的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以来,培养了二十余位以少数民族族属为主的音乐学博士,其中有的是本民族的国内第一位音乐学博士,如纳西族的和云峰博士、白族的杨民康博士(田先生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蒙古族的包爱军教授、藏族的嘉雍群培以及蒙古族第一位女音乐学博士崔玲玲和满族音乐学博士李亚芳等。这些突起的“异军”打破了以往多由汉族学者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的队伍构成,他(她)们偏于“局内”的视角和所拥有的包括语言文字和生长历程在内的种种优势条件,铸成了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无可替代性,尤其有益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其中,几位较早获得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学者们,承继田先生的教学和培养理念,又招收了多位北方少数民族族属或以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音乐学博士,如杨民康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红梅(蒙古族)、李红梅、宁颖(蒙古族)、苗金海、张林,并担任哈斯巴特尔(蒙古族)、关冰阳的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包爱军教授指导的博士齐占柱(蒙古族)、包明德(蒙古族)、楚高娃(蒙古族)、娜仁娜(蒙古族)、楚悦(蒙古族)、兴安(蒙古族)、赵娜(蒙古族)、石秋月;嘉雍群培教授指导的博士王晓东等。其中多数博士或博士后以“局内”视角研究本民族音乐文化,其学位论文和学术成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
回顾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科发展史,田先生的培养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研究人才队伍的构成。随着少数民族族属“我者”的参与,不仅扩大和打破了以往以“他者”为主的较为单一的研究队伍格局,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事业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经第二代学者们的努力耕耘,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高级音乐理论人才已成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第三代生力军,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方法理念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倍受学界关注。
二、议题的多元化及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
直到20世纪末,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田先生清晰地看到: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人才培养,少数民族宫廷音乐、宗教音乐研究和“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入考察和比较研究工作极端薄弱的情况,有待于尽快解决。①田联韬:《回顾与展望——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考察研究工作50年》,《音乐研究》2000年第4期。因此,在他本人亲自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和第二代博士研究生的课题项目中,采取了有针对性地去逐步攻破上述领域的策略,致使相关研究范围不断得到了拓展和深化。
目前,田门一脉以北方少数民族音乐为研究课题,已获得博士学位和博士后资格的学者共有18位,其中研究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占多数,此外还有研究朝鲜族、满族、鄂温克族等民族音乐者;不仅有对北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深入和拓展性研究,也有运用历史民族音乐学方法开始涉猎近当代音乐研究的探索性课题。尤其宗教与祭祀音乐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已成为特色学科。
(一)宗教与祭祀音乐研究逐渐成为特色学科领域
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队伍中,蒙古族音乐的研究队伍是最为庞大且研究成果数量最多的一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相较于蒙古族宗教音乐,其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有不少专题论述成果及著述问世。但因历史和政治原因,学者们较少去碰触宗教音乐①蒙古宗教音乐可分为人文宗教音乐和原始宗教音乐。人文宗教音乐包括佛教音乐、基督教音乐和伊斯兰教音乐等;原始宗教音乐包括以万物有灵为主要观念的各种原始祭祀仪式音乐及萨满教或博教音乐,以及融合佛教和萨满教二者特质的莱青音乐文化等。,尤其专题探讨佛教音乐的成果甚为少见。
20世纪末,就读于厦门大学音乐学院的包爱军(包·达尔汗)已开始关注到了这一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并以《蒙古博教及其音乐文化的衰落、异变与幸存》为题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在博士阶段延续宗教音乐的研究,将视角聚焦于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特质,经田联韬先生“加持”,以《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②包·达尔汗:《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同名出版的著作已成为学习和了解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必读书目,对该领域的拓展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开始招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包爱军和嘉雍群培教授最先获得导师资格。两位教授承继田先生的教育理念,以培养少数民族音乐高级理论人才为教学目标,迄今为止共培养了20余位博士研究生。两位导师在关注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同时,将宗教与祭祀音乐研究作为特色学科,培养了王晓东、楚高娃、娜仁娜、王芳、兴安、马良等研究佛教与祭祀音乐的博士研究生。其中,既有对具体乐种的专题探讨,也有佛教寺院个案研究。如楚高娃的《蒙古佛教本尊与护法神诵经音乐之密律——以雅曼德迦和摩诃噶喇神祇为例》③楚高娃:《蒙古佛教本尊与护法神诵经音乐之密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文以蒙古地区较有代表性的雅曼德迦和摩诃噶喇两位神祇诵经音乐为研究对象,围绕法会仪轨中音乐本体、经书文本、经文佛理三层结构,从外显的音乐切入,紧扣佛教教义的原理论和传播变异表象,阐述其佛教音乐的“形”与“义”的交互意义。兴安博士将目光投向历史上具有极高政治地位的皇家寺庙——承德普宁寺,通过梳理该寺院历史文本和佛事仪式的记述,全面解释了历史进程中的《承德普宁寺佛教音乐的融合与重构》④兴安:《承德普宁寺佛教音乐的融合与重构》,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特征。上述两位博士的选题是佛教寺院最为普遍的音乐文化现象,而另外两位博士娜仁娜和王晓东则选择了蒙古佛教较为特殊的信仰文化——关公和莱青祭祀音乐。前者的《蒙古佛教关公祭祀仪轨音乐研究》⑤娜仁娜:《蒙古佛教关公祭祀仪轨音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主要对源于汉族地区的关公信仰在蒙古地区佛教寺院中的流变现象做了深入探析,通过对北京、内蒙古、青海、辽宁等地区佛教寺院关公祭祀音乐文化进行多点音乐民族志考察,揭示了该信仰文化在蒙古地区的地方化和本土化特征。王晓东的《科尔沁蒙古族莱青音乐研究》⑥王晓东:《科尔沁蒙古族莱青音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课题对象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之下,蒙古族原宗教博与藏传佛教在长期反复的激烈冲突中被迫妥协,渐趋形成的一种“变容”形态——莱青。作者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文案梳理的基础上对这个特殊的音乐文化现象予以全面而深入的解读。
从上,我们看到诸位博士课题是对包爱军教授学位论文中所提到的蒙古佛教音乐文化诸多质点——藏传佛教音乐因子、蒙古化的音乐因子、汉族音乐文化因子及蒙藏音乐文化融合而产生的文化因子为考察对象的个案研究。从中,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学科的承继脉络和该领域逐步在深化拓展的特点。
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前主要信仰萨满教。随着佛教在13世纪和16世纪两次大规模的传入,对原有的宗教祭祀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蒙古民间祭祀文化的变异更为多样,形态更为丰富,类型更为复杂,其中敖包祭祀就是较有代表性的文化形态之一。红梅博士是较早从音乐学角度研究该祭祀文化的学者。其博士论文《当代蒙古族敖包祭祀音乐研究——以呼伦贝尔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①红梅:《当代蒙古族敖包祭祀音乐研究——以呼伦贝尔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选择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音乐,以丰富的田野考察材料为依据,从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研究视角,对敖包祭祀仪式中所体现的藏传佛教本土化现象、蒙古博教信仰的遗留信息以及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杨民康先生曾述:“继这一较早开展蒙古族传统敖包祭祀仪式音乐研究的博士论文之后,至今又有多位来自内蒙古的蒙、汉学子已在我校完成或正在进行自己同类或类似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比起他们来说,红梅可以说先行了一步,并且在相关研究方向上扮演了一个蹚路人的摸索者的角色。”②红梅:《当代蒙古族敖包祭祀音乐研究——以呼伦贝尔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杨先生上述的“至今又有多位来自内蒙古的蒙、汉学子”中包括苗金海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同样以敖包祭祀音乐为研究对象,但探讨的是《敖包祭祀场域下鄂温克族音乐文化的建构与认同》③苗金海:《敖包祭祀场域下鄂温克族音乐文化的建构与认同》,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问题。文章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为重点调查区域,通过对宗教性的萨满敖包、藏传佛教寺院敖包和世俗性的家族敖包、政区敖包祭祀这四种不同类型的敖包祭祀仪式做民族志调查,指出:敖包祭祀活动的目的是出于相应的内群体对外区分、对内认同的需要。联结不同群体的敖包,凝聚着人们对亲人、对民族、对家乡、对宗教自然而朴素的情感,仪式过程中仪式音乐等象征性符号的建构与表征,将这种情感进一步激发和升华,成为铸造信仰和观念的有力武器。敖包祭祀仪式的结果是增加情感能量,增强归属感,增进了群体内部的身份认同。张林博士的《建构的传统——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④张林:《建构的传统——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立足于微观个案研究,并通过多点民族志、线索民族志的方法,对新宾满族民间丧葬仪式、萨满仪式、正月扭秧歌放路灯“撵鬼”习俗、传统婚礼习俗、清皇故里祭祖大典以及清永陵祭祀大典等民俗仪式做“穷尽”式的志述,借鉴仪式学、符号学、结构学等方法由微观、中观到宏观,由局部到整体的多层次把握,深入解读了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所建构的音乐文化所展现出的“认同差序”及“英雄圣祖历史心性”文化特征,并对文化建构现象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述和思考。上述两位博士对研究对象的观照较为全面,同时对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思考也较为深入,将在方法论部分做进一步的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师从于杨民康教授的另一位博士李红梅选择了蒙古族古老的祭祀仪式——鄂尔多斯地区成吉思汗祭祀音乐文化⑤李红梅:《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乐考察与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运用仪式音声研究视角、借鉴文化阐释相关理论,通过仪式音乐民族志的描述与文化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求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乐文化传统与当代变迁。
(二)自治区外蒙古族音乐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中国的蒙古族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及新疆、青海、甘肃、云南、辽宁、黑龙江、吉林、河北等省区,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质。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上看,对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音乐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对分布于自治区外的蒙古音乐文化的观照不够多,专题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崔玲玲博士是较早关注自治区外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学者之一,其博士论文《青海台吉乃尔蒙古人人生仪礼及其音乐研究》①崔玲玲:《青海台吉乃尔蒙古人人生仪礼及其音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通过对青海地区台吉乃尔蒙古人的出生礼、剪发礼、婚礼和丧礼等人生四大仪礼的仪式及其音乐的考察研究,阐释蒙古族古老文化的遗存及在历史发展历程中的变迁特征。第三代学者包明德和石秋月博士将研究视域投向东北地区的蒙古族。前者主要对嫩江流域蒙古族音乐在特定历史阶段因生产生活方式的嬗变其音乐文化所产生的变异特征予以阐释。②包明德:《论嫩江流域蒙古音乐变异》,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石秋月博士的《论民族主体更迭中东北三省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消散与再塑》③石秋月:《论民主主体更迭中东北三省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消散与再塑》,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课题,以行政区划为切入点,对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蒙古族音乐流变特征予以宏观叙事,指出在音乐文化历史变迁中除了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外,行政区划对其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对民族地区音乐文化的变迁研究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博士后哈斯巴特尔的课题④哈斯巴特尔:《西蒙古多声音乐研究——以呼麦、冒顿·潮尔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后课题,2018年,合作导师:杨民康研究员。从“跨界”角度比较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蒙古人多声音乐本体特点及当下状况,深入阐释了其流变特征。
(三)说唱类叙事音乐研究成果有所突破
叙述性说唱音乐在中国少数民族中数量极为丰富、形态多样。对其表现的内容、故事情节及人物特点等题材方面的研究在民间文学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说唱类叙事艺术中的音乐是主要服务于故事情节而被定名为形态较为单一的音乐形式,研究价值遇到了挑战。如何打破上述瓶颈是学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之一。齐占柱和宁颖博士较好地突破了上述难点,为学界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前者的《胡仁乌力格尔与乌力格尔图哆的亲缘关系研究》⑤齐占柱:《胡仁乌力格尔与乌力格尔图哆的亲缘关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课题,从区域音乐研究角度,将蒙古族传统的说唱音乐“胡仁·乌力格尔”和“乌力格尔图哆”(叙事歌曲)放置于“地方传统”语境中,通过分析胡仁乌力格尔和乌力格尔图哆共生文化丛形式的历史背景、社会根源及共存文化要素,解读胡仁乌力格尔与乌力格尔图哆的衍生与反叛现象,阐释其形成该特质的内在缘由,总结了该区域音乐的地域文化品格。宁颖博士的研究对象是朝鲜族的叙事音乐“盘索里”,课题《中韩跨界语境中延边朝鲜族“盘索里”溯源与变迁研究》⑥宁颖:《中韩跨界语境中延边朝鲜族“盘索里”溯源与变迁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以韩国“盘索里”为母体和参照,通过分析其音乐、表演等方面的主要特征,跨界溯源延边“盘索里”的传承支脉,阐释其歌手如何通过该艺术形式实现不同层级的认同问题。国内对“盘索里”音乐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以中、韩两国跨界田野为基础,专题研究该音乐艺术的成果仍为鲜见,因此该课题为我国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领域提供了较为新颖的实践案例。
(四)初涉近当代音乐史研究领域
相较于其他少数民族,蒙古族音乐史研究成果相对丰富,早在20世纪末呼格吉勒图和乌兰杰先生相继出版蒙、汉版本的专著《蒙古族音乐史》⑦呼格吉勒图:《蒙古族音乐史》(蒙古文),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系统梳理了蒙古族古代音乐的发展历程,篇幅原因未对蒙古族近现代和当代音乐展开详细讨论。对近当代音乐史的梳理和研究,同样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近些年随着学科的发展,也有不少博士开始关注近当代音乐的历史,如李亚芳博士的《透过文本:对西方传教士记录的鄂尔多斯音乐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考察与研究》①李亚芳:《透过文本:对西方传教士记录的鄂尔多斯音乐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考察与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以历史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比利时圣母圣心会(C.I.C.M)传教士约瑟夫·万·欧斯特神父(Joseph Van Oost)在20世纪初期收集、记录的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土默特地区的民间音乐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掌握大量的一手外文资料的基础上,对神父记录的音乐文化进行详细的翻译、整理和考证,通过多次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对来华传教士予以客观评价,探讨蒙、汉民族传统音乐流传过程中的传承与变迁。其相关文本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的音乐文化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样来自内蒙古的楚悦和赵娜博士将研究对象锁定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以来的专业创作音乐领域。赵娜博士的《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题材汉语歌剧研究》②赵娜:《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题材汉语歌剧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一文选取较有代表意义的《萨布素将军》《沙格德尔》《也兰公主》《舍楞将军》等汉语历史题材歌剧,通过分析其题材与文学内容、体裁与音乐文化、唱腔与表演三个层面,阐释其该类歌剧的“民族继承”性和“杂糅”性两大特征。楚悦的《内蒙古自治区六十年交响音乐蒙古化特征研究》③楚悦:《内蒙古自治区六十年交响音乐蒙古化特征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课题,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60年以来的交响音乐创作与发展予以梳理和研究,总结创作规律和蒙古化特征,对民族风格作品专业创作实践及中华民族交响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为建立中国特色交响音乐文化体系起到重要的示范意义。同时,为蒙古族近当代音乐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纵览上述课题项目,各位博士们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研究议题范围不断地拓展和深入,出现了诸多新颖和具有补白意义的成果。同时,与导师通力合作对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方法和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反思和深入的思考。这对于强调理论性为主要学科特点的民族音乐学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三、视角的多元化:跨学科角度探索学科前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理论思维的不断拓展,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和新颖的研究视角。上述十余位博士在研究理念和方法方面以田联韬先生的“重视田野考察和音乐本体分析的研究观念”④杨民康:《田联韬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人民音乐》2019年第4期。为“元理论”基底,在掌握学科动态“脉搏”的同时借鉴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和学术视角,逐渐将其民族音乐学本土化运用于课题研究中。从现有的成果来看,运用仪式音乐理论、历史民族音乐学、跨界比较研究等多学科角度探索性阐释的课题数量相对较多,故此重点探讨众位博士对上述民族音乐学方法所做的积极反思和实践运用。
(一)“仪式”:从描述对象到阐释路径
脱胎于宗教学的仪式学在学科理论上较早受到了宗教社会学及宗教人类学观念影响,除了关注仪式行为以外对信仰体系的象征性特征也予以重点观照。少数民族音乐的生成特质与该民族的民俗与信仰密不可分,除了有娱乐性功能以外更强调其象征功能和文化意义。宗教信仰多以仪式形式显现于民俗音乐文化之中,那么如何通过这些类型丰富、形态多样的仪式形式阐释其文化的意义和象征意义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对仪式呈现的音乐做类型判别,这是研究的关键环节,是描述的重点内容和对象,也是阐释文化的起点。杨民康先生认为“以宗教仪式音乐文化核心”的传统音乐类型内部可分为核心层、中介层、外围层三个层次:核心层次——封闭性仪式。这是宗教社团内部举行的崇拜仪式,例如日常课诵。主要在宗教组织和各级寺庙之间发生纵向的社会性联系。中介层次——开放性仪式。一般指僧、俗共同举行的仪式法会,也可指具有特定宗教信仰内涵的世俗性——政治性、社会性或民俗性仪式。外围层次——宗教节庆期间举行的公众仪典及歌舞音乐活动。这类节庆歌舞表演活动在古代传统社会唱词具有较浓烈的宗教信仰气氛,如今则较多衍生出民俗性节日的因素特点,甚至衍变为民俗节日。①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77—378页。上述宗教与祭祀音乐研究课题中既有对某一层次文化现象做微观探析的,也有对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文化特征予以整体观照的学位论文。如兴安、娜仁娜、王晓东博士的论文是对蒙古佛教音乐核心层次所做的微观课题研究,崔玲玲博士对青海台吉乃尔人生礼仪的文化意义的探讨属于中介层次文化现象的研究课题。而红梅、苗金海、李红梅、张林等博士的课题则从整体性观念出发对研究现象的核心、中介、外围等层次予以全面观照。
随着仪式音乐的范畴和类型的拓展,作为“文化中的仪式音乐”受“整体性”研究观念的影响,从以往的描述对象逐步发展成为阐释“文化活动文本”的路径之一。如苗金海和张林博士的课题中,记述的不同类型的仪式音乐文化所塑造的不同层级的文化认同就是典型的实践案例。个案中的仪式不仅仅是描述对象,更是阐释认同的路径之一。正如赖斯曾述:“音乐为以往存在或刚出现的认同现象提供符号性的形态,这种符号性的形态体现音乐的内在结构,常构成认同符号的标志性元素,音乐的时间性可以是认同的一个时序逻辑的符号。此外,音乐自身固有的多重属性(旋律、和声、节奏、音色等)有着标识多重认同之不同方面的能力。”②转引自张林:《音乐建构中的文化认同——以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因此,仪式音乐研究现在不仅仅是阐释的对象,逐渐发展成为阐释文化的路径之一。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博士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对仪式音乐方法论有所思考,如苗金海博士提出的“书写‘全息式’仪式音乐民族志的设想”和“仪式音乐文化认知的‘三层次’说”③苗金海:《书写“全息式”仪式音乐民族志——鄂温克族敖包祭祀仪式音乐研究反思》,《民族艺术》2018年第6期。概念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思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中我们也看到各位博士对音乐人类学理论的思考及探索精神。
(二)“历时”:阐释“共时”的另一个维度
以关注当下活态音乐资源为自己学科特色的民族音乐学,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不断反思将民族史学研究思维与田野调查相结合,为阐释“共时”现象提供了另一个维度。魏狄斯指出“每一类音乐及每一类社会都是绵延的历史过程的现代结局”应“将历史问题整合进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全面策略之中”④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页。,并且要“以揭示历史事件真相和按照变化的进程研究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作为它的两个目标,同时要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根据,包括当代社会音乐可观察到的连续性和变化的依据。”遵循“文献学研究、音乐符号的解释、译谱和分析”⑤李亚芳:《透过文本:对西方传教士记录的鄂尔多斯音乐的历史民族音乐学考察与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的研究步骤来解释“当下”的实践思路。对于具有文字传统的蒙古族、朝鲜族、满族等民族的音乐研究中,依据上述步骤进行实践是了解和阐释当下音乐文化的重要方法,也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近当代音乐史的一个重要思路。李亚芳博士对20世纪比利时传教士约瑟夫·万·欧斯特神父所撰写的手稿文本内容与“共时”状况做“历时”性的比较研究,一方面“重塑”了20世纪初期的音乐文化景观,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呈现了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变迁特征。同样,张林博士在课题中用历史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清朝历代皇帝东巡谒陵祭祖以及登基大典中的音乐发展脉络进行梳理,通过历史中的音乐变迁解读了当下的建构情况。笔者认为,在田野调查与案头工作中不仅要关注当下活态资源的考察研究,同时更应该针对性地对其过往的历史发展与变迁轨迹进行纵向的梳理和探究,将“共时—历时”维度的互相补充思路运用于中国少数民族近当代音乐史研究之中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路径。
(三)“跨界”:从研究对象到研究理念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三十余个民族为跨界(或跨境)族群。早在20世纪70年代,田先生对云南傣族地区和藏族地区作音乐考察时已意识到同一民族音乐品种和艺术特色在境内外迥然不同的现象,并在《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第一章的“关于跨界民族”部分专设论题强调指出“考察边疆地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跨界民族在国境内外的传统音乐种种情况。”①田联韬主编:《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呼吁学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比较研究和整体性宏观研究指明了方向。在田先生本人及第一代博士杨民康等诸位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于2011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成功举办了“首届跨界族群音乐学术研讨会”。经近20余年的努力和推进,“跨界”一词已成为当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术热点之一。其中,以杨民康为代表的南方少数民族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成果斐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中国少数民族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实践的参照性成果。从系列成果中不难看到,“跨界”已从对象性研究逐渐转向为学科方法理念,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和方法范式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新天地”。
对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跨界”研究,虽然其成果尚不及南方跨界族群民族音乐研究那样丰厚,但近些年也逐步显现出较为乐观的态势,有部分博士研究生开始运用多点音乐民族志方法对境内外“同源”族群的“同宗”音乐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如第三代学者宁颖、楚高娃博士和哈斯巴特博士后的学位论文和系列成果均属该领域课题。宁颖博士为溯源延边“盘索里”的传承支脉,阐释歌手如何通过该艺术形式实现不同层级的认同问题,于2012—2013年间赴韩国学习交流和考察长达13个月,在掌握丰富的文献和田野资料基础上对延边“盘索里”与韩国“盘索里”分别进行了横向比较,解答和阐释其上述问题。哈斯巴特尔的博士后课题②哈斯巴特尔:《西蒙古多声音乐研究——以呼麦、冒顿·潮尔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博士后课题,2018年。关注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图瓦共和国蒙古人多声音乐本体特点和音色建构、音乐文化现状及流变等特征。不同于上述两位博士所关注的“原生层”文化形态,楚高娃博士的研究对象则是“次生层”的蒙古佛教文化。自2012年起,对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共和国的佛教音乐进行定点式田野调查,完成了系列课题和成果。③楚高娃:《蒙古佛教诵经音乐之密律》(博士学位论文)、《神圣的帷幕:蒙古佛教音乐跨界研究》(博士后课题),《中蒙两国佛教音乐跨界比较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学科2016年青年项目)。
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中,我们不得不思考“那些当代世界格局中已经相对固定的‘政治边界’对于国境两侧族群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否关系到边界两侧族群音乐文化的交流和互融?最终,上述音乐文化互动对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变异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推动作用?”④杨民康:《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放性视野——代栏目主持人语》,《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等问题。确实,半个多世纪后的“边界”两侧族群音乐文化已呈现异质化特点,这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表层层面的变化,更是认知层面的变化所致。因此,在跨界族群研究中后者也是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楚高娃博士近期进行的“蒙古国音乐研究文献综录”课题关注的则是该国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史。与对“同宗”音乐类别进行比较研究所不同,该课题旨在为边界两侧音乐文化的交流、互动、对话起到“桥梁”作用,是一项具有实践价值的课题项目。同时,我们也看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不仅仅是对文化现象的境内外横向比较,而逐步转向为一种兼音乐类型、历史文化、社会语境、学科史等内容的多重学科方法论和研究理念。其开放性的视野和理念对于当下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藏彝走廊”及其现时版“一带一路”等涉及传统与现实的“跨界”(跨学科)研究方向,为其提供最为直接、具体、鲜活的学术资料和文化灵感。①杨民康:《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中国音乐》2016年第3期。
(四)运用其他理论方法和视角探索性研究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
除了上述研究视角和方法以外,也有多部采用较为独特的研究方法或视角探索性研究的成果。如包爱军教授受文化人类学文化形态层理论启示提出的“质点扩散性文化关照法”②质点扩散性文化观照法,是以文化系统中某一质点为基点,逐步逐层梳理它与其他文化质点间亲疏关系的文化关照方法。,之所以提出该方法,在其著作中写道:“文化人类学将人类文化形态分为物质、行为、精神等三种,这种形态分布于文化整体结构的外层、中层和核心等三个层面,他们的组合共同展示了文化的特点。无论是大文化系统还是较小的文化系统,他们共同的特点均是属于相对完整的整体,整体的结构同样都包括物质和行为、精神等因素,其区别只不过是整体结构所含每一种因素数量的多数而已。”③包·达尔汗:《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作者运用该方法将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系统划分为基础技术层、社会组织层以及内隐的思想意识层等三个层面。通过解剖、重组、归类其文化质点,阐释了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特质,成果得到了业界的广泛好评。田联韬先生曾写道:“这篇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宗教音乐研究工作的空缺部分……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文化系统不同层级观察和剖析蒙古佛教音乐所包含的文化质点,从而获取分析的结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蒙古族的青年学者了解和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广度与深度,也可感受到年轻学者锐意进取的学术探索精神。”④包·达尔汗:《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这种探索精神深深影响着学生们,如楚高娃博士受阐释人类学“对文化持有者的阐释的再阐释”之理念影响,在田野调查中关注到研究对象的系统化理论特质,重点关注和搜集整理佛教音乐相关的文献资料,并从文化本位分析角度出发“以佛法研究佛教音乐”为理念,运用佛教大小五明之《工巧明》(蒙文《大藏经·丹珠尔部》第221卷)中的相关音乐理论对“五蕴”“五具”“七音品”“十律”等概念的语义和语用层予以解读和分析,阐释了蒙古佛教音乐生成的自律和他律特征。同样运用这种“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的课题有宁颖博士对盘索里的生成特质的探讨。作者通过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从模式—变体二元关系出发,分别以简化还原和转换生成两种双向互逆又互补的路径,解决了歌手如何创造“盘索里”音乐的问题。
诚然,随着研究对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以及跨学科研究理念的不断渗入,从多学科、多维度阐释研究对象已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必然趋势。上述几则方法论只是对诸位博士在论文中普遍所运用的理论方法的举要简述,也是目前学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其选题、还是对于方法论的思考,因学者的旨趣不同有所侧重而已,其实每一篇论文都具有创新性和前沿性特质。
结 语
通过梳理田联韬一脉几代博士生的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我们看到这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视野的开拓以及推进做出了积极的引领和启发。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很多领域仍需要进一步地深入和拓展。正如田先生所述:“60年来,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的考察、研究,中国的音乐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不少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大量考察、采集、研究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而如何吸收和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如何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如何使自己提高理论素养、开阔眼界,使少数民族音乐的考察、研究工作向更深层次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待进一步努力的课题。60年对个人来说,几乎是人生的整体,但就整个事业而言,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我们的事业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方兴未艾,前途似锦。”①田联韬:《走向边疆——田联韬民族音乐文论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作为这个“大家庭”成员之一,我相信这支朝气蓬勃的学术团体,继承学统,努力探索,立足学科前沿、攀登学术高点,定会引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事业的未来。
仅以拙文悼念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科奠基人——田联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