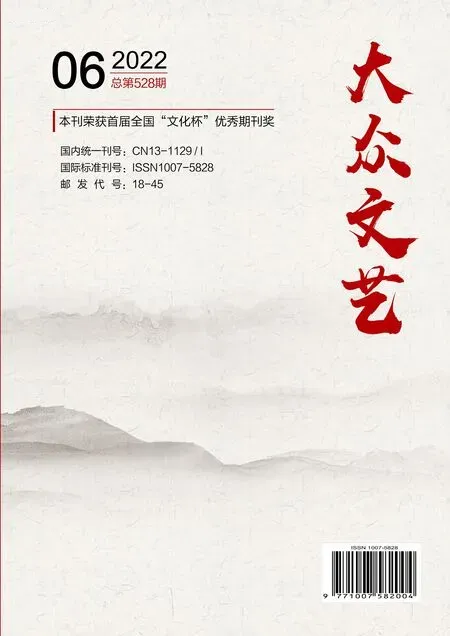试论郑观应的教育改良思想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贵阳 550000)
清代的教育制度可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教育体系。其制度基本延续自明朝。在中央设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和八旗官学。在地方既有官办的府学、州学、县学、社学和义学;也有书院、里家和私塾。初级教育以私塾为主。私塾作为私人教育机构,又分为教馆、族塾、家塾等种类。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仍然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而教学目的也依然停留在“代圣人立言”,维系皇权的层面上。随着民族危机的日渐深重,有识之士开始将变革的目光对准封建教育制度,郑观应就是其中之一。
一、“各有次第”的学制改良倡议
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维新派中,变革之声络绎不绝。康有为通过对比中西教育的内容对“八股取士”的弊病进行批驳。他指出“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应将八股废除“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中出题考试”。[可以说,“八股取士”的华而不实同西方“经世致用”的教育制度形成鲜明对比“夫西人之于民,皆思教之而得其用,故自童幼至冠,教之以算数图史,天文地理,化光电重,内政外交之学,唯恐其民之不智;而吾之教民,自丱角以至壮岁。束缚于八股帖括之中,若惟恐其民之不愚也者,是与自缚到戈,何以异哉”。洋人自幼就开始学习自然科学,而中国士子则一直束缚在八股之中,最终导致民智不开,国势衰微。
在郑观应看来,改良教育,首先在于革新学制。就学校开设的意义而言“先王之意,必使治天下之学皆出于学校,而后所设学校非虚”,所以在上古时代,人才“出于学校者独盛也”。但是今日之书院,学人士子风气散漫,很少有刻苦钻研之人,就算有也是没有规章制度,任凭其来去自由。而在学科内容的设置上,士子所作之文“不过尘羹土饭,陈陈相因之语,于国家利病,政治得失,未尝一及”。[文章的浮华空疏,以及对天文、物理、算数等学科的绝口不谈,都导致了书院的设置偏离其“育才”之初衷,而变为了“锢才”之囚笼。
为进一步说明中西之间教育的差距,郑氏以西方各国的学制和内容加以比较“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其学校规制大略相同,而德国尤为明备。学之大、小,各有次第。”郑氏指出,西方各国的学制契合古风,以学校大小、次第因材施教。其所教内容并非空疏之义理,而是“皆以实学为主”。孩童幼年的教学内容,以早教和数学入门、本国地理书为基础。也正是在日益熏陶训练下,幼童的心智得到启迪。反观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才材”。为师者皆是迂腐老儒,他们终日沉浸在词章考据之中,授课的内容更是留在四书五经的陈旧议题上。如若问及五洲之形式,各国之政治以及动植、格致、形声之学“皆懵然漠然,不知所对”。可以说中西教育的差异,在根本上决定了两国人才储备的差距,而人才储备则与国力之强弱息息相关。中国封建教育制度下的产物“蠢愚迂谬不可向迩,腹笥空虚毫无心得”。这就导致了中国之人才很难与西方竞争。
所以郑观应提出中国要效仿西方,进行学制改革。作为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他是“中西汇通”的坚定推崇者。他指出中国需要根据本国国情进行教育制度的革新。以小学学制为例,可以效仿德国小学堂章程“教分七班,每年历一班”。而所学课程则可分置成十大种类,此十大种类又以中学和西学相区分。其中既包括传统的经学、中国文学、史学、中国书法等内容;也包含西方的算数、生物学、物理学、美术及体育等现代学科。传统教学存在的一大弊病是他着重批判的对象,即在科目的教授上,老师并非职能分明。不论教授何种学问,先生往往只是一人。故此郑氏认为,需要“班有专师,有专教算学之师,有专教格物之师,有专教重学、理学、史鉴、舆地、绘画、各国语言文字之师”。[科目教授的精细划分更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也更利于学生理解。他正是看到这一点,点明了“设置专师”的必要性。
二、“各专一艺”的职业教育举措
分置学科和“设置专师”之目的在于储备精尖人才,因为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故而“需才之急,较泰西各国尤众”。郑观应认识到中国对专业人才需求的急迫性,所以发展新式教育必须依靠各国经验“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而精专一艺的专才国家更应给予重视“凡自备资斧游学外邦,专习一艺,回国者准给凭照,优奖录用”。在各类专业人才的培育中,郑氏认为通晓工艺者较为关键。首先,中国穷人较多,而且国家尚且没有工艺院,如果设立此院则使贫民能够有养家糊口的技能,而不至于盗贼横行。以西洋各国为例,他们将工艺院的设立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诸国富强的根基全在于工艺。因为工艺不但有益于商务、还有益于人心。对此,郑氏提出工艺学校所教课程应分为五等,第一等是物理、机械、绘图和化学;第二等是专门针对贫民子女,教授其谋生技艺;第三等是工艺实习;第四等是根据学生所学和实践的疏漏纠正弊病;第五等是着重教授复杂之处。可以说,郑观应系统性地提出了开展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可以为百姓解决生计,不至于让贫民衣食无着;另一方面还可以有利于道德教化,维护社会稳定,可谓一举两得。
工艺作为一种职业技能,不能仅仅之局限在书本之中,否则便会“终身习之而莫能尽其巧”。由此,在学员的招收上,郑氏提出但凡收录的学员,皆需通晓算数、识得书籍。因为若要精通工作,绘图原理和勾股之学是必讲课程。只有具备一定的基础才能成器在胸,否则便会难以测量清楚。在他看来,英国的工匠学堂在设置上就较为完备。学生在学院学习就算不能毕业,却也不至于每况愈下。所以一般学工艺者,学校会要求他们先通习工程类书籍,研究机械原理。在理论基础夯实以后,各习所业,最终则能“不独与师异曲同工,且变化神明,进而宜上”。
为避免急于求成,他对教育的成效作出警示“彼萃数十国人材,穷数百年智力,掷亿万兆资材而后得之”。人才培育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西方各国莫不如此,他们都是在一代又一代的积淀之后才实现人才的涌现,急于求成有违教育之规律。所以,为振兴中国之工艺,郑观应认为要面向社会募集资金,开设工艺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以物理学为基础,以制造各类器械为目的,且聘用西洋名师悉心教授。由此,中国之工艺必然不为列强所轻慢。郑氏还看到,缺乏竞争环境会使学子懈怠。据此,他提出要举办“博物会”。所谓“博物会”,即是网罗各国精美之产品,以质量的优劣进行评判。在这种评比竞争下,必然刺激物品制造工艺的进步和革新。
可见,郑观应的职业教育举措,其背后是以中国之富强为最终目的。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士大夫对洋务事宜大为鄙夷,却不知“强弱无常,盛衰迭变”。但凡中国能开展职业教育,培育精通工艺的人才,必将由弱变强。
三、不分男女的平等教育观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女性受教育权利一直得不到保障。及至近代,随着资产阶级新思想的传入,有不少开明士子为女性获得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奔走呐喊。
梁启超从承接三代遗风的角度言明了兴办女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兴女学不是效仿美日诸国,而是对祖先文化的传承。因为“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就目的而言,我国女学是在“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针对不平等的教育现象,郑观应同样提出“无论贵贱男女,自六岁后需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可以说,早期维新派看到了兴女权,办女教的重要性,这和国家的兴盛甚至是紧密相关的,中国古代教育所讲的“妇容”“妇德”“妇容”“妇功”等内容,都是又名而无实。最终也导致了“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也”。
在谈论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问题上,郑氏同样以西方教育制度作为范例,他指出,西方各国都视女学和男丁并重,但凡到入学年龄之时,不论男女都要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不分性别一律平等,皆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为主要授课内容,且可以根据她们的兴趣选择专攻方向。接受教育的女性在行事上更符合现代新女性的标准。她们不仅能晓畅文字,还能察明道理,更可通达纺织、烹饪、绘画之理。同时也兼习女工、中馈、相夫教子之道,可称之为“贤内助”。
所以,中国可以根据自身传统筹办女学。在学堂之中仍然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可以看到,尽管郑氏对女学的思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范畴,但是相对于保守派对妇女权益的漠视和人身的压榨,他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他肯定了女性作为“人”的存在和意义,也极力促进她们由封建时代的“闺中人”变革为现代意义上的“新女性”。为确保贫民女子也有受教育的权利,他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首先,可由富人出资,贫民入学。同时依靠官府的力量“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罚”。为对出资者作为嘉奖,可以由官方做媒,对出资者从中匹配姻缘。其次,还需效法西洋,以严格、谨慎的态度设立女塾章程。经此种种,培育出来的新女性不至于荒度岁月。一方面,她们具有相夫教子的能力;另一方面,她们也拥有优良的生存技能。
封建时代女子缠足的陋习同样为郑观应所抨击。此等陋习,遍观万国,唯独中国还存在。缠足甚为残忍“或五六岁,或七八岁,严词厉色,陵逼百端,必使骨断筋催,其心乃快”。这不仅是在生理上摧残了女性,还在心理上让她们自幼就接受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此无疑是在人格上对她们进行毁灭。郑观应大声疾呼“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男子下哉?”废除缠足,即是实现对女性的解放。让更多女性进入学堂、接受教育,于国于民而言,皆为善举。所以他郑重提出官府要重申禁令,禁止缠足,对屡禁不止者书写“裹足”二字高悬其门,以儆效尤。地方官吏、贵臣望族及诗书礼仪之家更应当起表率作用。以此而行,不出十年“缠足”陋习便可废除。
四、结语
郑观应的教育改良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进步意义,他站在“中西并重”的角度对改革教育内容、兴办职业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今视之,仍然可以获得启发。他提出的一系列举措也体现了《盛世危言》一书所具有的特点,即通过介绍各国经验,改革本国教育存在的弊端。同时他以对人性的关怀,表达了废除缠足弊病的必要性。只有不断打破晚清封建教育对人的束缚,人才方能涌现,国家也才能摆脱疲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