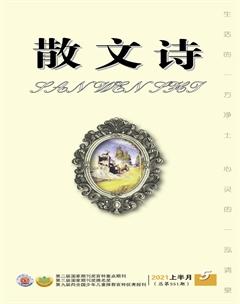父亲在田亩上弯腰 (外二章)
川梅
面朝田亩,低头弯腰,屁股仿佛翘到天上。用两手在泥土里划拉生活,拨动着岁月的短长。
从春播到秋收,父亲都是没头没脑、没黑没夜忙碌,从不偷工减料、偷奸耍滑。就这样,说一不二地把农业盘来算去。
父亲总是爱说他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一辈子认定土地不亏人,他在土地里忙碌了一辈子,如今那么老了,不知道他收成了什么。
我从不敢细想土地,到底有没有亏过父亲。一生,他拿得出手的不只是山清水秀,还有最不值钱的时光。
这些东西,没有谁打他的主意。
多年以后,每次见到父亲,他都是跟一头苍老的牛一起,那头早已不耕农事的老牛,忠诚厚道,伏在父亲身边。两条苍老的背影,活脱脱一幅唐朝的水墨,一半写意,一半抒情。
狗在半夜叫是为自己
苍老,也是狗的宿命。
山里的狗老了的时候,常常爱蹲到屋后坡上,朝着无边苍茫,漫无目的地吠叫。
它的叫声,让多少乡亲午夜梦醒。
它也许是看到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看到。它只是觉得守护了一辈子老村,现在自己终于老了。一辈子,看见什么就奋不顾身冲上前;一辈子,看见主人的亲友和村长就摆阔气;一辈子,都是看主人的脸色;一辈子,都是低眉顺眼,把日子过得人不是人、鬼不是鬼。如今时日无多,想在夜深人静时候,对着远山的深处,只为自己使劲地吠上几嗓子。
在九岭山腹地,狗的日月要比人的短些。只是短的程度,没有人会去丈量。狗忠心不二,主人也从不把它们当人,不跟它们真心过日子。
每次狗叫了之后,九岭山里仿佛就有什么发生过,又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山里的过客
那时候,黄昏挂在山坡上,季节在另一番气候里摇曳。不事张扬的菊花笑得低眉顺眼,让被收割的苞谷有些羞怯。
一个赶路的人坐在苞谷地边歇息,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也无从知道他将要去的方向。
只有疲惫的歌声,悄悄融入夕阳。
林子后面的木屋,屋顶上爬满了很多的青藤,一個少妇正在自己种植的炊烟下,用勤劳的手指翻动生活。
她如水的目光漫过来,歌声,把目光撞落到地头上。
成了秋意。
背着破旧的行襄,赶路人的方向无边苍茫,他也许走了很远的路途了,前面,今夜只怕也没有尽头。
夜色漫上来了,弯月却还没有爬到柳梢。
九岭山深处,这个没有浪漫的黄昏,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天,就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