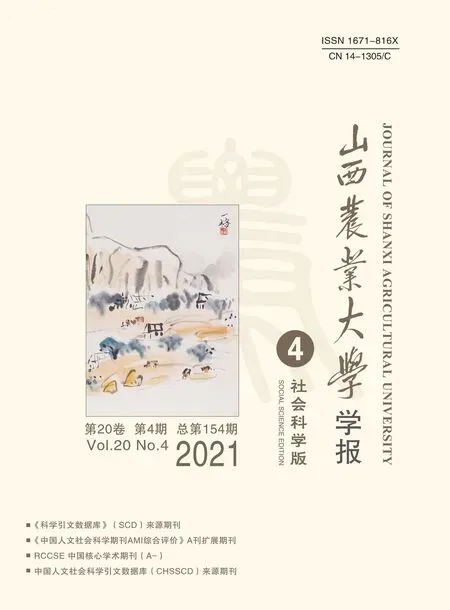资源拼凑视角下贫乏型乡村的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四类不同村庄的案例考察
李志敏
(1.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2.阳光学院 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5)
资源禀赋是乡村振兴的基石[1],而资源贫乏是多数乡村面临的实际情境。内生式的发展理念,提倡利用区域内的技术、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培养乡村的造血功能,从而构建独特的发展优势。[2-3]但多数乡村本已处于资源贫乏的劣势,如何才能构建持续发展的优势?拼凑理论(bricolage)分析组织如何在资源贫乏中,利用手头廉价资源突破限制、实现创新,为劣势乡村提供了创新发展的思路[4-5]。国家在提到乡村振兴战略时,也多次强调应该“因地制宜”。可见,让乡村中原本被忽视的或廉价的资源实现价值转化,在劣势中求创新,才是研究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部分乡村在处于资源劣势的情境下,通过拼凑的方式走向创新,值得深入探讨。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贫乏型乡村资源议题相关综述
关于“资源贫乏型乡村”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研究者从几个角度对其进行评判。一是以自然资源禀赋为标准,将乡村划分为资源丰裕型和资源贫乏型[6-7];二是以村庄集体经济的强弱程度来划分资源丰富和资源贫乏的村庄[8];三是从综合评判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源贫乏型乡村”主要指在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经济产业、人文社会、组织治理等资源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的乡村[9]。本研究所指乡村为第三种评判标准下的乡村,这类乡村大多位置偏远、交通不便、产业凋零、人口流失严重,具有贫乏型乡村的典型特点。资源的运用能力是乡村克服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10],然而高质量的资源在多数乡村又是稀缺的,同时乡村独特的社会结构、规范和习俗,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源挑战[11-12]。归根到底,乡村的发展问题是资源的问题。
现有文献对贫乏型乡村的人力资源、产业资源和景观资源等多方面的资源开发做了论述。在人力资源方面,谭诗赞探讨了资源贫乏型乡村从庇护式治理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型问题[7];胡卫卫等从内生性培育视角探讨了资源型贫困村的柔性治理路径[6];现有文献还对乡村人力资源之间的多种合作关系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模式、“自下而上”的居民主导模式,以及参与主体之间的水平互动关系[13]。近期的研究认为乡贤、社会企业、营利组织等是贫乏型乡村得以发展的重要资源[14-15]。在产业资源方面,现有文献提出实现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相对贫困人口长效机制的前提,乡村通过对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来改善经济状况[16-17]。李冬慧等认为贫困地区应该根据乡村不同的产业类型,打造地方特色品牌,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18];赵欣等总结了内蒙古库伦旗农牧业特色产业的运行机制和模式[19]。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和乡村再生则是通过挖掘地方的生活文化,结合产业化开发形成了“生活文创+产业发展”特色[20-21]。在乡村景观资源方面,文献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生态景观、文化景观、体验景观等模式的探讨[22-23]。朱珈莹等阐述了生态资源在贫乏型乡村中的发展作用,并提出了生态旅游扶贫的实现路径[24];肖远平等总结了文化遗产民族村寨开发的“西江模式”[25]。现有研究虽然关注到资源在贫乏型乡村发展中的作用,但较多关注乡村的特色资源,较少提及农村无人无产并存的现实情况,造成了所提策略很难在实际情境中执行[26]。如何在资源受限的情境下,通过建构既有资源,实现乡村创新发展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资源拼凑理论注重如何在资源限制的情况下,通过既有资源的建构逻辑,进行创新活动[27]。现有研究对资源拼凑和组织创新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多数研究认为拼凑行为有利于资源受限的组织实现创新[28-29],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整合能力[30-31],一定程度的资源约束可以迫使组织重视既有资源,从而发现资源的潜在价值,产生创新[32-33]。虽然现有拼凑理论的发展已从企业拼凑延伸到社会拼凑领域,拼凑的对象也从物质资源向创意、文化等非物质资源扩展,但研究成果更多集中于新创企业,在乡村社会中的探索较少。乡村虽非新生,但却弱小,资源贫乏是多数农村的常态,如何借助拼凑行为促使乡村形成资源能力,需引起关注。
(二)分析框架
学者们总结了资源拼凑的三个维度:资源清单、拼凑过程以及拼凑结果[34-35]。初始的资源清单可以来自于内部,也可以来自于外部[27,36]。对于内部的资源,需要对其进行评估、筛选和设计,对于外部资源,则需要对其进行借鉴、融入与整合。资源的拼凑过程既涉及内部资源的利用,也涉及外部资源的植入。拼凑的结果则是对初始资源要素的重新排列组合,一般包括“无用之用”和“无中生有”。“无用之用”是对手边既有资源价值的转化[37];“无中生有”则是通过对内外资源的融合,产生新的创意。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图1 的拼凑分析框架。乡村借助手头资源清单,通过利用和植入的手段,产生资源转化或者资源创意的结果。为此,根据资源拼凑的过程和结果,对乡村中的四类拼凑行为进行比较,Ⅰ是资源利用——创意式拼凑,Ⅱ是资源植入——创意式拼凑,Ⅲ是植入——转化式拼凑,Ⅳ是利用——转化式拼凑。通过典型案例研究,探究不同情境下资源建构过程的异同。
二、研究设计
(一)案例选择及数据收集
本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资源贫乏的情境下,乡村如何通过不同的拼凑行为突破限制,此类问题可以借助多案例研究进行探索性研究[38]。在选取案例对象时,遵循典型性和可行性相互结合的原则。主要关注:(1) 案例的典型性。研究选取四个曾经面临不同资源困境的乡村,通过资源拼凑突破限制,进而走向良性发展的典型案例。(2)案例的可行性。所选案例均为多年来调研和跟踪的乡村,这为数据的收集提供了可行性。四个村分别为我国台湾地区南投县的桃米村、妖怪村和福建省平南县的漈下村、北墘村。四个乡村均地处山区,较为偏远,面临不同的资源贫乏困境。桃米村曾是垃圾掩埋场,并在921 地震后面临生存危机,因采取资源利用+创意的形式实现创新,故匹配Ⅰ型拼凑行为;妖怪村因所在地溪头风景区没落而面临发展困境,后采取资源植入+创意的形式实现创新,故匹配Ⅱ型拼凑行为;漈下村是空心村,人口外流严重,是典型的人口衰退地区,因采取资源植入+转化的形式摆脱困境,故匹配Ⅲ型拼凑行为;北墘村虽然有黄酒酿造技艺,但因交通不便,产业单一,发展受限,后因采取资源利用+转化的形式摆脱困境,故匹配Ⅳ型拼凑行为。四个案例所处的贫乏型情景不同,遵循多案例研究的差异性复制逻辑,这为得出普适性的结论提供了保障[39]。四个案例的贫乏类型及简要介绍如表1 所示。

图1 资源拼凑行为分析框架

表1 案例样本简介
为了提高信度和效度,采取了多种调研方式,包括实地走访、深度访谈,并同时通过二手资料、现场观察、参与观察等多种形式,形成证据三角形。调研概况如表2 所示。同时为了让关键构念能够从案例中涌现,选择了拼凑过程中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维度对案例进行分析,主要包括:(1)拼凑清单,不同的拼凑对象对于拼凑的路径选择有直接的影响作用[35]。(2)拼凑过程,即拼凑的各项活动,对拼凑创新过程的梳理,有利于发现乡村解决资源贫乏问题的策略。(3)拼凑结果,即资源所产生的创新价值。
(二)数据分析
首先,结合文献回顾、案例调研和文档资料在前期准备中确定了概念界定及案例归纳的方向,进而明确了案例的分析框架。其次,通过三角验证保证数据信效度,将案例的内容根据分析框架进行归纳,再对分析结果进行比较,使得不同拼凑行为中的拼凑情境、对象、逻辑、活动和效果不断呈现,通过编码过程的迭代进行,案例数据、构念和文献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理论模型将逐步完善[40]。最后,对模型和文献内容进行比较,进一步补充数据,直到理论饱和。

表2 调研概况
三、案例分析
(一) Ⅰ型:资源利用——创意式拼凑行为分析
桃米村在921 地震后面临生存危机,在抗震救灾中利用农村随处可见的青蛙,打造了生态社区,传统农村变为生态保育和教育基地,并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桃米村的资源拼凑行为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见表3。
1. 拼凑对象
桃米村主要利用人力、物质和技能资源展开拼凑。新故乡基金会因灾后重建加入村庄,进而成为桃米村得以整合各界资源的重要平台,由基金会引介的生物研究员在对资源进行调查后发现了丰富的青蛙品种(A13)。这一在农村随处可见的生物成了桃米社区生态转型的重要物质资源。随着开发的深入,更多的资源包括稻草、厨余、居民手作(A11、A31) 等加入拼凑清单,这些低价值资源在桃米村的建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 拼凑过程
桃米村主要的拼凑活动包括创新探索、社会网络和角色多元,这些活动通过横向连接和无中生有的拼凑逻辑展开。一方面,基金会利用自身平台,让社区居民和社会资源之间建立起了横向连接关系,在提出生态发展的理念后,基金会鼓励村民角色转变,通过与保育中心合作获得“生态解说员”资格,居民承担了多重角色。另一方面,“生活与文化”、“历史与个性”的结合(A11) 让社区无中生有,开发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从日本搬迁到桃米村的纸教堂不仅是桃米村重要景点,也是应对困境的精神象征,促进了桃米周边的跨域合作(A21)。桃米通过与个人设计师、企业横向合作,开发出多种青蛙主题创意产品。村民的手工创作如布偶猫头鹰、布偶青蛙也是村落的热销文创产品(A34)。
3. 拼凑结果
桃米村通过物质、人力和技能资源拼凑达到创意结果。从营造空间来看,桃米村形成了农之园、艺之地、工之坊、食之堂、市之集、学之房六大功能互补的创意空间。从产业网络来看,桃米不仅建立起了生态旅游产业网络,也与设计师、厂商合作开发文创产品,振兴了地方产业。从居民角色来看,居民兼顾农民生态解说员、民宿业者等多重角色,提高了收入(A21)。从组织机构来看,新故乡基金会从公益机构转型为社会企业,进一步促进了村落发展。桃米村的资源拼凑路径如图2 所示。

表3 桃米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

图2 桃米村资源拼凑路径
(二) Ⅱ型:资源植入——创意式拼凑行为分析
妖怪村并非传统意义的村落,却带动了当地村落的转型。妖怪村原名“松林町”,最初改造为商业街,但生意惨淡。直到无意间被网友称为“妖怪村”,从而开始打造可爱版妖怪形象,现已成为溪头最出名的景点,并带动整个溪头向文化主题村落转型。妖怪村的资源拼凑行为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如表4 所示。

表4 妖怪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
1. 拼凑对象
从拼凑对象来看,妖怪村最重要的资源是异文化,异文化与长辈流传下来的妖怪传说融合,一起植入村落的主题开发中。妖怪村对物质资源进行了主题包装,比如有毒蕨类开发为“咬人猫”面包、会馆改造为妖怪主题房、并打造了妖怪形象和打卡地。同时妖怪文化还与当地传统节庆融合,也为周边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2. 拼凑过程
妖怪村主要的拼凑活动包括创新探索、网络传播和反客为主,这些活动通过纵向延伸和无中生有的拼凑逻辑展开。一方面,妖怪村的发展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原本商业街的名字是“松林町”,知名的妖怪形象“枯麻”和“八豆”原本只是神龛中的吉祥物(B21)。只是网友将松林町戏称“妖怪村”后,经营者转变了思路,将客房打造为妖怪主题房,并将“枯麻”和“八豆”两只妖怪符号化。另一方面,妖怪村是在统一主题之下的纵向延伸,通过对妖怪主题的深耕细作,妖怪村的景点均有了自己的主题故事。同时利用社交网络的人气,妖怪村与当地的传统节庆结合,变成了节庆活动的一大亮点,现已反客为主,知名度超过溪头景区(B15)。外来文化与本地传说的深度融合是妖怪村成功的关键所在(B13、B14)。
3. 拼凑结果
妖怪村实现了传说文化的创意价值。妖怪文化在网络的助力之下逐渐打开了知名度,进一步异文化与本地传说的融合,形成了带有乡土特色的“妖怪传说文化”。借助于妖怪形象,打造出自有系列妖怪品牌,并开发出妖怪主题的各类文创产品,如泡面、面包、包子以及纪念品等。除此之外,妖怪村现在举办的主题活动,通过造节的形式结合在地文化、产业、节庆等,不断优化客户体验,发展出了独特的体验经济。妖怪村的资源拼凑路径如图3 所示。

图3 妖怪村资源拼凑路径
(三) Ⅲ型:资源植入——转化式拼凑行为分析
漈下村全村超过三分之二人口为了谋生外移,留守的几乎都为弱势群体。2015 年由于公益艺术教育机构的入驻,开始探索艺术乡村振兴之路。村民绘画作品逐渐带来经济收益,漈下开始发展乡村画室、民宿、餐厅等基础服务,为逐年增加的外地学员提供保障。漈下村的资源拼凑行为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见表5。
1. 拼凑对象
从拼凑对象来看,漈下村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但这些人并非精英群体,而是弱势群体。在艺术机构驻村之前,他们的价值一直未被认可,直到这些人开始学习创作,画作远销国外,成为漈下村最宝贵的资源。随着村民主动性增强,古村传统的文化也受到关注,村中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外来植入的油画和古村的人、建筑、自然生态融合发展,艺术这一多数人认为高门槛的技能,在漈下村得到了新的诠释。
2. 拼凑过程
1)电压暂降发生后恢复过程迅速,基波电压有效值变化过程大致呈矩形;在整个故障期间,可能出现多次暂降;电压暂降幅值在突变点之间基本保持不变,而只在开始与结束瞬间发生了突变[13-22]。
漈下村主要的拼凑活动包括用途的转化、网络传播和产业的带动,这些活动通过无用之用和纵向延伸的拼凑逻辑展开。一方面,艺术机构在漈下村起了关键的助推作用,油画艺术植入乡村,让农民甚至弱势群体转化为这个村的核心价值资源,是“无用之用”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漈下村还采取了纵向延伸的拼凑逻辑。随着知名度的提高,由闲置古宅修缮改建的画室、书吧、工作室、咖啡屋等投入运营,深度旅游的配套产业逐渐成形。
3. 拼凑结果
从拼凑结果来看,漈下村实现了弱势资源的价值转化,将“油画”和“农民”融合,让弱势群体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认知,成为有艺术贡献的人。这种自我身份和能力的认同又促使身边的多数村民开始行动,真正参与到古村的建设中来,让闲置空间得到合理利用和转化。漈下村的资源拼凑路径如图4 所示。
(四) Ⅳ型:资源利用——转化式拼凑行为分析
北墘村虽然保留古法酿酒的技能,但北墘村交通条件欠佳,无法吸引商客前来,黄酒商业价值较小,家庭作坊的酿酒方式,既是北墘的特色,也造成了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2016 年以“黄酒文化节”为契机构建的跨域合作平台,促进了黄酒产业的振兴。北墘村的资源拼凑行为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见表6。

表5 漈下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

图4 漈下村资源拼凑路径
1. 拼凑对象
从拼凑对象来看,酿酒技术并非北墘独有,但在酒文化的运用上,代溪镇北墘村运用了创新的手法,将“黄酒文化”打造为文化节,以此为平台,整合了北墘多项传统技艺,形成了较为丰满的文化呈现方式。同时,借助社会资源进行智力帮扶,北墘已和高校、企业等形成了多种合作模式,这些力量的加入逐步提高了村民的认可度和参与度。

表6 北墘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关键构念及引证举例
北墘村主要的拼凑活动有用途转化、社会网络和主体多元,这些活动通过无用之用和横向连接的拼凑逻辑展开。一方面,黄酒文化节的构想,将传统的酒文化、手作工艺、原生态农耕文化整合在一起,同时以“红曲黄酒之乡”为主题申请了3A 景区,成为闽东地区文化旅游的品牌。另一方面,北墘村黄酒文化节为村民搭建了一个与外界交流的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北墘村先后与多所高校、企业进行了项目合作式开发。随着项目的开展,村民传统木作工艺也得到了传承和保护。同时,部分手工已经走入在地院校的课堂,开始了文创产品的开发研究,扩展了传统技艺的开发领域,将传统技艺与文化创意结合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传统技艺的附加值及传承性。
3. 拼凑结果
从拼凑结果来看,北墘村主要是使文化、技能等资源产生价值的转化。虽然酿酒文化在闽东地区不能算作独特优势,但北墘通过打造黄酒文化节为其带来了发展的契机,进而带动资源进入北墘。村民看到发展契机后自发改造古宅,并打造了黄酒文化展示馆等体验项目。外地企业和个人也可以和村民协商认租,开发黄酒酒吧、民宿等项目,为村民带来了实质性的经济收入。同时项目以多元主体的合作为主,高校、乡贤、企业的共同参与为项目的可行性提供了保障。北墘村的资源拼凑路径如图5 所示。
四、研究结论
(一)跨案例讨论
通过资源拼凑去回应制约,获取发展的优势不仅对于创业型组织来说是新的研究焦点,对乡村同样重要,关注弱势乡村如何在制约中实现创新发展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发现,乡村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创造性组合,可以使得同质性的资源产生异质性的结果[4],而创新的关键就在于拼凑的过程如何展开。为此,通过多案例的研究,探讨了四种不同贫乏型情境下的乡村资源拼凑行为的开展过程,以总结其共同点和差异性,如图6 所示。

图5 北墘村资源拼凑路径

图6 资源拼凑行为的理论模型构建
首先,从拼凑清单来看,四个案例所用资源在农村随处可见,如桃米用青蛙打造了主题文创;整个闽东地区均有酿酒传统,但黄酒文化节的平台,给北墘带来了更为重要的后续资源。除了现有内部资源利用,植入外部资源也是可取手段。妖怪村是妖怪文化和本地传说的深度融合;漈下村则是将油画植入乡村,并激发了弱势群体的创作热情。四个案例的共同点是通过对组织内外部易获得的物质、人力、文化和技能进行了重新组合。
其次,从拼凑活动来看,桃米村(Ⅰ型)采取了“社会网络+创新探索+角色多元”的拼凑活动。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平台为桃米和外界资源提供了对接渠道,并通过青蛙这一主题进行了创意探索。青蛙在桃米承担了多元角色,如生态教学的载体、文创的主题、建筑元素,同时,村民也具有多重角色。北墘村(Ⅳ型) 采用的是“社会网络+用途转化+主体多元”的拼凑活动。酿酒文化转化为黄酒文化节即为用途的转化,古民居的再开发也让闲置老宅产生价值转化,同时北墘村引来企业、高校等诸多资源,形成了多元共建主体的发展模式。妖怪村(Ⅱ型) 采用了“网络传播+创新探索+反客为主”的拼凑模式,妖怪文化的植入最先在网络发酵,带来了妖怪村“妖怪+传说”的故事演绎创新探索,并进一步带动了民宿、文创产品、体验活动的发展,从而反客为主成为溪头最重要的景点。漈下村(Ⅲ型)采用了“网络传播+用途转化+产业带动”的拼凑模式,同样农民创作成为网络热门话题的效应使大家主动了解漈下村,并带动了更多的艺术家、游客、学员来漈下创作,同时带动了漈下其他配套产业的发展。可见,对于资源利用型的乡村,横向连接资源是拼凑活动的共同之处,社会网络在资源利用型乡村起到关键作用。对于资源植入型的乡村,纵向延伸同一主题是共同之处,而网络传播能使得资源主题与外界良性互动。同时,Ⅰ、Ⅱ型乡村表现出了创意探索的过程共性,Ⅲ、Ⅳ型乡村则表现出用途转化的过程共性。
第三,从拼凑结果来看,以创意探索为主的拼凑活动通过“无中生有”的拼凑逻辑,产生了创意式的拼凑结果。以资源用途转化为主的拼凑活动,让原本闲置的、低价值的资源发挥了作用,是一种“无用之用”的拼凑逻辑,产生了转化式的拼凑结果。
(二)创新策略探讨
1. 重新审视乡村既有资源
过度地强调引入优势资源,不仅代价高昂,而且往往求之不得。这就需要乡村从现有的资源入手,如何让现有资源通过附加值更高的形式表现是拼凑的重点。在确定资源清单时,应该对资源的既有用途做扩展性的思考,不能忽视廉价资源,不对资源设限,重新审视资源用途是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创造性开发的前提。
2. 注重不同资源情境的分析,从实际出发选择创新方式
现有乡村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存在过度解读创新的现象。对于贫乏型乡村而言,一味追求高水平的创意、高水平的技术可能没有与之匹配的人财物,从而造成产业无法持续发展的现象。创新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考量。创新不仅包括高新技术对乡村资源的改造,同时对现有资源创意式思考,甚至是对现有资源用途的转化式利用也是一种创新。
3. 乡村资源的劣势往往也能创造优势
乡村以往的劣势也可能会成为后续发展的资源优势。以桃米村为例,其最初作为垃圾掩埋场,存在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但却发展为生态社区。其他三个案例也是把资源的短板通过一定的拼凑逻辑变为优势。劣势和短板更容易引起居民的关注和共鸣,促使更多居民参与,集思广义,从而将创新活动和乡村实际情况深度融合。
本研究结合资源拼凑的理论分析了乡村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拼凑行为及逻辑,以探索处于资源贫乏情境中的乡村应该如何破解资源难题。本研究的研究限制主要有,一是在案例的动态性方面有所欠缺,资源拼凑是一项延续性的活动,本研究在分析的过程中,侧重点在于资源情境和拼凑逻辑,对资源拼凑动态性展开的考虑有所不足,即不同阶段的组织,拼凑行为应该有所差异,这在后续研究中再做详细分析;二是资源拼凑的效果问题。资源拼凑行为在组织中是一个长期过程还是短期过渡,拼凑所形成的长期效果也是应该关注的焦点。如何界定拼凑效果,识别无效拼凑的模式,也是未来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