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有观念的当代艺术
王春辰
写札记,就是写下此刻的随感,记录当下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会有不一样的问题,遇到了就把它们记下来,供我们持续思考和回应。从事艺术行业,就需要面对各种艺术现象,去表达我们的意见,也需要将这些艺术现象整理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对象。
我在上一篇札记《艺术是一个问题》里,零零散散记下的那些情况和杂想,实际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对海外的了解和认知远远不够,不彻底、不深入、不切实际。用“海外”这个词是想指出中文语言的奥妙:我们说“西方”,指的是欧美,连日本都不包括。虽然从国际关系上看,欧美日是一体,但文化心理上,我们依然把日本当作近邻;而我们说“世界”,又特指发达国家。如果说我们向世界学习,恐怕指的还是欧美这样的西方。用“海外”这个词,就是要指出,除了西方世界,还有其他地区的世界;我们说“走向世界”,实际上是指走出国门、到达海外的任何地方,并不是只走向欧美。这在文化心理上,我们需要反省,如果不对东南亚、印度、中东有所了解,我们就无法全面认识世界的丰富性,总是以中西对比来看世界。比如,我们没有亚洲艺术博物馆、非洲艺术博物馆或南美艺术博物馆。我们对世界艺术的了解总是偏于欧美,甚至连近邻韩国、日本、印度、东南亚的当代艺术也没有多加了解,出版、研究相当少,甚至稀缺。
这样去看我们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可以探知我们的文化心理还是有“中华中心主义”,即便是中西比较,也是为了证明“中”的悠久辉煌和博大精深。当我们努力去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也应该反省一下“中华中心主义”;如果我们能热情地、认真地去研究印度、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当代艺术,我们就不会一味地认为“世界”对艺术的话语权那么值得迷信或畏惧;固然,西方拥有书写与阐释现代到当代艺术的话语权的先机,但话语权不等于唯一准则,而应注重自身的创新性和独特性。以身处中、西之外的视角去看世界,一定会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乃至趋同性。
比如,以“当代艺术”为例,韩国、东南亚都是以它作为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和交流话语,呈现的是一种开放的姿态和行动,这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姿态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他们都先后用“现当代美术馆”来命名他们的国家美术馆;而在我国,以“现代”“当代”命名官方美术馆的少之又少,这其实意味着在我们的内心里,对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仍然存疑,甚至存有很深的误解。对比一下,在东南亚以及其他非欧美国家,从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都是它们用以表征自己的现代身份和新的国家形象。那么,近代以来的中国不也是以“美术革命”来寻找自身的艺术身份吗?按理,这个追求和思路与建立共和是一脉相承的,与徐悲鸿等去欧洲学习的目的是一致的。这就是历史语境的道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对现代身份的追求与对传统的固守(或作为盾牌)都伴随着我们的艺术之路,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是在这两种心态和情绪里打摆。
在我们的共和追求的政治实践中,艺术也是以新的姿态参与其中,如写实手法与其艺术作品,这是革命最需要的一种艺术语言和形式。清王朝结束以来的中国处于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世界史来观看艺术史的发展和变化,必然是以追求艺术的现代化为目标的,也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但是,在中国,这一点却特殊了起来。这个结至今依然没有解开。本来,现代国家是最欢迎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的,而在我们这里,可能因为历史长久、古代艺术丰富、积累了太多可以用来玩味的东西,所以现代艺术还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文化意识,最具象征意味的,就是我们没有“中国现代美术馆”这样的命名。但是地方或民间却强烈地感受着现代和当代的锋芒与时代感,所以才有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银川当代美术馆”“民生现代美术馆”“成都当代美术馆”“山西当代美术馆”等。而在某些时候,我们仍然处于尴尬的境地。在很多官方的语言里,“当代艺术”似乎是一种禁忌,被某些意识困扰着。明明“当代艺术”是最具国际话语共性的一种称谓,但在我们这里的某些环节里却成了需要回避的事情。比如最近,一些出版社就对当代艺术的选题申报持谨慎态度。
综览当今世界,凡是经济繁荣、国力增长的地方,都是把当代艺术看作新的文化身份的体现和表征,但是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守,复古倒越来越流行甚至强势。整体地看,我们的现代化追求仍然不彻底,也没有完成。没有现代意识的现代艺术观和当代艺术观,意味着我们仍然在骨子里没有跟进世界历史的趋势。在追求现代化国家的早期,艺术的现代化与传统的艺术之间有着激烈的争论、争辩和对垒,但是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或者等到实现了现代化之时,现代艺术便应成为日常行为和常识。如果这时候艺术没有实现现代化,就意味着这样的现代化经济和国体是单边的、缺少多样性的。
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看一看,就是去欧美的国家,在它们的书店里,很少看到大量讨论传统艺术与当代艺术纠结的书,研究传统就研究传统,如文艺复兴,无须惊慌这样的传统丢失或黯淡;研究当代艺术就研究当代艺术,大张旗鼓地写作、饱满地出版。在泰特美术馆、MoMA、白教堂美术馆等的书店里,你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现当代艺术的书籍,铺天盖地,论题新颖、多方涉及,而且每次去这些书店,都会发现又有一批新书已经出版了。我们自己很多研究传统的书籍,就只谈传统艺术,非常好,也耐看,但一说到当代艺术就非要对立起来。当代艺术自然有很多东西来自传统,但和传统艺术有着非常鲜明的创作态度与观念的差异。忽视这种差異就很可能消解了当代艺术的意义,也使得我们的意识总是以传统为正统、道统,食古不化。
应该是,在保持传统的同时,让“当代艺术”发展当代艺术,两不误。因为在今天,更多的群体是青年、是未来、是创想新科技与新文化的一代,他们不可能绕开“当代艺术”这个世界共同意识。英国艺术批评家彼得·奥斯波恩(Peter Osborne)在他2018年的新书《后观念状态》中谈到“当代艺术是浓缩了大量各种社会的与历史的力量、经济的与政治的形式以及图像生产的多种技术的东西”,它大量运用它们作为艺术材料和主题,从它们的日常功能中来发掘它们的力量,然后使之焕然一新。一般来讲,人们多从经济上讨论全球化,但是如果从当代艺术的全球化现象去看,则将是用另一种视角来解读世界的全球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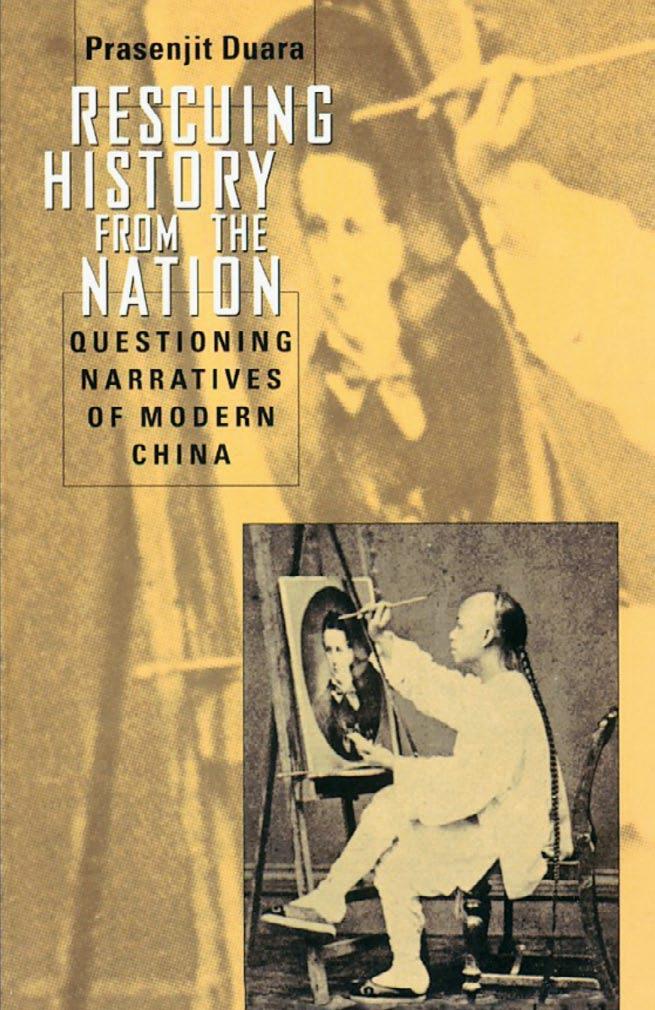
历史上,伴随着战争、冲突、攻城略地,族裔、族群、部落、城邦、朝代、王朝都相继更迭、消亡或变化;一面是冲突,一面又是贸易交往,其中包含各自文化的互相交流。我们今天看到的各国家民族的不同文化,也都有着历史上的交流和彼此吸收,这些都被大量研究证实,也有实物、文献佐证。历史上这种文化的交流也并非都那么顺畅,也有冲突,如“十字军东征”就是文化宗教观念的冲突所致;中国历史上的多次灭佛,也是为维护当时的王朝正统思想才发生的。但是今天的全球化大大地异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这是各个国家、族群、文化体、宗教体都在思考、讨论、应对的问题。全球化发生了,看似不可逆转,但是对全球化的反对、抵制还是大量存在的,因此也波及“当代艺术”及其“艺术史”这一现象。美国学者埃尔金斯(James Elkins)在2007年主编了一本书《艺术史是全球化的吗?》,这是他于2005年在爱尔兰组织的一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讨论、点评的合集。它探讨了当下国际上各个国家所开展的艺术史研究与教学的情况,由此可见诸多问题。可以说,艺术各个地方都有,但艺术史的研究和教学不一定都有,即便有,很多也是套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教材来教学。这也是全球后殖民主义所要做的工作,不消除欧美中心主义,就无法实现多元化。但另一方面,面对欧美已经发生的艺术史研究方法及其叙事要不要学习、吸取?这是从研究的学科角度去思考问题的。那么从艺术实践的角度,我们又清清楚楚地看到全球都在开展一种全球化的艺术,彼此不再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或传统艺术特征,而是呈现了一种共同的艺术手法或观念意图。这也是人们经常诟病的一个原因:这些艺术看不出是哪种文化身份做的,从欧美到亚洲到非洲,从装置、录像、行为、新媒体到绘画,都是这么做的。面对这种现象,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提出了“全球艺术”这个概念,试图勾勒出一种全球化时代下的艺术的共性特征及文化特征。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也是这种倾向的创作,不仅是留学海外的青年艺术家们,本国毕业的大批艺术家也有这种现象和倾向,因为他们都是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学习艺术,他们得到的艺术资讯也都是全球化传播的结果。
由此可知,经济的全球化已经带来了文化与艺术的全球化,对于很多缺少历史的文化文献、遗产资源积累的地区来说,一下子拥抱当代艺术是非常简便高效的全球化艺术诉求。而在中国,情况就非常复杂了:一是我们拥有历史很长的艺术积累和成就,有自成一体的美学理论,它让古人迷恋,也让今人喜爱;二是近代以来,中国(清朝)和西方的关系是对抗性的关系,使得今天的我们总会泛起敌对西方的心理、心态,甚至姿态。本来,对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我们今天的经济模式与方法也正是西方做过的事情,而与之对应的现代艺术及当代艺术也是相应的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这样做,虽然过程中磕磕碰碰。但到了今天,基本上,我们在艺术的现代化理解上和学科的建制上都直追欧美,甚至不乏创新。但是也要看到,在很多的深层认识上,依然有偏颇。如艺术要不要观念化,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是否有绝对化倾向,为什么意识形态化一直缠绕在当代艺术(乃至西方理论)的认知上。
其实,大国崛起显示的是文化自信,“自信”二字意味着取用自由、兼容并蓄、处变不惊。从前,我们用了那么大的力气和时间,将写实艺术语言融入中国的艺术中,同样,对于今天以藝术为一种观念的呈现的时候,同样需要我们用些力气,去做足功课。10年前,我翻译了一本书要出版,多次校改,直至前两年又过了一遍,但是这一次却是大篇幅地删减,甚至有一章都去掉。对此,我也无奈,固然我们理解这种情况,但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心理还是很脆弱的,弱到对文字感到惊诧。
再展望未来一下,我们的艺术需要做的依然是吸收与创新并举,不要沉湎在过去的幻觉中。
责任编辑:孟 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