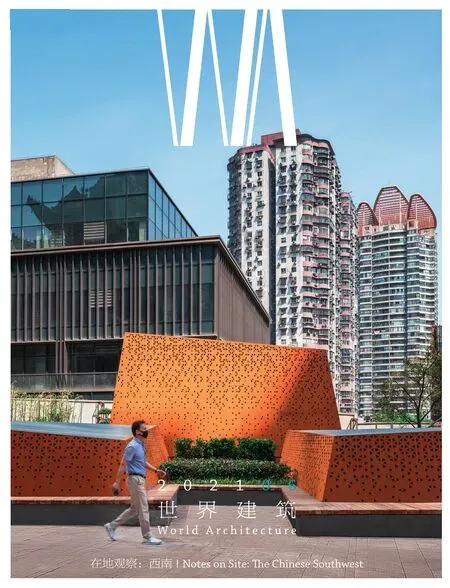分割与连接
——城市再生视野下的山地城市公共空间重塑,以重庆主城区为例
卢峰,王振文,陶陶/LU Feng,WANG Zhenwen,TAO Tao
1 山地城市公共空间面临的诸多挑战
长期以来,多中心、组团式紧凑发展,是山地城市适应特定山地条件的主要发展模式,而各组团中心区,既是其经济、产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空间,也是现阶段城市更新改造的重点和难点。以重庆为例,自直辖以来,各组团中心区的开发强度不断增大,呈现出高密度的城市历史肌理区域与高强度的点状再开发区域相互交织,城市轮廓线由簇群状的“图底关系”向自然与人工形态间插的方向转变等特点[1]。
在山地城市中心区,受建成环境的制约,已难以开展大规模的改造或再开发建设,以街区为主要尺度的局部性、渐进式更新模式将成为未来发展常态。2010 年以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城市双修”理念的提出,均将城市存量资源的再开发利用作为推动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此背景下,为适应动态、复杂的山地城市中心区发展变化,客观上要求城市设计在拓展现有的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要创新城市空间发展引导机制。而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景观多样性与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及对高端人才、高附加值产业吸引力的核心要素。因此,营造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具有良好生活氛围和归属感的城市环境,是城市适应未来发展的必备特质之一。
从国内外城市更新研究与实践的发展态势来看,城市再生理论及其策略与方法,由于更加强调基于城市存量资源的城市物质环境改造与城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城市改善老城环境、振兴城市经济、恢复社区活力的主要选择,也为山地城市中心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与城市更新概念相比,城市再生特别强调了对城市原有物质环境的再利用、原有经济功能的再提升和原有社区的再发展,而不是通过空间扩张、城市物质结构拆除和重建、原有居民的迁移等“置换”措施来消除城市的衰败空间。因此,城市再生是一种“零用地增长”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即在维持城市现有物质空间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经济社会职能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更注重对城市文化历史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2]。而城市公共空间所具有的与城市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也成为彰显城市文化特色的重要物质载体,并成为地域性城市设计的主要关注焦点[3]。
受地形条件、开发时序、既存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重庆建成区的城市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场地碎片化、景观可识别性弱、可达性不足、可停留性差、功能单一等问题。而经过近20 年的高强度开发,山地城市中心区的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其长期演变形成的山水城相融的景观空间格局正面临诸多挑战:
(1)间插式、高强度、大街区的综合体开发模式,显著改变了原有城市肌理以及多层次的城市景观体系,而大量老旧社区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基础设施滞后等突出问题,导致城市空间形态碎片化与公共空间活力的丧失;
(2)城市中心区大量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的旧街区、旧建筑,在快速开发进程中逐渐消失,尤其是重庆开埠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批重要标志性建筑的消失,形成了明显的近现代历史断层,城市特色丧失严重;
(3)城市中心区经济功能和开发容量的不断提升,使交通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山地城市普遍存在路网密度低、连通性差等结构性问题而建设的高架道路设施,对城市整体景观和公共空间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4)城市滨水空间受滨江快速干道影响,普遍存在建筑形态与功能单一、可达性差、开放性不足、与城市腹地联系不足等问题,没有有效发挥城市开放空间的作用(图1)。

1 重庆主城区滨水空间现状
为此,需要围绕紧凑型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区域性的实地调研找出现存城市消极空间的分布和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三维复杂城市空间的城市设计与建筑景观一体化设计,将分散割裂的碎片化城市空间进行资源优化与整合,提高其与城市交通空间、大型城市综合体内部空间、商业街区等不同层次城市公共空间节点的连接性,进一步密切其与市民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所的步行联系,同时通过定期举办有特色的公共活动和社区活动,提升市民对城市空间的体验感和获得感,从而真正构建起具有山地特色和人文内涵的宜人城市环境。
2 与城市微更新相呼应,构建具有山地特色的微型公园体系
高密度的山地城市建成区域,很难在城市中心区形成相对集中、边界清晰、规模适当的城市绿地或开放空间,一方面,高强度建设所造成的巨大建筑体量和绿色景观要素的缺乏,造成了城市空间认知失序和人们视觉景观的封闭感,进而导致心理上的压抑感,而大量在城市中心区生活、工作、游览的人群,由于缺少必要的休憩、交流、停留空间以及可以辨析的城市景观节点,往往容易在复杂三维的城市空间中迷失方向,也无法构建起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整体意向;另一方面,由于开发建设周期的差异和复杂的地形条件,在山地城市中心区存在大量分散的、因地形高差和开发边界的不规则性所导致的城市边角空间,其空间形态的随机性、灵活性与多变性,是山地城市空间与地方文化特色的一种体现,但由于缺少针对性的设计、管理与维护,在现实中常常沦为消极空间。为此,可以借鉴美国纽约、费城等城市的口袋公园(pocket parks)建设经验[4],将这些不规则的边角空间从城市消极空间转化为支撑城市日常生活、提升社区活力的积极空间,让市民和外来游客都可以通过其独特的空间使用体验,逐渐建立对山城地方特色的日常经验与身体感知,最终转化为城市集体记忆和特色城市文化认知的一部分。
利用不同城市开发地块边界的剩余用地因地制宜地建设城市微型公园,具有建设投资少、见效快、贴近城市生活、使用便利等特点,是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活力的一个有效手段,也有助于形成与山水自然地景相呼应的、特色突出的城市日常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当代城市文化特色。为了提高微型公园使用的包容性与开放性,需要解决好场地高差处理、多功能使用分区以及各分散场地的体系化连接等问题;从现场调研来看,山地城市的微型公园往往依据地形条件和立体步行体系,形成平行与垂直等高线的两种条状形态;平行等高线的条状微型公园多处于地形高差变化较大的位置,且与水平步行路径紧密结合,具有边界轮廓不规整、分布分散、侧向景观视野较好等特点,由于用地狭窄,多采用硬质铺地结合乔木、休息座椅的布置方式(图2a);垂直等高线的条状微型公园往往与立体步行系统结合,利用不同标高的不规则台地因地制宜地构建休息、健身、观景等空间,形成具有多维视面的立体景观体系(图2b)。

2 重庆渝中区人民公园
微型公园不仅可以明显改善高密度建成区域生硬、冷漠的城市面貌,而且可为置身其中的人们提供一个就近使用的交流休憩空间,进而成为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活力、促进城市再生的一个重要途经。如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学田湾社区,结合老旧社区建筑修缮,对住区的边坡、内部小院、室外踏步等边角空间进行改造,不仅显著改善了住区环境,而且通过增设服务设施、打造居民与游客共享的特色观景平台等措施,进一步提高了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图3)。

3 重庆上清寺街道嘉西村观景平台
3 以延续城市文脉为目标,构建具有历史记忆的山地城市街道空间体系
近几年,重庆作为世界上城市规模最大的高密度山地城市,以其多层次的立体城市风貌、独特的近现代发展历程、平民化的城市日常生活以及丰富的城市空间体验,成为受到诸多影视作品拍摄和网络传媒青睐的“网红”城市。然而除了洪崖洞、轻轨穿楼、磁器口等几个网红景点以外,散布于整个老城区、能真正体现重庆城市发展深厚历史积淀和人文特色的诸多文化景观,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与彰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高强度、大规模的城市再开发过程中,老城区内随地形转折的特色街道空间和小尺度的街区格局遭到严重损坏,以步行为主要功能的街道体系逐渐被快速交通所代替,导致依赖小尺度街区的日常生活服务设施以及手工艺店、主题书店、小型剧场、古董市场等特色文化设施失去了其存在的社区与市场基础,被单一的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所代替;另一方面,老城区传统街区内往往遗存了许多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建筑文化艺术价值的历史建筑,以及失去原有功能的近代产业建筑。这些建筑是城市历史记忆和城市肌理的重要构成单元,但由于缺少与城市公共空间、特别是城市街道空间的直接联系,大部分混杂在破败的城市环境中,彼此相互孤立,与城市日常生活缺少关联性,无法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空间资源转化为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特色资源。因此,可以借鉴美国波士顿“自由足迹”的建设经验,将历史建筑保护再利用与城市特色景观塑造结合起来,同时嵌入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与服务功能,构建以历史建筑与特定场景为核心的城市文化线路以及相应的公共空间体系[5]。
重庆主城区滨江两岸自开埠以来,逐渐形成了多个以码头为核心的历史街区,如渝中半岛的湖广会馆片区、长江南岸租界区和领事馆区的近代建筑群、嘉陵江畔的磁器口历史文化街区等,这些历史街区往往位于地势复杂的江岸台地上,经过长期演变形成了立体、复合、层次丰富的城市整体风貌,具有突出的历史与在地景观价值。为此,为了进一步突出这些历史街区的风貌特色,需要以立体街道为主体,构建山地城市文化景观线路,垂直等高线的立体街道网络,不仅可为历史建筑提供更好的展示空间,而且将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不同标高的历史建筑与场所通过多层次的立体步行体系串联起来,从而为市民和游客构建连续的、具有体验感的城市历史与文化认知地图,而历史建筑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景观要素,也提高了其可识别性与文化意涵。如重庆南岸龙门浩历史街区片区,结合历史建筑再利用与传统街区整治,将开放街区建设、历史建筑改造再利用、新的服务功能植入与垂直等高线的立体街巷空间和周边环境改造同步进行,形成了多个兼具地域特征与文化功能的景观节点,成为城市中新的文化名片(图4)。

4 重庆南岸区龙门浩老街(绘制:王振文)
4 依托多层次立体步行体系,激发山地城市滨水空间活力
近20 年来,山地城市滨水区域在“退二进三”政策的推动下,由传统的产业和运输空间向城市生活空间转变,成为改善城市景观品质、展示城市整体风貌、提升城市活力的重点区域。为了解决山地滨水区域长期存在的消落带问题,同时争取更多的滨江开发用地,目前主城区普遍采用路堤结合的滨江路建设方式,不仅显著改变了滨水区域的自然岸线,而且其快速交通功能成为阻断城市腹地与滨水区域步行连接的主要障碍,使滨水空间这一山地城市中最重要的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被滨江快速干道切割成相互隔绝的条状消极空间,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图5)。因此,为了加强不同标高的城市公共空间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与滨水空间的联系,可以借鉴香港、西雅图等滨水城市的立体步道体系建设经验[6],依托轨道站点等公共交通枢纽,形成由室外踏步、自动扶梯以及山地城市特有的垂直电梯、缆车、过江索道等不同交通形式构成的复合交通体系,同时在城市滨水区域的主要景观节点上,构建跨越城市滨江道路的步行平台或步行广场,形成从城市山顶到滨水岸线连续的步行通道与景观通廊[7],并利用场地的天然高差和特殊地形地貌构建不同方向的远景眺望点,形成彰显城市特色、可包容多种城市活动的立体步行景观体系。

5 重庆渝中区李子坝段滨水空间(1-3,5图片来源: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可达性与亲水性是提升山地城市滨水区域活力的主要途经,也是其景观设计与建设的难点,关键是要在滨江机动交通道路的外侧创造具有亲水性和远眺景观的公共活动平台和体验性的步行空间,为此,需要从场地剖面分析入手,依据不同的滨水活动需求,构建立体的滨江景观网络:
(1)利用场地的自然高差,构建跨越滨江交通干道的步行和景观平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分流,大幅提升滨水区域的可达性;
(2)消除原有的多个孤立建设项目的场地边界,将封闭、消极的边界空间转化为开放的共享城市空间;
(3)考虑到山地滨水空间的消落带变化较大,设置与不同季节的常年水位高程相对应的滨江步道和亲水空间,越临近水体(江面),越突出其岸线的生态特征和自然属性,形成从城市腹地到滨水空间、由人工向自然逐渐过渡的景观层级(图6);

6 与不同水位线相对应的景观分台设计示意(绘制:王振文)
如位于重庆市南岸区滨江区域的长嘉汇购物公园,结合跨越滨江路的坡地景观公园建设,形成了多层次面向江面的城市观景平台,同时,较好地解决了车行道阻碍滨江可达性的问题(图7),其临近江岸的区域,根据不同的常年水位高程设置了兼具防洪和景观功能的坡地景观和步行道,将平行滨水岸线步行体系与垂直等高线的步行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

7 重庆南岸区长嘉汇段滨水公园设计剖面(改绘:王振文,底图由香港梁黄顾建筑师事务所高方明建筑师提供)
5 加强山地公共空间景观体系建构
从城市网络的角度来看,城市的物质空间要素可以理解为:节点-路径-体系的结构关系,在不同尺度、不同层级之间的连接体系间遵循一种严格的秩序:从最小的尺度开始(步行路径),逐渐发展到更高等级的尺度(车行路径)[8]。在这样一种多层级的网络结构中,每一个微型公园、每一栋历史建筑与场所、每一处滨水空间都是市民活动的节点。物质性的城市网络,如步行路径、车行道路、轨道交通等将这些节点彼此连接起来。在实际利用过程中,用于连接各个节点的网络联系越强,其可达性越高,使用率越大,城市越有活力。因此,除了考虑场地周边的步行可达性之外,还要考虑其在整个城市网络中的拓扑关系。在建设时序上,车行及轨道交通覆盖范围内的公共空间节点可以优先考虑,以便发挥其“触媒”效应,带动周边公共空间的微更新。
除了借助物质交通网络的连接,加强山地城市公共空间景观体系的联系之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媒体平台等非物质手段构建市民的城市“认知地图”。通过环境行为的人为干预,建立人与物的空间关联。
6 结语
在高密度的城市建设环境下,公共空间的景观重塑成为促进山地城市再生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其中,可达性、可体验性、可停留性、功能的包容性和日常性,以及景观的多样性、体系化和特色彰显,是山地城市公共空间景观重塑的要点和难点。为了构建多层次、多功能、一体化的山地城市公共空间体系,需要整合城市建设、市政、园林、交通、航运等不同领域的城市公共资源。为此,一方面需要反思现有的以单一地块用地红线为核心的二维城市规划管理模式,从整合城市公共空间资源、构建一体化山地城市景观的角度,明确城市边坡空间、边缘空间、桥下空间、防护绿地等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形成的封闭空间的产权使用和管理归属,并针对这些特定的城市空间形态制定相应的管理与引导措施,使之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公共空间体系,以缓解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山地城市中心区对公共空间和宜人城市景观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打破不同城市管理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通过管理制度和机制创新,借助中微观层面的城市设计,深入挖掘各用地边界之间剩余城市空间的生态和景观价值,同时通过构建全方位的公众参与平台,使城市再生过程真正成为凝聚社会共识、振兴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归属感的重要平台,并由此构建“以人为本”的山地宜居城市[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