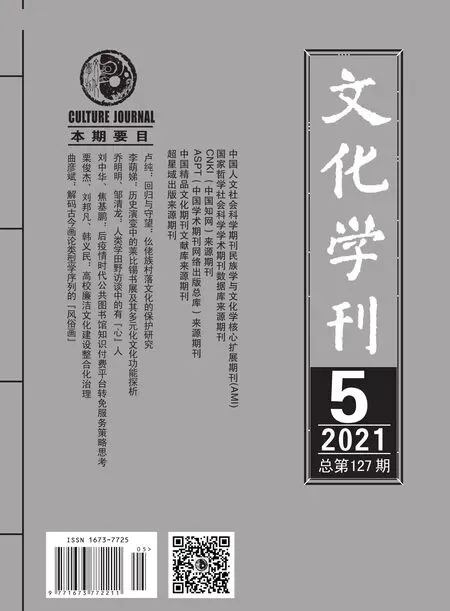解码古今画论类型学序列的“风俗画”
曲彦斌
在哲学意义上,中国的类型学观念至少有三个应予关注的节点,一是“类”,二是“属”,三是“体”。汉字“类”的初义为犬种之别。《说文解字》:“类,种类相似,唯犬为甚。从犬、頪声。”汉字“属”的初义,通指一些社会事象的分别。《说文解字》:“属,连也。从尾、蜀声。”《说文段注》:“连者,负车也。今字以为联字。属,今韵分之欲市玉二切。其义实通也。凡异而同者曰属。郑注司徒序官云。州党族闾比者,乡之属别。注司市云。介次市亭之属别小者也。凡言属而别在其中。如秔曰稻属,秏曰稻属是也。言别而属在其中。如稗曰禾别是也。从尾。取尾之连于体也。蜀声。之欲切。三部。今作属。”汉语的“体”,由人类“身体”的初义,逐渐引申为本质、法式、准则、规矩等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体”制“礼”,以“体”为绳施行“礼治”。分别品类的目的,在于“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
考之将文体比之于人体形质体相的形成轨迹,同样源于对《说文解字》关于“体”本义的引申解读路径。追溯汉字“体”的本义,《说文》谓:“體,总十二属也。”《说文段注》注云:“十二属者:顶、面、颐,首属三;肩、脊、臀,身属三;肱、臂、手,手属三;股、胫、足,足属三也。”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云:“十二属,谓十二经络也。”总十二属者,十二类属也。在此引申意义上,“体”是一种类别现象。作为类别现象,汉语所谓的“文体”,是个比较模糊而且很宽泛的概念。
“体态”的意义,既指人体的姿态、样子,亦泛指其他物体或现象的形态。可以说,汉语的“文体”是一个“大小由之”的业已用来泛指多种层面文化形态的概念。例如,《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亦即“通五经贯六艺”之“六艺”,是一种国家层面文化形态的类型概念。色彩形态的七种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勘谓一种色彩视觉层面文化形态的类型概念。味觉形态,酸、甜、苦、辣、咸、香、臭,勘谓一种味觉或嗅觉层面文化形态的类型概念。市井社会“五行八作”,作为职事行业分工,则属于社会文化形态的类型。各种各样的“体”(类),无不基于相应的形态类型文本的“体态”而存在。
考之“文体”应用场域的各种解读,主要还是用指书面的、以文学文体为主要文本的概念。文学的文体,是以其语言表达的样式之特色而存在的类别现象。书面的文学的文体,亦包含着诗词歌赋吟诵、吟唱等是有声的文体形式。因而,戏曲文体,尽管是有声的文体,但其戏文文本仍属文学性的文字。这样,戏曲学家在考察戏曲文体特征时,往往需要关注到与考察诗、词、文、赋既相同但又相异的方法与角度。绘画文体,是视觉艺术为本位的文体。由于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1)宋·苏轼《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境界的绘画理念,同样要关注到多种传统文学体裁和题材的意境与题旨情趣。凡此种种,“风俗画”画论与艺术实践,并非置身于“三界外”,尽在其中。“风俗画”之“体”或说“科”“风俗画”所在序列及其所属各体,均属于不同层面的类别现象;或言之,主要是以其绘画艺术语言表达的题旨情趣亦即题材而存在的类别现象。
一、确定“风俗图”类属的前提:本质特征
确定“风俗图”类属的前提,是其本质特征。那么“风俗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考察如今被视为“风俗画”的历代作品,我们看到,“风俗画”的绘画形式、工具、载体材质、技艺等必备的基础要素,与其他画种都是共同的。例如,呈现的形式,均属平面画,包括圆、弯等形状载体经处理展开后仍可视为平面的画;载体材料,举凡石(含玉石)、绢、帛、砖、纸、木、漆、陶瓷、金属乃至玻璃等,均可;常用绘制工具,有石(刻),刀,笔,颜料等;色彩不拘,可彩色,可黑白色,亦可载体材质原色;绘制方法,有刻、画、涂抹、雕(不含雕塑)、指绘(指画)、蜡染、剪纸(刻纸)乃至手撕等;作为体材类型,国画、版画、砖画、壁画、烟画、水彩画、白描画、漫画(含涂鸦),等等,大都属于绘制技法范畴。
除了作为“画”的绘画形式、工具、载体材质、技艺和题材等必备的基础要素之外,“风俗画”,之与各种绘画作品“与众不同”的最主要区别,在于“题材”。或言之,作为“题材”核心点的“风俗”,是“风俗画”作为“画”的本质特征。绘画的题材与文学的题材的一个共同点,均为其社会性所制约的属性。因而,以题材而论的“风俗画”的本质特征,亦正是其社会性属性所在。反言之,题材的社会性属性决定了风俗画的本质特征。或可言之,“风俗画”本质特征最核心的关键词是“风俗”。英国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在论述尼德兰风俗画时谈到,“画家有意识地画一些画来发展某一分支的题材或某一种类的题材,特别是日常生活场景,这种画后来就叫作风俗画”[1]。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6册)所言,风俗画是“以题材划分的绘画类别名称,指以人物为中心展现世俗风物为题材的绘画门类”,即很是切合其题材的本质特征。
“风俗”亦即民俗,是人类社会长时期相沿积久而形成的习俗惯制、礼仪、信仰、风尚等民间文化传承现象的总和,是经群体或社会约定俗成并流行、传承的民间文化模式,是规范个体行为、社会秩序和调解社会心理的非主导性生活模式。民俗作为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样式的复合模式,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社会文明进程的基本要素,具有对社会生活的制衡与调控功能。
简言之,风俗即民间风俗习惯,是人类社会长时期相沿积久而形成的习俗惯制、礼仪、信仰、风尚等民间文化传承现象。
古代画论通常将“风俗画”归类于以社会生活风习为题材的人物画,似乎失之于不够完整。“风俗画”的题材类型:人物,历史,宗教(神话),仪式(人生礼仪),风物(地方特有的景物),民间传说,年画,民俗器物画(如茶具、博具、玩具、消寒图、耕织工具、市井招幌等世俗生活日用器物)以及“涂鸦”等。
风俗画,是以表现人在特定民俗场景情境的活动,各种民俗事象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勘谓民俗活动“道具”的民俗器物(如“器物谱”和关于特定器物的故实掌故等)为题材和题旨情趣的绘画。作为绘画语言艺术的风俗画,是以绘画或刻写的图画语言创制的以风俗画为载体和艺术形式的语言民俗景观。
中国的风俗画,滥觞于岩画、彩陶画、绢帛画三个源头,三个递近的开先河历史时期,以绘画、版画为主体形式,以唐宋元明清为成熟和高峰期,至近现代得以普及。
二、从韩滉及其“风俗图”说起:寻迹探析中国画类型学轨迹
唐代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著录的南朝画家顾宝光的《越中风俗图》,是迄今历史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风俗图”之说。或言之,仅就画题用语而言,其言语所表达的中国“风俗画”意识,至少可以追溯至南北朝时期。
为什么从韩滉(见图1)说起?两个缘由。一是,韩滉是中国风俗画成熟期的主要画家,且后世评述其画时,再次使用了“风俗图”之说。

图1 唐·郑国公韩滉像
新旧《唐书》的韩滉传,皆未及韩滉画事,无由否其原有的题旨例则。但是,亦不能因此而否定韩滉在中国绘画史上作为一代卓有成就的画家这一历史事实。史实所据至少有二: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妙品上八人》,宋人《宣和画谱》卷七《人物》,二者中关于韩滉画事的记述。而且,两者评价甚高。如《唐朝名画录·妙品上八人》:
韩滉,德宗朝宰相。当建中末,值兹丧乱,遂兼统六道节制,出为镇海军、江浙东西兼荆湖洪鄂等道节度使、中书令、晋国公。按《唐书》:“公天纵聪明,神干正直,出入显重,周旋令猷,出律严肃,万里无虞。”然尝以公退之暇,雅爱丹青,词高格逸,在僧繇、子云之上。又学书与画,画则师于陆,书则师于张;画体生成之踪,书合自然之理。时车驾南狩,征天下兵。虽两浙兴师,劳心计,而六法之妙,无逃笔精。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议者谓驴牛虽目前之畜,状最难图也,惟晋公於此工之,能绝其妙。人间图轴,往往有之,或得其纸本者,其画亦薛少保之比,居妙品之上也。
继《贞观公私画史》的著录之后,古代画论还出现了一个类似“风俗画”的说法,叫作“风俗图”。此即宋《宣和画谱》卷七《人物二》中关于韩滉画事的记述。由于后面还将言及,且迻录如下:
韩滉,字太冲,官止捡挍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退食之暇,好鼔琴,书得张颠笔法,画与宗人韩干相埒。其画人物、牛马尤工。昔人以谓牛马目前近习,状最难似,滉落笔絶人,然世罕得之。盖滉尝自言:“不能定笔,不可论书画。”以非急务,故自晦不传于人。今御府所藏三十有六:李徳裕见客图一,七才图一,才子图二,孝行图二,醉学士图一,田家风俗图一,田家移居图一,髙士图一,村社图一,丰稔图三,村社醉散图一,风雨僧图一,逸人图一,尧民击壤图二,醉客图一,潇湘逢故人图一,村夫子移居图一,村童戏蚁图一,雪猎图一,渔父图一,集社斗牛图二,归牧图五,古岸鸣牛图一,乳牛图三。
而且,历代诗文亦可见载类似事迹。如宋人蔡肇《大港即事次韵》其一:“村落家家有酒沽,黄童白叟醉相扶。恨无韩滉丹青手,更作丰年几幅图。”元人苏伯达认为,“晋国公韩太冲所画”《田家风俗图》,“神气迥出,笔不停毫,真得探微一笔之妙。历唐以来出探微之右者其太冲耶!虽张僧繇、展子虔亦奚过焉”。明代杨荣《题韩滉田家移居图》:“平生称善画,笔法真能工。值兹多难馀,出镇观民风。公退展毫素,天机发心胸。偶为田家图,情态谁能同。策蹇仍跨牛,前行忽匆匆。萧然村野姿,有此媪与翁。”至清,又有弘历《题韩滉丰稔图真迹》:“开元贤相有肖子,书传张旭画孙繇。老笔萧萧写村牧,不异丙吉问喘牛。”
凡此,这些记述所著录的身为一代名相兼著名画家韩滉的这些绘画作品,大多属于现代美术学视野的“风俗画”界域。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具有官修色彩的《宣和画谱》中,首见“风俗图”之说。
历史文献记载韩滉创作了很多画作,可惜罕有传世。除《五牛图》外,即或有清代乾隆皇帝题诗题识的《题韩滉田家风俗图用旧题者韵》(九首)和《田家风俗图识语》(见图2)两段题记,真伪尚属存疑。弘历题诗题识的所谓“田家风俗图”之谓并非画题名称,疑似为其就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丰稔图》内容的概括性说法,并非画题。

图2 清·乾隆年间 御批唐·韩滉《田家风俗图》识语
通过中外画论比较研究,有绘画学专家在讨论“画体的内涵与创造”时提出,“画体是画家经过画法实践后最终完成的、可见的作品的体态;它是画意的定态寄托,是画法的物化成品;也是画家与观众进行精神交流的具体媒介,并标志着作者的风格面貌。故画体的意义也有两层:一是具体的作品体态,二是画家的风格体态”。“画体体现着作者的具体感受、构思、技巧,同时也体现着作者的风格特色。成熟的画家每件作品都各具形态,而所有作品又有总的统一形态,具有明显独特的作风,自成一家之体。”[2]显然,如此以作品本身及其风格“体态”的“画体”,尚非直指传统画论以“画科”为说的类型学。
“风俗画”之说,是现代美术画论的术语。顾名思义,是描绘“风俗”的画。“风俗画”题材源远流长,但其在传统画论尤其是“画科”分类中,受关注却较晚。
中国画的“画科”思想,是基于习画、识画和赏画观念的,以题材为本位的“画体”类型学分野。例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分六门:即人物、屋宇、山水、鞍马、鬼神、花鸟;北宋《宣和画谱》分十门,即道释门、人物门、宫室门、番族门、龙鱼门、山水门、畜兽门、花鸟门、墨竹门、蔬菜门;南宋邓椿《画继》所分八类(门),即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元代汤垕《画鉴》的“世俗立画家十三科,山水打头,界画打底”;明代陶宗仪《辍耕录》所说佛菩萨相、玉帝君王道相、金刚鬼神罗汉圣僧、风云龙虎、宿世人物、全境山林、花竹翎毛、野骡走兽、人间动用、界画楼台、一切傍生、耕种机织、雕青嵌绿等“画家十三科”。凡此种种,“风俗画”皆不在其列。
三、画论类型学视野的“风俗画”
现代绘画学按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类别。例如,按使用工具与材料可分为中国画、油画、版画、水粉画、水彩画、铅笔画、木炭画、钢笔画等;按所描绘的对象和表现的内容可分为宗教画、历史画、军事画、风俗画、人物画、肖像画、人体画、风景画、静物画等;按其功能用途,则可分为年画、宣传画、电影广告画、商业广告画、电影动画、装饰画、建筑画、服装画、书籍插图、漫画乃至舞台美术和电影美术绘画。
美术界通常把“风俗画”归类于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三大画科”中的“人物画”,这并非切合事实。因为,风俗画不仅仅表现人物的民俗活动,还包括民俗事象的特定场景情境,以及与之关联密切的勘谓民俗活动“道具”的民俗器物,如“器物谱”和关于特定器物的故实掌故等,是以表现民俗生活内容为题旨情趣的绘画作品。
“传统中国画是根据所描绘对象、题材、内容的不同,将绘画分成若干个科类的。”[3]有人曾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潮流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全面性、定位精准的发展,风俗画成为一个独立画科的专门研究趋势亦更为明显。因此,必须从各种可能的研究方向中汇整出一个系统,使得中国古代的风俗性水墨绘画能够具备有效的理论信度。”[4]20世纪30年代,有的画史学家曾使用过“画门”分类法[5],但仍未跳出以往窠臼。那么,画论类型学序列的“风俗画”应当是一个怎样的类属呢?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曹丕《典论·论文》)文有“文体”,字有“字体”,史书有“史体”(如“通史体”“断代体”“专门史体”等),画亦当有“画体”。辨析“风俗画”所在层面之“体”及其“体性”,方可不“失本体”(借用“杂纂”语)。张彦远《论画体工用拓写》中并未阐述“画体”这个命题。“画体”或是画的“品类”分别。或说是“品”之“类别”,因“品格”而区分的“类别”。“品格”,亦即“品性”(指品质的性格和特征,其中“品质”即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事物存在的根据),区别于其他的特别“品性”。以往的画论,对“风俗画”的界定一向语焉不详。关键在于,时至今日“风俗画”未“入流”古今画论类型学序列,基于画坛画史事实,需要让其“入列”,这样才有利于画坛画史的有序。当然,也有益于“风俗画”画论研究和推进其发展。这是古今画论亟待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应予以关注的话题。
因此,风俗画的类属,主要是根据风俗画题材的本质特征,基于人类学、社会文化学视野的分类。如有学者谈到的,“风俗画是以表现社会生活风习而获得独立的一个画种。受社会生活习俗特殊性的制约,风俗画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艺术品格与审美取向。民俗风习的集体性决定了风俗画的通俗化特点;民俗活动的程序性决定了风俗画的情节性特点;社会生活风习的丰富性决定了风俗画形式语言的多样化特点;民俗事象的主体决定了风俗画人的主体性特点。基于民俗学视域研究风俗画,可以丰富风俗画的理论建设,活跃风俗画的创作实践,促进风俗画健康良性发展”[6]。
基于风俗画的本质特征,并综合之前所言及的多种绘画分类,若将风俗画纳入绘画类型学序列的话,与“风俗画”处于同一层面的按题材类型分类的绘画类别即为:人物画(如仕女画,像赞),人体画(如春宫画),肖像画(如写真),风景画(如山水风光),动物画(如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汉王元昌善画马,笔踪妙绝,后无人见。画鹰鹘、雉兔见在人间,佳手降叹矣。江都王善画雀蝉、驴子,应制明皇《潞府十九瑞应图》,实造神极妙。嗣滕王善画蜂蝉、燕雀、驴子、水牛,曾见一本,能巧之外,曲尽情理,未敢定其品格。”亦包括唐韩滉《五牛图》),植物画(如松梅兰竹,《出水芙蓉图》),花鸟画(如明王渊《花竹禽雀图》),历史画(如《帝鉴图说》),军事画(如清宫廷画家金昆等奉命所绘的《八旗阅阵图》郎世宁《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静物画(文人生活中的如文房器物,书册、清供图、博古图以及宫苑图、村寨图等),白描画(如北宋李公麟《免胄图》)等。
基于风俗画的画史,将之突破传统“画科”界域,归位于现代绘画类型学的应有系列,视为一个独立的种类,显然顺理成章。那么,风俗画亦存在其自身种类的“种属”问题。风俗画以题材跻身于现代绘画类型,其“属类”便首当以题材分类,亦即风俗的各种事象,如人生礼仪、游艺娱乐、节庆活动、民间信仰、民俗器物、餐饮、亲族、生产方式、市商集市等方面的习俗惯制内容。
此外,除前述如人物画、人体画、肖像画等题材之外,与风俗画构成各种体裁“类型关系”的,还有关涉绘画工具与载体材料的中国画、油画、版画、水粉画、水彩画、铅笔画、木炭画、钢笔画等;有关技艺层面的,如刻、画、涂抹、雕(不含雕塑)、指绘(指画)、蜡染、剪纸(刻纸)乃至手撕等。
事实上,除了“题材”这个本质特征的画种类型之外,风俗画并不可能脱离作为绘画的其他基本构成要素。否则,其不具有成为“绘画”的这一根本属性。

秦 云纹 咸阳窑店牛羊村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