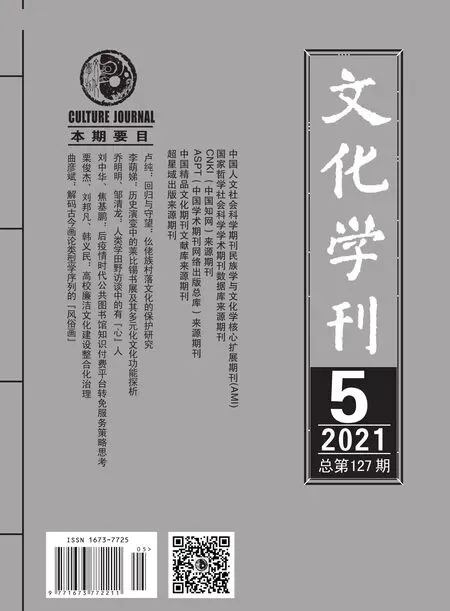从《采菽堂古诗选》看陈祚明的女性观
洪雅诗
中国的文学长河中不乏杰出的女性,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第一位有姓可查的女性作家——许穆夫人,她创作的《鄘风·载驰》是吊唁亡国的佳作。之后西汉有王昭君,东汉有班昭、蔡琰,魏晋有谢道韫,唐朝有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宋朝有李清照、朱淑真,元朝有张玉娘,明朝有端淑卿、刘淑等[1]。在先秦时期,出现了情感题材的诗作。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说:“若就宋人训诗‘国风男女之词多淫奔之诗’一语观之,则古之妇人,矢口成章,女子之作,《国风》盖居大半矣。”据统计,《诗经》的十五国风中的一百六十篇存诗中,有关女性问题的就近八十五篇[2]。综上所言,女性数量占据人类社会的半壁江山,其中也不乏优秀的女性作家,在诗歌史上论理应是男女作家各占一半、地位平等才是,但事实是女性作家在诗歌史上数量少且地位总体上没有男性作家高。中国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转为以男权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后,一方面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种种限制严重阻碍了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另一方面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对女性才情和作品不够重视甚至是轻视。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中说:“古代名媛之集,镌印不多,……流传极少,搜求非易,著录所载,或一书而数名,或名同而实异,或有目而无书,或名亡而实存,年代久远,难以考究。”[3]部分文人士大夫更是赤裸裸地表现出对女性才情的轻视,如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谈到被称赞其文清拔的南朝梁代女诗人、刘孝绰之三妹刘令娴时高呼:“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质既雌,词意亦荡。勉名臣,悱名士,得此女,抑不幸耶!”宋代的程朱理学主张“三纲五常”,对女子的身心更是加强了禁锢。梁昭明太子的《文选》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的最早的文学总集,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宋朝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就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文选》根据“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作品,但惊奇的这部皇皇巨著竟没有收入任何一位女性作家作品。即便是被钟嵘列为上品,称赞其“辞旨清捷,深怨文绮,得匹妇之致”的汉班婕妤的作品也未见收入。可见,以男权为主导的封建社会对女性诗文创作的压制,连带着女性作家也很难得到足够的尊重。明清之际,公安派、竟陵派和袁枚大肆批判程朱理学,刮起了自由解放之风,清朝文人对女性的态度有所改观,陈祚明便是其中得此先风的一位。以下拟通过陈祚明选录的女性作家作品及其对吐露女性情感的诗作的点评,探究陈祚明对女性的态度。
一、对女性作家作品及女性美的尊重
(一)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尊重
明代著名学者王夫之编选了《古诗评选》,选辑西汉至隋代总共百余位诗人的八百多首诗歌作品(包括历代乐府诗),通观全书只收入了寥寥5位女性作家的作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收录了30位女性作家作品,如表1所示。陈作明对女性作家作品的收录数量大且范围广,女性作家的身份上至贵族,下至最底层的妇女。另外,历来诗歌编选者在选择女性诗歌方面存在陋习。有女性作家创作了作品,亦有幸留存于世,但由于男性不平等目光的审视和评判,会将其作品单列于总集,如钱谦益的《列朝诗集·闺集》把女诗人和僧人作家列在“香奁”的名目下,沈德潜编纂的《清诗别裁集》把清初至中期的代表女诗人专门归在卷三十一。对此,陈祚明在《凡例》中就指出“妇女诗载卷尾旧矣”,《采菽堂古诗选》的体例排列给予了女性作家和男性文人同样的尊重。

表1 《采菽堂古诗选》中收录的女性作家及其作品
(二)不以女子是否失节来评判作家成就
宋代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一颗明珠。她与赵明诚的爱情是一段佳话。赵明诚不幸离世后,其晚年为了有所依靠而改嫁,遂成为以后历代不少文人墨客口诛笔伐的污点。女性作家的才华再高,没有固守名节,也会被部分封建士大夫诟病。但陈祚明则为女性破开了这一观念羁绊。蔡邕之女蔡琰才华横溢,不幸身逢乱世,无法左右自身以致失节,对此陈祚明报以宽容的态度,即“亦未可以轻责于人也”。陈祚明对这位多舛女子的才华不吝溢美之词,称赞她为“此史迁手笔也”,欣赏蔡琰的“能写真情,无微不尽”“俚语出之则雅”“实事状之则活”的“斐然佳文”。
(三)在尊重的基础上欣赏女性美
南北朝后期的《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文选》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除春秋时期的《越人歌》)自汉至梁表现男女之情及与女性有关的诗歌660首左右[4]。这部总集创造了一个在中国诗歌总集编纂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就是收入了有名姓可考的15位女性诗人的作品40余首。唐人刘肃在《大唐新语》卷三中说:
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台集》以大其体。[5]
《玉台新咏》的编纂宗旨是推广发扬宫体诗,宫体诗是指围绕在萧纲、萧绎等生活优裕的皇族周围的庾肩吾、徐陵等文学侍从,以女性为吟咏对象所创作的,内容上涉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则追求辞藻靡丽的诗作。这些诗作仅着力于对女子形容服饰的描绘,多冰凉冷漠,以致后来人们也称艳情诗为宫体诗。与宫体诗对女子持“亵玩”的态度形成对比,陈祚明在选诗和点评此类女性诗作时多怀着“远观”的敬意。曹植在《美女篇》中塑造了一位“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妖且闲”的美女,陈祚明的态度是“夫华腴亦非细事也,诗质而能古,非老手不能。质而不古,俚率不足观矣!无宁遁而饰于华。要之立言贵雅”。晋代傅玄《艳歌行有女篇》用了众多精美的配饰和华服,精细地描摹了美女的五官。陈祚明对此诗塑造的艳丽多姿的美女评价为“托意雅正”,可以看出陈祚明不仅在体例编排上给予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同等的地位,对诗歌描摹刻画出的女性美也怀抱着尊重欣赏的态度。
二、对女性悲欢离合的情感具有强烈的共情能力
(一)以情为本,“情”字评语频现
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凡例》中径直点出的“诗之大旨,惟情与辞”,以至于其点评诗作中,颇喜好使用“情”字。如汉朝秦嘉写的《留郡赠妇诗三首》,作者评价“伉俪之情甚真”“情深缱绻”“絮絮意长”。评魏晋时期曹丕《燕歌行》“声欲止而情自流”,评《妇病行》“情深至,语极高古”,评魏明帝《种瓜篇》“情思悱恻”。翻开《采菽堂古诗选》,除表现男女关系之情的作品外,惯用“情”字落脚,其他内容的作品出现“情”字的评价也不胜枚举,如对魏武帝曹操《短歌行》二首其二的点评为“情见乎辞”。评另一类作品如《古诗三首》其二(十五从军征)“悲痛之极”,评《古诗一首》(行行随道)“凄怆至极”,在点评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情”这个字眼,但同样也是落脚在“情真”上。作者对“情”字的紧抓不放,体现了作者心灵绵长的情感厚度。
(二)遭遇抛弃,女子面临绝望处境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男女关系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便自然而然相伴随产生,是人类社会永恒关注的主题。男女关系中,两情相悦者有之,因种种原因导致分离的痴男怨女亦有之。女性面临被男子抛弃境遇抒发的悲怨作品得到陈祚明不少关注与同情。如《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
翩翩床前帐,张以蔽光辉。昔将尔同去,今将尔同归。缄藏箧笥里,当复何时披?(其一)(1)本文所引诗歌皆选自陈祚明评选的《采菽堂古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以下不再说明。
谁言去妇薄,去妇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远望未为遥,踟蹰不得共。(其二)
陈祚明点评:
此章心伤断绝,借物形己。(其一)
此章惓惓不忘,情怀忠厚。初不言司马氏女,略露怨怼,甚得性情之正。语不须琢,婉曲缠绵矣。(其二)
陈祚明能在情感上把自己代入为被弃之女,以床前帐被收回娘家的箧笥里比喻被弃之女王宋的惨痛经历,感受被弃之女的“心伤断绝”,体会弃女对前夫“惓惓不忘”的深情。前夫不仁,弃女却不会不义。“语不须琢,婉曲缠绵”,体现了作者对“辞雅”的欣赏。
同样“借物形己”的还有班婕妤的《怨歌行》:“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质量品相上乘的扇子在夏天颇得君子恩宠,但时时担忧秋天凉气降临,沦落到被抛弃的处境。陈祚明敏感地嗅出此诗“是未见弃时作”,是“虑远之词”,陈祚明不仅能对已经遭遇抛弃的妇女的绝望之情感同身受,亦能对行将被弃之女的忧虑深有体认,不能不赞叹陈祚明对古代女子不得不完全依附于男子生活,对女子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的复杂处境和心绪变化的关注和把握能力较强。
《舂歌》是汉高祖晚年宠幸的戚夫人所作。原文如下: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陈祚明点评:
妇人无知,当尔时子岂能自保?况能救母耶?然天性之亲,自是他无可诉。
汉高祖死后,戚夫人遭到了吕后的虐待,在孤苦无依的处境中一边凿舂一边对爱子发出求救的凄苦之声。陈祚明清醒地洞察出戚夫人在高祖去世后的危险处境,但同时也理解失去高祖庇佑后的戚夫人无助的心理,明白她向儿子求助的不聪明做法背后包含的人伦亲情。
魏晋时期有类似凄惨经历的如原为袁熙的妻子后被掳为文帝的夫人,最后被文帝赐死后宫的甄后,其作品有《塘上行》,原文如下: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此首,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评:“《塘上》之作,朴茂真至,可与《纨扇》《白头》姨拟。”相较于王世贞对此诗只是浅浅地落脚于“朴”的特点上,陈祚明评为“淋漓恻伤,情至之语,不忍多读”,再一次突出了陈祚明对女性的代入感之强,对封建社会中女子命运任由男子摆布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悲怨情感的强烈同情与共情的能力。
三、对女性怨诗的欣赏仍保持地儒家温柔敦厚的美学理念
《礼记·经解》说:“温柔敦厚,诗教也。”《毛诗序》说:“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源流一贯讲求情感抒发要不偏不倚,不落两端,追求温柔敦厚的诗歌美学。陈祚明作为自小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学者,对《采菽堂古诗选》的选录同样贯彻这一原则。
陈祚明在对孙楚《除妇服诗》悼亡诗的评点中道:“八语耳,足当安仁悼亡数篇。发乎情止乎礼仪,雅音之足贵若此。此诗遂为王武子非常叹赏,故知古人诚知诗。”陈祚明能把孙楚的悼亡诗和潘岳的悼亡诗相比,是因为此诗符合“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
《种瓜篇》:
种瓜东井上,冉冉自逾垣。与君新为婚,瓜葛相结连。寄托不肖躯,有如倚太山。兔丝无根株,蔓延自登缘。萍藻托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贱妾执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陈祚明点评:
情思悱恻。“冉冉逾垣”句,生动。
这首诗通篇都是新婚之夜新妇的心理描绘,刚一结婚却想到了日后可能被遗弃的悲惨命运,面临这一悲惨的可能,新妇也只能借用瓜藤相依连的处境委婉地发出近似哀求的声音。《为陆思远妇作》讲的是夫君外出游宦与新婚女子别离三年,“离君多悲心”,满腹苦楚与思念,也只能“淡淡”地吐露。即使是妙龄十五、备受石季伦宠爱、既有美貌又有才华的翔凤,在短短十多年的宠幸后,亦被退为房老,昔日的无限恩宠与年老色衰后的凉薄形成尖锐对比,她也只能化为一句“憔悴空自嗤”。即使冠以怨字名篇的佳作,也多被陈祚明评以“婉”字,如评王昭君的《怨诗》“颇细婉”,班婕妤《怨歌行》“音节婉约”。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大多是描写游子面临追求人生理想和陪伴家人的矛盾,长年在外宦游,人生理想茫茫没有出路,旅途漂泊孤苦,而妇人独守在家年复一年苦苦等待。自被昭明太子选在《文选》之日起,《古诗十九首》愈来愈受到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推崇,究其根源,很大程度还是《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仍然尊崇了儒家敦厚的审美特征。陈祚明在对《古诗十九首》的总评中也说:“《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
在解读诗歌的时候偶尔有类似汉儒解经的情况存在。汉儒经常用君臣国家等政治关系解读诗歌。就《关雎》的主旨来说,在五四之后诸多学者将其视为反映普通男女爱恋之诗。闻一多认为《关雎》本意为“女子采荇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余冠英认为《关雎》写男恋女之情,高亨云也说这首诗描述的是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最后与之结婚的故事。但是,几千年前的《毛诗序》却认为《关雎》是讲后妃之德,以教化普天之下的夫妇伦理关系。陈祚明在汉乐府《鼓吹曲子》中的《上邪》也有类似汉儒解经惯用君臣比附的习气。《上邪》列举了五种绝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以说明女子对男子的爱情誓言忠贞不变。但陈祚明却认为是表达“人臣之死不变之心”。现列举几位相邻时期学者对《上邪》的看法:
明代胡应麟《诗薮》:
《上邪》言情,临高台言景,并短篇中神品,无一字难通者[6]。
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
此陈忠心于上之时。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申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叠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7]。
此两人均没有同陈祚明直接将《上邪》断为君臣关系。长沙理工大学杨洛、袁志勤在《解读〈上邪〉》一文提出:“前一句是表白爱情的态度,后一句是进一步表白爱情的坚贞。爱情与坚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更能体现出无比纯洁美好。”笔者也颇为认同杨洛、袁志勤所认为的爱情观。
四、结语
笔者通过《采菽堂古诗选》中收录女性作家创作的诗作以及对吐露女性情感的诗歌的点评发现,陈祚明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尊重女性作家作品,对女性美的欣赏能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对封建时代女性丧失生活独立性,不得不完全依附男性生存,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离怨情感的强烈的同情与共情的能力;能挣脱传统要求女子守节的观念,毫不保留地激赏女性才气。细细观之,陈祚明的解诗也存在拥护儒家一贯倡导的温柔敦厚的美学范畴,个别篇章的解读有类似汉儒解经的情况。但毫无疑问,陈祚明是古代最优秀的诗选家与诗论家之一。他在选诗过程中流露出的男女平等的思想观念,同情弱势群体,不拘泥于女子是否贞洁的评判标准,值得后世激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