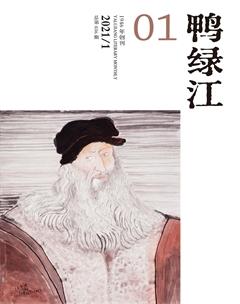小说:虚有世界的奇迹
《慢读与快感——短篇小说十三讲》是刁斗的随笔新著。作为热衷于文本实验的小说家和资深的小说读者,在这本书里,刁斗为读者讲述了来自十三种语言的十三个短篇,其间充满睿智独到的经验之谈与释疑解惑的引经据典。值得玩味的是,《慢读与快感》中的作品解读不按常理出牌,不像在有些小说家那里,光接受技艺的剔刀庖丁解牛;相反,它常常离题、打岔、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习惯性地游离到小说之外,即便言归正传了,其字里行间的语意表达也往往呈发散式辐射状:处处都闻话外之音,时时都见言外之意。这是作家精心策划的一场游戏吗?就像“慢读与快感”这件戏谑的外衣——它的确需要“慢读”,因为它的难度,但由此伴生的“快感”也将无约而至不请自来。
不过,游戏与严肃,从来都像长在同一颗头颅上的两具身体,想分开它们是件难事。不惮于离题的《慢读与快感》越是逃避教条疏远规范,反倒越能衬托出它深挚和持重的另一副面孔,在这点上,它显然出自小说思维。书中关于小说的真知灼见,有时很像庄严的布道与虔诚的宣讲,也正是在这“念唱经歌”式的严肃之中,小说家的思想世界被展示得纤毫毕现。有思想的小说家并不鲜见,但有理论的小说家却不很多,从思想到理论的跨越,需要的是体系的建构。而刁斗随笔的突出特征,便是在思想砖瓦的不断垒砌中,终于把一座理论(不唯小说理论)的大厦建筑了起来。就此而言,《慢读与快感》从未离题,它就像作家之前出版的随笔集《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和《虚有》一样,都是情难自禁的思想输出的结果。
这些思想以小说为名,却又超越了小说,它们在小说文本间穿梭流溢,自成一体,来去自如。我猜想,也许正因为思想对小说的僭越与冒犯,才逼得刁斗不得不写下这些随笔,只是这一次,他思考的冲动,让小说例外地扮演了一回虚实难辨的次要角色。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他曾借自己的小说人物说过的话:“书这东西的好处在于:它既是你之外的别人、社会、世界,同时它又什么都不是。”若以这层意思单独指涉小说,我相信作家本人也会同意——小说既是你之外的别人、社会、世界,同时它又什么都不是。
与产量不低、质量上乘的小说创作相比,刁斗的随笔作品毫不逊色。无论是《慢读与快感》中惊艳的小说理论,《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里“生活中的想象”与“想象中的生活”,还是《虚有》中对生命虚无的形而上探索以及与之相伴的激越反抗……都十分值得前往游历。
虚有
擅长文字游戏的刁斗创造了“虚有”一词,它的意思一目了然。虚,是空、无、假,与实、有、真相对;虚有,是无中生有,是空无中的存在,是虚妄中的真实或意义。既然游戏般地造了新词,给它个身份就在情理之中,随笔《虚有》即是刁斗毫不游戏的严正声明。他严肃,他像哲学家那样,正襟危坐地探究实在和虚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实在肯定先于虚有,涵容虚有,因为虚有必须出自于作为实在的人的精神活动。”小说家有板有眼的思辨,尽显一个唯物论者的本色。看来,把人的灵魂视为实在的柏拉图,还有把名句“在万物混沌中,思想产生并创造了秩序”留在残篇里的阿那克萨戈拉,都不是他的思想战友。“上帝是实在吗?我以为,如果是,它也只能是一种虚有属性下的实在,因为它首先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创造的虚有。”这里所说的上帝是造物主的意思,无论是上帝还是造物主,都是人的精神生活虚构出来的虚有之物。不过,即便如此,唯物论者刁斗仍然把上帝视为虚有世界的一大奇迹。
抱歉,这并不是一堂哲学课,尽管“虚有”一词天然地带有哲学属性。好在我们的小说家比我更懂读者心理,懂得适可而止,懂得在恰当的时机扭转机锋。在短文《虚有》的三分之二处,“哲学论辩”结束了——这让我长舒一口气,因为我一直担心,他会把一个形而上学难题,引向鸡生蛋、蛋生鸡的死胡同里——就在读者深陷于认识论的迷宫之时,爱玩游戏的刁斗向米诺斯的公主阿里阿德涅借来了那个著名的线团:“我想引申的,其实是虚有世界里上帝之外的另一个奇迹:小说。”
原来,虚有的诞生,与小说有关。原来小说和上帝,是刁斗虚有世界的两大奇迹。
把小说抬高到上帝的地位,乍一看有点匪夷所思。但在这里,刁斗凸显的是小说的虚有属性,他说的小说不指物理文本,而指观念文本:“小说由虚有孕育,幻觉与想象是它的羊水,虚构与悬拟是它的胎盘,可随着它的呱呱坠地,它所呈示的独立的虚有世界,竟可以与实在世界彼此呼应,互为镜像,相辅相成,并能以一己无形之躯,为无际无涯的实在世界提供栖息之所。”这句洞见之语,通過对小说进行由内而外、从局部到整体的审视,既描述了它的生成机制和独立品格,也指出了它的存在意义与真理价值,还仿佛为亚里士多德那句著名的论断提供了注脚:“诗歌比历史更真实。”
如此一来,事情也就明了了:为了凸显小说的重要性,刁斗虚构了虚有;虚有是他建立小说大厦的地基,能把毋庸置疑的合法性交付给小说。那么,对刁斗来说,小说何以如此重要,它又如何成为他的奇迹呢?随笔《有小说的生活》回答了这些问题。有小说的生活由读小说和写小说构成,小说借此成为刁斗精神生活的全部。是小说让他在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找到了平衡,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快乐和幸福,乃至于成了他“有必要活下去”的一个理由。小说源自小说家丰盈的心灵生活,却又不是不着边际的乌托邦寄托,不是偶尔拿来膜拜的尊崇之物,而是与实实在在的生命、与脚踏实地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我用我的整个身心去享受那种有小说的灵化的生活,并不是为了作茧自缚,而是为了更好地去享受那足以包容小说包容一切的物化的生活。”如此说来,因为小说已经成了与小说家血肉相连而不仅仅是心心相印的一种存在,那么有小说的生活,便“不啻是完美的生活”了。
然而不论有小说的生活如何“完美”,刁斗在此的一句告白,仍然因过于扎眼而不太合群:“甚至严重一点说,这也为我还有必要活下去准备了一条堂皇的理由。”这条有点“严重”的“理由”,因为让我立刻想起了《西西弗神话》那惊悚的开篇,我接受起来还算心平气和:“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人活着,如同进行一场没有剧本、无法彩排也不能中场休息的表演,而负责监工的死神正躲在幕后,什么时候反转剧情,什么时候踢谁出局,什么时候终止演出拉上大幕,全凭他一时的喜好决定,任何人都无法提前知晓故事的走向。所以,“活下去”也好,“自杀”也罢,都是在沮丧、空虚、荒诞、绝望、无意义……中,苦苦挣扎并寻找出路。
死亡和虚无是有限人生的两大威胁,无论我们是否能意识到,它们都是人类无法挣脱的宿命。向死而生的生存让我们面临抉择,凭借主动的自我选择,活着才有机会跃升为“存在”,而存在即是对死亡和虚无的反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特别看重刁斗的“虚有”,因为构建虚有这一思想的行为本身即是一种决绝的反抗,是存在主义者的自我选择。“虚”中之“有”,是對“虚”的漠视与僭越,是在虚空中创生实在,在虚幻中创造真实,在虚无中建构意义。正是在人之“存在”的维度上,通过虚有,刁斗所展示的他挑战生存和反抗虚无的人生信念,才有着漂漂亮亮的透辟与完整。这在他的随笔《我的小说主题(一)》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论短暂的希望快乐还是长久的虚妄痛苦,都会像“爱与死”一样,与人类永恒地相伴下去,如果我们不想束手待毙,就只能坚持不懈地奋力反抗,夺取希望快乐,阻击虚妄痛苦。当然,反抗的形式多种多样,写作只是形式之一。但对我来说,写作则是唯一的形式。
反抗即是自救,而自救没有终点。
游戏法
我喜欢“虚有”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它几乎瞬间就能变身“游戏”。虚,既是虚空虚无,也是虚拟。有,是实,亦是真。虚有,由此变格升级为“虚拟真实”。在如今这个数字时代,虚拟真实的VR影像大行其道,改变了人们对感官系统与世界关系的认知,而比它古老得多的小说和艺术,在本质上也许与它没什么不同。戴上小说的仿真眼镜后,我们会进入一个虚拟真实的游戏世界。
游戏是人的本能,这在儿童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像妇孺皆知的“狼来了”的故事,那个放羊的孩子就是主角。只不过这故事有点暗黑,那孩子不仅把自己玩成了一个“说谎者”,更玩到了一个被视为“该死”的地步。可是,真的是谎言害死了屡教不改的牧羊童吗?不,是“事实”,是“正确”,是刻板僵死的“道德”,在扼杀孩童游戏的天性时,顺便杀死了这个不识时务的游戏者。
耐人寻味的是,刁斗在随笔《说谎者说》中续写这个故事时,让那孩子摆脱了道德训诫牺牲品的角色。侥幸从狼口脱身的孩子并未“改邪归正”,反倒立志成为说谎高手,在不懈的冥思苦想和刻苦实践中,他渐入佳境,技艺日精,使自己的骗术产生了魔力,进而让这种编瞎话的游戏行为演化成了小说创作这一职业。如此一来,这一隐喻色彩浓厚的“故事新编”,不仅名正言顺地把游戏还给了孩子,还含蓄地道出了小说的游戏本质:
在人类所能从事的诸多项类的智力活动中,写作小说,是为数不多的能把极端的严肃认真与极端的荒谬随意结合起来的益智游戏,正是这严肃认真与荒谬随意的结盟共谋,才使得小说的游戏精神获得了本体化与绝对化的地位,使之进入了一重“虚有”的境界。
这句点穴式的描述实在精彩,令人长久地浮想联翩。作为席勒艺术游戏说的虔诚信徒,刁斗一向认为,小说写作是一种智力游戏,游戏精神是小说的根本属性。智力探索与游戏趣味、认真严肃与荒谬随意,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不同面向,刁斗对它们的透视与解析,既是在洞察人性的本质,也是在伸展和升华小说的精神,而他有意为游戏贴上的“本体化”“绝对化”的护身符,更能使其地位不可撼动。有一个他践行其理论的极端化例子,让我每每想到都深感讶异,然后莞尔。十七年前,他曾写过一篇名为《的》的避字小说,在近三万字的篇幅里,除了标题,再无一个“的”字出现——这种骇人听闻、可以表征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所引,在确立了游戏精神至高无上的地位之后,又再次让“虚有”浮出了水面。显然,对刁斗而言,小说、虚有、游戏,是三个彼此缠绕的词语,让它们同时现身没什么意外。在以小说为名的思想闭环内,它们常常追逐嬉闹,玩语词和意义的回形游戏:小说是虚有世界的奇迹;小说是反抗的方式;小说是智力游戏;游戏是对枯燥和虚无的反抗;游戏让小说进入虚有之境;虚有既是反抗也是游戏;虚有的意义是神性的;小说走在通往神性的路上……这一个个从刁斗随笔中逃逸出来的、意义丰赡的思想晶体,很像物理世界里双缝实验中的奇异光子,以一种神秘和诡谲的方式彼此连接。它们不是语义简单一目了然的绕口令训练,而是灵动的形而上探求,它们充满智性的魅力。
将游戏精神融入思考和表达,甚至内化为生存方式,这也许是刁斗的主动选择。对他来说,思想的游戏化表达和游戏的形而上冲动之间,并不需要一条清晰的界限,他本人其实很喜欢陶醉在这种模糊混沌中自得其乐。但也正是这种游戏的冲动,让刁斗在写作随笔时,下意识地为阅读设置了门槛——当然,门槛这类事从不在他操心的范围,他在意的只是游戏是否好玩。所以,不论通过小说还是随笔,要进入刁斗那由双重游戏着的思想和语言所构筑的世界,都不是一件轻巧的事。就像在《慢读与快感》中他似乎刻意为之的那样:非要上挂下联地避重就轻,甘愿吃力不讨好地迂回跋涉,但觑着目标的他光一脸坏笑,就是不肯“雅俗共赏”地掰开瓤说馅。他对文字永无厌倦的把玩,他那称得上是炫技的繁复修辞,他不断追求话外之音言外之意的曲里拐弯缠缠绕绕,他通过复句中的复句和重重的语义叠加所追求的春秋笔法……常常让我想起后人对古罗马哲人塞涅卡的一句评价:“他的修辞技艺一直显得过分。”但是,或许正是这种“过分”的修辞,才更能吸引诱惑阅读者,去自觉自愿地沉陷于作家那些语言的演练与思想的实验。
刁斗关于小说写作是游戏的断语,与奥登为诗歌做出的定论不谋而合:“小说是智力游戏”“诗歌是知识游戏”。当然了,这只是他们各自的前半句话。后边奥登又补充道:“却是一场严肃、有序、意味深远的游戏”,而刁斗的后半句话,则可以化自他长篇小说《游戏法》的书名:游戏有“法”。是的,游戏越有规则、越形式化、受限越大越多,对游戏者的技能要求也就越高,而玩的时候,也就越需要严谨认真慎重,因此,便也越容易精彩刺激妙不可言。
思想者说
作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小说行脚僧,刁斗的写作始终与思考同步,许多深邃诱人的小说思想源源而来,并且它们也像小说那样,常常以一种感性的游戏化方式现身登场,所以,它们并不用“理论”标榜自己。然而,正是这些拒绝坚硬面孔的感性话语,却星罗棋布,构建出一个小说的理论空间,令人目眩神迷,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纵观刁斗的三本随笔集,如果说《慢读与快感》相对集中地书写了小说理论的话,那么,时而彼此映照致意、时而互相交汇融合的《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和《虚有》,则如同它的出身和来路。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慢读与快感》中,刁斗几次提到了他的口号性思想——关于小说的“阅读三忌”:“忌提炼中心思想、忌找寻教育意义、忌对号真人真事。”表面看去,这极具启发意义的“三忌”好像只是剑指当下中国的语文教育、人文教育,是接受美学问题,实则它掘开的是人类根性中一处贻害巨大的致命病灶:以教条代替感受,以简化排挤丰盈,核心的病根是拒绝思考。刁斗认为,思考源于认知,而小說是认知的触手,所以,刁斗推崇具有百科全书品质的小说:“小说作为百科全书,尤其作为情感生活和观念世界的百科全书,其使命只是表达还没被意识到或只被意识到个别侧面某些局部的存在景观,以帮助读者的认知不断走向广阔和深入。”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刁斗所说的百科全书,并不意在信息集合和知识汇总,更不是产品说明书、经典家常菜、考试攻略大全、性爱知识手册之类,它只属于“情感生活和观念世界”。“情感”指向伦理,“观念”指向思想,这意味着,在视小说为认知手段的同时,刁斗正在越过形而下的物化世界而直面形而上的终极问题:“小说的格物,终为致知,以格物生趣固然很妙,由致知通道则为大好。”一股强烈的形而上冲动,支配着刁斗把小说作为探究世界、发现真相、求索真理、追问人的存在之谜的媒介和手段:
我愿意把踏上小说的玩乐之途,视为走上确认和把握和解剖事物间诸关系的便捷之旅。现实生活沿可行性前进,虚构故事靠可能性发展,小说作为存在的勘探器,往远了说从庄子开始,从近处讲自塞万提斯以降,其实,从来都不仅仅满足于充当镜子去映照复制已知的现实,它更乐于成为的,事实上也确实成为的,是现实的发掘者和创造者:赋虚无以形状,化虚有为实在。
正是基于此,我更愿意强调,刁斗首先是思想者,其次才是小说家。
当然了,读小说写小说构成了刁斗的虚有生活,但他的虚有世界要想正常运转,唯此为大的又唯有游戏:“玩乐是我的第一需要,甚至也是唯一的需要。”那么爱玩乐的刁斗与善思想的刁斗,两者不会颉颃龃龉吗?还真不,因为在刁斗这里只有游戏,也就是说,玩乐和思想,都是他愉悦身心、欣快精神的游戏手段。在随笔里,刁斗不止一次地提到,攫取知性乐趣与体验智力快感,是他沉迷读写的最大动力。为此,他还“发明”了一套判断小说的特殊标准,其中最惹眼、最重要的一条名曰“骚动”——“诱人骚动,这才是好小说的共同指标”。
在评价文艺作品好不好时,“感动”是个司空见惯的笼统标准,看电视、观电影、读文学、赏戏剧时,这几乎是我们听得最多的评价。可是,如果泪腺分泌指数真的能成为艺术标准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恐怕是检测人体基因序列和考察感知系统,而非探究艺术作品。愚忠般的感动,它与艺术作品构成的,多半只是被动的主仆关系;但作为孤本的艺术作品所召唤的,又永远是打着私人烙印的个体化感受,欣赏时,体验的触角若要更深地抵达其内部,首先要做到的恰恰是防范各种表面化情感的过度泛滥,以避免注意力只投射于故事情节的戏剧性和同理共情的经验性。而骚动所生成的不安状态,则可以代言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体验,对于它的私密和神秘,即便感受者本人,也常常无从探听其真伪虚实,无法摸清其来龙去脉,所以,“它的悲喜是莫名的,它的好恶是夹缠的,它的苦甜是不确的,它的痛快是伴生的”,它更像一道诱人的幻影,只负责撩拨着你去奋力追逐。当然了,作为幻影,你越是接近它,越会发现它变化莫测;而它越是莫测难料,也便越吸引着你的追逐不停不歇。
依据我们惯常的概念,骚这个字眼有点轻佻,不低眉顺眼,不中规中矩,不道貌岸然,而是目光蒙眬身段妖娆,作为一种不和谐音,奏鸣在以伪道学假正经为时代主旋律的交响乐中。但我喜欢它的异端品质。它的奔放与暧昧,犹疑与坦荡,享乐主义与戏谑精神,以及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的冒犯的勇气——通过牢骚和骚扰,去以弱抗强以卵击石——几乎就是小说的性格写照。
显然,刁斗对骚动的迷恋,不仅有感性的沉醉,更有理性的投射,而他对它天然具有的异端品质尤为看重。异端的骚动与玩乐为伍,与反抗为伴,当然也必然与思想结盟,它如同一面多棱的镜子,能清晰地映照出小说自身的模样。于是在刁斗那里,骚动,作为无视羁绊桀骜不驯的、其重要性仅在游戏之下的一个关键词,便等于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职责,在参与小说游戏的过程之中,它“通过挑剔以审视成见扩大认知,通过批判以摆脱拘囿更新架构”的神奇功能,便也义不容辞地宣示了刁斗极具个性的美学态度和小说理念。
如此一路寻踪觅迹,刁斗那不可遏止的认识论诉求和形而上冲动,也就被我们找到了源头看清了轨迹。于是,他那些“匪夷所思”的小说思想也就不再难以索解了,我们终于了然,在时时渴望洞察人与事的刁斗的笔下,他是怎样通过小说语言编织出一个流光溢彩的思想世界的——这个世界里,自然也包括了他为小说所开凿的坚牢宽敞的理论空间。
是的,讨论刁斗,指涉他的观念时,我的用词更偏向“思想”而非“理论”,这可能主要因为它们与令人生厌的八股文完全绝缘。可这就是理由的全部吗?我说不好,我只想强调一点,在刁斗的三本随笔集中,箴言警句信手可拈,许多值得细细品味,甚至能令人醍醐灌顶,而那些朗朗上口的“金句”尽管也充满了“理论”,或者就是“理论”,但怎么打量,它们又都特别“思想”,都非常“思想”格外“思想”。比如,与他的“阅读三忌”相对应的好小说的三个标准:语言的魅惑力、结构的建设性、故事的延展度;再比如,他对现代主义小说气质的描述:“重气氛营造而不是人物刻画,重观念辨析而不是戏剧冲突,重客观陈述而不是臧否评判”;还比如如下的一些说法:“自从小说诞生,梦游就是它的特质:不拘泥,能僭越”“人这个东西,只有独立起来,个别起来,如钻石般让五花八门的不同棱面都自成格局地闪烁起来,才能达致一个精神化生命所该有的样子”“生命只是存在的过程,它的诞生只为湮灭,面对死亡这一常胜杀手,它上阵之前就败局已定。但恰恰是它的绝望属性,能从反抗的徒劳中昭示人性的尊严,能在失败的悲壮里彰显精神的高贵”……这些属于一个小说家的、生机勃勃且戛戛独造的“思想”,总能令人过目不忘。
在一篇关于加缪的随笔中,刁斗这样谈论自己的写作,亦即他那严肃的游戏与游戏的严肃:“推着加缪这块哲学的巨石暗夜行路,我的踉踉跄跄竟越来越像优美的舞蹈。”而在读到这一句时,我正读的另一本克尔凯郭尔的书里,刚好也有一句让我动容的近似的表述:“关于死亡的思想是位曼妙的舞伴,我的舞伴,其他任何人对我来说都太沉重了。因此,我请求,向神请求:谁也别请我跳舞,因为我不跳舞。”我读克尔凯郭尔稍多一点,知道这位承受了太多苦难却仍然不惮与命运赌博的思想的舞者并非拒绝跳舞,他是不与红尘跳舞,不与凡俗跳舞,不与庸众跳舞……因为他的舞伴只是他自己,是他时时进行着的独立思考,是他处处用以冒险的个人生活。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一个合格的舞蹈观众,但我知道,与欢天喜地的轮舞群舞广场舞相比,我的确更欣赏以自己的思想行为为伴的独舞,不论它是刁斗跳的文学舞蹈,还是克尔凯郭尔跳的哲学宗教舞蹈,抑或其他什么人跳的其他舞蹈。
作者简介:
牛寒婷,1979年出生,本科学经济,研究生读文学,曾从事编辑工作十余年,现在辽宁文学院文艺创作研究发展中心做研究工作,已发表艺术随笔与文学批评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