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伟强影像考古口述系列之“发现舒新城”
王昕璨
一、发现舒新城
王昕璨(以下简称王):
龚老师,您好!您为什么一直强调“私纪录片”,比如您前段时间发现的翁万戈,以及最近发现的舒新城?龚伟强(以下简称龚)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先要强调的是翁万戈的影片绝对不是私纪录片。他的影片拍摄是基于电影公司化的生产需求,并不是个人行为。虽然很多影片拍摄是个人化的,如拍摄的常熟、北京、天津等地的影像,但是他摄制的目的是为了后期公映和传播中华文化,具有商业性。相反,私纪录片的目的不是传播,它更多的是在小圈子里放映,不具有商业性。比如,舒新城的影片就是很好的代表。舒新城非常擅长摄影,出过很多摄影方面的书籍和写意性的摄影作品集,拍“电影”只是他的个人爱好而已。他的影片不像翁万戈的影片,因为它没有商业性,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纪念或者说回忆的方式。例如,《相泽十周岁》《杭州之游》《苏州之游》《宜兴》等个人生活纪录片。
值得一提的是,舒新城的纪录片里也有区别于一般私纪录片的内容,这些内容记录了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1932年5月28日,他在苏州公园拍摄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这一历史事件也被当时的新闻机构拍摄,但是舒新城是用自己的摄影机去拍摄所见所闻的内容,不具有官方性,而是私人属性,这是独家的私纪录片。
王:
像这种“私纪录片”有什么价值、意义呢?龚:
如果你了解“一·二八”事变,那么你就更能体会《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1932,拟名)这部私纪录片的意义。当时中日停战,中国军队撤到苏州以西。在撤离前,“第五军”“十九路军”等在苏州开追悼会,实际上是对“一·二八”事变的一个总结。事先获知此消息后,在上海的舒新城便携带自备的电影摄影机,坐火车提前赶到苏州拍摄。现在,我们从舒新城拍摄的影像中可以看到,此次追悼会非常隆重,对抗战人士、爱国人士来说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重大事件。作为个人去记录历史的重要事件也可以从侧面感受到舒新城等一批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像民国一代的文人、学者,大多抱有教育救国、实业报国的理念。同样,舒新城也是一位热心、热衷于教育与社会活动的学者,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周边事物十分敏感。爱好摄影与电影拍摄,舒新城用自己的摄像机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幕幕场景,为中国现代史进程中的又一个关键节点留下了珍贵的活动影像。
当然,从电影史的角度考量,私纪录片是有实际意义的。对于地方博物馆、资料馆、档案馆来说,它的意义就更大了。以前,我们只能从文献、档案、日记、照片中了解相关的资料;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影像来考古。目前而言,私纪录片没有形成研究气候,很多东西没有考证,也没有研究体系。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集中地找寻这类影像且修复它,也希望可以引起学界、媒体的更多关注,将作为历史佐证或者艺术欣赏的影像资料呈现在众人面前。
王:
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发现舒新城影像资料的?龚:
舒新城的电影胶片实际上是上海音像资料馆第一次采集的电影胶片。在这之前,上海音像资料馆虽然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其主要是做数字拷贝,如从全球的相关机构对上海有关的历史影像进行采集。2011年,我来到了上海音像资料馆。第二年,我向馆里提出了直接采集最原始的资料的意见,即不再单纯地从其他机构购买、收集数字拷贝。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衡量,还是从内容的角度考虑,数字的拷贝都是复制品。电影胶片不是这样,它就是最原始的,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巧合,2012年,我从国内的收藏品市场打听到有一批不知道拍摄者是谁的老旧电影胶片,于是对其追踪,并以上海音像资料馆的名义花费很大一笔资金才将其收藏入馆。随后,我们将这批电影胶片送至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技术厂进行物理清洁、整理和修复,并在此基础上对胶片进行了数字化(逐帧扫描)处理。扫描后获取的视频格式文件,经与民国时期出版的舒新城日记、书信等文字材料比对后确认,该旧电影胶片为舒新城拍摄,是他私人的纪录影像。
王:
发现这批影像后,您或者上海音像资料馆做了哪些工作?
图1.杭州景观(截图)②
龚:
第一步,是把其有关的资料收回来,收藏入馆;第二步,对其进行清洁、整理和修复,并进行数字化(逐帧扫描)处理——第一次是标清处理,第二次是高清处理,目的是让这些原始电影胶片更好地保存;第三步,对扫描后获取的视频格式文件,进行复制、传播;第四步,用于节目制作或者学术研究使用。王:
这批影片有多少部?龚:
这批电影胶片共有八本16毫米胶片,两本8毫米胶片。目前,我们已确认的影像时长有60多分钟,且全部为默片。这里一半以上的内容是拍摄于1930年9月12日至10月23日的《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其他的短片有《杭州之游》(1930)、《苏州之游》(1930)、《虹口公园》(1930)、《兆丰公园》(1930)、《北平之游》(1931)、《开封》(1931,拟名)、《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1932,拟名)、《宜兴》(1932,拟名)、《中华书局二十周年庆祝活动》(1932,拟名)、《庆祝上海市政府十周年纪念》(1937,拟名)等,以及拍摄年份不详的《相泽十周岁》(又名,《佛教会花园》)。王:
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辞学家,舒新城是如何与电影结缘的?龚:
一生爱好摄影的舒新城,曾出版了摄影作品集《晨曦》《习作集》《西湖百景》《美的西湖》和专著《摄影初步》等。他在纪录片方面的摄像作品与成就其实很少有人知晓的。拿到这批影像后,我们前往上海辞书出版社访问且借阅了舒新城捐赠给中华书局图书馆的资料,随后又到北京访问舒新城的儿子舒泽池先生。在访问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舒泽池并不知道他的父亲舒新城曾经拥有过摄影机、拍摄过电影,也从未见过他放映过影片。然而,当我们一起看了这批影片后,舒泽池确定了这些影像中的人物就是他的父亲和继母,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舒新城一家的生活记录。舒新城与电影结缘,我觉得有三个原因。一方面,应该是舒新城对电影的喜爱。通过舒新城早年散文集《漫游日记》《狂顾录》和通信集《十年书》,我们便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其中,屡有影片拍摄的记载。但是,它到现在都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例如,1930年9-10月,舒新城随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访日,在散文随笔集《漫游日记》(中华书局1945年版)中有专门一章《扶桑纪游》对此详述,譬如某天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拍了几幅照片,摄了多少尺胶片电影等,事无巨细,均有详尽记录。另一方面,出于舒新城对于国难和社会责任的反思。例如,《狂顾录·苏锡之行》中记载了1932年5月28日舒新城在苏州拍摄“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的经历,随后他又前往无锡、宜兴等地进行拍摄。
除此之外,在于记录的用处。在拍摄的影片中,舒新城摄入的学校教育占有很大比重,如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一直拍到幼儿园,从北京的清华园拍到初高中(目前没法考证)等。与此同时,他会通过摄影机来记录校园风光、学生课堂、课间活动等,将民族振兴,教育救国时刻放在心上。
王:
大家比较熟知的是舒新城的摄影作品,其作品多以“美术摄影”见长,不知道这一点在影像中是否有所体现?龚:
客观来说,从目前收集到的舒新城影像来看,舒新城在拍摄技巧上是很生疏的,尤其是他早期的那些片子。例如,在《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中,他并不清楚电影的拍摄规律,镜头没有起幅和落幅且摇晃得很严重,这给我们后期修复、剪辑也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到了30年代后期,他的镜头感就逐渐增强,出现了固定镜头、大全景、特写等。当然,舒新城曾在《电化教育讲话》一书的序言中,也谈到:“我以电影和无线电为业余的消遣,对于电影与无线电有相当的常识,但从不打算把这些常识写成一本书。”因此,舒新城的作品不能以太过严苛的拍摄技巧去做衡量,而是要以“美术摄影”所涉及的使用摄影机揭示人内心的问题去诠释,毕竟其不是单纯地记录镜头前的拍摄对象。
图2.杭州景观(截图)③
王:
舒新城的影像大多是记录了苏州、杭州的景象吗?龚:
这部分的内容相对较多。我们看到的《杭州之游》《苏州之游》等短片,是舒新城于1930年拍摄的,他携其亲友前往苏杭名胜旅游休闲时拍摄的纪念性影片。通过这些影片我们看到“湖滨公园”“西湖中”“六和塔”“龙井”等自然风光、江南名园“留园”“西园”等人文景观和当年的社会现象,这些地方的选景都很别致,拍摄的镜头意境美好。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看到他的《西湖百景》《美的西湖》《实地步行杭州西湖游览指南》等,这些都与苏州、杭州有关。王:
舒新城曾在《蜀游心影》说:“一个人的思想,精密讲来,都是反映时代的镜子。”用此对照他拍摄的影像倒是可以呼应,尤其是他选择拍摄的时间、地点、事件均较为特殊,对于这一点,您是如何看的?龚:
舒新城的这批影片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片段:一是,拍摄于1930年的片段。在陪同时任中华书局的老板陆费逵去日本为期40天的考察里,舒新城的影片中记录了陆费逵。陆费逵先生的照片存世的很少,国内外很多出版社常常把他和舒新城、张元济等人的照片搞错。这批影像中有大量有关陆费逵先生的镜头,这为我们提供了陆费逵人物研究的影像资料,也无疑是陆费逵和中华书局早期涉外业务活动的重要影像文献与档案,更是中日企业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佐证;二是,舒新城作为游客参与记录重大历史件的一部重要短片,叫做《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这在前面也有提到过,它的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就不多说了。此外,1931年的清华大学牌楼、清华园的风貌、1937年上海建市10周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虹口公园、兆丰公园、北京市民的休闲生活等影像,都在这批影像资料中可以找到。毋庸说,这批舒新城的影像资料是最原始的。其实,我们也发现,舒新城影像的拍摄视角是具有一定的含义性,地点也是其甄别、筛选后所决定的,这大概与当时胶片昂贵有关,即拍摄往往会选择更有纪念价值的地方、人和事。
二、舒新城的电化教育
王:
舒新城作为早期电化教育研究的倡导者,他撰写了相当多的教育类文章,谈及“新教育”。1945年之后,他参与过多部教学影片的摄制,还曾担任上海市业余广播学校校长。您对舒新城电化教育有了解吗?龚:
除了之前提到的舒新城拍摄照片以及摄影中体现的“反映时代的镜子”,这在电化教育上也有所体现。舒新城曾提到,“经过抗日战争国民政府教育部对电化教育的大力宣传和推广,战后电化教育活动有所增多,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在这阶段,舒新城所倡导的理念对彼时电化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其实,从他喜欢摄影、电影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推崇技术和崇尚科技进步的人,他对媒体技术及其效力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例如,自1945年11月起,舒新城主持购置了外国的科学教育影片200余部,并尝试摄制教学影片。1946年,他借到影片,在吴兴县放映一周,观众达四万余人。1947年3月,舒新城参加“第一次电化教育座谈会”,强调了发展电化教育的理念和意义。并且,他应邀主持制作有声教育电影和幻灯片,在中华书局设立教育电影室。
王:
舒新城为什么深得中华书局器重?龚:
其实用“器重”这两个字很难概括舒新城与中华书局的关系。柳斌杰主编的《中国出版家·舒新城》中谈及舒新城和中华书局的关系,除了与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私交甚好,并在情感、工作、学术上多能与其达成共识之外,舒新城一生都将中华书局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一是,舒新城编纂了《辞海》;二是,舒新城在摄影、摄像和电化教育等方面,践行了中华书局的发展理念。1947年起,在《中华教育界》上,舒新城每一期都会写一篇有关电化教育的文章,之后加上一些讲演稿集成《电化教育讲话》一书,这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电化教育专著之一。该书收录了《电化教育的实际问题》《以耳代目建国法》等重要文章,既讨论了教育电影制片、摄制技术等问题,又诠释了其所推崇的电化教育理念。1948年后,舒新城担任中国教育学会电影与播音教育研究委员会会议召集人。该委员会只有两名会议召集人,另一位是孙明经先生。
王:
您觉得他论及的电化教育理念对当下有什么启示意义?有关电影的教育是不是也应该这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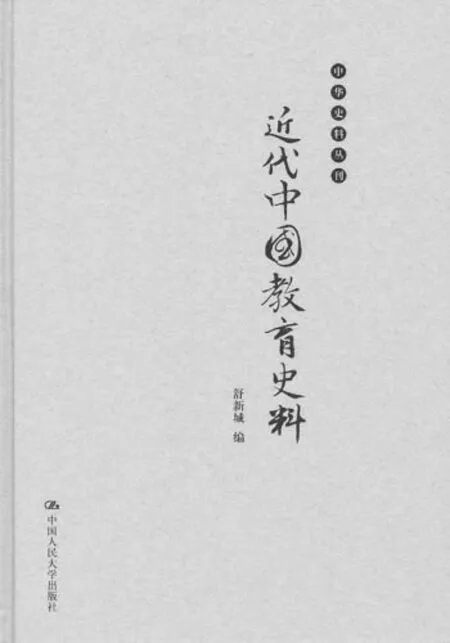
图3.舒新城图书《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封面
龚:
舒新城曾在《教育电影的教育观》的第四部分提及了“教育观点在教育影片上的应用”问题。他说:“电影之所以能教育人,是因一般电影有戏剧性的故事而又能使故事继续不断映放下来,同时又有音乐及语言以增加画面的刺激力,使主要感官——视觉与听觉——均能满足其需要。教育电影的取材则应以富于积极的教育性者为主,其戏剧性虽不一定能与娱乐电影比,但亦应有戏剧性。不过故事的编制与画面的布置应多具现实性。在原则上固当注意教育观点及注意如何发扬民族性的优点与如何铲除民族性的劣点,在内容上也应当尽量采取现实的题材。”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生与电影艺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而这同样适用于当下的教育与电影艺术。此外,他对教育广播节目和教育电影制作等方面也进行了详析,认为“(电影)在教育上发生最大的作用,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绝不是任何人或任何教育家所能担当得起的”,“需要于艺术家者更多”。与此同时,舒新城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认为电化教育需要培养“专才”和“通才”。放在当下来看,电影依旧具有这样的优势,依旧需要培养相应的艺术人才。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新建电影学院,做电影通识课。但我觉得电影院校在全方面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学生的专业性训练,培养电影“专才”和“通才”,如此,它才更有价值,也将助推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三、舒新城影像的价值、意义
王:
舒新城影片的主要艺术风格及特点是什么?龚:
舒新城的摄影作品和他的影片一脉相承,极具主观性。他在影片中的画面既富有诗意,又具唯美性,如北京的天坛、颐和园、北海、清华园等在构图上都可见其摄影方面的艺术功底。40年代,舒新城的影像出现了固定镜头,画面较之以往更为唯美,这是从美学的角度考量的。如果从技术的角度考虑,他的拍摄技巧相对较弱,推、拉、摇等缺少摄影的镜头感。目前,我们想将他的影像重新剪辑,按照他的时间线或者活动线梳理一遍,再进行放映,并在上海或者他的家乡开一个舒新城影片放映会。王:
此次发现舒新城的影像资料有什么价值?在重写电影史上,他是否能够像孙明经一样,获得一定的历史地位?龚:
舒新城在中国的电影史书上是没有记录的,不像孙明经有大量的资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得到电影界的重视。舒新城影像资料的发现所具有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或者历史价值,我们目前还无法衡量。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的也只有八本16毫米胶片,两本8毫米胶片,资料性的东西还是太少。当然,这一定不是全部。我们还需继续寻找。作为一个已故的知名人士,舒新城所拍摄的私纪录片肯定可以看做是历史的佐证,应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