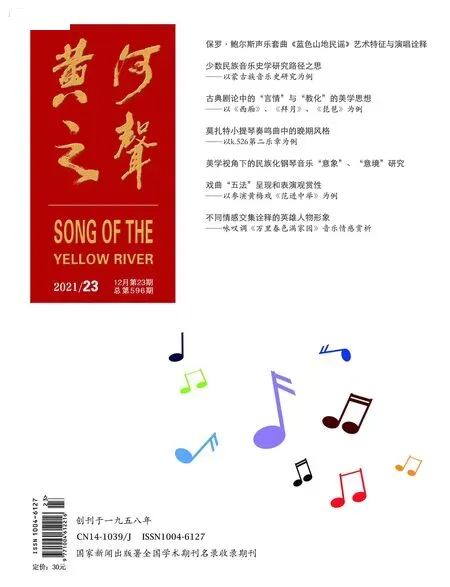少数民族音乐史学研究路径之思
——以蒙古族音乐史研究为例
郭 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形成了璀璨多元的文化,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与汉族音乐历史共同构成了中国音乐历史。蒙古族音乐学家乌兰杰先生说过:“没有音乐史的民族,在音乐上是不成熟的。[1]”每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音乐历史,但不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音乐史学。要想丰富完善中华民族的音乐史,必须要撰写56个民族甚至更小族群的地域及多元的音乐文化史。
一、少数民族音乐史学研究概览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踪迹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此时期少数民族的音乐就与汉族中原音乐有着广泛的交流。周代流行的“四夷之乐”就是少数民族音乐进入宫廷的重要表现,并且从周代开始许多朝代都设置了诸如“四夷乐部”,以吸纳并展示王朝周边族群的音乐艺术。中原地区音乐历史中,在汉武帝之前出现的乐器大多可称为“华夏旧器”,随着西汉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音乐传入中原,七部伎、九部伎更是体现了我国古代少数民族音乐及周边国家音乐的繁荣发展。宋元时期,中原及江南地区市民音乐的繁荣,使得音乐出现多样化、民间化的特点。此时的少数民族音乐早已更多地吸纳中原音乐,产生众多相融相合的乐种,如金杂剧、纳西族的白沙细乐,明清时期宫廷演出的萨满乐舞、南方各地的歌圩、踏歌、维吾尔族的木卡姆等。在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的发展中,少数民族音乐一直在历史的长河蜿蜒流淌,与中原汉族音乐碰撞、融会。
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专家学者们开始注重对民族音乐作共时性的考察,进入80年代中后期,逐渐开始进行历时性的民族音乐史学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吕骥、阴法鲁、冯光钰、伍国栋等专家学者提出了应重视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1991年,撰写一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课题被列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议事日程。同年4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编撰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学者们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课题的立项和编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学会学术年会”(辽宁抚顺,1993年8月11-15日)上与会学者宣读了乌兰杰的《蒙古族音乐史》、杨民康的《布朗族音乐史》、吴荣发的《苗族音乐史》等多个少数民族音乐史论文提纲,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有关少数民族音乐史的专题研讨会。到“第六届中国少数民族学会学术年会”(南宁市,1995年8月20-26日)时,已经有20多个民族的音乐史已全部完成或基本完成。在“第七届中国少数民族学会学术年会”(贵阳,1997年8月15-20日)上,关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问题”成为中心议题之一,并备受关注,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冯光钰的《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问题》(《人民音乐》,1993年第10期);袁炳昌的《少数民族音乐在中国音乐史的地位——兼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工作》(《艺术探索》,1997年第3期);伍国栋的《关于撰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几个问题》(《人民音乐》,1998年第1期)等,专家学者们对少数民族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以及撰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若干学术问题发表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关于少数民族音乐史史料研究的成果,主要有张瑛华的《石寨山型铜鼓图像反映的歌舞种类考释》(《民族艺术研究》,1990年第2期);黄翔鹏的《两宋胡夷里巷遗音初探》(《音乐文化》,1991年第1期);胡家勋的《古彝文文献中的乐舞史料钩沉》(《音乐研究》,1996年第2期);石峥嵘的《〈巴渝舞〉名称考辨——土家族古代音乐史系列研究之二》(《交响》,1999年第1期)等。
关于少数民族区域音乐史的著述,主要有伍国栋的《白族音乐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许常惠的《台湾音乐史初稿》(全音乐谱出版社,1991年);林济庄的《齐鲁音乐文化源流》(齐鲁书社,1995年);边多的《西藏音乐史话》(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更堆培杰的《西藏音乐史略》(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
关于断代史的研究著述,主要有孙星群的《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和陈秉义、杨娜妮的《中国古代契丹(辽)音乐文化考察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等。
关于族群音乐通史的研究,主要有乌兰杰出版的汉文版《蒙古族音乐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呼格吉勒图出版的蒙文版《蒙古族音乐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云峰的《纳西族音乐史》(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等。
关于专题史的研究大多数论文是以乐种为研究对象,或者以整个民族音乐的发展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述。秦序《我国南方高山、佤、苗等族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上)(《中国音乐学》,1985年第2期);秦序《我国南方高山、佤、苗等族体鸣木鼓与有关音乐起源的几个问题》(下)(《中国音乐学》,1986年第1期);伍国栋《长鼓研究——兼论细腰鼓之起源》(《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谷苞《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冯明洋《“百越文化”中的音乐》(《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边多《西藏堆谐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品种》(《音乐研究》,1988年第1期);赵星《略论“蒙汉调”的渊源以及艺术特征》(《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周青葆《中国维吾尔木卡姆形成发展史述略》(《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2期);边多《西藏民族音乐史略》(《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第1期)等。
专家学者们以不同论述角度对不同的考察对象,借鉴民族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和方法,梳理各民族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线索,研究探讨各民族的音乐历史。
二、乌兰杰先生的蒙古族音乐史学探索
随着少数民族音乐史在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专家学者们也意识到少数民族音乐史对于整个中国音乐史研究发展的重要性。各个少数民族的音乐史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蒙古族音乐史学研究中最有代表的是乌兰杰先生对于蒙古族音乐史学的研究。他的著作《蒙古族音乐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于2019年由远方出版社再版,再版的《蒙古族音乐史》在2020年12月28日获得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首届“杨荫浏音乐学术提名”奖。
阅读再版的《蒙古族音乐史》,可以发现乌兰杰先生将其初稿作了一定的修整。比如,标题文字表述的更改,将第五章的“北元”、漠北时期的音乐更改为北元、塞北时期蒙古族音乐;将第七章近现代蒙古族音乐(1911-1949)更改为中华民国时期蒙古族音乐;并在全书的最后增加了草原乐坛反思录。“漠北”与“塞北”的概念置换,“近代蒙古族音乐”与“中华民国时期蒙古族音乐”的更改,体现了乌兰杰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另外,在文字内容上,乌兰杰先生将初版介绍音乐家的顺序进行了调整,补充了从1998年之后所涌现的新人、新成果和新资料。内容上的补充和更新,为蒙古族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全面、详实的资料。
音乐史的分期问题,是音乐史撰写的核心和关键。赵宋光先生曾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分期问题讨论缘起》一文中指出:“音乐文化历史发展的分期划界,以往沿用史学界的习惯,以朝代更迭的事件及年代为界。但是在事实上‘文化滞后’是常见的现象。”赵宋光先生对认定分期界标的传统史学方法论观念提出了质疑,旨在提醒我们应该注重每个时期的社会音乐文化生活总体,只有从总体面貌定位,才能发现某些文化事象对总体面貌形式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不能完全照搬以往的音乐史分期方法,要结合每个民族的特点合理斟酌。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是以音乐的自身发展线索为轴心展开的,乌兰杰先生根据蒙古族社会发展的特点,将蒙古族音乐历史划分为三个文化形态时期——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时期、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半农半牧音乐文化时期,并以三种文化形态的演变为主线,遵循蒙古族音乐发展的特殊性,合理地解决了音乐史的分期问题。
乌兰杰先生在撰写《蒙古族音乐史》之前已做了大量的资料积累,曾相继出版《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和《草原文化论稿》(台湾“蒙藏委员会”印行,1997年),这两部著作是专门研究蒙古族歌舞文化的专题性论文集。《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共有16篇关于蒙古族古代音乐分析的论文,其中《蒙古乐风三变论》是乌兰杰先生第一次对蒙古族音乐的历史时间划分问题进行的系统阐述,为日后构建蒙古族音乐历史框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乌兰杰先生从音乐史、音乐形态、音乐美学等多个角度对蒙古族各历史时期的音乐题材进行研究,建立了蒙古族音乐史的宏观理论框架,为撰写《蒙古族音乐史》积累了丰厚的理论成果基础。乌兰杰先生经过20多年的资料积累和实地采风以及理论上的潜心研究,完成了从早期的专题史研究逐步积累成通史的研究。
乌兰杰先生撰写的《蒙古族音乐史》中关于蒙古族佛教音乐、蒙古族近代史部分和有关音乐形态的论述是相对较少的,但是他在《蒙古族音乐史》(1998年版)出版之后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又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蒙古族佛教音乐概述》(《音乐研究》,1999年第4期);《北方草原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交流中的整合现象》(《音乐研究》,2002年第1期)等。乌兰杰先生突破性的学术成果,丰富和完善了蒙古族音乐史的认知,为研究蒙古族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更加完善的研究方法。他孜孜不倦、务实严谨的学术作风,值得年轻学者学习。
乌兰杰先生曾较早接受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并运用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理论,根据蒙古族音乐发展的特殊性,以蒙古族音乐自身发展线索为轴心,结合整个中国音乐史的发展脉络进行全面、生动地论述,提出了以风格变换为依据的蒙古族音乐发展“三阶段论”。并对蒙汉文献以及国外的蒙古学相关文献进行系统、详实地整理,加上自己大量丰富的民间音乐第一手资料,架构了蒙古族音乐史研究的基本框架,运用文献、考古和今乐逆向考证的三重历史学方法,完成了蒙古族音乐通史的研究。乌兰杰先生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史学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在田野资料收集上,充分发挥了民族音乐学重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常年深入内蒙古各地牧区亲自挖掘一手资料;在文献资料的收集上,他不仅对传统汉文经史、蒙文文献做深入解读,还放眼到地方志中,去获得更充足的资料来源。另外,在研究视角上,乌兰杰先生注重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双视角”——即“主位”与“客位”观去撰写蒙古族音乐史。乌兰杰先生既是民族音乐学家,也是著名的蒙古族长调歌手,先生自己是“局内人”,同时又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客观评价分析蒙古族音乐。乌兰杰先生开辟了蒙古族音乐史的系统研究,奠定了蒙古族音乐历史研究的基础,为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撰写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推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贡献了积极力量。
三、蒙古族音乐史研究的总体进展
乌兰杰先生的《蒙古族音乐史》对于蒙古族音乐史和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发展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尤其对于蒙古族音乐的书写和诠释,以及对后续蒙古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都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笔者从中国知网(www.cnki.net)通过搜索主题和篇名两种方式进行了初步检索,查到从1996年到2020年为止,关于蒙古族音乐史研究相关的论文达144篇,其中最早即是乌兰杰先生在1996年发表的《蒙古族音乐历史轨迹初探》。研读这些成果,发现无论是论文数量和质量都体现了对于蒙古族音乐史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相关成果情况请见下图)。

面对蒙古族音乐史领域的研究,乌兰杰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曾说:“如果说我做了什么有益的工作的话,那就是我用20年的时间,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首先是一条竖线,代表着蒙古族音乐发展从古至今的一条时间轴;接着是一条横线,排列着草原音乐的各个门类--民歌、器乐、歌舞、史诗、宗教音乐、宫廷音乐等,以此构筑了一个理论框架。后来的学者们可以根据这个框架按图索骥或谱写新章,有所发展,有所发现,有所补充。”在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方面,乌兰杰先生及其蒙古族音乐史研究,对全国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史撰写具有引领性的意义。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除了乌兰杰先生的成果外,还有满都夫的《蒙古族美学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作者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对蒙古族的民歌、史诗、萨满音乐、器乐音乐等进行诠释,是一部难得的蒙古族美学史著作。蒙古族音乐史研究早期出现的优秀学者们,用自己的努力去探索研究蒙古族音乐的历史,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音乐理论观点。诸如,乌兰杰先生提出的蒙古族音乐史“三阶段论”和莫尔吉胡提出的蒙古族古代音乐传承的“多纳茨”论等,学者们根据蒙古族历史的发展特点,认真扎实地研究本民族音乐,深入研究蒙古族音乐历史的发展进程,为后续更加广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蒙古族音乐史的研究出现了大量优秀的硕、博论文。诸如,张琨琨的硕士论文《明清蒙古族音乐初步研究》,是以断代史的研究角度论述明清时期的蒙古族音乐发展概况,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明清蒙古族音乐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研究,通过对发展、体裁、风格和交流等方面研究,探讨明清蒙古族音乐的发展脉络,多角度分析了蒙古族音乐题材及其发展,从民族风格发展和地区风格形成特点来阐述蒙古族音乐风格,并从蒙藏、蒙汉两个方向探讨蒙古族音乐与其他民族音乐的交流与融合。王伽娜的《元大都音乐的初步研究》是从城市的角度观察元大都时期的音乐,通过对这一时期音乐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多角度探讨、梳理其城市音乐的基本面貌,总结元大都音乐在古代繁华都市中的特点、地位,并以民族关系的角度考察其音乐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情况。这两篇硕士论文都是通过梳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蒙古族音乐的发展状况,从多个视角对其音乐进行分析,以探讨这一时期的音乐历史发展脉络。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述过程中,这两篇论文都非常重视研究蒙古族与其他民族、地区的交流,并且将研究对象放置在整个中国音乐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这对于研究蒙古族古代音乐史以及中国古代音乐史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蒙古族音乐史专题性研究成果丰硕。张珂的硕士论文《乾隆乐队编制:分隔交融的满汉礼乐观》,着眼于乾隆时期蒙古族宫廷礼乐的情况,提出了蒙古礼乐在清王朝的重要地位,分析得出王族音乐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特点。张喆的《蒙古族宫廷音乐研究》,是以蒙古族宫廷音乐中的歌曲和乐曲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蒙古族宫廷音乐的类型、音律、传承等方面的研究,分析蒙古族宫廷音乐与传统音乐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挖掘蒙古族宫廷音乐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明清两代蒙古族音乐产生的影响。姜兆蕾的《论蒙古汗廷音乐的历史演进与恢复重建》,介绍了蒙古汗廷音乐的历史渊源,梳理了蒙古汗国时期、元朝时期及北元时期蒙古汗廷音乐的历史脉络。文章通过文献研究与记实相结合的方法,将古代音乐作品、现存文献资料与访谈、调查分析、演出记录等进行融合,多角度论述了蒙古汗廷音乐及其历史价值。这三篇论文都是以某一种音乐体裁为研究对象,对其音乐体裁进行细致的梳理与归纳,深入研究其意义与价值。
通拉嘎的博士论文《马头琴及其文化变迁》,选取马头琴为切入点,从艺术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的角度,论述整个蒙古族音乐文化的变迁轨迹,通过梳理马头琴的发展变迁过程,观照传统马头琴向现代马头琴的文化变迁,延伸到当代蒙古族音乐文化呈现的多样性问题,进而对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出建议。
纵观蒙古族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其中对于蒙元帝国和清朝时期的研究相对较多,其他时期的研究相对匮乏,并且关于乐种和音乐作品的研究也相对薄弱。在整个音乐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对音乐家的音乐行为、音乐理念以及艺术成果进行梳理、评价,来了解音乐家的音乐贡献与音乐思想;也可以通过音乐事件了解当时的音乐史实和音乐人物、音乐制度、乐律理论;还可以对某一乐种的发展路径进行细致地梳理,这些均可作为音乐史研究的切入点,以此探究音乐历史的发展进程。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持续关注并全面深入地探究蒙古族古代音乐历史,这不仅对于研究蒙古族的近现代音乐历史,更对于丰富和完善蒙古族音乐史学研究有着紧迫和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少数民族音乐史学研究的思考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硕果累累,特别是蒙古族、藏族、瑶族、侗族、土家族、鄂伦春、达斡尔等族群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目前只有蒙古族、藏族、纳西族、白族等有一定的音乐史学研究成果,而对于其他少数民族通史和单一族群音乐史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尤其缺乏对西南少数民族单一族群音乐史的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可大致归纳为区域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专题史的研究、断代史的研究和族群音乐通史的研究等,其中涉及乐器源流的纵向考察和乐舞的历时性研究较多,断代史、少数民族戏曲史(如藏戏、侗戏等)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史(尤其是同类型宗教音乐在不同族群之间发展史的比较研究)相对匮乏。对于族群研究中的某一族群不同支系音乐历史发展现状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尤其不够重视族源相近族群音乐史的考察,诸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少民族”音乐史的研究等。
我们在加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当前地方院校的中国音乐史教学中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汉文化中心论”与“西方音乐教育模式”的双重影响,导致少数民族音乐史的学科教学与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只有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开设了“少数民族音乐史”研究的硕士点,其研究方向是西藏音乐史。从师资来看,目前大多数音乐院校的中国音乐史教师多以传统音乐或理论作曲专业的教师为主,缺乏有史学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事教学工作。另外,少数民族音乐史的教学成果反映在教材和教学上面还很薄弱,很多学者的科研成果实际应用性不强,并不适合直接当教材,还有一些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没有被很好的按需所用,作为为教材的补充来丰富教学。根据笔者调查了解,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中对少数民族音乐的重视与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丰硕成果,比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内蒙古艺术学院和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两所高校,都开设了民族音乐的本科、研究生专业,还有特色的民族音乐传承班,都开展的有声有色。同时也发现,大多数学生对本民族音乐的表演艺术各有所长,但也有很多学生对于其表演作品的民族音乐特点、文化发展脉络等却不甚了解。高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和发展传承的重要阵地,对于民族音乐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会唱民歌、会演奏乐器、会跳民族舞蹈的技术层面,应该加强对少数民族音乐理论教学的重视,在教授学生作品赏析的同时,教师还应更好地向学生阐释其音乐表演背后的历史渊源以及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从现有的学术成果中按需择取,梳理补充,将学术成果融入到课堂中去,让课堂真正的丰富起来。
笔者曾经在内蒙古马头琴艺术学校担任中国音乐史的授课教师,由于学校的专业特殊性,学生基本上都是牧区招收的蒙古族学生,在课堂上发现大多数学生对于中国音乐史这门学科兴趣不高,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古代史部分音像资料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是以汉族音乐史为主的授课内容,学生们认为这门课与他们的专业有一定的距离感。如果我们能够将蒙古族音乐史与中国音乐史同时开课并建立紧密联系,让学生感受这两门课的交汇与融合,让学生自发的产生求知的欲望,这样的课程设置会让中国音乐史的课也跟着“活”起来。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教授学生音乐史学的基本知识内容,更应该让学生通过这门课程了解、掌握音乐史学所涉及和相关的学科知识,如音乐文献学、音乐史学等,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探索学习的热情。在音乐史的教材方面,陈荃有教授曾指出“我们课堂上所学习的中国音乐史课程,其实是由音乐史学家根据多年研究的积累所形成的基于客观史实的个人主观化认识”。作为授课教师,在备课时要对教学所需的教材上多下些功夫,博览群书客观地总结归纳,丰富补充学校指定教材上的知识点。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层次,多关注新的学术动态,及时将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从教授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方面来看,能力水平和专业性参差不齐也是造成地方院校中国音乐史课程的教学存在问题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借鉴民族音乐学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比如张天彤教授曾提出传统音乐课程的“四位一体化教学”——即教师+传承人+地方音乐家+地方学者。这种观念的提出旨在让知识变得鲜活,生动,不仅会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也让课堂教学变得丰富多彩。希望这样的教学理念可以被中国音乐史教学和少数民族音乐史教学充分借鉴和运用。
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应该做到跨学科研究,向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相关学科借鉴,运用多重证据法深化中国音乐史学的史证范式研究。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整体的治学观,还要有批判意识,在对比和思考中树立正确的史学观,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格局。中国音乐史学早已走出“书斋”接通历史,运用多视角进行综合、立体的研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孕育着他们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精髓,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联结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与汉族音乐的历史共同构成了中国音乐历史,要想让中国音乐史这棵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地完善和丰富各个民族的音乐史研究。“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只有维护和传承好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才能促进中国音乐文化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