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正义战争?
周艳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战争似乎就是人类文明挥之不去的顽疾。人类历史一再上演战争的悲剧,而且愈演愈烈,终于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顶峰。那么,战争能否得到道义的支持和合法性辩护呢?这是犹太裔美籍政治哲学家M.沃尔泽长期关注的一个主题。在其被公认为当代正义战争理论新经典的《正义和非正义战争》(Just and Unjust Wars)中,他对此做了深入而细致的探究。
1977年《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出版后,正义战争论便得到了极大的复兴。相关书籍、文章日益增多,而且,还推动了有关课程不仅在一般的大学甚至是美国的军事院校的开设。
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吗?
关于战争的性质,一直是难以表清的。不同的人根据不同原由,出于不同的目标和意义,对同一战争的性质亦可得出各种各样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
反战主义者把通过战争来争取和平看成是一种以恶求善的行为,而战争是跟暴力相联的,所以所有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自然主义者以人的自然普遍性为出发点,重视目的和动机,出于不道德的动机和目的而发的战争就是不正义的战争。他们往往坚持人权高于主权。现实主义者则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特别注重的是国家的利益和结果,反对将和平视为正义,例如以和平维持暴政就是非正义的。现实主义者更多的是坚守主权高于人权。
M.沃尔泽并不完全赞同其中的任何一种,他通过分析如下一些战争类别中的例子,将自己的观点隐蕴其中。
在所有战争形式中,对独立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的所有侵犯都称之为侵略。侵略挑战了人们值得为之牺牲的权利(rights)。侵略者的罪恶在于他们迫使男人们和女人们为其自由和安全权而卷入丧失生命的危险中,使他们陷入一种抉择:要权利还是要生命。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反应,有时是投降,有时是战斗,这要看他们国家和军队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怎样。不过,人们通常会选择战斗。
为此,M.沃尔泽对比了抢劫犯罪。抢劫犯罪也会让人们做出选择:要钱还是要命。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容易地做出回答,把钱交给他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同时抢劫犯也不会变成杀人犯,从而其罪恶相对要小些。但是,对于侵略却不能采取同样的反应。即便如此,侵略者没遭到反抗,其罪恶也不会有所减轻。正如1939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发动的侵略战争——前者在未做反抗(因而没有发生“流血”)的情况下丧失了主权,而波兰在抗战中死伤人员诸多并最终沦陷,战后的审判要求德国承担同样的罪行。
M.沃尔泽承认,许多实际上仍然只能算是暴力来源的20世纪的战争也不是完全的公平,或是采取了适当的方式。举一个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何种意义上的正义都站在武装反抗法西斯的这一方)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实施了大规模的经过精心策划的对平民的轰炸以便达到摧毁对手民心和生产力的目的。如果说,这种被同盟国委婉地称作“战略性轰炸”的策略,是对国际法赋予的公平原则的背离,那么,1945年8月美国做出的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决定的背离,又将是多么严重呢?难道这种戏剧性的背离真的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所必需的吗?难道只有使用原子武器才能尽快地结束太平洋战争吗?
由于存在这些对平民免疫原则的无视,M.沃尔泽提出,这些在二战中对“正义战争”原则的极大背离,鼓励了无政府组织采用恐怖主义的方式:“从严格意义上说,恐怖主义就是随意地残害无辜平民,它只是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里表现为一种革命斗争的策略。在那之后成为常规战争的一个特征。”
正义战争必须是防卫战吗?
“正义战争”观念在西方社会已有很久的历史。例如,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载有大量演说词,参战各方频频使用“正义”“非正义”为自己辩护或抨击对方。
M.沃尔泽认为,正义战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战争必须具有正义的理由和正义的手段: 第一,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可以合法地使用军事力量;第二,战争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正当地进行。
“正义战争是有限战争。”有限战争在战争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进行着有意的克制,如目标、战争持续的时间和空间、有效目标的选择、使用的武器和手段等等。任何战争都会引起伤亡。正义战争之所以被称为正义战争,关键就在于正义战争的领导者能够尽最大可能避免伤害无辜。这一原则立场构成了正义战争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道德意识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战争论上的一种体现。
这意味着,对于本国人民而言,如果肯定战争会导致本国大部分生命的毁灭,那么,这样的保卫战就会丧失其正义性。换言之,战争的目的再好,如果手段特别不当,就会导致战争的性质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对于敌国人民而言,在极端不幸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无辜民众的伤亡,必须完完全全是由于战争的副作用,而这副作用是由一种为了阻止巨大灾难或为了实现一种更高的道德目标的行动所导致的,且这一行动又是极为紧急和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说,正义的战争是存在的,但它必须是防卫战。尤其要避免因滥用暴力,造成更为严重的、特别是从全局和长远看得不偿失的非正义后果。由人道主义干涉引发的战争,就是正义战争。
用一次战争结束所有战争能实现吗?
战争的行为是另一个直接影响战争正义性的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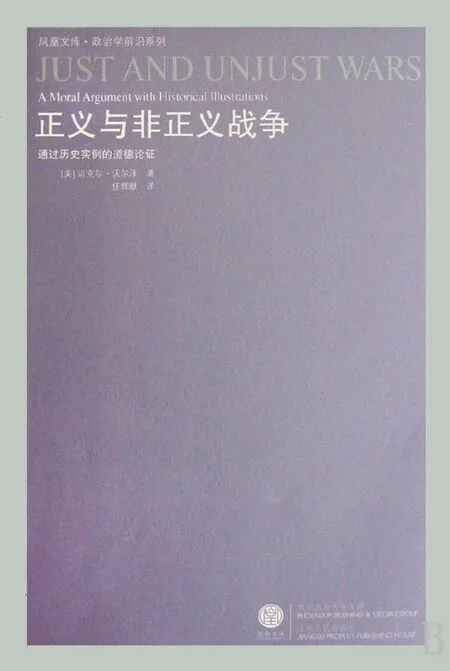
>> 资料图
自然主义者认为,必须用同样的道德法则来制约战争理由和战争行为。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每个士兵,都必须按照道德原则来从事战争。这些道德原则包括,不得为仇恨而战,不得为杀戮而战,不得以无辜平民的生命作为战争手段,应当尽量避免战争的伤害和破坏,应当区别对待军民和不杀害非战斗人员,等等。那些显然以平民为目标的军事或暴力攻击,则绝对是必须谴责的恐怖主义行为。现实主义者也主张约束战争行为,但它是从后果决定论出发的,这和从普遍的仁慈原则出发不一样。政治现实主义者提倡适度暴力,这是因为暴力行为的目的一旦达到,暴力便无须再继续下去。它重视自己人的伤亡远甚于对方的伤亡,所以会采取一切军事手段,尽量降低己方伤亡。
M.沃尔泽则强调,正义战争应当不伤害无辜的平民,即使是在封锁时期,也必须保证食品和医疗物资得以流入,哪怕这些人最后可能会因为战争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及其引发的各种疾病蔓延等而死亡。此外,他坚决反对炸毁电力、供水等民生必需的设施。在这一点上,两个最基本、最广为承认的人权(生命和自由不受剥夺)有着决定性意义。此外,正义战争还应当确定一个适当的、有限的目标,一旦胜利,战争就应停止。他主张战争意在“恢复”而非“报复”。否则,它将与侵略战争类似。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战争也是残忍的,它“播种的是正义,收获的却是死亡”。
战争中的正义,要求不伤害已经放下武器的投降军人。不过,M.沃尔泽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当溃不成军的敌人逃亡时,我们是否仍有道德权利屠杀他们?这些逃亡的军人不同于投降者,他们有可能还会卷土重来进行战斗,或者被利用以镇压内部人民。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基于美国的情况。他们一直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一方面要发动干涉战争,另一方面又不能突破干涉的底线,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困境。
M.沃尔泽主张,战争伦理只是一种稀薄的价值,一种关心禁止甚于关心提倡的伦理。战争伦理关心的首先是如何在战争与不战争、约束与不约束之间进行选择,而不是如何建立一种正义的国际秩序,以使战争永远消除。想用一次战争结束所有战争,获得永久和平,不再有任何武装斗争等,不过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这无异于想让狮子与羔羊和平地偎依在一起。
因此,正义战争论也有它的局限性:一方面,它认识不到或掩盖了现存的国际利益格局和国际关系的不合理性及不平等性。另一方面,在各文化传统对正义的理解尚存在分歧、各国之间对某些国际争端的解决尚未形成道德共识的情况下,正义战争论为超级大国利用其军事优势追求它们所理解的“正义”的霸权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辩护。正义战争论对先发制人战略的肯定,更是为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行为提供了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