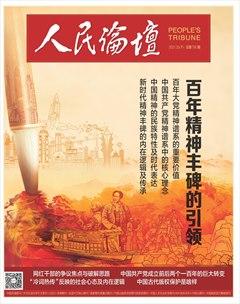网红干部的争议焦点与破解思路
李春成
【摘要】干部当“网红”至今已存续十余年,并呈现出从零星化、业余化向规模化、长期化甚至专业化的发展态势。民间议论多持赞赏态度,但也不乏质疑之声。只要规范得当、未来发展“不走调”,“网红”干部就会因政治立场坚定,行动上契合互联网逻辑,经济上能够带动地方发展,从而在争议中不断规范、在规范中不断调适、在调适中不断发展。
【关键词】基层干部 网红 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互动式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云端多渠道整合平台的发展……不仅更新着“在者”的存在效能、内容和空间,而且还与“在者”共同进化出一些新的存在形态,譬如职业性的游戏导播、网络直播、网络创业者,以及其他非职业性的网络红人(简称“网红”)。较之普通民众,机关干部对待网络的态度更加谨慎,更具风险意识,但仍有一些干部积极融入互联网时代潮流,“在网络平台或现实生活中因为某个举动或事件而被广大网友知晓关注且因此走红”,成为“网红”干部。
迄今为止,我国出现了三波“网红”干部。第一波是“微博元年”(2010年)前后的“大V”官员,如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原主任陈里、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巡视员陈士渠、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原副主任陆群、广东省卫生厅原副廳长廖新波等。他们大多扮演关键民意领袖(KOL)的角色,通过微博回应民意、批评不良风气、评论社会热点事件等,因言论而走红。第二波“网红”干部盛产于“中国网红元年”(2016年)前后,与第一波“大V”官员主要通过言论意识流引发作为“读者”的网民的广泛关注、旨在伸张正义弘扬正气不同,第二波“网红”干部主要通过具有事件效应的个人化行为短视频和直播吸引作为“看客”的网民的注意力,实现为地方代言的目的。典型例子有原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为宣传当地旅游录制MV、直播3000米高空跳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县委书记董斌直播烧鱼,安徽淮南市九龙岗镇女副镇长王雪自费拍写真为家乡代言,山西省万荣县县长李永辉摆摊为当地三白瓜吆喝等。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线上消费需求剧增,许多基层干部进入网络直播平台,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等为地方特产和旅游业拉流量、做广告,成为第三波“网红”干部,人们称之为“流量”干部。譬如新疆伊犁昭苏县副县长贺娇龙、黑龙江大兴安岭塔河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都波、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80后”县长组合等。所谓“流量”干部,是以公职身份背书,通过个性化言行在互联网上吸引网民注意力,并将其导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干部。较之第二波“网红”官员,第三波“流量”干部呈现出诸种不同:人数规模显著增大,借助专业的直播平台,引流活动更具连续性,深谙“网红经济”之道,直播和短视频的制作水平明显提升,对网民的期望也从“看客”升级到“消费者”。总之,有规模化、专业化、长期化的发展势头。
干部当“网红”的争议焦点
干部当“网红”呈现出从零星出现到波浪式、规模化的发展趋势,民间议论多持赞赏态度,但也不乏质疑之声。概括起来,争议的焦点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
“网红”干部是否有损干部形象?自古至今,人们对衙门中的当差者、机关中的公务员都心存敬畏,正统的干部形象似乎应该是低调、严肃、去个性、讲话带官腔、举止有架势。第二、三波“网红”干部为了吸引网民注意力,唱歌跳舞秀才艺、骑马跳伞卖吆喝等,“喜欢搞些夸张的言论和动作而博得眼球”。在批评者看来,这些都“不成体统”,有损官员形象。然而,支持者却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官老爷的形象早就该被淘汰了,如果官员言行不令老百姓喜闻乐见,大家会觉得没有亲和力,没有魅力,甚至对其执政能力产生怀疑”。“那种愿意走下权力神坛的官员,他们失去的是官员的架子,得到的是老百姓的欢迎,这应当是官员最有面子的事”。如今,官员的形象应该是亲民、爱民、为民,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评价标准。
“网红”干部行为目的是否正当?在缺乏既正统又有效的手段的情况下,“网红”干部与其他“网红”一样,都是通过一些个性化的、生活化的甚至夸张的、奇特的表演来吸引网民的注意力。在批评者看来,这就是在搞“个人秀”、炒作自己、把自己明星化。然而,支持者却认为,“网红”干部为了地方发展、民众利益,牺牲自己的(部分)业余时间与精力,奉献自己的才华与智慧。而且目前看来,“网红”干部的网络言行有利于弘扬主流价值观、宣传地方特色、推销地方特产、推介地方旅游等。
“网红”干部是否“不务正业”?批评者认为,党政干部是党和政府部门的成员,其岗位职责在于履行和实现党政部门的公共职能,而推销特产、宣介旅游等活动显然不属于党政组织的法定责任,因此,即使官员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从事网红活动,也是分外之事、“越界”行为,只能作为个人业余奉献。进而言之,既然只能是业余活动,就不能使用公职身份;否则,就有不当竞争之嫌。针对这种批评,支持者的辩护是:首先,“网红”干部主观上没有与其他“网红”竞争的意图,客观上也未构成对其他“网红”的威胁,更谈不上搅乱市场秩序;其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公共利益是政府公共治理的目标,因此,只要“网红”干部活动的目的是为民谋利、谋求公共利益,那么,它就是干部的“正业”,当然可以利用公职身份来“务正业”。
“网红”干部在经济上是否划算?即使“网红”干部的身份、目的、手段的正当性都没有问题,但如果“网红”干部在成本—效益上没有优势的话,仍然缺乏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由于明星代言成本较高,不少地方政府官员亲自“披挂上阵”。可以说,“网红”干部的原生逻辑正是经济逻辑。除了活动本身的花费(如策划、录制、道具等)以外,如果占用工作时间就还要计算“机会成本”(“网红”干部在活动时间从事其传统本职工作所产生的效益),以及“网红”干部的言行可能产生的(政治)风险成本。从逻辑上讲,至少到目前为止,“网红”干部不收代言费,并且奉献了一部分工作之外的时间,加之干部代言短视频、直播带货尚属网络热点,因此是经得起成本—效益检验的,经济上是划算的。
搭载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互联网正日益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加速深化人类社会的演进,不仅改变着国家治理的空间和对象,而且激荡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变革。有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互联网发展之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除了技术支撑、信息安全之外,还意味着什么?除了建设政府网站、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重视网络信息安全之外,还应该重视一个事实,即国民时间、国民注意力、国民社交空间已经“上网”,国民基本上“网民化”。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我国31个省(区、市)均已开通政务机构微博、政务抖音号,各级政府共开通政务抖音号26098个。政务新媒体可以发挥哪些功能?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这方面“网红”干部无疑是公共部门中的先行者。如果说“注意力是互联网的第一推动力”、网络空间中“注意力为王”“流量就是王道”,那么,我们就需要大量懂网络、善用网络的“网红”干部,需要大量善用短视频和直播的“流量”干部。
“网红”干部规范化管理的基本思路
尽管人们对“网红”干部还存在质疑,但是,只要规范得当、未来发展“不走调”,那么,他们就会因政治立场坚定,行动上契合互联网逻辑,经济上能够带动地方发展,从而在争议中不断规范、在规范中不断调适、在调适中不断发展。
首先,在中央出台统一规范文件之前,地方组织人事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管理规定。主要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一是要肯定“网红”干部尤其是“流量”干部的作用与意义,为其“正名”,并号召广大党政机关干部学习他们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如何走群众路线、如何利用新媒体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公共利益的精神;二是将干部利用互联网和政务新媒体开展工作纳入工作职责范畴,并对工作之外的此类活动给予表彰和必要的资源支持;三是明确要求相关部门积极支持和配合“网红”干部的活动,构建相关平台;四是要明确规定“网红”干部行为的目的必须是为民谋利,禁止干部以公职身份背书进行纯粹的个人炒作;五是制定“网红”干部行为的“负面清单”,譬如不准违背公务员的法定义务,禁止有违党纪国法的言行,禁止有伤风化、激起公愤、制造社会矛盾的言行,禁止显失公平的选择性直播带货,禁止接受受益者的馈赠,禁止利用公权力和组织力量制造虚假流量,等等。“有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不但流量注水、销量造假、大搞摊派,还组织水军齐呼‘领导好帅”的做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值得高度警惕。预防政治风险应该成为“网红”干部管理的重点。此外,如果有必要,还可建立“网红”干部遴选机制。
其次,除了向互联网专业组织和专业人士咨询和学习以外,地方党政领导和“网红”干部还应积极探索工作的发展路径,创新公共部门“流量”工作机制。一般来说,那些让网民感觉到有关系、有好处、有意思、有期待、有情感的內容,更能引发他们的关注和分享。因此,在信奉自由平等的互联网空间,在不触犯“不忘初衷”和“负面清单”的前提下,“流量”干部可以适当地使用网络语言,还可以将一些符合政务公开或以往通过其他方式公开的、老百姓比较关心和感兴趣的线下业务行为,如领导调研、行政执法、政府服务、公益活动甚至一些会议等,进行网络直播或“脱敏”处理后制作成短视频。这种盘活“存量”、以“存量”换“流量”的办法或可明显节省成本。此外,对“流量”干部直播带货或文旅宣传而言,以点击量、关注量、回帖量、转发量等作为评价指标的网络流量本身不是其工作目的,销量才是目的,因此,还应该考虑如何提升流量到销量的转化率。参照企业界“流量经济”的发展经验,公共部门的“流量经济”工作不能止步于发挥供需中介联结作用,还应该优化整合线下“存量”,发挥“中台”的作用,促使“流量”干部实现由“ego”(个人)向“eco”(生态)发展,譬如促进地方“供方”企业或个人的整合、优化营商环境和消费体验、强化产品质量监测,为销量提供公信力背书等。
最后,互联网经济已经出现从“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向“意愿经济”(Intention Economy)发展的态势。“意愿经济是围绕着用户的消费意愿来组织整个服务体系,从而使消费者获得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同时降低商户寻找目标客户的成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民情民意,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新治理”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这对于摸清网民的消费意愿、提高流量转换率、促使流量工作向意愿工作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信网,2021年2月3日。
责编/银冰瑶 美编/王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