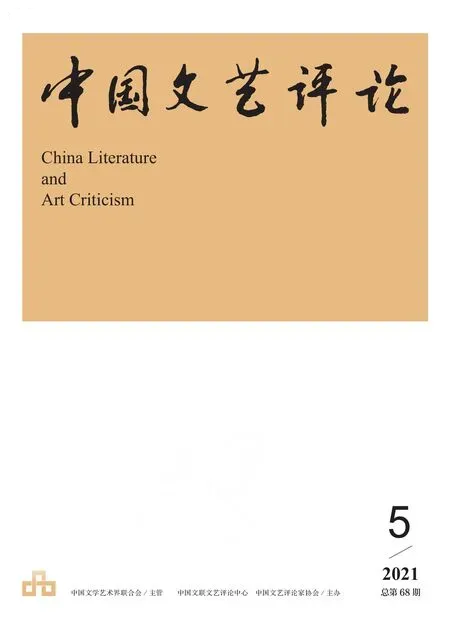在实践中开拓中国西方现代音乐的研究之路
——访音乐学家钟子林
采访人:韩江雪

钟子林简介:
浙江杭州人,生于1933年1月,西方现代音乐研究专家,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6月至1955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华东军区)特种纵队文工团队员,1956年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后转音乐学系,1960年留校任教。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开设课程有中国民歌、西方现代音乐等。中国西方现代音乐研究、流行音乐研究的开拓者,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的重要建设者。曾应邀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和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讲授中国音乐,同时在美国耶鲁大学、东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中国音乐学术讲座。2000年中央音乐学院建院50周年获杰出贡献奖。主要著作有《西方现代音乐概述》、“20世纪音乐”(《西方音乐通史》第七编)、《摇滚乐的历史与风格》等。一、忆学术生涯:从音乐创作到理论研究,从民族音乐到西方现代音乐
韩江雪(以下简称“韩”):
钟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作为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科的建设者,以及西方现代音乐最早的研究者,您能否讲讲您的学术生涯以及其中令您印象深刻的经历?
图1 1949年,钟子林参军
钟子林(以下简称“钟”):
关于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总体来说可以分成两段,从1979年到现在,我是在从事西方现代音乐研究。而在此之前的经历,现在看来都可以看作是准备。这些准备主要是作曲、西方传统音乐学习以及民族音乐的采集和调查。我想还是从1949年讲起。上海是1949年5月25日解放的,同年6月底,大概6月30日我就去了部队文工团。1949年当年就下连队。当时下连队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辅导连队的文艺活动,另一个就是体验生活。那个时候很重视这个,因为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要创作表演反映部队生活的文艺作品,就要去了解、熟悉他们。所以,我们经常下连队和战士们一起生活。同时,也进行一点创作。文工团大概有二三百人,大家到连队去回来后都会交上来作品,这样就形成了一批歌曲,当然也有小剧本等。从歌曲来说,交上来的很多。团里就选择可以由我们文工团自己表演的歌曲,就选了两首,这两首都是我写的。那么这就变得很突出,因为那个时候我才16岁,还是一个中学生。我记得那个时候,团长非常鼓励我,希望我在音乐创作方面可以做一些努力。文工团有一段时间成立了创作组,我成为了创作组的成员,我们那个文工团是特种纵队的,不是大军区的,所以很难有专职搞作曲的,搞作曲的都是演奏人员。后来,特纵文工团解散,我又到了师文工队,当了一年的文化教员。韩:
后来您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开始走上音乐创作和专业音乐的学习道路,那段时间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钟:
1956年,我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上海音乐学院我也考取了,不过我选择了去天津。那个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是1958年才搬到北京来的。在作曲系的时间大概是从1956年到1959年。这也可以算作一段。期间,我还去了青海一年,到青海去收集民歌,收集土族、撒拉族和藏族民歌。1959年到1970年,又是一段,包含了“文革”初期。如果说在音乐学院这几年,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那应当就是姚锦新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在我心中,从对我的影响来说没有任何其他一个老师可以跟她相比。当然别的老师也都很优秀,我也从他们的教学中学到很多东西,如和声、复调等。当时我在作曲系,主要学习四大件,跟姚先生学习作品分析。从治学来看,姚锦新本人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人,她到德国、美国留学,见识很广,本身有很好的老师教,钢琴也弹得好,刚回国的时候原本是请她去钢琴系的。在她的作品分析课上有时是同学来弹,有的时候她就自己弹,她的课对我影响很深。这期间所学的是作品分析,还有别的课程,当然那个时候举的例子都是西方古典音乐,举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例子,因此听了很多这方面的音乐。那个时候也有民族音乐的课。中央音乐学院那个时候课比较少,还不像现在,主要就是作曲四大件、民族音乐的课程,还有就是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这几门课。不像现在有音乐美学、心理学等各种各样的课程。我主要在作曲这个方面。在民族音乐方面,我们有民歌、说唱、戏曲等课程。
韩:
后来您逐渐开始了西方现代音乐研究,是在什么机遇的推动之下开始的?
图2 1959年,钟子林在青海玉树采集民歌
钟:
197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德伦把我们几个人调到《光明日报》去,就开始搞西方音乐。在此之前我是民族音乐教研室的。去《光明日报》就是要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音乐,是江青提出来的。我们一共四个人,有吴祖强、韩里、黄晓和和我。他们三人都是留苏的,其实为什么把我找去我也不清楚,但是这个经历的确是我接触西方20世纪音乐的开始。所以我很感谢李德伦同志。说起来,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批判,也不可能批判。因为,什么是修正主义,完全是政治上的概念。所谓的批判对象是以肖斯塔科维奇为主的一系列的苏联音乐家和他们的作品,能批判他们什么呢?但是对我来说,倒是听了很多的苏联音乐。因为要批判,就要先熟悉。但是事实上后来也没有结论。我们所写的东西,“苏联音乐概况”“苏联音乐家的言论集”等,由《光明日报》用很大的字排版印刷,然后往上送。所以,那一段我主要就是研究苏联音乐。后来音乐学院要重新开课,重新教学,我们又回到音乐学院。因为我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音乐的,属于外国音乐史的领域,所以就参加了西方音乐史教研室。“文化大革命”后,我就从本来的民族音乐教研室到了西方音乐史教研室,就弄起西方现代音乐来了。周文中1977年来中国,送来很多现代音乐唱片,后来图书馆也买来了很多唱片,我有多少听多少,边听边看乐曲介绍,然后在学校做一些介绍讲座。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介绍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像江定仙、喻宜萱这样的老教授都来了,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李佺民,廖乃雄老师刚好在北京也远道赶来听。讲座上介绍了周文中的《渔歌》、瓦雷兹的《沙漠》、乔治•克拉姆的《远古童声》等。应当说除了周文中,这些作曲家当时都没人听说过,不知道他们名气如何,更不知道这些作品在现代音乐创作中是什么位置。后来,我还介绍过大家现在都比较熟悉的勋伯格的反法西斯的十二音作品《华沙幸存者》以及他的《五首管弦乐小品》、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选曲、潘德列茨基的《广岛罹难者的哀歌》、梅西安的《异国鸟》等。这样我就开始搞西方现代音乐,名正言顺地变成了西方音乐史教研室的一员。1979年是个时间节点,教研室开会、分工,让我搞西方现代音乐,1981年正式开课。二、探索现代音乐研究:理论认知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
韩:
您的艺术生涯以作曲起始,后来到青海采集民歌,还对其中一些具体问题如“阔步型”六度等做过研究。您认为这些学习和研究经历,与您后期所做的西方现代音乐研究是否有关联?钟:
接触西方现代音乐不久,我就有一个认识,它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不只是了解一段历史。我曾经接触的民族音乐对于我研究西方现代音乐也是有用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所对比。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的就是西方现代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共通之处,文章没有公开发表,是我在美国的一次讲座。这种共通之处,具体来说有几个方面。首先从音高上,比如勋伯格1912年创作的《月迷彼埃罗》,我们介绍这个作品,会说它是先锋的东西,是语言和音乐的结合,用的是念唱音调(sprechstimme),其实就是说唱。而说唱,中国很早就有了,在西方人看来,它那么先锋、前卫,是一种创新技法。但是我们唱和念的结合有很古老的传统,在民间音乐中有很多。杨荫浏先生说过,除了说唱音乐,民间的叫卖声调,吟诵古诗词的音调,这些东西都有待被吸收到专业音乐创作中去,还有大量的可开掘的空间。再比如说,瓦雷兹1931年写的《电离》这个作品,成为西方第一首著名的打击乐曲。它被说得那么重要,其实就是一个由打击乐组成的作品。反观中国,我们的打击乐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汉书》和《礼记》上记载先秦就有打击乐乐谱,而民间流传的打击乐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我们曾经请民间的打击乐团在音乐学院大礼堂表演,那种打击乐的表现力真的很丰富。钹有很多打法,亮打、闷打、侧打、揉打,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的表演是那么投入,很自在,很热闹,没有什么禁忌,就像过年大家凑在一起玩儿,有时还把钹甩起来。我后来得出一个观点:西方现代音乐的反传统为中国作曲家更好地继承我们自己民族的传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作曲专业原来就是学四大件,音乐创作事实上就是按照19世纪民族乐派的路子走的。曲调是中国的,但是要学作曲四大件,即和声、复调、曲式、配器。和声呢,也尽量想办法做到民族化。想办法避免I-IV-V-I,使功能倾向性不那么明显。总之,在西方传统音乐的框架里进行民族化。这是不是一条路子?是,这条路子应该被充分肯定。我们做出了成绩,有不少成功的作品。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音乐中还有很多独特的东西被排除在专业音乐创作之外,这和我们的专业创作受到18、19世纪西方传统音乐框架的限制有关。然而1945年以后,西方作曲家自己突破了自己的传统,成了“现代派”,而这其中,结合东方因素恰恰成了现代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韩:
西方作曲家将视角转向非西方文化,这在西方现代音乐创作实践中并不罕见,能否请您再谈谈中西交流与碰撞中中国音乐传统的当代认知与呈现?钟:
如何看待传统的问题,我觉得传统当中,有些东西反映了中外共通的艺术发展基本规律,不能违背。但是也应该看到,传统中有一些就是习惯,而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当我们习惯了“四大件+民族曲调”,就会产生错觉,认为这就是“民族音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如果你了解西方现代音乐,通过它可以把眼睛朝向中国传统的东西,重新把中国传统音乐作为出发点,在我看来,这就是另外一条路子。例如,中国的旋律没有和声,但旋律本身有很多装饰,有很多细致的变化,音色很丰富。组成旋律的音,有人称它为“腔音”,这个名词起得很好,它有细致的音高、力度、音色上的变化,区别于西方音乐中具有固定音高的“乐音”,也很难记谱。怎么把它表现出来,靠配和声表现出来吗?借鉴西方现代音乐手法,可以启发中国现代音乐创作,找到新思路。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韩:
的确如您所说,现代音乐提供了一条可供中国专业作曲家继承本民族传统的新思路。那么现代音乐本身有技巧的拓展,也有理念的反叛,您认为现代音乐本身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或者最重要的研究价值是什么?
图3 20世纪80年代,钟子林参加会见访问中国的波兰作曲家潘德列茨基
钟:
西方现代音乐的价值我想主要在于对音乐进行了各种实验,这是它对世界音乐的贡献。首先,它可以让我们打开思路,而不是继续沿着19世纪民族乐派的这一条路子来创作,这里面就包含了你所说的理念的反叛,以及必然带来的各种新手法的出现,比如音乐是不是一定要有调性?无调性音乐、十二音音乐作出了回答。又如,音乐是不是一定由乐音所组成?噪音音乐、具体音乐、电子音乐作出了回答。再如,音乐是不是“有序”的,一定要有“组织”?偶然音乐作出了回答。当然,对于这一点,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序”“无序”也是相对的,完全取消“有序”,也就是等于取消音乐,一定程度地使用偶然手法,未必没有效果。举个例子,林乐培曾经写过以《窦娥冤》为源头的《秋决》,其中有一段,他用擂琴来模仿戏曲里面的说白“冤枉啊”,擂琴之后胡琴等声部就陆续进来了,再后来声部越来越多,各个声部都在模仿“冤枉啊”,直至最终形成冤枉声一片的效果。它很明显是采用了一定的偶然手法,这个手法有没有用?事实证明演出效果不错。西方现代音乐扩充和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手段,我之前在文章中也提到过,如多调性,虽然是1945年之前出现的,但是是现代手法,朱践耳在《黔灵素描》中采用了;十二音手法,罗宗镕在《涉江采芙蓉》中使用了;“音块”(tone cluster)手法,谭盾在《离骚》中使用了;具体音乐手法,王立平在影片《戴手铐的旅客》序曲中采用了,都受到了好评。因为这些手法的运用都经过了作曲家的分析、消化和处理,符合作品表现特定思想内容的要求。所以,手法不嫌多,也没有好坏之分,就看你怎么使用。韩:
从研究层面来说,西方现代音乐的研究与传统的西方音乐也不太相同,您认为现代音乐研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钟:
我想,首先,西方现代音乐很需要研究。有人认为,比起现代音乐,我们应该更多地研究传统音乐。我不这样认为。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同样应该研究。当然,作为个人选择,我们应当尊重。但是从道理上来说,两者不可偏废。对西方现代音乐来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把实际情况了解清楚,要实事求是。有些讨论在进行的时候显然并没有把实际情况弄清楚。当初学界刚开始搞现代音乐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是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改革开放的潮流太大了,西方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依然还是进来了。对于西方现代音乐,原先认为西方现代音乐就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都是腐朽、没落的,其实使用的都是一些苏联传过来的人云亦云的评价,因为那时实行“一边倒”,但事实上,大家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即便20世纪7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如果看杂志,还经常会有花絮的小文章,来讽刺西方现代音乐。当然,西方现代音乐中,也会出现一些故弄玄虚的东西,瞎胡闹的东西,但那不是主流,在西方也是没有市场的。比如,演奏家爬到钢琴里面去,让钢琴来演奏他,指挥看着蝌蚪游动的上下来决定音乐上的高低变化。当然,良莠不齐的现象,无论在哪个时代的音乐发展中都存在。但是也要看到,传统是发展的,不是僵死的。音乐在当下需要继续发展,需要开拓者。开拓和发展需要有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有些东西将保留下来,有些东西将被淘汰。我们应该允许探索,鼓励创新。韩:
我记得您在文章中提到过现代音乐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抱着一种向前看的态度,您可以举一些例子具体说一说吗?钟:
可以。20世纪以前的古典音乐演出,观众都是比较安静的,很有礼貌的。可是到了20世纪,反传统的音乐出现了,听众席中就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有时甚至争吵起来,吵得不可开交。比如著名的舞剧《春之祭》的首演,遭到了部分观众的嘲笑和反对,后来勋伯格的音乐会也是如此,因此勋伯格就成立了私人演出协会,关起门来,不邀请一般的听众和评论家参加。但恰恰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成为了20世纪音乐最有代表性的两位大作曲家。再如巴托克,也是20世纪的重要作曲家,有人赞赏他和传统结合的那一面,也就是民族性的那一面;有人推崇他不谐和的那一面,就是和现代音乐语言相结合的一面。又如噪音音乐最后是以失败告终了,但是这种扩展新音源、探索新音响的做法,影响了拉威尔、奥涅格,特别是瓦雷兹等一批作曲家。二战之后出现的电子音乐,一方面是科技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噪音音乐在新时期继续实验的产物。现在的音乐会,如果有实验性的现代音乐出现,演出很少坐满,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到场聆听,听众也都很热情,热烈鼓掌。大家尊重个人的爱好,很少出现起哄的现象,这是一个进步,也说明现代音乐已经扎下根来了,已经有了一批观众。韩:
您曾在文章中谈到音乐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您认为研究音乐中的现代与后现代有什么价值?钟:
关于这个问题,我只写过一篇文章,当时是为了商榷。之所以商榷,主要是两个问题,因为有学者提出20世纪初是反浪漫主义的;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进入到音乐的后现代主义时期,我认为说的不符合实际。当时的想法就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作为讨论的一种意见。这种说法为什么不妥呢?首先,所谓的20世纪初的音乐是反浪漫主义的,而表现主义,它其实是继承浪漫主义的,怎么会是反浪漫主义的呢?表现主义最重要的就是以勋伯格为主的新维也纳乐派,而他的音乐根源在晚期浪漫主义,其音乐语言中的“无调性”是从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半音化发展而来的。还有后现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被认为是后现代了,这个也不对,五六十年代正是实验音乐高潮的时候。事实上音乐上的后现代大概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事情。现在人们更多地认为是20世纪最后25年。美学界可能有人认为后现代就是瓦解、解构,但是音乐上不是,音乐是“回归”,消融传统与求新之间的隔阂。韩:
那您认为后现代音乐有什么特点呢?钟:
也是在我刚刚提到的这篇文章里,我最后总结了后现代音乐的几个特点:一是多元,在后现代音乐中,没有哪一种流派或风格的音乐占据绝对主流,打破了序列主义音乐“一统天下”或现代与传统两极分化的单调格局。二是兼容,在一部作品里综合运用各种创作方法,不同风格音乐的“并置”成为普遍现象。三是可听。当然,这些看法不一定正确。之所以这样认识,是因为接触到了一些文字材料,但也和1993年至1994年去美国实地考察有关。当时我听了很多音乐会,有公开演出的,也有学校内部的,和作曲家交谈,对他们访问,也与我形成这样的认识有关系。这个问题比较重要,因为涉及西方现代音乐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我们应当了解。但你要问我眼下西方音乐是什么样子,我真不知道,因为我脱离的时间太长了。韩:
您对当代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如何评价?您认为中国当代的专业音乐创作是否有形成“流派”或者“学派”的基础及条件?钟:
我们当下的专业音乐创作是否可以形成流派或者学派,我之前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一个学派能够真正形成,有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当音乐创作、学术积淀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这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并不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事实上,中国当下的作曲家们的创作的确有共同点,他们不约而同面向中国传统的东西,把这些传统的要素和西方现代的音乐相结合。流派可以是泛泛的,如中国流派,也可以是有特定指向的,如包括哪几个作曲家。不管怎么样,流派总需要有人承认,被大家所接受。要有一定数量的作曲家,有代表性的作品,虽然其中的作曲家依旧会突出自己的个人风格。比如当初的新潮音乐,指向是非常明确的,指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那一批人。西方的音乐流派,比如说“六人团”,之所以能够被大家承认是因为在他们的创作中有共同的东西,评论者当时撰文称其为“六人团”,最终在历史书写中成为六个人的团体,但是事实上他们主观上没有组成团体的意愿。中国的作曲家也是这样。中国的作品在国际的作曲比赛上屡屡获奖,音乐创作水平很高,这方面与西方不相上下。比如说青年作曲家梁雷,在美国变成继谭盾之后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他荣获2020年格文美尔作曲奖,是古典音乐界最负盛名的奖项。国内音乐学院现在也有一批年轻的作曲家,作品很有独创性,像郭文景、叶小刚和瞿小松,他们作为作曲家就是写自己的作品,专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流派或者学派是不是通常由理论家在评论中提出?我对这个问题没什么研究,所以没多少发言权。三、评大众音乐文化:流行音乐同样需要学术研究
韩:
您是国内学术界最早研究流行音乐的,您曾研究过爵士乐、摇滚乐的历史发展、音乐类型等,还曾真实记录过在美流行音乐的真实情形。这些研究不仅从知识上,还从理论层面为后面流行音乐的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流行音乐在大众的文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也有很多观点认为,艺术性与大众性是矛盾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钟:
流行音乐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它是一种大众文化。比如摇滚乐,不论是从思想内容、艺术趣味还是表演技巧,一般来说都很难和古典音乐相比。它们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艺术。但是摇滚乐很有市场,深入到千家万户和各种公众场合。你可以不喜欢它,但是不能无视它。音乐本来就有雅俗之分,在过去,俗音乐主要是民间音乐。而雅俗并非形同水火,民间音乐对专业音乐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大作曲家的创作显然更精美、更高雅、更有艺术性,但不能脱离民间音乐,后者是创作的养料和素材。进入20世纪之后,流行音乐慢慢替代民间音乐成了俗文化的代表。它的地盘不断扩大,民间音乐的地盘在缩小,再加上民间音乐的流传本来就受特定区域的限制,所以,流行音乐成了俗文化的主要代表。既然流行音乐的欣赏对象是一般群众,是大多数人,那么,我们了解和研究音乐历史或者音乐现状,就不能只顾少数人的爱好,而不顾多数人的爱好,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古典音乐有着永久的魅力,虽然欣赏群体有限,我们应该研究;流行音乐可能只流行一阵子,但欣赏对象广泛,是不是更应该研究?不一定,但是也应该研究。关于艺术性与大众性的矛盾问题,这个历来都是这样,但是这种矛盾又是可以协调的。就像过去的作曲家常常把民间音乐当作自己创作的素材一样,也有一些专业作曲家融合流行音乐进行创作。何况,流行音乐已经成了民众文艺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作曲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结合流行音乐元素来表现生活,也能使自己的创作趋向通俗化,便于群众接受。大众音乐会受到小众音乐的影响,流行音乐通过学习和吸收现代专业音乐,可以提高自己。我写过文章讨论“严肃音乐通俗化”,是20世纪90年代英国作曲家大卫•赫勒韦尔音乐会后的思考。赫勒韦尔的音乐风格是综合古典音乐、爵士音乐、摇滚音乐、拉美音乐、巴洛克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特点发展而成的,所以你说它是严肃音乐的通俗化也可以,说它是通俗音乐的严肃化也可以。好像是把摇滚音乐的“疯”、古典音乐的“雅”和先锋音乐的“怪”这三种色调调和在一起的音乐格调,产生出了热烈、明快而新鲜的音乐,充满生机。而舒勒(Gunther Schuller)所提出的“第三潮流”,指的就是那些综合艺术音乐和各个民族、地区音乐的乐曲,这个糅合过程不只是模仿,而是“重新发现”。他认为艺术音乐和爵士乐这两种音乐可以取长补短:艺术音乐可以学习爵士乐丰富的节奏和独特的韵味,而爵士乐也可以从古典音乐的大型曲式和复杂的调性体系中为自己开辟出新的道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有协调的一方面的。大众音乐艺术性不如艺术音乐,但是老百姓喜欢,我们同样应该研究。至于实验性的东西,是一种探索,当然不可能马上大众化,需要时间。在实际创作中,把专业的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等不同的文化结合起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像以前,搞严肃音乐的人往往看不起流行音乐。越来越多的音乐学家们在他们的历史著述和评论中,表现了对流行音乐的重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韩:
流行音乐的学术研究,跟专业音乐的侧重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对流行音乐应当持何种态度?钟:
首先,像我刚才说的,应该把流行音乐的研究纳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在西方最先研究流行音乐的是社会学家,把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我过去也说过,没有流行音乐的音乐史不是完整的音乐史。流行音乐的研究方法,很少就音乐本体,而是应当从另一些角度出发,比如音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音乐与社会的关系等。有些民族音乐学家也把城市流行音乐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关注的是大众,研究大众的心理与需求。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更是把流行音乐,以及其中反映出的各种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当作它们的重要研究课题。不过,所谓流行音乐,也有相对小众的,比如摇滚音乐,爵士音乐,要看研究的是哪种爵士?哪种摇滚?爵士就可能完全是学院派的,我曾听过一场爵士音乐会,是美国一位音乐系系主任搞的乐队,带有更多实验性的部分,那就不是流行音乐意义上的爵士,是非常专业的。我们可以把流行音乐看成音乐的一个种类,每种音乐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功能,但无好坏之分。认为“古典音乐是好的,流行音乐是坏的”,这种观点应当被抛弃。体裁没有好坏,只有作品才有好坏之分。从流行音乐的实际情况来看,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有好也有坏,还有大量介乎于好坏之间的平庸作品。流行音乐中质量参差不齐、格调高低不等的现象,可能比古典音乐、民间音乐更为复杂,而且它也不像古典音乐、传统的民间音乐那样已经经过了历史和时间的筛选与沉淀。我们不能对复杂的事情采取简单化的态度,一概地否定或肯定,而是要具体分析。如果一味地吹捧那些格调不高情趣不高的流行音乐,不符合实际地为它辩护,还会造成对社会、对青少年的有害影响。韩:
如您所说,对待流行音乐,我们不能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对于流行音乐的创作与传播,您认为评论有哪些作用?钟:
评论作为音乐实践活动中一个重要环节,当然会对音乐创作、音乐表演起到推动作用。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种推动更多地表现在艺术音乐领域,而在流行音乐领域里或许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流行音乐是一种大众文化,对它的取舍、好坏,更多由大众决定。例如,在西方流行音乐历史上,无论是爵士乐还是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评论家好像开始都很反对,甚至反感,而青少年照样接受、喜爱,形成潮流。但是,评论家对于不良音乐现象的及时批评和流行音乐杰作的价值肯定,可以帮助流行音乐更好地发展。韩:
作为西方音乐史学科老一辈的研究者,您对西方音乐史学科未来的发展,以及后辈学人的研究有何期待?钟: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今天的年轻人主观、客观条件都比我们好多了。他们的眼界更开阔,知识面更宽,既然从事的是西方音乐史教学和研究,不能闭塞是不言而喻的,要多出去走走。有人提出中国视野、国际视野的问题,我想它们各有各的定位和上下文,视野一定要开阔,但是视角应该是中国的视角。我们要有自己的学术成果,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声,要与西方同行多交流,取得同样的话语权。访后跋语:
尽管在之前的学习中,钟子林先生的著述和其中的深透观点早已在案头、在心中,但此番我仍然在重读钟先生的著作论文之后,才怀揣着敬畏和景仰之情与钟先生约定了采访时间,登门拜访。钟先生已88岁高龄,他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对毕生所研究的课题在当下的继续发展热切地关注着。回答我的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思考再三,以最凝练和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不论是追忆学科发展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还是讲述音乐史学研究朝气蓬勃的当下,他的目光一直坚定、热忱而理性。钟先生的艺术生涯从音乐创作起始,采访中钟先生哼唱起他十几岁时在文工团所写的革命歌曲,歌词与音调那么生动地激活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记忆。后以作曲、传统音乐的采集与研究作为桥梁,最终到达所精研深拓的西方现代音乐专题研究,同时也对摇滚音乐、爵士音乐等流行音乐形态做出最早的调研、梳理和研究。就国内学界而言,钟先生不仅是西方现代音乐最早的引介人,还积极著书立说,身体力行开课教学,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国内学界对于西方现代音乐最早的认知。他所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和《西方音乐通史》(第七编)几乎是每一位音乐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他是我国西方现代音乐研究的“首席专家”和名副其实的“开拓者”。
钟先生做学问大胆开拓,勇于先行,做人则秉持谦谦君子之风,用钟先生的学生班丽霞教授的话讲,钟先生是“光而不耀,静水流深”,令人油然而生敬仰之情。上海音乐学院孙国忠教授曾动情地向我提起一段令他印象深刻的往事:20世纪90年代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读博士时,钟子林先生和何乾三先生赴美访学。一个下午,孙老师向钟先生与何先生闲聊起在UCLA的学习情况和体会,却没有想到两位教授居然拿出笔记本来,认真地聆听并记录着“一个学生的话”,这个场景着实令孙老师难以忘怀。钟先生带给后辈的不仅是他丰厚的学术成果和睿智的学术思想,更是海纳百川、严谨求实,在宁静中获得真知的治学精神,而这一切都成为钟先生“学问人生”的崇高人格境界,值得后辈学人学习、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