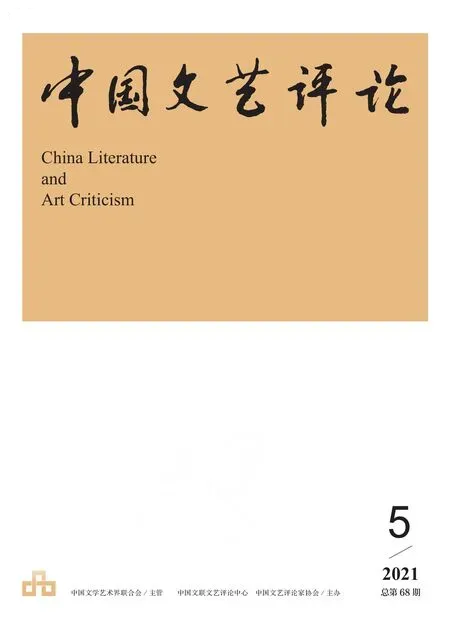工艺美术与书法相结合的双重价值
——论张仃的书法观
高文兴
一、工艺美术的先行者与书法家
工艺美术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艺术门类。工艺美术理论家田自秉归纳了工艺美术的定义:
工艺美术是艺术、科学、经济等学科交融的综合体,它体现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等方面。从物质文化看,各个工艺美术品种及其功能,都直接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以及一个时代的物质生活面貌、生活方式;从精神文化看,它形象体现人们的意识情感和审美观念;从行为文化看,它表示出社会的生活行为和活动指向。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工艺美术则是内含着这各个方面。所以,工艺美术不只是一种美术活动,更不是一种绘画形式;它是体现科学实践的创造成果的一种科学文化,也是反映人的感知和认识以及意识观念的一种人文文化。
1956年,由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以及清华大学营造建筑系等院系合并重组而成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这是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张仃进入中央工艺美院,担任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从此和工艺美术结下了深深的缘分。
张仃在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时,就曾负责过解放区的装饰艺术设计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工作,也曾多次提出学习民间传统艺术、创造新装饰艺术的观念。进入中央工艺美院主持工作后,他更是大声疾呼,要重视民间艺人,抢救民间艺术,还将包括泥人张、面人汤等民间艺人请进工艺美院,令濒临消亡的街头艺术获得了新生。张仃还鼓励学生去地方采风,他曾多次带领学生赴云南、甘肃等地,通过观摩石窟、壁画、年画等艺术作品,创作出许多融合了中国传统艺术特色和现代风格的工艺美术作品。比如张仃创作的大型装饰壁画《哪吒闹海》,就是参考了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木版年画等中国古代民间工匠的艺术杰作后诞生的。
担任中央工艺美院的院长,从事工艺美术的创作和教育工作,是张仃艺术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作为新中国工艺美术和工艺美术教育的先行者,张仃也将自己对工艺美术的认识,融入到对绘画、书法的理解当中,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艺术观。
二、搭建工艺美术与书法之间的桥梁
在李兆忠编选的张仃艺术评论《它山画跋》中,可以读到张仃对中国工艺美术与民族绘画关系的论述,而发表于1985年5月《装饰》上的《书法与工艺结合——可喜的新尝试(侯德昌的书法刻漆艺术)》(下文简称《书法与工艺》)一文,则集中表达了张仃在书法与工艺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的观点。
1.书法始于工艺
在《书法与工艺》一文中,张仃从原始文字的来源与早期书法的载体两个方面,论证了中国的书法艺术始于工艺:
中国书法艺术,一开始就与工艺相结合。彩陶上的原始文字和甲骨文字,虽属先民装饰之图腾或巫卜之用,但从金文起,就铭刻在商、周钟鼎之上,这些青铜器,本身是工艺品,有阶级的功利目的。而铭文,又是这些工艺品的有机组成部分,铭文“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亦流传于后世——美的书法艺术。
张仃敏锐地注意到原始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装饰纹样,是中国书法与绘画两门艺术的共同起源。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支持者和践行者,张仃在1986年中央工艺美院干训班演讲时指出,“马克思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实用”,而属于工艺美术范畴的彩陶美术、彩陶文化,正是中国美术史的开端。
中国史前文化中,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堪称后世工艺美术的先声。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距今7500到6900年的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挖掘出土的陶器多为素式,但陶器上已有简单的纹样。这类纹样多由线条构成,粗细深浅组合为装饰性效果,令陶器在实用的同时,也成为可供欣赏的工艺品。而通过对这类陶器上线条纹样的观察,可以联想到中国书法、绘画对线条和用笔的重视。远古时期陶器上线条的律动与自然书写,流露出先民们生活的真实性与史前艺术的再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书写载体由陶器变为甲骨、青铜器、石碑,有了大篆书体《石鼓文》,青铜器铭文《大盂鼎》《散氏盘》,及北魏时期用笔方劲、雄强的魏碑体、法度森严的唐碑。从书写材料来分析,精细昂贵的“绢”“帛”出现,开始有了工笔画,清代宣纸、羊毫笔的诞生带来了大写意花鸟画。从本质来看,工艺和书法虽然是两种艺术类型,却有实质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彼此产生了划时代的艺术产物。从特征来看,载体不同、书写材料不同,艺术风格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形成了富有个性化的艺术品及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分布于长江中上游的甘肃、河南等地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到5000年,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最繁荣的文化之一。在陶坯制作成型后,使用能烧出不同颜色的材料,在器物表面刷图并作画,经过入窑烧制,即成为不褪色的彩陶。
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以动物纹和花卉纹为主。先民们在绘制彩陶纹样时,往往对真实物体进行夸张、变形、简化,利用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将具象化为抽象。这些纹样为后世象形文字的诞生,打下了一定基础。正如张仃曾指出的:
中国字都是象形的,文字与图画是浑然一体的,既是字又是画。等我们的祖先对自然认识逐步提高后,物质精神生活慢慢都丰富起来,文字与图画向两极发展。……文字越来越向抽象的符号发展,但再怎么抽象,总还有形象性,于是变成了没有形象的象形字,抽象性越来越强。而画却向具象发展,可仍然有抽象的成分。
从中国彩陶纹样的巅峰——距今5000年左右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器上纹样与甲骨文的对比上,可以印证张仃这一观点。
马家窑出土的彩陶纹样种类繁多,其中以线条组合为主的几何纹最多。这些几何纹有不少都是对具象事物抽象后的结果,比如波浪纹:
在与水接触的过程中,汲水、洗涤、鱼跃、风刮、捕鱼、捞虾等人为和自然现象,集中于人的大脑,形成一种概念,尔后通过形象思维,表现在彩陶上,利用波浪纹、旋涡纹等与水有关的图案表现出来。

张仃之所以能够意识到中国文字、甚至书法艺术起源于彩陶,与他一直以来对民间工艺、彩陶文化的重视有很大的关系。张仃热爱中国民间艺术,“以土为荣,以土为美”,尤其是在延安解放区工作期间,他感受到自己对民间工艺的热爱和推崇,与解放区的气氛和文化路线是一致的,因此成为了装饰艺术家。1941年,张汀在延安设计了作家俱乐部,将之“变成延安最漂亮、最摩登的地方”,而俱乐部中的装饰品,就包括延安地区的土窑彩陶——史前彩陶艺术的延续。
在中央工艺美院的教学工作中,张仃同样重视史前彩陶美术。对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生,他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毕业于工美装潢美术系壁画专业的张朋川,长期从事考古工作,尤其醉心于彩陶研究。据他回忆:“当张仃了解到我的彩陶研究后,就在不同场合赞扬过我。”1990年,张朋川的研究著作《中国彩陶图谱》出版。同年,张仃路过兰州,为张朋川题字“天道酬勤”,并在这幅字上题跋:“朋川同志多年从事彩陶研究,刻苦钻研,终获大成。”张仃对张朋川的赞扬,既出于对后辈的关爱,更是对史前彩陶美术的不懈关注。
2.书法载体与装饰性的关系
除了考察彩陶美术与文字起源的关系外,张仃也注意到历代书法的载体与工艺美术之间的关系。
商周特别是周代书法的代表金文书法,铭刻于钟鼎,即青铜器上。而青铜器的铸造,凝结着中国古代工匠对金属铜认识及使用的智慧,“是我国古代继彩陶艺术之后兴起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独特民族风格和鲜明时代特点的工艺美术,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第二个高峰”。商周时期,青铜器盛行,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不同类型,其中以礼器和兵器上的铭文最为丰富。
西周中期铸造的毛公鼎,于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歧山地区,其上铭文多达32行四百九十余字,记载了周王因重臣毛公辅佐朝政,卓有功勋,给予他丰厚赏赐之事。这篇《毛公鼎》铭文,用笔高度成熟,结构偏长,笔法坚韧而曲折回转,极具特色,被视为“金文之冠”。
作为青铜礼器,《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本身的制作非常精良,器型浑厚凝重,纹饰典雅简练,这使得铭文在器型上显得尤其突出。纹饰减少,铭文增多,是西周中晚期以后青铜器装饰的特点之一。这一方面令青铜器得以宣扬政绩、记录历史,另一方面也把青铜器变成了书法作品,更成为后世学习、了解周人书法的绝好材料。
青铜器是金文书法的载体,而书法铭文,也是青铜器上兼具实用性和艺术美感的装饰。正如张仃所述,是“美的书法艺术”。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周代彝铭进化观》中,也注意到青铜铭文的装饰性:
要之钟鼎铭文在其进化之第二阶段有书史之性质,此性质以西周遗器为最著,自春秋中叶以降而衰微,盖竹帛之用已繁,文史亦逐渐茂密,不能为鼎彝所容也。有周而后,书史之性质而变为文饰,如钟镈之铭文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又如齐器国差(缶詹)亦韵语,勒于器肩,以一兽环为中轴而整列成九十度之扇面形。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然自彝铭而言,则其第三段之进化。
郭沫若认为,春秋以后青铜器铭文的装饰性增强,是铭文变化的第三阶段。鸟篆、蚊脚书、虫书等富有艺术感的篆书字体,在这一时期频繁出现于青铜器上。这些特殊的铭文字体,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铸造这些亦书法亦花纹的铭文时,工匠们使用了金属精细生产的错金银工艺,令文字色彩鲜明,富有立体感。这同样也丰富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表现手法。
张仃本人在研习书法的过程中,曾长时间临摹大篆、小篆。这一经历令他注意到,书法艺术最重要的载体石与碑,也是具有实用与艺术双重价值的工艺品:
汉魏碑刻大盛,为述德、铭功、纪事、纂言……刻石立碑,于是书法以碑传,碑以书法传矣。——形成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大观。
刻石以传书法,可以追溯战国时期的《石鼓文》与秦始皇时期的《峄山碑》《泰山刻石》《会稽刻石》。从天然石块到石碑,石质书法载体的这一发展过程,是匠人加以人工修治的结果。而在石上摩刻文字的工匠,实际上就是在创作工艺美术作品。张仃自小学习书法,曾系统临习隶书《张迁碑》和《石鼓文》等篆书。他对于刻石与书法关系的思考,应是在学习实践过程中所得到的。汉碑石刻与书法的互相成就,与青铜器异曲同工。《石鼓文》的内容与狩猎相关,而秦始皇巡游天下、树立刻石,则是出于统一天下后稳固政权的考量。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在其著作中分析道:
石刻的意义、功效,正是立足于它们与这些场所的物理依附,刻石者还要跨越地理空间以置放这些铭文,将文本与场所结合在一起。……将功绩铭刻于可以传之后世的物质载体,以及在所控制的疆域内活动,这两种行为都沿袭了既有的模式,刻石于山巅的帝王礼仪背景,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混合了作为政治表征的、长期尊奉的不同礼仪活动,即巡历四方(包括狩猎)、在宗庙宣告功绩。
上述即张仃所说的“述德、铭功、纪事、纂言”。而这些有着明确实用目的的石刻与碑文,又因撰文、书写者的书法素养,而成为后世的书法范本。如秦《峄山刻石》开启了小篆、规范统一了全国文字的使用,由丞相李斯撰文并书写,因此成为历代书法家学习、临摹秦小篆书体的标准版本。
三、工艺表现书法的实践
张仃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时,曾多次向学生们强调,工艺美院不是培养画家的,应树立工艺美术的专业思想,甘当无名英雄。但好的工艺美术作品,一定拥有高的艺术价值。所以张仃认为,工艺表现书法,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金、石、竹、木、漆板等,其艺术价值首先决定于书法艺术水平。他以篆刻艺术为例,指出拥有高超艺术成就的篆刻家如邓石如、吴昌硕、齐白石等,都是出色的书法家。
侯德昌的漆板书法,是工艺与书法结合的实践活动,也符合张仃一直以来借鉴传统艺术、创造有新时代新气象的作品的工艺美术观。张仃同时也注意到,书法在民间艺术的表达当中,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虽然明清以来,在我国园林建筑中,有时也采用木刻牌匾、楹联来作装饰。宫廷中也有卍字锦帐,百寿屏风之类,但在民间,把书法艺术经过再加工,成为独立装饰艺术,这还是新尝试。——我国人民将愈来愈要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更美的生活环境。我们把书法艺术,以新的形式来满足与提高这方面的要求,从厅、堂、馆、舍以及书斋、居室等等,根据不同需要,可以开创丰富多采的漆板书法艺术。
张仃对于侯德昌漆板书法的认可和鼓励,是基于他对书法与工艺关系的认识而产生的,也是对更多书法与工艺结合的实践尝试的认可与鼓励。这是一个具备深厚书法素养的工艺美术先行者对工艺美术未来前进方向的探索,也是一个有着工艺美术背景的书法家对书法的全新思考。
结语
张仃的书法观点对于推动书法与工艺美术设计,在当代有着“桥梁式”的链接性的意义,从汉字书法的独特性来看,书法是工艺美术的一部分,从书法的载体与装饰,再到工艺表现书法的实践,具有重构新时期工艺美术与书法相结合的双重价值。有人主张当代书法独立成为“纯粹的艺术形式”,这其实将中国历史上书法一直与工艺美术相结合的传统丢掉了,张仃的观点无论对于重筑汉字书法的土壤根基,还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都具有非凡的启示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