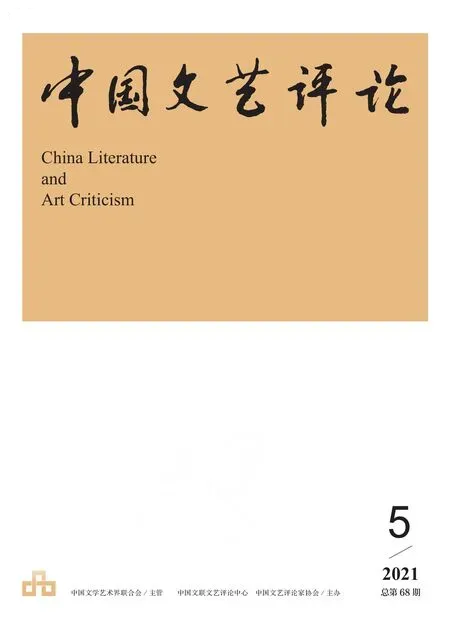以身体极限喻精神超拔
——评大型当代杂技剧《化•蝶》
申霞艳
2021年春暖花开之际,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创作的《化•蝶》在广州大剧院首演多场,场场爆满,公众号、朋友圈竞相传播,好评如潮。《化•蝶》的总导演赵明、编剧喻荣军、艺术指导宁根福、舞美设计师秦立运、服装造型设计师李锐丁等制作人员形成国内高水准的制作团队,主演吴正丹、魏葆华夫妇同台共演的肩上芭蕾乃人间一绝,成为该领域当之无愧的标杆。此剧排练历时半年多,融合了戏剧、舞蹈、魔术等多种艺术和现代科技,舞台效果又惊又险又美。全程笔者都在紧张和快乐中度过,几度屏气凝神,几度提心吊胆,真可谓与表演者们同呼吸,闭幕时掌声经久不息,观众沉浸其中,长时间不愿离去。总导演赵明在采访中谈到《化•蝶》融入了杂技32个科目,可谓倾其家珍,毫无保留。面对如此高难度系数的杂技表演,演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不能有半点闪失。蹬、顶、抖杠、软功等目不暇接,哪一门功夫都是力与美的融合,是对身体限度的突破,需要长期艰苦训练才能实现,从而变不可能为可能。杂技是现场实力的大比拼,必须要有硬功夫,来不得半点敷衍,它不像视频可以反复录制、剪辑、润饰,以达到最佳瞬间。这种不可复制的现场难度也构成杂技演出的魅力之一。大型杂技剧必须日复一日地排练、反复磨合才能获得舞台整体效果,每项科目的传情达意都依赖表演的理解力、表现力及情感调度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观众已经接受了诸多审美形式的洗礼,对观演有越来越高的心理预期,尤其是大都市里的观众几乎都很成熟,欣赏水准堪比专业。然而表演仅有硬技术、高难度还是不够的,审美余韵、精神“净化”才是艺术的比拼空间。《化•蝶》最大的特点是以当代的平等自由观塑造全新的“梁祝”精神,以美轮美奂的杂技表演呈现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爱情追求,并对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进行有力嘲讽。当代杂技剧《化•蝶》探索出对经典进行创造性演绎的可能:一是主创团队对梁祝故事神韵的现代理解、凝练与改造;二是表达重心由显及隐,由身体奇观向审美愉悦位移,让杂技剧承担复杂的内涵,传达饱满的感情,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三是杂技剧对其他艺术门类与现代科技的开放融合、以求美化雅化。

图1 《化•蝶》剧照
一、《化•蝶》之美雅化
大型当代杂技剧《化•蝶》全面更新了笔者对杂技的认识。对大多数非杂技职业的观众来说,杂技因其技杂而风格模糊,对我们而言是娱乐匮乏时代的甜点,还停留在翻跟斗、藏扑克、搞杂耍的童年记忆中。《化•蝶》将更高、更强的体育精神与更美、更雅的艺术精神相融合,通过对比、反衬、夸张、互鉴互镜、通感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调动气氛,激发观众隐性的情感系统。在已知的故事止步处,表演延长了观众的感受,叫人回味无穷。
《化•蝶》全剧分两幕十场,另加序幕和尾声。总体表演节奏张弛有致、动静结合、虚实相生。杂技剧努力将多种身体语言与高雅的审美、深邃的思想结合起来,通过布景、灯光、道具、音乐、色彩、字幕来共同营造古雅的氛围和耐人寻味的意象,背景借鉴了中国绘画的大写意,而前景常常通过舞台切割、矛盾并置、对照呈现来形成张力,场与场之间留有恰如其分的情绪空间。
序幕“蝶生”中,背景清朗空明,一轮高度简约杂以线条的“圆”在空中高悬。空灵的圆与穿梭的丝构成“茧”的意象,美得让人心悸,紧张感油然而生。舞台前方是舞者在“单杆”上艰难困窘地挣扎,几近窒息。伴随着灯光的渐强,独舞者消失,远景中男女双人舞化的“蝶”渐次分明,破茧化蝶,点明主题。
蝶是全剧的灵魂,为求具象地表演蝶,剧组可谓殚精竭虑,调动全部的想象力:有拟象的方式,也有谐音(转碟)的方式;或男女主演的芭蕾着装刚好合成一只蝶;或几对不同的蝶呈现蝶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形态。融汇“蹬伞”科目的蝶伞戏、化“抖空竹”来呈现蝴蝶精灵,以裙裾摇曳呈现蝴蝶天使的精灵之美,以男性健美的躯体和刚劲的双臂呈现蝶虫的蜕变之艰,最后舞者身着彩绘蝴蝶,以肩上芭蕾和头顶芭蕾来阐释梁祝“化蝶”,堪称美轮美奂。蝴蝶是大自然的精灵,“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蝴蝶出双入对在天地之间、万花丛中飞翔,集对称、深邃、玄奥于一体,是东方神秘美的象征。蝴蝶是深邃之美的典型意象,它们形体对称,出双入对,且色彩斑斓,尤以幽深的蓝紫多见。康定斯基曾对色彩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蓝色向深处发展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至当它的调子越深,它的内在感染力就越是有力。”并认为“蓝色是典型的天堂色彩。它所唤起的最基本的感觉是宁静。当它几乎成为黑色时,它会发出一种仿佛是非人类所有的悲哀;当它趋于白色时,它对人的感染力就会变弱。”《化•蝶》的宣传册封面传神地展示了蝴蝶的深邃之美,传递出该剧的神髓——以突破身体极限隐喻自我的超越。
演出开门见山,破茧蝶生的意象直击观众心灵,构成杂技剧的序曲。布景的圆既可以理解为具象的“茧”,也可以隐喻我们潜意识中对团圆的渴望。对爱的寻求来源于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渴望找到另一半。中国古代戏剧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深入人心。现实的桎梏并不妨碍我们在艺术中做“白日梦”来“净化”心灵。卢梭曾宣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爱将人导向自我,爱本身亦是枷锁。文艺作品讲述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人们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万事万物,此理大化。

图2 《化•蝶》剧照
在“闺念”“共读”“情生”这几场中,英台活泼、烂漫而叛逆的个性使她脱颖而出,读书启蒙加强了她的自我认知。梁山伯沉湎书斋,懵懂实诚。两位主人公的性格差异是通过叙事节奏的轻重缓急对比来呈现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已于美雅之中生出浓浓的爱意,倾心于庄重诚恳的山伯。这一部分我们既看到创作者对中国古人喜爱的扇、毛笔、伞等道具的娴熟运用,也看到以足投篮等具有当代意趣的科目改造。“蹬人”科目中两位紫翼小天使的着装亦紧扣主题,让人联想蝴蝶翻飞。书院背景以竹、兰构筑清幽之境,三载共读,人间至乐。
“婚变”一场极具现代意味,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成功。媒婆色彩鲜艳的衣着引人注目,暗示其夸夸其谈、花言巧语,夸张的举止将“媒妁之言”的蛊惑性发挥到极致,令人莞尔。纨绔子弟马文才有恃无恐的模样和贪财的祝家父母的形象亦叫人会心。“踩高跷”以形象的高低分明展示传统等级观念的森严;“钻圈”具象地表现了人“钻”到钱眼里,祝父“抛飞盘”表达金银数不胜数。整个舞台珠光宝气,琳琅满目,创作者巧妙地融合魔术来展示金钱的魔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让祝家上下全都迷失其中,构思与表演之精妙让人忍俊不禁。这对消费社会欲望膨胀的当下尤具警示意义。

图3 《化•蝶》剧照

图4 《化•蝶》剧照
“情别”一节以“蹬伞”来表现有情人无奈分散,伞谐音“散”。伶俐的英台机智地在伞中夹了红纱绸来向山伯挑明自己的女性身份。信物红纱在整个送别的场景中格外夺目。后文“梦聚”中不断调动红纱意象,以此载情纷飞。别后山伯因思成疾、奔赴黄泉而英台随之,最终双双化蝶。在英台的狂想和梦境中,纱巾仿佛有灵,在缥缈的梦境中不断交织,红、白两色的纱巾透明似蝶翼,轻盈、灵巧、飞升,思与爱交织、升华。表演以轻驭重,空灵之境成就凄迷之美。
“抗婚”一幕中,舞台左边是大型的“绸吊”,右边的小角落是英台困在具象的红色“茧”屋中,两相并列,形成无比鲜明的对比。随后以杆比喻“棒打鸳鸯”,并辅之以几声惊人的鞭地声,让观众心惊肉跳,象征着残酷的封建秩序叫人无从挣脱。古代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大户人家只顾门庭体面,却没有人真正理解主人公的心情。轿中的英台悲伤不已,而抬轿的队伍以大幅度抖杆表现婚礼的喜气洋洋。
接下来几幕如梦如幻,每一幕均选取与情景匹配的技艺来反衬或渲染“梁祝”的一往情深,起承转合处衔接得十分流畅,现实的残忍与梦境的唯美交替并进。表演充分调动了纱巾、蝴蝶、花丛、白云等意象表达春意、生机勃勃,轻盈的云、轻盈的花瓣、轻盈的蝶羽、轻盈的天使……互相叠积,极尽空灵、极尽唯美,表达“梁祝”之爱的纯洁、专注、出神。在堂皇高雅的广州大剧院,空阔纵深的舞台上,布景、灯光、色彩、道具无不融合高科技的现代元素,新的主题歌曲与经典的梁祝音乐萦绕耳际,不断回旋,与蝴蝶的流连徘徊相映成趣。
二、《化•蝶》之当代化
《化•蝶》要从已知的故事中提炼出新意,要从古老的爱情故事中萃取当代感,让当代观众产生共情,这是改编的难度。福柯曾说过:“重要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观众掏钱到剧院去是希望看今人如何演绎古老的爱情故事,如何以只有身体语汇的杂技来呈现经久不衰的民族审美。
《化•蝶》的底本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文本。中国古代有两个著名的女扮男装的故事:一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另一个是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两个故事从侧面反映了男权文化下古代女性的大创举,反映她们对爱情的追求以及对责任的承担,成为后世女性自我激励和现代启蒙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
“梁祝”故事自西晋传播至今历时近1500年,经历了地方戏、舞剧、影视等多种文艺形式的传播、改编,经过与时间的赛跑,与历史心灵的对谈,最终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潜意识,“梁祝”被认为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亦被西方人赞颂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祝”至凄、至美、至真、至纯,代表了中国文化和审美情趣的高峰,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源泉,这种超越生死的爱情追求感天动地,启发了后世文学艺术的大胆想象。
光辉的经典如何进行现代性的转化,这是20世纪以来整个民族国家共同思考的重大攻关课题。鲁迅的“从来如此,便对么”让我们对传统进行深刻的质疑和反思,传统文化经受着极为严苛的省察。历千年而不绝的经典,如何将其亘古不衰的魅力融入到现代文明秩序当中来,这是困扰我们所有文化人的难题。杂技固然要表现精湛的技艺,需要一定程度的炫技,但技艺的炫酷得服从剧情讲述的需要,杂技要以契合故事情节的身体语言传递梁祝的凄美爱情。杂技剧要融合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来传递复杂的思绪,承载丰富的情感,表达悠长的意蕴,这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杂技和戏剧的渗融拓展了杂技的表意空间,使通俗的杂技登上大雅之堂。《化•蝶》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尝试,让杂技突破了单纯的逗乐来承载人物的丰富感情和命运起伏,传递高雅的审美情趣。《化•蝶》的演出效果证明杂技亦能高端、大气,关键是创演对杂技科目的合理运用,最大限度地利用综合艺术的通感,使观感更为丰富、更多层次、更有联想空间和余韵。

图5 《化•蝶》剧照
“梁祝”的灵韵在于爱的超越性。对爱的专注、钟情让他们反抗世俗,超越生死。“梁祝”的爱情故事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它代表着人类对爱、自由和纯粹永恒的追求。文本包含两重大胆的想象,一是祝英台女扮男装,纯属离经叛道之举,大胆的梦想使她能够离开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去读书,而读书本身就是启蒙。在读书的过程中,她爱上了同窗梁山伯,所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不是本能的欲望,而是有理解和共同爱好为基础的深情,具有现代意识,而这恰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抵牾,与古老的门第观念相冲突。二是化蝶,这是更为非凡的灵感,也为后世文学的出生入死以及死后复活开创了先河。《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可以为爱而死,又可为爱死而复生,情感的力量感天动地。“梁祝”的化蝶双飞、为爱重生与西方基督的复活异曲同工,都是人类渴望不朽的美好想象,以灵魂的永恒超越生命的短暂。因爱而死的凄凉与因爱化蝶的纯美构成鲜明对比,让人唏嘘、叹息且忧伤。斯达尔夫人说:“忧伤是最能够深入到人的精神结构中去的。”《化•蝶》整场戏中氤氲着这种忧伤,既让人肝肠寸断,又让人产生一种清朗的升华,感受到一种勇气、生机和仁意。结茧成蛹、破茧变蝶是一种生物性的过程,但中国哲人从中悟到一种智慧,那就是山穷水复与柳暗花明的关系,磨难与光辉、痛苦与喜悦、现实与浪漫、此生与不朽的关系。所以,在具象的双飞蝴蝶之外还有一只更为古老的蝴蝶,庄周梦蝶中的那只道家文化的蝴蝶,那只主体与客体难以分辨的蝴蝶,犹如梦之真实和真实之梦的难以分辨。这无中生有的蝶凝结着博大玄奥的道家文化,为主流的儒家文化提供了大有裨益的补充,充实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宇宙。
剧作必须激动创作者,激活表演者,方能撞击观众。杂技剧《化•蝶》遵循杂技艺术的特点,前半部分以我们钟爱的扇、毛笔为道具展示旧式私塾同窗三载的深情厚谊,以蹬伞与长亭暗示送别的痛苦;下半部分以马文才送订亲礼的繁华与结婚的热闹反衬祝英台内心的凄苦。接下来是英台相思致幻,物我两忘,最后化蝶,到达全剧的高潮。“化”是梁祝的精髓,也是此次改编和表演的精髓所在。东方哲学强调“化”——出神入化。吴正丹、魏葆华夫妇的肩上芭蕾正是出神入化的最佳演绎,以身体的极限将《化•蝶》的灵魂具象化。此刻,万籁寂静,白云缭绕,宛如仙境,祝英台立于梁山伯的头顶,立于世界之巅,爱情让她光芒万丈,万众瞩目。“梁祝”的精神与爱盈于天地之间,肉身的沉重与灵魂的轻盈浑然统一,刚柔相济,那一举一动都充满着美、柔情和生机,仿佛蝴蝶在春天的怀抱中翅翼扑闪,扩散饱满的情思。
杂技剧以人体来模拟蝶的飞舞,当吴正丹单脚立在丈夫魏葆华头顶旋转时,轻盈的身体追求灵魂的极致。污浊的俗世被他们踩在脚下,唯有精神至高无上。这段水乳交融的表演将大家带至飞翔之境、忘我之境、灵异之境,重新感受初恋的惊喜、唯美与洁净,感受初恋对自我的震惊和启迪。杂技剧中有魏葆华夫妇常年工作上的默契,更有他们生活中对彼此深深的理解、欣赏和爱,以及他们作为现代人对生命的理解、对自由的追求、对身体极限和年龄的不断突破。表演让舞者的内心和身体一道成长,每天迎接崭新的自己,《化•蝶》让舞者脱胎换骨,亦让观众振奋,生命能量灌注在了整个空间。
杂技抓住了“蜕变”这个生物性的意象转化过程,以“抖空竹”来表现贯穿全剧的化蝶过程。“抖空竹”是杂技最常用的科目,在《化•蝶》中推陈出新,常用常新,如一男一女的“对手空竹”,隐喻山伯与英台的默契、情投意合;而缠绕在英台腰上的“线”仿佛是爱情的线索,总是要将她的心与山伯牵连在一起;群舞“抖空竹”则意味着爱情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必然经历从茧到蝶的艰难蜕变。由此可见,作品在大的科目设计上,都注重技术与情趣、审美的相互融合。

图6 《化•蝶》剧照

图7 《化•蝶》剧照
《化•蝶》叙事传情,以蝴蝶的轻盈战胜肉身的沉重,以精神的空灵永生战胜俗世的污浊腐朽。爱情是对世俗极限的突破,青春、初恋的纯洁、纯粹是世间最为美好而珍贵的事物,引领我们的精神飞抵美的境地,值得我们生生世世去歌颂和追求。肩上芭蕾之后,群舞转碟(谐音“蝶”)延续了高潮的精彩,象征着“梁祝”精神的开枝散叶,满台均流溢着这种极致之美——道生一,一生万物。尾声“蝶恋”戏仿穿越,实则落脚于当代。舞台切分,左边是一对现代男女相知相爱、并肩共读,右边是“梁祝”旷世蝶恋。“梁祝”精神从古延绵至今,我们今天拥有的恋爱自由中亦包含着祝英台、杜丽娘、林黛玉这些女性形象不屈的抗争,灵魂深处的自我依然有她们追求的印痕。
当代杂技精神不是浅层的逗乐,而是对身体极限的突破,是不断突破障碍,扩大自我的限度,这种较量既有身体有形的层面,更有精神广延的内涵,身体的每一次历险都包含着精神的拔节。在突破个体限度这一点上,所有的文学、艺术、体育运动都是相通的,这是引领人类不屈不挠、奋发向前的动力。而技艺的突破、日臻完善更是建立在天真和纯粹的基础之上的,杂技艺术中,无论是翻、滚、蹬,还是高空平衡和稳定,都需要表演者摒除杂念、胆大心细、放松与控制均衡。不可否认,所有的艺术都在以不同的形式追求卓越、挑战极限、创造高峰,惟其如此,方能出新出彩。
大型当代杂技剧《化•蝶》抓住了古老故事焕发的大灵感、大气象和大肯定。随着叙事的层层推进,团队表演技艺的难度系数不断增大,肩上芭蕾为杂技剧画龙点睛。在此,柔润与力量,放松与控制,点与面,中心与边缘相得益彰。我们能感受到全体演员的倾情投入,看到他们对理想的不懈坚持,对自身限度的不断突破。身体有自己的限度,它以酸、疼、痛和伤口来发号施令让我们暂停,可是精神依然强驱直入,美持续地提出自己不尽情理的要求。突破极限,不断扩张自我,走出舒适区,扩大自身限度,这就是对卓越的追求,对尽善尽美的追求。这种精神在表演者、创作者、编剧和全体观众之间流淌共生,最终形成流淌的艺术氛围。当代杂技剧《化•蝶》以极高难度的芭蕾动作凸显这一璀璨追求,将《化•蝶》升华。整个剧场仿佛都因此受到陶冶,人们摆脱自己的褊狭,蜕变为蝶,长出透明的双翼翩翩起舞,周围的黑暗也随之变淡了,爱,在剧场充盈、荡漾。祝英台、梁山伯在我们的心中复活,熠熠生辉,气韵盎然,阻隔在我们之间的千年光阴顿时不存在了。英台立在世界之巅,与白云共舞,尘世消隐,精神长存。如此,传统爆发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三、结语
当代杂技剧《化•蝶》美轮美奂、出新出彩,长久地占据着观众的心灵空间,让人情不自禁地去回想、回味。伟大的经典召唤伟大的阐释,传统与当代是同一条河流,意义在今古流动中生成,经典的流传和新生中有人类生生不息的力量。杂技剧将古典的化蝶之“化”,从精神和肉身的双重层面传递给生活在现代文明秩序中的我们,我们从中领略到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感受到传统题材的杂技剧背后是活生生的具有当代意识的舞者和编者。杜甫诗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杂技剧《化•蝶》出神入化,意境空灵,余韵悠长,它对美雅化和当代化的追求令人叹为观止,它为经典的创造性转化作出了积极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