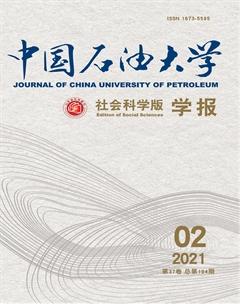生态殖民主义与国家生态安全
摘要:国家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生态殖民主义既是生态范畴又是经济政治范畴;其实质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经济发展权和生态安全权的双重剥夺,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新”的殖民形态;其表征是生态系统的殖民化扩张、生态资源的系统化掠夺、生态壁垒的制度化设计;其生成的逻辑体系是,欧洲中心主义是其思想根源,生态循环体系是其物质基础,生态资本化是其逻辑主线,生态政治化是其前提条件。生态殖民主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必须超越生态殖民主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成全球生态善治。
关键词:生态殖民主义;国家生态安全;资本逻辑;生态正义
中图分类号:D035.29;X2;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2-0081-07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契合新时代的新安全形态。国家生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等,恰如诺曼·迈尔斯在《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中谈到的,生态资源安全是国家生存的基础,生态资源退化终将导致国家的经济基础退化和国家的政治结构混乱。发展中国家生态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发达国家布控的生态殖民主义,这一威胁试图剥夺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经济发展权和生态安全权。生态殖民主义“是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独占环境收益而输出环境污染,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干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行径”[1]。目前,学界同仁已经取得了国家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的丰硕成果。不过,系统探讨国家生态安全受到生态殖民主义的具体威胁、生态殖民主义的本质表征和生成逻辑、超越生态殖民主义逻辑以保障国家经济发展权和生态安全权之可行性等问题,仍是学界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拓展的方向。
一、生态殖民主义是国家生态安全的主要威胁
在民族资本日益成为国际资本、世界各国日渐“寰球同此凉热”的时代,生态殖民主义已然构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生态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必须首先剖析生态殖民主义的本质及其表现特征。
(一)生态殖民主义的本质
生态殖民主义不同于历史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1986年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用“生态帝国主义”概念描述欧洲殖民者对澳洲、美洲、非洲的“生物侵害”①。据词源学,“生态”在古希腊意为“住所/栖息地”,泛指生物及其环境间构成的生存样态。进而,生态不仅指生物生态,也包括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等。所以,生态殖民主义既是生态范畴,又是经济政治范畴。生态殖民主义是发达国家实行的“新”的殖民形态,是发达国家在资本全球化布控下不平等经济政治之世界体系中,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维度进行的剥削性与剥夺性的经济、政治、生态行为的总称。作为客观事实,生态殖民主义是资本全球化时期殖民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新自由主义肆虐全球几十年后,地区性的生态破坏问题已经升级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自然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存续的严峻挑战。对此,贝米拉·福斯特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生态殖民主义并非什么阴谋诡计,而是根源于资产阶级统治需要和帝国主义原动力中的共识;生态殖民主义更不是帝国主义的一项单纯的政策行為,它的本质是根植于资本主义本性中的有规则的现实。[2]
易言之,生态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生态维度的集中呈现,始作于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15世纪左右开启的以殖民主义扩张为政治方案的经济、政治、生态进程,这一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以加速度变化、系统性结构呈现到全人类眼前。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生态殖民主义,直接伴以军事占领、生命屠戮、经济掠夺、政治压迫等方式。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能源供应地、工业商品倾销地。欧洲殖民者的入侵,通过生物侵占破坏了亚非拉原有的生态平衡,以建立适合欧洲殖民者生产、生活、生存所需的新型生态空间。[3]彼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剥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权,而生态安全权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来讲就是纯粹的“无”。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展为“新型”的生态殖民主义则披上了“民主、自由、人权、发展”的外衣,把生态殖民主义赤裸裸的统治方式加以意识形态化和“文化与文明化”,以生态问题为切口、以“援助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履行国际义务”为借口,故意给发展中国家制造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生态安全的“二元悖论”。“碳政治”②正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权和生态安全权之双重剥夺的真实写照。由此可见,无论发达国家殖民主义的具体形式怎样,生态殖民主义始终是其伴生产物。
(二)生态殖民主义的表征
第一,生态系统的殖民化扩张。生态系统的殖民化扩张是指,发达国家凭靠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军事武力之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原生态系统进行强制入侵和系统改造。在殖民主义早期,生态系统的殖民化扩张主要通过屠戮原住居民、迁移外生动植物、带入新的病菌细菌等方式,对亚非拉地区的生态系统进行“生物换血”。这是一种明火执仗的、“外科手术式”的强制入侵。而今天,发达国家假以“自由贸易”的面纱、通过高端前沿的生物技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重塑当地的生态系统,进而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循环永久性地、系统性地、结构性地殖民化。例如,美国转基因物种在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种植,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土壤条件,打破了生态系统中当地原有生物种群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破坏了当地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另外,目前对人类食用转基因食物可能出现的危害也存有争论[4]。
第二,对生态资源的系统化掠夺。掠夺生态资源是生态殖民主义游走于国际间的重要目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变为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地的做法,本就是一种公开掠夺后发展国家丰富而廉价的资源材料的令人发指的手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利用国际垄断资本的优势,通过所谓的国际自由贸易不断从发展中国家“吸血”。例如,从1980年至1995年间,拉丁美洲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量增长了245%。发达国家一边保护自己的森林植被,一边去发展中国家乱砍滥伐,美国去南美、欧洲去非洲、日本去东南亚。当日本把东南亚热带雨林几乎砍尽后,又去拉丁美洲砍伐了。中国稀土储量占世界总量的30%,却承担着世界稀土消费90%的供应量,供给发达国家的要占60%;美国稀土储量世界第二,却几乎不开采。2010年,中国开始限制稀土开采量,立即遭到发达国家的指责报复。海外和中东国家遭受的“石油诅咒”也铁板钉钉般地控诉着发达国家实施的对生态资源的系统性掠夺。
第三,生态污染的结构化转移。如果说,对生态资源的系统性掠夺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索取,那么,生态污染的结构化转移就是一种负面的、隐晦的“生态贡献”。有人十分向往欧美日国家优质的生态环境,但却无视这种优质环境是以污染发展中国家为条件和代价的。一方面,发达国家严格禁止其国内的高污染、高消耗的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因其处于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中低端,经济技术落后但急于引进外资,法律严重缺失而又无法监管外资。发达国家的“污染出口”和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引入似乎“一拍即合”。因此看到,美国把二分之一污染严重、消耗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日本将2/3到3/4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地区。而将危险有害垃圾倾倒在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治理生态环境的又一项“伟大发明”。正如世界著名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曾载的一篇题为《让他们吃下污染》的文章所窥测到的,发展中国家约有7亿处于极端饥饿状态的穷人,为了得到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从发达国家“进口”数百万吨的有毒垃圾并以此为生!王久良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获奖的《塑料王国》血泪般地痛斥了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光辉杰作”!2010年之前,中国是发达国家的“最大垃圾处理场”!中国环保部2013年首度承认的中国存在的“癌症村”,正是发达国家对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
第四,生态壁垒的制度化设计。生态壁垒的制度化设计最能集中体现生态殖民主义的本质,能最好地诠释生态殖民主义威胁国家生态安全之实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应享有的经济发展权和生态安全权的双重剥夺。发达国家凭借和依靠其自身的科学技术优势、经济体系优势、政治秩序优势,以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发达国家宰制下的“生态正义”为旗号,设置各种非关税的制度化壁垒,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代价、以保护发达国家享受全球生态资源为目的,通过输出“生态赤字”和输入“生态红利”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利于发达国家自己的生态壁垒的制度设计。发达国家设计的“生态正义”方案看似公平,实则不然。它们要求发展中国家遵照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这其实是双重标准,即要求后进发展中国家也承担由先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欠下的很大一部分的“生态债务”,逼迫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过其承受能力的生态保护的义务;并通过技术优势钳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生态结果,进而彻底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生态、社会的发展空间。贝米拉·福斯特以《京都协议》的失败为典型案例,来揭露发达国家生态殖民主义的真实面目。
二、生态殖民主义生成的逻辑体系
生态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存有内在耦合性。虽然,“生态殖民主义(包括广义的生态危机)是生态资本化的产物”的观点为学界多数同仁所赞同,该观点也极具学理价值和实践意蕴,但笔者认为,既然生态殖民主义是发达国家实行的“新”的殖民形态,是发达国家在资本全球化布控下不平等经济政治之世界体系中,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维度进行的剥削性与剥夺性的经济、政治、生态等行为的总称,那么生态殖民主义并非单纯的“生态资本化”的产物,作为历史呈现出的现实,生态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整体性结构的复杂化的产物,即“生态资本主义化”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国有资本的存在,雄辩地证明了,资本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关联但彼此又有实质性区别的两个概念。如果生态殖民主义仅仅是“生态资本化”的产物,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的逻辑就不成立。通过论述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成逻辑,一方面能够有效和有力地证明笔者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深刻地回溯生态殖民主义的本质和表征。
(一)生态殖民主义生成逻辑的思想根源:欧洲中心主义
生态殖民主义有着深厚的思想根源即欧洲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为不少人所接受的思想偏见,是西方资产阶级为自己主宰世界、制造历史合法性的说教。“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产生于欧洲,近现代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也出现在欧洲,这就重新安排了欧洲的经济政治结构、科学文化结构、社会阶级结构、生态循环结构,使欧洲走在了整个人类社会近现代发展的最前列,并为欧洲资本主义的远洋殖民提供了科学动力和历史合法性。从那以后,整个世界就被分成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包括半边缘地区,下同)两个部分。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物质文明越来越对边缘地区呈现出发展的巨大优越性,并由此陷入无限向下的死循环:发达国家的先发优越性是通过无情剥削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生态资源和转移生态危机到边缘地区等方式维持的;这种优越性反过来又被发达国家的“传教士”对边缘地区人民反复传颂,告诉这些地区的人民“如果想要过发达国家的生活,就走发达国家的道路”。
欧洲中心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支撑,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二是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并非一个严格而狭隘的地域范畴,而是泛指以盎克鲁-撒克逊为核心的白人至上主义观念。白人至上主义观念的哲学根源是,以白人为唯一目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率先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欧洲人把自己打扮成文明、进步的化身,把落后的亚非拉地区的国家的人民视作野蛮、愚昧、无知的下等生物。因此,欧洲人一方面把自己等同于人类本身,另一方面,在落后的亚非拉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面前,又把自己打扮成“上帝”。同时,开启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欧洲人还把自己装扮成科学、真理、理性的化身,高舉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宣扬“人为自然立法”,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解释为主奴关系。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就强调了科学技术和理性知识在殖民开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形塑了一个新的伦理,支持对自然的剥削”[5]。由此可见,以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为根源的生态殖民主义蕴含着自然控制和种族控制的法西斯倾向的意识形态。所以,世界著名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在2019年9月26日发送这样一条推文,我们就不应对此感到奇怪:“More poor people are eating meat around the world. That means they will live longer, healthier lives, but it is bad news for the environment.”③
(二)生态殖民主义生成逻辑的物质基础:生态循环体系
生态殖民主义生成逻辑的物质基础是,生态循环体系自身具有的扩张功能。生态循环体系的扩张事实往往被研究生态殖民主义的学者所忽略。生态殖民主义是内含了生态学内容的经济政治范畴,反过来看,即生态殖民主义是以生态学内容为物质基础的经济政治范畴。生态殖民主义得以落地生根,并不只取决于殖民者是如何假定或怎样假设生态系统的,因为,殖民者的生态殖民行为是建立在罗伊·拉波特所说的“生物生存能力”[6]的生态循环体系扩张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一旦殖民者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开启了生物物种变更的“大门”,就会打破当地原有的、稳定的生态循环体系,新生物群落在新物种联合体的基础上被创造出来,从而新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生态循环体系便会启动。此时,被选中的物种群就会出现生物学性质的爆发性的增加。当然,当地原有的一些物种群落如果能够“从由殖民遭遇过程本身提供的外在物质或能量的融合中发现新的活力”[7]277,也可能异常茂盛。假以时日,作为先前入侵的物种群落已经内生化为新的稳定的生态循环体系。在殖民者的强力开创下,这样的体系通过生物学内容自身的生态逻辑(这是内因)生长出来,因而永久地改变了原生的生态循环体系,进而不可逆转地适应了殖民者带来的新的殖民体系。这样的生态循环体系具有容含的共生性质:“创造共生群落相互作用的稳定模式,这种创造是通过回溯人口振荡,以及在本土物质循环和能量脉冲的参量内进行调整以适应他人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生态系统趋向于创造一些群落,这些群落能够
防止物质能量流入或流出某种局部性可持续的物质循环体系,该体系
建立在太阳能持续流动的基础上。”[7]278
(三)生态殖民主义生成逻辑的逻辑主线:生态的资本化
生态的资本化是指把生态的相关构素简化成可以实现市场利润最大化的商品库,这样做“是为了掩盖现实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8]。资本积累逻辑势必把包括生态资源在内的一切生产和生活要素统统商品化。毫无疑问,生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因而具有各种形式的使用价值。这意味着,在市场竞争机制(也包括竞争型垄断机制,下同)中,生态资源的背后隐匿着不同资本对它的权力和权利的争夺。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要在人的生产生活中才能被消费,而分配本属于公共和共享性质的生态资源的方式是市场竞争。从而生态资源的质量、数量、种类、性质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的规模、商品生产的质量、市场竞争的能力等。如此,在资本主导的市场体系当中,没有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生态资源获得了被市场竞争规定的价格。正如马克思所言,良心、名誉等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换取金钱,并通过价格获得商品的形式。[9]所以,把庞大的生态资源视为巨大的商品库即生态的商品化是生态资本化的第一步。因为这时,作为商品性质存在的生态资源是市场竞争机制的逻辑预设和前提规定。可是,一旦生态资源进入到现实的市场竞争过程中,生态资源就会取得相应的价格,而获得了价格的生态资源就真正地实现了自己作为商品的属性。与此同时,这样的生态资源也就从商品化阶段进入到货币化阶段,即生态的货币化。
但是,生态的货币化只是个短暂的中间形式。参与到市场竞争中的生态资源是为资本积累服务的,即生态资源本身要成为某种具体的资本形式即生态资本。作为资本存在的生态资源服从的唯一规律就是增殖。事实上,如果生态资源没有作为资本形态的可能,生态资源是不可能取得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的;如果生态资源不能在竞争机制中带来剩余利润,生态资源就不可能作为资本而存在。由此,在资本积累逻辑中,生态资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这是“上帝”免费馈赠的,没有成本、没有抱怨、没有抗拒、没有索取,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生态资源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才是资本家醉心的事业。毕竟,在资本家眼里,“保护自然”也只是一门盈利的“生意”,而非惠及大众的“主义”。至于拯救自然灾难、解决生态危机其实压根儿不在资本家关心的视域里。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营建自己私有的、优质的生态空间。
不管早期抑或当下,生态殖民主义的生成与扩张,始终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以市场竞争机制为中介发生作用。市场竞争机制是以资本积累逻辑为驱动力。所以,生态资本化是生态殖民主义的逻辑主线。
(四)生态殖民主义生成逻辑的前提条件:生态的政治化
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中,生态殖民主义内在地要求生态政治化,生态政治化是生态殖民主义的前提条件。2017年6月5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再次表现了发达国家一贯以来的公然挑衅国际正义原则的政治傲慢,是发达国家“在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基础上,延续与拓展历史形成的国际等级化优势或排斥性霸权的表现,也是创建更加公平、民主与有效的全球气候或环境治理体制的内在性障碍”[10]。在今天的全球层面,有关生态问题的国际商讨都是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架构中展开的,总体形势自然对发达国家更加有利。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关乎生死存亡的生态问题不过是发达国家圆桌上的政治筹码而已。这一筹码归根到底只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和无限盈利的目的。“资本控制者所追求的利润、私人财产保障、低风险等经济目标,通常与经济相对平等和安全、环境安全、平等获得食物等社会目标相冲突”。[11]就此而言,生态殖民主义就是殖民主义。因为,对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来讲,游戏规则本身比游戏具体内容要核心和关键得多。毕竟,在游戏者和游戏规则之间的关系中,游戏规则才是真正的主体。[12]
目前,生态殖民主义政治化操作生態问题的主要方式如下:(1)发达国家将自己制定国际政治秩序的政治话语主导权具体化为国际交往规则中对生态资源的定价权,即通过操纵价格提高自己的工业商品价格、降低生态资源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攫取巨大的“价值剪刀差”;(2)通过政治胁迫(必要时还加上军事打压)扰乱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与落后的目标国签订不平等政治条款,进而实现其生态剥削目的;(3)构建只有发达国家等少数个体才能拥有的霸权政治结构,例如,IMF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而美国近年来投票权基本在17%左右,因此美国事实上享有一票否决的权力。可见,生态政治化包含了国际性政策议题的设定、理论话语的阐释、发展路径的供给等层面的生态霸权性的和排斥性的话语、制度、力量,是一种刚性而尖锐的柔性政治,是一种实体化的制度构架。这一点,当然不同于早期殖民主义简单粗暴的“肆意妄为”。
三、超越生态殖民主义逻辑,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殖民主义给民族国家的生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发达国家布控的生态殖民主义双重地剥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和生态安全权。这个“紧箍咒”不破除,发展中国家就没有未来和希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正在走进世界中央并努力搭建真正公平正义国际新秩序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议者和实践者,中国应该且必须为自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人类探索一条超越生态殖民主义逻辑的现实可行的道路,构筑自己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和有效的中国经验。
(一)规范生态资本化,杜绝生态资本主义化
生态殖民主义是包含了“生态资本化”的“生态资本主义化”,但是“生态资本化”不等于“生态资本主义化”。马克思有“利用发展资本来限制超越资本”的思想,邓小平有“资本手段论”的观点。而在“资本的历史优势”[13]已完全确立的今天,“任何脱离资本谈中国现代化,脱离资本逻辑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切实际的”[14]。资本主义不可能“变绿”,可是,资本在可控条件下是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的。这已经为中国的实践所证明。资本积累逻辑的一般原则是增殖逐利,因此,通过有力、有效地引导资本投到生态文明建设中,能够充分使资本化的生态资源作为积极性质的生产要素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之有效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能够驾驭和规范资本积累逻辑、能够引导和形塑资本市场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合理科学地处理了发展利用资本与限制超越资本之微妙的平衡关系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发展难题,从而取得今日之成就的。[15]
(二)夯实国有资本,管控境外投资
国有资本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经济力量。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家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民族国家的生存大计,只有坚强有力的国有资本才能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建设是一项公共化和社会化事业,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石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实地保证该事业的普遍性和普适性,而只有国有资本才能在国家生态安全建设中“身先士卒”,发挥关键且主要的作用。的确,不管国有资本还是非国有资本,既然是资本就不可避免地遵循资本积累的一般逻辑——盈利。但二者的根本不同点是,非公性质的资本以利润为最终且唯一之目的;国有资本的根本宗旨不是赚钱,赚钱只是服务人民群众之根本利益这一宗旨的必要的手段。
境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其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究竟如何释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和管理方式。中国外资主要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显然,境外资本不是抱着做“生态慈善”的目的来到中国。所以,中国必须在引进、利用外资的过程中保持足够的警惕,防范其对中国国家生态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胁和损害。当然,这需要中国完善各项机制体制和政策法规,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引导,鼓励、利用、引导外资积极参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
(三)加强国家生态安全管理,提升国家生态现代化治理能力
完善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有关的贸易和投资制度,不给生态殖民主义向中国延伸以漏洞可钻。为此,应该把国家生态安全纳入法治轨道,加快国家生态安全重点领域的立法和修法工作,建立和健全国家生态安全的监管体系、法律体系、应急体系、预警体系、救援体系,完善国家生态安全的管理制度,着力提升国家生态现代化治理能力。增强国家生态安全的“硬件设施”,提高国家生态安全的“软件韧性”。一方面,要运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建构国家生态安全系统,全面提增国家生态安全的知识化、信息化、智能化、可控化水平,加快建设环境污染源监控管理信息系统、环境保护管理信息系统、环境质量监测管理信息系统、核安全与辐射管理信息系统、环境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等;另一方面,强化社会和公民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责任意识,提升社会和公民履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责任的能力,增强社会和公民在逆变环境中的反应、承受、适应和迅速恢复的能力,培育社会和公民在环境灾难和环境压力面前具有坚不可摧的韧性和弹性。
(四)警惕生态殖民主义“变种”,防止生态殖民主义“近亲”
生态殖民主义的“变种”和“近亲”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态殖民主义的逻辑结构出现了国内化的和国内地区化的趋势。[16]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境内有一些征兆了。所以,有学者十分担忧地指出,生态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变相存在,例如把东部经济社会发达地区的污染挪移到中西部等经济社会欠發达地区,使经济社会落后省市成为经济社会发达省市的“污染避难所”。[17]国内的这一情况与国际的生态殖民主义具有结构上的“家族相似性”。今天,中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重数量规模的经济高速发展模式升级为重质量效益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东部沿海地区开始“腾笼换鸟”。在国家整体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下,产业转移是实现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发挥经济生态资源比较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国家大计。同时,也的确存在把一些技术含量较弱、资源消耗较多、环保达标较差、生产效益较低的产业梯度式地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省际地区之间的公平正义,不能及时有效地实施绿色生产和进行绿色监管,产业转移就会退化为污染转移。因此,应该充分保障国内生态领域的省际地区公平正义,不能陷入“落后就要被污染的发展陷阱”[18]。
(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成全球生态善治
促成全球生态善治、实现全球生态正义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实践而言,超越生态殖民主义需要坚持“经济发展权和生态安全权”相统一、“全球生态权利和全球生态责任”相统一、“享受生态红利和补贴生态赤字”相同一的原则。这些原则要求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享有的权利大小承担对等的责任。各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应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因此获得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也应有所差别。虽然直到今天,国际社会都没有形成一个有效应对全球生态问题的治理体系,但是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成全球生态善治的实践中,为世界人民做出新贡献,以逐步破除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生态的等级秩序。在积极参与包括生态在内的全球治理的同时,与不公正势力进行有利有力的坚决斗争,推动实现互惠共赢的国际机制,为携手建构合作共赢、 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机制而努力。[19]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正是中国领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成全球生态善治的光辉实践。和谐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核心追求,这意味着,中国的全球生态治理与发达国家主导的生态殖民主义有本质区别:中国明确反对国际生态殖民主义,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权和生态安全权的剥夺,积极布局和践行契合国际正义原则的生态外交策略,对生态殖民主义保持足够警惕,全力推动国际政治民主化建设,努力打破发达国家布控的生态殖民主义话语霸权,在竞争与合作中增强国家生态安全、营造国际生态优质环境。总之,中国要在错综复杂的外交架构中推进生态外交战略,增强生态文明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在维护全球生态正义的同时,担负起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民族重任。
注释:
① 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认为,欧洲的殖民者对新大陆(美洲、澳洲、非洲等地)的成功殖民,得益于他们偶然或者蓄意将旧大陆的动植物、病菌等带到了新大陆,使得新大陆的生态环境和人口发生了重要转换。欧洲殖民者带去的很多病原体感染了当地人口,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这种人口毁灭更甚于武器。所以,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便用“生态帝国主义”概念描述这一事实。由此可见,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的“生态帝国主义”概念是基于纯粹生态学角度的。
② 详见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③ 译文:“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穷人吃肉。这意味着他们会活得更长、更健康,但这对环境来说是个坏消息。”
参考文献:
[1] 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视点[J]. 浙江学刊,2004(4):67-73.
[2] J B Foster. The New Age of Imperialism[J]. Monthly Review,2003(3):55.
[3] 董慧.生态帝国主义:一个初步考察[J].江海学刊,2014(4):60.
[4] 欧庭高,王也.关于转基因技术安全争论的深层思考:兼论现代技术的不确定性与风险[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1):49-53.
[5] Merchant C. The Death of Nature:Women,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M].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3:164.
[6] Roy Rappaort. The Flow of Energy in an Agricultural Society[J]. Scientific American,September 1971(225):122.
[7] Weiskel T. Agents of Empire: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Imperialism[J].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Winter 1987,11(4).
[8]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8.
[9]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3.
[10] 郇庆治.“碳政治”的生态帝国主义逻辑批判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6(3):24-41.
[11] 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M].姚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48.
[12]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14.
[13] 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M].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
[14] 田辉玉,张三元.资本逻辑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J].现代哲学,2016(2):32.
[15] 叶险明.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J].天津社会科学,2014(3):19-26.
[16] 刘顺.资本逻辑与生态正义——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与超越[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6.
[17] 解保,李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J].鄱阳湖学刊,2011(1):63.
[18] 俞可平.生态治理现代化越显重要和紧迫[N].北京日报,2015-11-02(17).
[19] 赵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共识[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2):52-56.
责任编辑:陈可阔
Ecological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XIONG Xiaoguo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130, China)
Abstract: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Ecological colonialism is both an ecological category and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ategory. Its essence is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deprive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the right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which is a "new" colonial form dominat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lonization and expansion of ecosystem, systematic plunder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ed design of ecological barriers. The generated logical system is that eurocentrism is the ideological source, ecological circulation system is the material basis, ecological capitalization is the logical main line, and ecological politiciz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Ecological colonialism pose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We must surpass ecological colonialism and build a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to promote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Key words:ecological colonialism;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capital logic; ecological justice
收稿日期: 2020-10-04
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XJC710010);四川农业大学社会科学专项项目(2019PTYB01)
作者简介: 熊小果(1986—),男,重庆巴南人,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