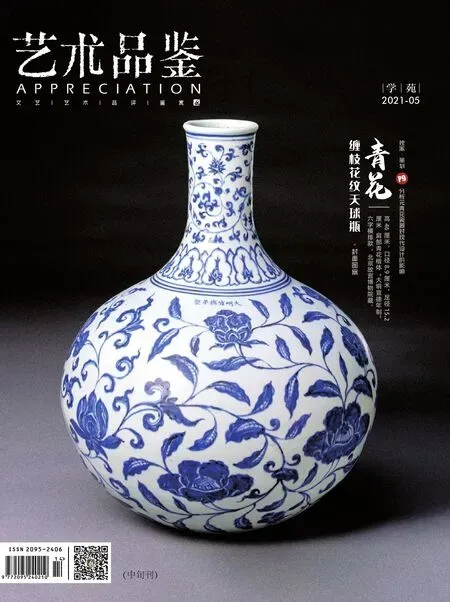大地艺术中的线性时间观念
杜方红
一、近代线性时间观念的影响
人造计时装置是近代线性时间观念产生的源头,利用物理过程将时间均匀分割,使时间呈现出一种线性的递增或者递减。这种技术的不断成熟与普及,使时间成为一条单向延展的直线,这种单向的时间模式彻底改变了世界和人们的生活。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影响最大的发明或许并非蒸汽机,而是钟表。当人类步入工业时代,不再受土地经济的制约,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成为一种必然。从钟表获取时间信息的世界成为一个离开自然界独立运转的人工世界,人类似乎将自身独立于自然之外,像时间一样被人为地分割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控制着人类。近代的线性时间观念下的一切都得以高效率的运转,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产生的后果必然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时间独立于自然之外也注定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漠视。
20 世纪60 年代,人们开始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心理变化反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形式上。作为大地艺术(Land Art)发源地的美国早已处在城市化进程的成熟期,这种成熟的“城市化”背后隐藏着的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地索取。城市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随着空气和水被污染,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的日益增多而逐渐加剧。在短短的二百年内,北美的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近代的线性时间观念使人们的眼光紧盯前方,正如这条时间之轴将永远向前延伸,没有尽头。人们只能被时间追赶再反过来追赶时间,城市在高速运转,人们在肆意挥霍着大自然对这片土地的馈赠。
大地艺术一定程度上是对“冰冷的”近代线性时间观念所产生后果的一种反抗,大地艺术家们将注意力放在了自然问题上,对被破坏的环境感到惋惜。加之环保运动使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连,使大地艺术选择向自然回归成为一种必然。相比“冰冷的”时钟所代表的近代线性时间观念,大地艺术家们更希望通过作品使人们在自然中感知时间。
1973 年到1976 年美国艺术家南希·霍尔特(Nancy Holt)用了近四年的时间在美国犹他州完成了《太阳隧道》(Sun Tunnel)这件作品,混凝土制作而成的隧道创造出了一个观看太阳景观的阴凉庇护所。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四个特殊的时间点,这四个节点标志着新的季节的到来,艺术家根据这四天日出日落的角度放置隧道。在《太阳隧道》中观众能够看到的太阳起落、光斑的变幻通过隧道的孔洞投射在隧道之中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换位置。
在作品完成后不久,南希与艺术家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和电影制作人兼媒体活动家迪迪·哈勒克(DeeDee Halleck)一同参观隧道。三人傍晚时分到达那里,晚上就分别睡在了三个不同隧道之中,根据哈勒克回忆的,三人在日出时很早就醒了,他当时在想,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在阳光的照射下时间有了温度,有了自然界赋予他的面貌。
以太阳作为计时依据的日晷体现着古代人类对于自然计时依据的依赖性,依附于自然的计时方式使人们能够在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之间唤起对自然的崇敬以及对宇宙的遐想。南希·霍尔特的《太阳隧道》正是生活在钟表这种计时装置的笼罩之下的艺术家对近代线性时间观念的一种反抗,倡导一种时间观念的回归,以一种更有“温度”的方式感知时间。
二、时间存在于“消亡”之中
线性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是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时间的流逝不可终止。时间之轴有着明确的方向性,是一条单方向的箭头,这种单一的方向性区别了过去和未来。时间没有尽头,存在于时间之中的任何生命形式都不能避免走向“消亡”。万物皆有终结,时间才有它的意义。
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是来源于对可视物体变化的观察,这个过程漫长或短暂,透过事物的变化得以“看见”单方向的时间流逝,看到了流动着的时间并感知到时间的存在。人们并不能通过各种有关时间的理论去直接感受时间,在艺术作品中我们需要感受到的也只是物体“消亡”引发的时间流逝的感受本身。
在纪录片《河流与潮汐》中,安迪·戈兹沃西运用了大量的冰、雪作为原材料,艺术家在极寒的雪地中拾起的冰锥将其粘合,形成蜿蜒的线条。这个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仅用双手和唾液进行制作,不断地调整位置和长度,最终的作品浑然天成。但在制作的过程中,温度和光线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作品的呈现。安迪·戈兹沃西手捏着冰锥等待冻结,他形容这种感觉像是好几年一样漫长,然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看着他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失。《仲夏雪球》(Midsummer Sonwballs)是安迪·戈兹沃西的一件四屏影像作品,它表现的是在仲夏时节将13 个1 吨重的大雪球放置在伦敦不同街区之中的消融过程。安迪·戈兹沃西认为,能让一件作品具有生命气息的事情,正是能让他消亡的那件事。
大地艺术不可避免的“消亡”属性与艺术所追求的“永恒性”产生了一种矛盾。我们会在这些大地艺术品“消亡”时感到不舍,因为时间经验告诉我们时间有着明显的方向性,事物的“消亡”不可逆转。就像杯子中洒出去的水不会再自己汇集起来回到杯子中。我们的世界就像一支单方向的箭,事物开始于此,而终止于彼,却无法调转回来。
三、时间存在于“绵延”之中
“绵延”一词源于法语La durée(英语译为duration),意为持久、持续、持续期间等,体现为一种没有中断的永恒持续。
如果说在线性时间的前提条件下,“消亡”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绵延”则是我们得以体验时间的一个过程。“绵延”被看作是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分割的延续,那么我们生命就是一个从起点走向终点持续运动的过程。
大地艺术家善于运用自然材料自身的时间属性与作品的构成形式使时间变得可视化,作品的发生过程以及有方向性的持续状态,使我们在作品中得以看到时间的持续流动。相比于空间,时间往往会显得更加抽象,人们对时间的理解有时需要借助对空间的感知来完成。在大地艺术中呈现出的则是一种充分利用了空间性特征、制作与观赏方面的持续性与过程性来表现时间。
安迪·戈兹沃西钟情于蜿蜒的线带来的这种视觉延伸感和时间感的表现力,相比于他更多的瞬时性作品,他在1997 年到1998年间创作的《斯特姆国王之墙》(Storm King Wall)或《去散步的墙》(Wall That Went for a Walk)这件作品在制作过程中就已经可以感知到时间的延伸。这件作品也可称为石墙,它建立在纽约斯特姆国王艺术中心中的树林间,这件作品的建造历时两年,在苏格兰的工匠帮助下建成,这面弯曲延伸的墙宽约5 英尺,长度约2278 英尺。这面石墙从山坡上下来,进入池塘,被池塘淹没又从另一端跃出水面,进入树林,这面墙在树林间蜿蜒穿行。整件作品除了形式上的美感之外,在于艺术家在有意无意之中使人跟随石墙的线条进行视觉上的蔓延,从而感知到时间的延伸。

理查德·朗的行走艺术有着明显的持续性与过程性。时间在他的作品里显现的面貌是他在大地上留下的一条条“走出来的线”,这条“线”从起点开始随着足迹向前延伸,从行为发生、行为结束到最终呈现的结果,在过程与结果中表现了顺时针的时间次序。《走出来的线》(A Line Made by walking)产生在理查德·朗于1967 年就读于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St.Martin’s School of Art)期间,当时的他开始进行将身体作为艺术表现语言的可能性初探。理查德·朗在一条通向茂密森林的青草地上来回多次的往返,作品的表达形式和物质载体是由艺术家在大地上进行的方向性的运动。这种身体的移动所留下的痕迹形成一条直线线条,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无疑是有着过程艺术的影响与表达方式。这种过程性体现在艺术家在行走过程中点状步伐痕迹的单向性累积,这种持续性的重复动作以时间作为支撑并伴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步伐痕迹的不断叠加,这种足迹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时间存在过的痕迹,点动成线形成了一种直线形式,最终呈现的是一种在观赏中视线与心灵不自觉的线性延伸。这种线性的延伸并不是偶然的一次艺术尝试,在之后的艺术创作中,理查德·朗曾多次呈现出这种线性延伸的作品。
如果时间是可视的,除却钟表上的数字,我们亦能在艺术家的创作过程、艺术品的形式中感知到时间的存在。这些以线作为表现形式的大地艺术与上文提到以事物“消亡”为结果的作品形成了一种反差,这种线的形式以及创作方式具有相对的持久性,能让人们在作品中获得时间段的体验。延伸的线无论是蜿蜒的或垂直向前的,在视觉上都会带来一种延伸感,而这种空间上的延伸感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以时间为基础才得以表现出来的。作为艺术作品必然有着限定的尺寸,戈兹沃西的石墙以及理查德·朗的行走的线不会真的无止境地“绵延”下去,艺术家也无意于此,但至少在作品中表达的以及我们获得的是对生命中一段时间的重视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