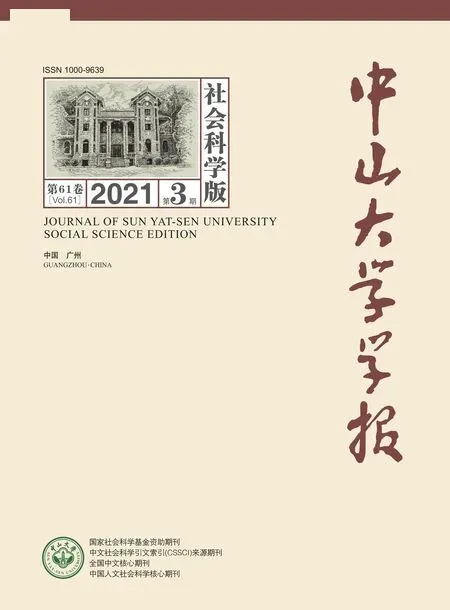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王 磊
佛教律藏之传译,在5世纪上半叶达到高峰。以《十诵律》为始,二十余年内,四部广律的汉译本相继问世,为中国佛教戒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鸠摩罗什参与翻译的《十诵律》作为第一部汉译广律,在中国佛教戒律史上意义重大。与当时的很多佛教经典一样,《十诵律》的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文本形态。这些不同时代的文本,有的被收藏在大藏经中,承续至今,有些则遗失在藏外,逐渐湮没。关于唐宋时期大藏经内的文本,笔者已有另文介绍①王磊:《中古时期〈十诵律〉文本结构之演变——以藏经本为中心的考察》,《文献》(待刊)。,本篇论文则着重讨论几件比藏经本渊源更为古老的敦煌写本。
敦煌遗书中收藏的《十诵律》多为藏外文本,其中几种写卷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如果说藏内文本展示了唐宋以来《十诵律》的成熟面貌,那么六朝时期的敦煌写卷则保留了早期译本的原初形态。因为,不仅它们的抄写年代与《十诵律》的汉译年代相近,如同后文所述,它们的内容也更为接近鸠摩罗什译本的原貌。
关于《十诵律》的翻译、流传、修订经过,乃至六朝时期对佛教僧团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藉重《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等文献的记载,采用的《十诵律》文本也主要依据唐代以后的大藏经本。而敦煌遗书中的《十诵律》六朝写卷,则向我们展示了与藏经本大相径庭的文本形态。这些敦煌写卷有助于我们理解《十诵律》在传译过程中发生的具体变化,使我们对该广律的传译及六朝时期的传播有全新的认识,对于当时中土佛教与印度佛教之间的关系,也能有更直观的认识。
下面,笔者将首先介绍三件独特的六朝《十诵律》写卷,并力图在《十诵律》翻译史的背景下理解这几件六朝写卷的重要意义,同时进一步反观《十诵律》的翻译经过,以期对鸠摩罗什的翻译有全新的认识。
一、三件独特的敦煌写本——S.797、S.6661、BD03375
敦煌写本中与戒律相关者,就广律而言,主要以《四分律》为大宗,其他几种广律写本则相对少见。根据笔者个人的粗略统计,目前分藏于各处的敦煌写本中,《十诵律》各卷的写本共有20个左右。本文择取其中的三件,S.797、S.6661、BD03375,作为重点的讨论对象。之所以将目光聚焦于这三件写本,是因为它们的文本结构和文本内容与其他写本以及唐宋以后的藏经本相比均有很多独特之处,对于我们了解《十诵律》的翻译及其在中古时期的传播,有重要价值。
为斯坦因所获、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S.797,在敦煌写本的研究史上一直不乏关注①图版可参见方广锠、吴芳思主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写本正反两面书写,一面内容为十诵律,卷首残,卷尾全,存567行。尾部有尾题“第七卷”,尾题下有题记“比(丘)德祐书一校竟”。原写本在校勘时曾增补大量内容,以小字书于行间。
写本背面为比丘戒经,戒经条文后接七佛偈②此戒经内容与今各大藏经收录之十诵戒本有很大的不同。偈语文字亦如是。前六佛之偈语,与《增一阿含经》卷四十四“十事品”中过去六佛之偈语文句基本一样,第七佛释迦文佛则与《增一阿含经》及藏经本所收十诵戒本均不同显然此戒本为十诵戒本之一新版本。从题记可知其译出年代当在藏经本《十诵》戒本之前,但具体的来龙去脉尚无深入的研究。方广锠在该写本的“条记目录”中称它可能是昙摩持共竺佛念译本,但尚缺乏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戒本中的部分条文与《十诵》戒本并不相合,而与唐代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戒经》相合。,偈语后为受岁羯磨文。之后有比丘德祐所书之题记:
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时,比丘德祐于敦煌城南受具戒,和上僧法性,戒师宝慧,教师惠颖。/时同戒场者,道辅、惠御等十二人。到夏安居写。到③到:疑为“对”之讹误。戒讽之,趣成,具【拙】字而/已。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义,莫笑其字也。故记之。④题记录文可参见池田温編:『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80頁。此处标点有调整。写本于方括号内的“拙”字处有删除符。
从题记内容看,该戒本是敦煌比丘德祐受戒时所书,所以戒本后还附有受岁羯磨文,整个写本正反映了当时受戒之仪式。由题记可知,此戒经写于西凉建初二年,即公元406年⑤以往学者均将此写本的年代定为405年。方广锠在该件写本的条记目录中首次对该写本的年代做出了修正他指出,题记中虽提及建初元年,但那是德祐等人受戒的时间,题记实际写于受戒之后的夏安居,即建初二年。。抄写者比丘德祐与背面《十诵律》的抄写者德祐当为一人,这件写本最初应当是德祐的私人物品。戒经写于建初二年,《十诵律》当也写于此年前后。带有“建初元年”的题记使它被认为是敦煌藏经洞中有确切纪年的最早佛教写本,所以备受学者的关注⑥矢吹庆辉在《鸣沙余韵》(解说篇)首次提到这是斯坦因搜集写本中有纪年佛典写本中最早的一件(京都:临川书店,1980年,第123页),之后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也都将它作为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写本加以介绍。不过现存佛经写本中有甘露元年《譬喻经》及麟嘉五年(393)《维摩诘经》,但目前学界认为这里的甘露可能是高昌年号,而非前秦甘露元年(359)(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7页),池田温则认为麟嘉五年的《维摩诘经》可能出自吐鲁番,而非敦煌(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02—103页)。所以目前可以确认的有纪年的最早敦煌佛经写本仍然为S.797。。但是就写本内容,除了平川彰的一篇短文⑦平川彰:「敦煌寫本十誦律の草稿訳と敦煌への伝播」,载『岩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東京:岩井博士古稀記念事業會,1963年,第545—551頁。,目前关注的尚少。
从下文可知,无论是分卷形式还是文本内容,此写本正面的《十诵律》,均与目前所见的各种刊本藏经所收录的《十诵律》有很大不同。无独有偶,在敦煌本中,S.797并不是孤例。在斯坦因所得敦煌文献中,还有另一件与S.797内容几乎完全一样的写本S.6661⑧图版参见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5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47—56页。。该写卷首残尾全,存513行。文本有校勘的痕迹,校勘时增补了大量的文字,写于行间。卷末有尾题及题记:“衣法第七(已二校)僧灵寂僧弘文僧腾。”该写本内容与S.797基本完全一样,甚至连写本校勘时所增补的内容大部分都能对应,可知二个写本所据底本及校勘本均有相同的文本来源。写本尾题并未交代书写年代,但从字体判断,与S.797年代当相差不远,也在5世纪初①翟理斯(Lionel Giles)作《英国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写本注记目录》(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7),也将此件定为5世纪早期写本(第164页)。。
第三件要介绍的写本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最初的千字文编号为雨075,新的馆藏号为BD03375②图版参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4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95—208页。。该写本首尾均残,尾部正文部分内容完整,但写本恰在正文结束之后断开,是否有尾题和题记不得而知。从字体判断,写本当抄写于5世纪初,与S.797也相差不远。前两件写本的内容同属七法中的衣法,此件则为七法中的“自恣法”,相当于藏经本卷23。但因未见首题与尾题,不知本来的分卷情况。与上面两个写本一样,此件写本的文本内容与藏经本亦有大量不同之处。
S.797、S.6661、BD03375三件写本均抄写于5世纪初,与《十诵律》的翻译差不多同时。但在文本结构和内容上,与唐宋之后的各种藏经本均有很大的不同。这提示我们,在现存的藏经本《十诵律》之外,尚存在另一种和它内容差异较大的文本,而且文本的年代早于目前所知的各种藏经本。这些抄写于翻译年代前后的六朝写本,为我们更深入了解《十诵律》的翻译提供了重要的信息。下面我们就先从文本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看看这几个敦煌本③为行文方便,下文均以“敦煌本”代指S.797、S.6661和BD03375三件写本,如有特殊情况,另行说明。和藏经本的差异。
二、敦煌本所见六朝时期《十诵律》之文本结构
《十诵律》的文本结构,或称分卷形式,在中古时期的各种藏经本中即体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大致而言,一为毗尼序位置的变动,二因第七诵分卷不同导致前五十八卷分卷不同,进而导致部分卷帙的分合。而将敦煌本也纳入考虑范围之后,分卷形式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前文介绍过的S.797与S.6661,两本首部皆残,目前残存内容大致相当于刊本藏经《十诵律》之卷二十七中部到卷二十八末。根据S.6661的尾题“衣法第七”,该卷当囊括了七法中衣法之全部内容,也即它们是将藏经本廿七、廿八两卷合为一卷,写本卷首相当于藏经本卷二十七之首。就目前所见各种资料,从宋代两种刊本藏经,往前到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日本正仓院所藏圣语藏本,再到六朝时期《翻梵语》所引《十诵律》,衣法部分均分为两卷④《翻梵语》卷八“桑祇陀国”一词取自《十诵律》的“七法第八卷”(CBETA,T54,p.1035b22),翻检大正藏《十诵》经本,该词见于卷二十八,可知《翻梵语》所据之本衣法部分已经分为两卷。,S.797与S.6661的这种分卷方式为目前各种版本所未见,属一种新的分卷系统。
除分卷不同之外,S.797和S.6661的尾题更值得关注。S.797的尾题作“第七卷”⑤写本“卷”写作“”,平川彰可能对写本的书体不熟悉,所以将该字认作长度单位“弓”,在文章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解释此处用“弓”之意涵。,而其内容相当于藏经本廿七、廿八两卷,如果这里的第七卷是指该卷在整部《十诵律》本中的卷数,显然难以对应。结合S.6661的尾题“衣法第七”,显然S.797的“第七卷”指的正是“七法”的第七卷。它们所属的十诵律系统当是将第四诵七法部分每法一卷,第七法衣法恰为第七卷,而如今的藏经本则皆将第七法分为两卷。S.797和S.6661的尾题显示六朝时期对《十诵律》文本组织形式的认识与唐宋之后的藏经本有很大不同。它们更注重各卷在每诵之内的卷数与位置,对于其在整体《十诵律》内的位置卷数则不甚关心。可能当时的《十诵律》是以诵为单位组织的。这种标注方式在《翻梵语》《经律异相》等六朝文献中也有很清楚的体现。
《翻梵语》目前藏经本均无作者,现在一般认为是南朝梁代宝唱所撰①小野玄妙:「梁莊嚴寺寶唱の翻梵語と飛鳥寺信行の梵語集」,载小野氏著『仏教の美術と歴史』,東京:大藏出版社1937年,第859—866頁;船山徹:『六朝隋唐仏教展開史』,京都:法藏馆,2019年,第13頁。。该书所引译语多有出自《十诵律》者,且在每一词后会注明该词出自书中何卷。而在注释时,并不直接说十诵律卷某,均用“某诵第〇卷”的方式,而第四、五、六、七、九、十各诵,因皆有专名,引用时又直以专名代之。《经律异相》在引用《十诵律》时,亦采取相同的标注方式。进而有时“某诵”也被省略,径直以“十诵律某卷”称引。如《翻梵语》卷一“佛名第二”引“那罗延力”,注明出自“十诵律第五卷”②CBETA,T54,p.982a9.,翻检藏经本,此词只见于卷二十五,正当第四诵七法之第五法皮革法,这里的“第五卷”指的是第四诵第五卷,而不是《十诵律》的总卷数。这与S.797的尾题“第七卷”如出一辙。
这种标注方式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十诵律》本上找到例证。如同为敦煌写本的S.751,该写卷无题记,方广锠判断是5世纪东晋时期的写本③《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3册“条记目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十诵律》翻译时已是东晋末年,此写本是否是东晋时所写不能骤断,但从字体判断写于5世纪当无疑议,和S.797、S.6661一样,都属《十诵律》译出之后不久的写本。写卷首残尾全,尾题写作“十诵毗尼初诵第五卷”,这个尾题显然要强调的是,该卷为初诵的第五卷,也是以诵为单位来定位每卷的位置④而且该卷的分卷也很有特色。它的尾题写作“初诵第五卷”,内容为三十尼萨耆十四事至二十八事竟,相当于藏经本第七卷下半到第八卷中,显然写本分卷与藏经本不同。而且藏经本该部分属第二诵之一到二,但写卷则属初诵,显然二者诵与诵之间的分界也不同,这中分卷方式目前尚未见于他处。。
日本的圣语藏和金刚寺等寺院所藏写本一切经也部分保存了这种卷帙标注方式。如圣语藏天平十二年御愿经之《十诵律》卷三十四,首题大字书“十诵律第五诵卷第六”,下小字书“卅四”二字,“六”字旁有红笔圈注,亦书“卅四”二字。原卷无尾题,在尾部题记前有红笔补书尾题“十诵律第五诵卷第卅四”一行。显然原写卷之标题更着意于强调该卷为第五诵之第五卷,而红笔圈注及补书之尾题则代表了后世僧人对于《十诵律》文本构成方式与前代不同的新认识⑤圣语藏CD光盘。光盘资料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池丽梅教授代为查询,特此致谢。。金刚寺写经之《十诵律》卷五十九,标题作“十诵律善诵卷第二”,尾题也直接写作“十诵律卷第二”⑥本文所涉金刚寺写本信息,均由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落合俊典先生不吝惠赐,特此致谢。。
金刚寺写经的《十诵律》“第三卷”更清晰地反映了这种旧的标注方式对藏经本的影响。写经第三卷卷轴外题书“十诵律卷第三”,古写经研究所的数据库也将此卷作为全书的第三卷著录。但打开卷轴,该卷首题明白写作“十诵律第四诵卷第三”。尾题欠,据前文推测大概写作“十诵律卷第三”,后世僧人故径将此卷作为《十诵律》的卷三,现代整理者也没有发现这一错误,故在数据库中仍沿袭此误未改。
三、敦煌本与藏经本之文本对勘
目前所能见到的《十诵律》传世文本,无论是日本的古写经本,抑或宋代以后的各种刊本藏经本,虽然在分卷等文本结构上有各种不同,但是具体的文本内容并无明显差异。而S.797、S.6661、BD03375三件敦煌写本,除了分卷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文本内容上亦与目前所见之藏经本有非常大的不同。这几件敦煌本的抄写年代均在5世纪初,远远早于唐宋之后的藏经本。这三件写本都是残存数百行、篇幅巨大的长卷。限于文章篇幅,不能将全部录文附上,下面将截取写卷中的部分内容,与藏经本内容做对勘,以显示这几件写卷其文本内容的独特之处。
一个文本产生之后,在流通的过程中由于抄写、刊刻等原因造成文本讹误,在版本校勘学上是很常见的,在敦煌本和藏经本的对勘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S.797的374行“云何堕筹分是衣作两分应”之后的375行则以“佛在舍卫国”开头,显然两行的文义不能连贯,374行之后有脱文。S.6661此处果然多了十余行文字:

但S.6661在此处也有缺文,藏经本在这段话之后,又多出一百余字的内容①CBETA,T23,p.202a27-b4,p.195b17-c1.。但这三个敦煌本与藏经本的文本差异,大部分都不能以这种技术原因解释,而是刻意所为。这些非技术问题导致的文本差异,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种,写本与藏经本在翻译相同段落的文字时,虽然文意大致一样,但在具体的词句及语法表达上,常有大不同,有明显人为校改的痕迹。这种词序与表达的差异贯穿全文,几乎句句皆有不同,以下兹举两例。衣法部分有毗舍佉施舍雨浴衣因缘,其中有佛与阿难讨论星相的一段文字,该段文字S.797翻译如下:
其夜中间佛与阿难初夜空地经行,瞻视星宿。告阿难:“若是时知相诸披罗门,他问几时雨,彼当言七岁。阿难!过初夜,中夜来,此星宿相失,更星宿相出。是时若他问诸知相披罗门几时雨,彼当言七月。阿难!若过中夜,彼后夜来,是星宿相失,更星宿相出。是时若他问诸知相披罗几时雨,彼当言七日。若后夜竟,是时东方厚云起,状如盖遍布,如是南方西北一切云起遍雨,随高下悉满。佛告阿难令诸比丘知商浩云雨得除病安隐,告诸比丘欲路地浴者听。阿难受敕,告比丘诸长老知商浩云雨除病安隐,若比丘欲路地浴者听。是时诸比丘裸身路浴。(38—47行)
而藏经本则译作:
佛是初夜共阿难露地经行,佛看星宿相,语阿难言:“若今有人问知宿星相者何时当雨?彼必言七岁当雨。”佛语阿难:“初夜过已中夜至,是星相灭,更有异星相出。若尔时有人问知相者何时当雨?彼必言过七月当雨。”又语阿难:“中夜过已至后夜,是星相灭,更有异星相出。若尔时问知相者何时当雨?彼必言七日当雨。”是夜过地了,时东方有云出,形如圆椀(碗),遍满空中,是云能作大雨,满诸坑坎。尔时佛告阿难:“语诸比丘:‘是椀云雨有功德能除病,若诸比丘欲洗浴者露地立洗。’”阿难受教语诸比丘:“是碗云雨有功德能除病,诸比丘欲洗浴者露地立洗。”时诸比丘随意露地立洗浴。②C B E T A,T 2 3,p.2 0 2 a 2 7-b 4,p.1 9 5 b 1 7-c 1.
整体而言两段话的意思大致相同,能够从字里行间体察到二者的相似性,但是几乎每句话又都有不同之处。如“若是时知相诸婆罗门,他问几时雨”与“若今有人问知宿星相者何时当雨”两句,虽文义相同,但语序有异。“东方云起”一段,敦煌本有“如是南方西北一切云起遍雨”一句,但藏经本只言“遍满空中,是云能作大雨,满诸坑坎”,并无“南方西北”等语。而对于所起之云,敦煌本形容是“状如盖遍布”,藏经本则作“形如圆碗”,对表示云形状的形容词的翻译也全不同,而且布和碗,似乎对应的并不是一个词。
又比如在衣法的后半部分讲八种布施时在制限布施部分,敦煌本有一段文字翻译作:
佛言:“若一部上坐第二上坐,一部应受。若一部上坐,二部上坐,第二上坐是。”布施檀越二部不分别与,白佛言:“是布施诸衣物谁应受?”佛言:“一切应分。”诸比丘言:“何等应分?”佛言:“次第应分作四分,第四应与沙弥。”是为制限得布施。(S.797,第277—280行)
同段内容在藏经本中则翻译如下:
佛言:“随何部作上座,是物应属一部。”若檀越捉第一上座手、第二上座手言,是物施僧,是物应属谁?答言:“二上座是一部上座,应属一部。”“若二上座各是一部,应属二部,云何应分?”答言:“次第等分四分,第四分应与沙弥。”是名制限得布施。①CBETA,T23,p.200b23-c1.
这两处翻译中划线部分的差异较上文星相之例更有过之。就文意而言,藏经本的翻译更为流畅,敦煌本的语义表达相对混乱,较藏经本更难于理解。
同样是语词的不同,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形,即某些梵文词汇的译语,敦煌本与藏经本完全不同。如衣法部分藏经本多次出现的“迦那衣”一词,敦煌本均译作“一日衣”,这种译法与较《十诵律》译出更早的《鼻奈耶》更为接近②《鼻奈耶》此词均译作“一日竟衣”,如卷一:“结坐已竟,三月补纳衣裳,一日竟衣已办。”(CBETA,T24 p.851c11-12),如今“迦那衣”已成为僧团普遍接受的戒律术语,“一日衣”则被舍弃。藏经本中经常出现的“粪扫衣”一词,在敦煌本中也均译作“槃薮衣”或“波薮衣”。但在藏经本中,也有两处作“槃薮衣”③第一处见于“衣法”开头第一句:“佛在王舍城。五比丘白佛:‘应着何等衣?’佛言:‘应着槃薮衣。’”(CBETA T23,p0194b10-11)第二处见于粪扫衣部分的最后一句:“从今日若比丘欲着槃薮衣听着,若欲着居士施衣亦听着。(CBETA,T23,p0194c10-11)宫本此两处亦同,但“槃”作“般”。。BD03375中常出现的“我曹”“精舍”“异住处比丘”“是诸比丘”等词,藏经本中对应的则为“我等”“僧坊”“旧比丘”“彼”等词。BD03375在最后数行又数次出现“鼻贰”一词,在藏经本中皆替换作“比尼”。此词即梵文“vinaya”之音译,在隋唐时期的佛教经典中也常译作“毗奈耶”,即戒律中“律”之意。相较“比尼”,“鼻贰”这一译法出现的更早,在《鼻奈耶》中常见④CBETA,T24,p.899b24-26.该词在苻秦时所译《四阿鋡暮抄解》及《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也各出现一次。,BD03375的用法应该是继承了早期的译法,藏经本将之替换为“比尼”⑤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十三《佛说瞿昙弥记果经》音义部分有“鼻贰”一词(CBETA,K35,p.21b4-5)。现藏经中有刘宋慧简所译《瞿昙弥记果经》一卷,当即可洪音义之经。但今本中已不见“鼻贰”一词,被代之以“毗尼”(CBE TA,T01,p.857a7)。而根据《大正藏》的校记,《鼻奈耶》中“鼻贰”一词,江南系统的藏经本均作“毗尼”,显然也经校改。。
第二种文本差异表现在对重复文本的处理上。梵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叙述时对相同内容的不断重复,这主要是为了便于日常记诵⑥诺曼(K.R.Norman)著,陈世峰、纪赟译:《佛教文献学十讲》,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第63—67页。,而在书写时为了方便,这些重复内容常以各种方式被缩略。《十诵律》也有很多这类情形。不过敦煌本和藏经本对重复内容的缩略处理方式并不完全一致,有敦煌本未缩略而藏经本缩略者,也有敦煌本缩略而藏经本未缩略者,显示两种文本之间的差异。
首先是敦煌本未缩略而藏经本缩略者,最明显如BD03375末尾部分。该卷内容主要讲僧人自恣之法。藏经本在列举了多种自恣的情况之后,最后称“余如布萨中广说”⑦CBETA,T23,p.173a8-9.。但是BD03375则没有这句话,却较藏经本整整多出53行共1387字的内容(361—413行)。翻检《十诵律》本,此段文字恰与同样属七法的布萨法中一段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将“布萨”换为“自恣”⑧CBETA,T23,p.163c17-164c13.敦煌本自恣部分除了替换“布萨”二字外,与藏经本布萨部分亦有少许表达上的文字异同,当是因为藏经本布萨部分的文字也已经过改动。。因此藏经本以“余如布萨中广说”一句话替代了一千多字的内容,而敦煌本则保留了原文。
而在其他一些部分,也有敦煌本缩略而藏经本未作缩略者,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因文章篇幅限制,仅举一例。S.797第80—95行:
大德!我当问:“是长老曾来舍卫国不?”若我闻是长老比丘曾来,我思惟:“是长老或受我浴衣、或受客比丘饭食、若远行比丘饭食、若病比丘饭食、若瞻病饭食、若常与粥、若病比丘汤药及诸所需诸物。”大德!我作是因缘故觉意满……大德!我是时思惟:“是长老或受我浴衣乃至病比丘所须汤药及所须诸物。”大德我作是因缘故觉意满……我思惟:“是长老或受我浴衣乃至病比丘汤药所须诸物。”我作是思惟因缘故觉意满……我思惟:“是长老或受浴衣乃至病比丘汤药及所须诸物。”我作因缘觉意满。
藏经本对应段落则为:
大德!我当问:“是长老曾来舍卫国不?”若闻是比丘曾来舍卫国,我思惟:“是长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饮食、或远行比丘饮食、或随病饮食、或看病饮食、或常与粥、或病比丘汤药诸物。”大德!我以是因缘故觉意满。……我如是思惟:“是长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饮食、或受远行饮食、或随病饮食、或看病饮食,或常与粥、或病比丘汤药诸物。”大德!我以是因缘故觉意满。……我思惟:“是长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客比丘饮食、或远行饮食、随病饮食、或看病饮食、或常与粥、或病比丘汤药诸物。”大德!我以是因缘故觉意满……我思惟:“是长老或受我雨浴衣、或受客比丘饮食、远行饮食、随病饮食、看病饮食、或常与粥、病比丘汤药诸物。”我以是因缘故觉意满。①CBETA,T23,p.196b2-27。
事实上,这种对重复内容处理之不一致,不仅在敦煌本和藏经本之间存在,在唐宋时不同的藏经本之间也可以见到。守其《高丽国新雕大藏校正别录》(以下简称《校正别录》)卷二十有关于《十诵律》的校记一条,记录了国本(高丽藏初雕本)、宋本(开宝藏本)、丹本(契丹藏本)三个藏经本卷五的异文。据守其描述,“此卷第二十六张第二行‘夜提(之下)乃至三十日皆如上说者’,丹本无此中九字,而有‘又比丘得不具足衣(乃至)至三十日地了时尼萨耆波夜提(等)’凡九十一行文,国本宋本并无者,今依丹本递而足之”②CBETA,K38,p.647b21-c3.(K表示高丽藏再雕本)。显然宋本、国本均以“皆如上说”一句话,缩略了丹本所存的九十一行共1,296字。高丽再雕本根据守其的校勘,将这一千多字补入正文。而江南系统的宫本,也如“国本、宋本”,以“十二日乃至三十日亦如上说”十二字代此九十一行文字。初雕本等经本并非缺失了这一千多字,而是以“亦如上说”代替之。“亦如上说”,跟上文提到的“余如布萨中广说”,是一个道理。守其在校记中提到三处类似的情形。根据大正藏的校记,还有两处高丽再雕本未缩略而宋元明本等江南系统藏经缩略处。根据池丽梅的统计,合计此卷五处所有的缩略,契丹藏本大致比开宝藏本多3,935字,高丽再雕本较江南系统藏经本多出5,124字③池丽梅:「契丹藏が基づいた『一切經源品次錄』——高麗初雕藏本の再発見とその意義」,『日本古寫經研究所紀要』第6號,東京: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附置日本古写経研究所,2021年3月,第25—59頁。。三个系统的藏经本在此卷文本的缩略处理上均有不同。
第三种,则是写本与藏经本因具体的文本内容不同而导致文意有不同者。戒律是对僧人日常行为的规范,文意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僧人对戒律的理解与戒律实践。如衣法部分有佛与众比丘讨论各种材质制成之衣当着不当着的问题,列举了可着之衣与不可着之衣,敦煌本与藏经本在可着、不可着衣的名目上有多处不同,有些是译名的差异,不可着衣的种类藏经本也远多于敦煌本。而且藏经本可着之衣中之沙尼衣,据《翻梵语》可译为树皮衣④CBETA,T54,p.1005b4-5.此段衣物译名多为音译,《翻梵语》卷三对此处多数译语有解释,可参考。从其取词可知其所据底本与藏经本更为接近。,但在敦煌本中树皮衣则为不可着之衣。显然二者之规定不同,对于僧人的戒律实践也有直接的影响。
又比如藏经本与敦煌本在解释“堕筹分”这一概念时,也有一关键处不同。S.797“若堕者,诸比丘犯突吉罗。亦不应与异比丘共分”一句,藏经本作“亦应异比丘共分”,少一“不”字,文义恰相反。藏经本在多处提及堕筹分时皆是如此解释,显然不是偶然抄写错误。
以上是对三个敦煌写本与唐代以后的藏经本的文本内容比较。二者的文本在译语选择、文句语序、对重复内容处理上,都有很多的不同,在这三种不同情况的交织下,S.797、S.6661、BD03375三个敦煌写本的文本内容与藏经本相较,几乎句句有异,段段不同,部分地方还改变了文意,直接影响僧人的戒律实践。而BD03375与S.797、S.6661虽分属不同的卷次,但从文本内容表现的特征看无疑属同一系统。也就是说,在中古时期曾存在一个文本内容与今天所见有很大不同的《十诵律》本。
这三个敦煌本的抄写年代均为5世纪初,且据前文的分析,它们的译语多前接早先译出的《鼻奈耶》,表现出很多古老的特征。综合来看,这几个敦煌本所依据的底本,无疑要早于目前的藏经本。但就这二者在文本内容整体的同质性及所使用翻译表达的相似性看,无疑属于同一个翻译文本,二者在源头上属于同一个文本系统。前面在分析文本异同时曾提到有很多词,两种文本所使用的译语常有不同,如以精舍对僧坊等,但敦煌本所使用的译语在藏经本中常有零星出现,显示藏经本的译语是对敦煌本的替换,而零星残余则是替换时的遗漏,这也是藏经本校改敦煌本的最明显证据。敦煌本上接《鼻奈耶》的传统,而藏经本的用语则开启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新篇章①平川彰在《律の研究》(东京:山喜房佛书林,1960年)一书中曾专门讨论《十诵律》的译语对确立中国佛教戒律术语的重要贡献。目前僧团仍在使用的戒律术语有很多是《十诵律》首创。但从本文的分析可知《十诵律》的译语并非生就如此,而是译出之后再经替换,方成今日面貌。。至此,我们基本可以判定藏经本是在敦煌本的基础上校改而出现的一种新文本。
目前所见的敦煌写本,除了S.797等三件之外,其他写本的文本内容与藏经本已几无二致,这其中也包括前文提到的书写于5世纪的S.751。可知文本内容的校改在5世纪也即律本刚译出之时已经完成。由此可进一步推知,从S.797等三个敦煌本所代表的旧本到藏经本的文本变动,不大可能是在漫长时间内逐渐成形的,而是在译本出现之后在短时间内发生的一次突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文本内容的突变是如何出现的。结合目前掌握的各种材料,答案还要回到《十诵律》的翻译史中去寻找。
四、《十诵律》传译史梳理
《十诵律》的翻译过程,在僧祐《出三藏记集》(以下简称《祐录》)和慧皎《高僧传》等文献中都有相关的记载。《祐录》卷三“新集律来汉地四部记录”条对传译之经过记载颇详:
至秦弘始之中,有罽宾沙门弗若多罗,诵此《十诵》胡本,来游关右。罗什法师于长安逍遥园,三千僧中共译出之。始得二分,余未及竟而多罗亡。俄而有外国沙门昙摩流支,续至长安。于是庐山慧远慨律藏未备,思在究竟。闻其至止,乃与流支书曰……昙摩流支得书,方于关中共什出所余律,遂具一部,凡五十八卷。后有罽宾律师卑摩罗叉来游长安,罗什先在西域,从其受律。罗叉后从秦适晋,住寿春石涧寺,重校《十诵》律本,名品遂正,分为六十一卷,至今相传焉。②僧祐撰,苏晋仁、萧链子点校:《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16—117页。
《十诵律》的译出,前后经历数人,二十余年方告完成,过程颇为曲折。这其中所涉诸人,《高僧传》译经篇皆为立传,传记内容又颇有能对僧祐的记载补充之处。历来认为《十诵律》为鸠摩罗什所译,但实肇端于弗若多罗来华。《祐录》称他“诵此《十诵》胡本,来游关右”,《高僧传》弗若多罗传则曰“伪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罗什)集义学僧百余人,于长安中寺,请多罗诵出十诵梵本,罗什译为晋文”,此次翻译中多罗的角色是诵出胡本,然后由罗什译为中文。所以现在藏经本的译者署名为“弗若多罗共罗什译”①开宝藏系统和江南系统藏经的署名有些微不同,高丽再雕本作“后秦北印度三藏弗若多罗共罗什译”,江南系统则作“姚秦三藏弗若多罗共三藏鸠摩罗什译”。,多罗列在罗什之前,也显示他在此次翻译中的角色至关重要。至于多罗所诵出之本,《祐录》称是“胡本”,《高僧传》则曰“梵本”,考虑到多罗是罽宾僧人,六朝时期的罽宾为犍陀罗地区②罽宾的地望,学者们历来有争议,桑山正进结合佛钵的传说,认为六朝文献中的罽宾指的是犍陀罗(桑山正進:『カーピシー=ガンダーラ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0年,第35—59頁)。,当地使用犍陀罗语,目前考古也发现了很多犍陀罗语的佛教写本③邵瑞琪(Richard Salomon)著,心举、朗安译,会闲校:《犍陀罗古代佛教经卷:大英图书馆佉卢文残片概述》,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可能多罗所诵之本就是犍陀罗语本。多罗来华的时间,僧祐只言在秦弘始中,具体时间未明言,《高僧传》称是“伪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当公元404年,翻译应当开始于此时前后。但翻译工作的进展并不顺利,“三分获二,多罗遘疾奄然弃世”。多罗去世,无人诵本,翻译中辍。接续弗若多罗事业的是昙摩流支。据《流支传》④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1—62,54,63—64页。,他是西域人,“偏以律藏驰名”,“以弘始七年秋达于关中”,也即多罗来华之次年。据《祐录》,流支至长安在多罗去世之后,则多罗与罗什的翻译在弘始七年之前已经完成。
流支在关中接到庐山慧远的书信,希望他能够接续多罗未竟之业。“流支既得远书,及姚兴敦请,乃与什共译《十诵》都毕,研详考核,条制审定,而什犹恨文烦未善。既而什化,不获删治。”流支在翻译中的角色可能和多罗一样,也是诵出胡(梵)本。僧传只说他是西域人,不知道他诵出的是胡本、梵本抑或是犍陀罗语本?不过在目前的藏经本署名中,我们并未发现流支的名字,他与罗什合作翻译的部分到底是哪些,已经无从知晓⑤目前所见诸种藏经本,圣语藏及金刚寺古写经各卷卷首多无译者题名,其他宋代以后刊本藏经均标注为多罗共罗什译,而丝毫不及流支之名。。这次翻译直到罗什去世才勉强完成,而且只是完成了文字的翻译,尚不及删改⑥关于罗什去世的时间,文献记载有不同说法。《高僧传》称在弘始十一年(409),传记最后,慧皎又言:“然什死年月,诸记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或云十一年,寻七与十一,字或讹误。而译经录传中,犹有一年者。恐雷同三家,无以正焉。”显然慧皎已经看到数个不同的说法。而《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僧肇为罗什所写之诔文,则称在癸丑之年即弘始十五年(413)。塚本善隆曾对此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他采信弘始十一年的说法(「仏教史上における肇論の意義」,载塚本氏编『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馆,1955年,第130—135页),这个说法也被之后的学者所接受。。鸠摩罗什传也称“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唯《十诵》一部,未及删烦,存其本旨,必无差失”⑦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1—62,54,63—64页。。
后续删改的工作由罗什的老师卑摩罗叉完成。据《高僧传》,罗叉也是罽宾人,“先在龟兹,弘阐律藏,四方学者,竞往师之,鸠摩罗什时亦预焉”,则罗什曾从他学律。罗什在长安时,罗叉到长安,时在弘始八年(406)。“及罗什弃世,叉乃出游关左,逗于寿春,止石涧寺……罗什所译《十诵》本,五十八卷,最后一诵,谓明受戒法,及诸成善法事,逐其义要,名为‘善诵’。叉后赍往石涧,开为六十一卷,最后一诵,改为毗尼诵,故犹二名存焉。”⑧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 9 9 2年,第6 1—6 2,5 4,6 3—6 4页。《祐录》也称“罗叉后从秦适晋,住寿春石涧寺,重校《十诵》律本,名品遂正,分为六十一卷,至今相传”。可知在卑摩罗叉的手上,《十诵律》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罗叉的校改首先体现在卷数上。鸠摩罗什与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合译完成的《十诵》律本为五十八卷,经罗叉之手变为六十一卷,即今天所见《十诵》律本的卷数。卷数的增加,《祐录》用“分”,高僧传称“开”,显然都意指罗叉将原来的五十八卷析为六十一卷。但实际上卷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罗叉补译了三卷“毗尼诵”。《高僧传》称“毗尼诵”是改“善诵”之名,但它所举善诵之内容与今本所见“毗尼诵”之内容并不相合,且高丽再雕本和宫本此三卷的译者署名均为“卑摩罗叉补译”,因此最后的三卷“毗尼序”应当为卑摩罗叉补译,而非罗什原本所有①前辈学者如平川彰也认为“毗尼诵”乃罗什译本本有,非罗叉补译,且举日本圣语藏本为证(平川彰『律の研究』,第121—131页),但其观点不足据。。当然罗叉也确实对前五十八卷的分卷有调整。
但罗叉所做的并不仅此。罗什传称罗什的十诵译本“文烦未善”,因罗什去世而未及删治,《祐录》在提起罗叉的工作时也称他是“重校《十诵》律本”,经他校后“名品遂正”,可以想见罗叉对罗什译稿的文字也做了改动。《祐录》说卑摩罗叉校定的版本“至今相传”,现在我们看到的藏经本皆为六十一卷本,和卑摩罗叉改定之后的卷数相合,应该都是经卑摩罗叉改定之本,虽然现在藏经本中的《十诵律》前五十八卷仍署名是弗若多罗共罗什译,但实际上已经不是罗什译本的原貌。
五、《十诵律》六朝写卷之文本定位──鸠摩罗什原译《十诵律》
通过上节的介绍,我们知道在《十诵律》的翻译过程中,卑摩罗叉曾对罗什的译稿做了大的改动,再结合上述几件敦煌写本与藏经本文本的异同,对于这几件敦煌本的文本来源,应该只有一种可能,即它们就是未经卑摩罗叉改定的《十诵律》旧本,也就是鸠摩罗什的译稿。平川彰在讨论S.797的短文中已经点明这一点,他称这个本子为较原始的草稿,现在的藏经本则经罗什与罗叉的校定②平川彰:「敦煌寫本十誦律の草稿訳と敦煌への伝播」,载『岩井博士古稀記念典籍論集』,1963年,第545—551頁。。但从前面的翻译过程看,罗什完成了翻译的工作,并未参与校改,改动文本最关键的人物还是罗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几个写本就变得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罗什生前所译且未经改定的译稿,对我们了解鸠摩罗什的翻译有重要的价値,新旧本的文本差异,也使我们对六朝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当然,就如同当时的翻译都是多人合作完成,罗叉的校定当也不是由他一人完成,尤其考虑到校定之后的文本文意顺畅,更胜旧本,定然少不了中国僧人的参与。
在确定了敦煌本的性质之后,我们再深入地看一看它和藏经本之间的异同。首先是分卷。七法的衣法,目前能见到唐代以后的所有藏经本均分为两卷,而S.797和S.6661不分卷,这与所有的藏经本均不同,还有S.751的分卷也很特别。卑摩罗叉在校定律本时对《十诵律》分卷有开合,这几个敦煌本的分卷所反映的可能正是鸠摩罗什译稿的分卷。
其次是文本内容的异同。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卑摩罗叉对罗什等人所译草稿的校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分卷、字词、语序的改动,对重复文句的不同处理方式及文意的改动。而之所以罗叉的校改动作如此大,除了罗什译本本身不完善之外,可能罗叉在校改时并不仅只面对罗什等人翻译的汉文译本,还依据他自己所熟习的梵本或胡本,对罗什译本的内容做了很大的调整。也就是说,敦煌本与藏经本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系统的梵(胡)本。
之所以有这种推测,可以从两个文本的内容差异上看出一些端倪。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藏经本相对敦煌本,在处理文本中的重复内容时,态度并不是一贯的。在一些地方,藏经本对敦煌本保留的重复内容做了删减,而有些地方,又将敦煌本删改的重复内容补足,并不是一味地删减或补足。罗叉对罗什旧本重复内容态度的不一贯,可能正是因为他在校定时并非只面对罗什等人的中译本,还参考了自己熟习的梵(胡)本。罗叉所依据的底本,对这些重复内容的处理与罗什翻译时所依据的底本有不同,他在校定时也根据自己所知的底本对译稿文字做了相应的改动。佛典在从口头记诵向书写传统转变时,以往为了方便记诵而不断重复的内容,就成为书写的负担,因而开始出现缩略的情况。诺曼曾提到梵巴佛教经典在书写时常以pe或la等字指代重复内容③诺曼:《佛教文献学十讲》,第106页。据诺曼的说法,pe、la本身为巴利文peyyāla(梵文:paryāya)的缩写,意为“格式化语句”。。在吉尔吉特发现的梵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藏的《药事》(Bhaiṣajyavastu)中,有“广如《长阿含•六经集•大善见经》说”(vistareṇaMahāsudarśanasūtredīrghāgameṣaṭsūtrakanipāte)的语句,这也是省略与他经内容重复的一种方法①刘震:《禅定与苦修——关于佛传原初梵本的发现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页。。《十诵律》的梵本在写定的时候定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处理这些重复内容。但是一个佛教经典文本在写定之后,由于其作为佛教经典的神圣性,文本内容会逐渐固定下来,而后世的僧徒在阅读传承的过程中对经典文本的改动是非常谨慎的②T.W.Rhys Davids在1883年撰写的巴利圣典协会报告中提到,Oldenberg在处理Vinaya文本以及Morris在处理Aṅguttara文本时,“当某些词不断重复时,只给出它们的首字母”。这引起了锡兰(Ceylon)读者的抗议(JPTS,1883(I),pp.vi-vii)。。
中国早期的佛经翻译常根据汉语的语言习惯,对胡(梵)本进行删改,到东晋道安时期,他和其他一些译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道安认为翻译应该尽量保持原文的特色,并据此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五失本”中,后三条均是针对梵文喜重复、繁复的特点而言③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0页)。船山彻认为道安的“五失本”是认可对佛经做出这五种改动④船山徹:『仏典はどう漢訳されたのか——スートラが経典になるとき』,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第118頁。,横超慧日则认为道安并不是认可或禁止这五种行为,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些妥协⑤横超慧日:「中國佛教初期の翻譯論」,载横超氏著『中國佛教の研究』(第一),京都:法藏館,1958年,第219—255頁。。结合道安自己其他的文字,横超的解释可能更为合理。在不知作者的《僧伽罗刹集经后记》中,提到竺佛念在翻译时“每存莹饰,文句减其烦长。安公赵郎之所深疾……许其五失胡本,出此之外,毫不可差”⑥《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75,382页。。观其文意,虽然许其五失胡本,但对竺佛念删减文句的行为道安也是深疾之的,显然对于“五失本”他并不是无条件允许的。《鞞婆沙序》中,他也赞同赵政的看法,认为佛经翻译应该“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⑦《出三藏记集》卷十,第3 7 5,3 8 2页。。显然道安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翻译应该尽可能的保持原文的内容,只有万不得已时可以做一些变动。
而戒律文本因其性质又特殊于一般的佛教经典,在传承过程中内容的准确与完整更受僧人重视,文字的改动也更加谨慎。道安在《比丘大戒序》中对于戒本的翻译就有如下的议论:
考前常行世戒,其谬多矣。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昔从武遂法潜得一部戒,其言烦直,意常恨之。而今侍戒规矩与同,犹如合符,出门应辙也。然后乃知淡乎无味,乃真道味也。而嫌其丁宁,文多反复,称即命慧常,令斥重去复。常乃避席谓:“大不宜尔。戒犹礼也,礼执而不诵,重先制也,慎举止也。戒乃径广长舌相三达心制,八辈圣士珍之宝之,师师相付,一言乖本,有逐无赦。外国持律,其事实尔。此土《尚书》及与《河洛》,其文朴质,无敢措手,明祇先王之法言而慎神命也。何至佛戒,圣贤所贵,而可改之以从方言乎?恐失四依不严之教也。与其巧便,宁守雅正。译胡为秦,东教之士犹或非之,愿不刊削以从饰也。”众咸称善。于是案胡文书,唯有言倒,时从顺耳。⑧《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第413页。
道安接受慧常的意见,坚持戒本的翻译要尽可能忠实原文,重复内容也要一并照翻,“唯有言倒,时从顺耳”。回到《十诵律》,无论是鸠摩罗什翻译还是卑摩罗叉校定时,应该也是坚持这样的原则,不敢轻易对文本内容做出改动。敦煌本和藏经本对于重复内容的删略,应该不是他们私自为之,而是底本本来如此。二本对重复内容处理的不一致,是由于他们所依据底本的不同造成的。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卑摩罗叉在校改时,对某些重复内容会删减,而对另一些则是补全,增补必然需要有原文作为依据。部分地方经改动后文意也发生了变化,当也是底本的差异所致。封兴伯(Oskar Von Hinüber)在比较一个发现于尼泊尔的一千余年前的律藏文本与巴利圣典协会的版本后发现,二者在处理重复文本的缩略时并不完全保持一致。有些尼泊尔写本未缩略的地方,巴利圣典协会的版本则缩略了①诺曼:《佛教文献学十讲》,第106页。。卑摩罗叉和弗若多罗口诵的胡本可能也是类似这样两个不同的版本。
总之,《十诵律》在鸠摩罗什等人的译稿完成后,经卑摩罗叉之手被改订为文本内容差别甚大的另一种文本面貌。但是在卑摩罗叉的校定本出现之前,罗什等人的译稿就已经在坊间流传②在当时,尚未最后定本的译稿流传坊间并不少见。僧叡在罗什译《大品般若经》序中称:“文虽粗定,以《释论》检之,犹多不尽。是以随出其论,随而正之。《释论》即讫,尔乃文定。定之未已,已有写而传者;又有以意增损,私以‘般若波罗蜜’为题者。致使文言舛错,前后不同。”(《出三藏记集》卷八,第293页)可知此经未经刊定的稿本也曾流传坊间。。三个敦煌写本的抄写年代都在5世纪初,与鸠摩罗什等人的翻译活动差不多同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译稿就已经从长安传到敦煌,并被当地僧人抄写,可知当时经典的传播速度是很快的。不过《十诵律》译出于长安,但南北朝时期它主要流行于江南,长安所在的关中地方却流行《僧祇律》和《四分律》③慧皎《高僧传》“明律篇”所收诸习《十诵律》的律师,大多出自江南。道宣在《续高僧传》“明律”篇最后的《论》中,也称《十诵》“澄一江淮,无二奉矣”(CBETA,T50,p.620a5-6),《洪遵传》则称“先是关内素奉《僧祇》”(CBETA,T50,p.611c1-2),洪遵之后也就是北朝晚期也开始流行《四分律》。。而卑摩罗叉的校定工作也是他南下后在寿春完成,笔者认为,南朝江南流行《十诵律》与罗叉的南下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当时他除了校定律本,也积极传律,并经由慧观等人的宣传,在南方有很大的影响④《高僧传》卷二“卑摩罗叉传”。。正因为如此,当地流行的必然也是经罗叉改定之后的版本,唐宋之后藏经本中收录的也是这个版本。罗什未经删治的旧本则在长安逐渐被湮没。
在卑摩罗叉的改定本出现之后,旧的译稿并没有马上被取代,它们曾在一段时间内并行;且在并行的过程中,罗什译本对罗叉的改定本又有影响,它的部分内容混入了新的校订本中,而这也造成了唐代以后几种藏经本各自在文本内容上的差异。这些藏经本都可看作是以卑摩罗叉改定本为主体,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旧本影响的文本。比如前述三个不同系统的刊本藏经在卷五的文本内容上互有详略,这很可能就是它们所依据的底本在不同地方吸收了旧文本的内容。而大正藏的校记显示,日本所藏圣语藏本有些内容与宋代几种藏经本皆不同,如大正藏本卷二十三有一段149字的文字⑤CBETA,T23,p.170b5-14,p169b15,p169c01,p170a01,p170a12.,根据校记,不见于圣语藏,而BD03375在对应位置也无相应段落,可知此处圣语藏与敦煌本保持一致。又比如宋代以后藏经本在罗列僧人自恣时说比丘罪,其中有“能(不)自称过人法”一条⑥CBETA,T23,p.170b5-14,p169b15,p169c01,p170a01,p170a12.,但圣语藏本和敦煌本皆无。而宫本的部分用字与再雕本不同,却常能与敦煌本相合⑦如BD03375第40行“僧自恣,若是比丘当来”,大正藏“当”作“得”,江南系统诸藏均作“当”;又41行,“若得清净”,大正藏“得”作“与”,江南系统诸藏均作“得”,类似江南系统藏经与写本相合处尚有多处。,这些应当都是罗叉的改定本在流行过程中,不同的版本对罗什旧本内容的吸收。
目前,有部律在西域已发现梵文残本,亦有多个巴利本存世,之后我们可以依据这些不同语言的文本,对《十诵律》的翻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罗什译本在敦煌的发现,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鸠摩罗什的佛经翻译,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都是之后可以再深入探讨的新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