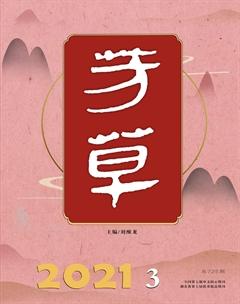狮子岩(十七首)
王彻之
狮子岩
利爪的太阳,红空气
揪着我们上升。在来到山顶之前,
好心的,难以分辨面孔的尼甘布人———
司机称呼他们为“丛林人士”———轻如羽毛,
随风粘在半山腰凸起的岩石上。不像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来自中国,南亚或欧洲,笨重而疲惫,
一群连休息也得供人观赏的土象,杂乱有序地
被编排在队列之中,头也不敢抬———他们也微微低下头,
克制着自己的趾高气昂,几乎与岩石融为一体。
和狮子相比,捕猎的技巧还不成熟,司机,
神态已经说明了一切。踌躇时,突然从岩石里显形,
仿佛我前面哪个人作了祈祷。“让我帮助你吧,”
一种混杂着当地语,咖喱与鱼腥草的英语,汗水中露出怜悯,
他感到自己会被需要,因而说出了“我们当地人———
来这儿,做好事。”后半句像个殖民者,强调着某种他们自己将信将疑,而道德性不容争辩的废话,直到转过山腰,语言露阴癖般,暴露出最混蛋的那个词———
也许还夹杂着翁达杰那特有的怯懦———而我们
拒绝的口气,更加正义,也更像野蛮人,
或者来自蒙古利亚,特洛伊和古阿拉伯的轻骑兵,
此刻高高地占据山顶,带着野兔挣脱厄运的兴奋。
两个世界一分为二,远处的三明治风景
典范于金枪鱼蛋黄般的光晕;欢呼恰到好处,
瘸着一只腿的狗摇着尾巴,新婚夫妇
趁小孩溜号的间隙疯狂亲吻。这片新被征服的土地上,
(只要有钱,每天会被征服百八十次),
旅行图册,从新的秩序中找到生机,
而已经打乱的,则并不在我们称之为生命的欢愉中。
穿越雅拉
出发时,朦胧的天色
尚未被月光最后的哀吟唤醒,
亚乐紧隨我们,朝向厄俄斯的双手
所推开的平原远去。月亮暗紫色,
尽可能俯身,以便让湿地狸藻自鸣得意,
闪烁像大地乐器上发光的箔片。
每一根弦都使我们低调,把自己缩进口袋,
而斑点苔像阴影般透露着恐惧,仿佛音乐
戏剧性的框架;反差中,水牛的重音
倒比它更羞涩,对越野车轻佻的喊叫无动于衷,
反而椭圆地上升,直到和风融为一体,
发出鲁特琴般暗箱的回音。有时被提醒,
操琴者,即使明知不完美,但依然保持克制,
脸青得像本地的石料加工员,不放过一点赭石色,
对待人和火星别无二致;但车灯滔滔不绝,
更强调你我周围,大海的碎片
如蓝孔雀般结晶在确切的岩石上。
通向现实的必经之路,是音乐成为它本身。
等待猎豹时,仿佛看穿另一种虚构,
我们自身也被缺乏象征性的树影沐浴着。
像蜥蜴般匍匐,苍凉的转音,谨慎地出没
并在沼泽的结尾吐露它的秘密,仿佛某团火焰
燃烧在我们自觉的内省中。但意识漫无目的,
构造如三明治般简单,你亲手固定了它的形态。
那些随我们的颠簸,猛烈扭动的是什么?
无声的,成熟的抽泣,在雨水来临之前减弱频率。
而在苍鹭所飞过的,以及曾经
幻想探险的风景之外,听众无关紧要,
一种啼鸣已不存在于我们想象的观察中。
敖包
即使最善欢呼的鸟
也不会盲目地厌倦它。
在每一个浪峰上,统治着运动,
尽管不动声色,任凭绿色的大海
在下方快速前移,太阳的血球飞速旋转,
我们的侧影为它分开了潮汐,
并怆然给它牵好缰绳。这欢快的小马,
昂着头,惊视着往来者,
他们祈祷仿佛死亡并不存在,
而水母色的月亮,正从西方下降,
沸腾另一侧的海面。光沉没入我们的眼睛,
以及悲哀,而我们的耳朵厌倦了帆。
乌鸫鸟
在希斯罗灰色的,
狂犬病般发作的阵雨中,
我提好行李箱,用黑手套
欺骗,并遮挡远处天使光线的灼烧,
我的大衣覆盖的心灵
焦黑如烤肉架下的煤球,
爱的锡纸融化于它的舌头上,
混入海德公园的烧酒,热狗摊的冷气
和停机坪腋窝的温度计里,
水银环形上升如戴安娜喷泉。
而我身体的星期五,在长途车
结巴的旅行与周末无事可做的恐惧中,
几乎笨拙地,把醉醺醺的
眼球充血的月亮和在我体内
与我内心河流分道扬镳的火星混为一谈,
仿佛灵魂此刻故地重游,
寻找我失落在我不能赋予它形式的
由于一种知识的确切性
而随风摇摆的树丛中的,
那惊慌逃窜如乌鸫鸟的天赋。
有时也叫百舌,虽然一言不发,
但也好过欧歌鸫(远看像白脸树鸭,
槲鸫,或者垂涎的纵纹腹小鸮),
仿佛来自欧洲,却和笼子里的画眉押头韵。
我用全部的时间走在笼子之外,
走在它碳土似的雨与稀薄的记忆空气中。
据赫拉克利特说,我们所失去的一切
都与火发生着联系,而我所获得的,
如你所见,此刻都在哑雨中成为暂时之火。
卡吕冬狩猎
来自大都市的希腊神像们
缺少它的幽默。海闪烁釉光,
拉奥孔的蛇缆索般,垂入地平线
拖拽着这颗冰冷行星;
而半裸的维纳斯,如水手观测着风,
通过她在海浪阴影下
一架咸湿的目光想象群岛有多远,
如何与大陆保持间性联系,
尽管断断续续,风格却必须
连贯;像批评家们对我们的欢乐
呼出的泡沫偏爱泰然处之———
可无论是对你从它陨石般的脸上
瞥见的那无数匹因狂喜而颤栗的流星,
还是在公里的加速消亡中,
对它生活波浪上鱼跃的呼喊
和马刀般弯曲的臀线,以及原始风度来说,
美,和它的悲剧性,一旦被确认,
就必然认同我们既是观众,又是它的发生之地。
悼W.H.奥登
头脑的统治崩溃
像厄尔巴岛的火山灰,
双眼的铁幕拉下,目光
也随之败退。在九月,
穿过维也纳舌头的晚风
不再与教堂的钟声押韵,
街道焚毁杉树的选票;
灵魂宣布,他身体的计划破产了,
而他牙齿的各个时代
根基都已经动摇。无人叛变,
更没有抗议,他死去
在关于他的死的意识里。
而那意识已经过期,
它签署的文件被另一个他撕碎,
尽管他们彼此熟悉,
如同拉琴者和琴弦,
但现在他的精神静静地躺在
他对象喷泉的殆尽中,
如此完善,恰似一个谐音。
他就像方济会的管风琴无人弹奏。
旋转木马
虽然圣诞集市结束得
比去年更早,但在集市尽头
小蒙古包似的木马棚下,
几匹错落有致地,上下移动
而彼此沉默无声的马,其感情
似乎全靠轴承相连。在夜晚
鼻翼吐着热气,在上釉的前腿筋腱,
光滑得让人想到爱奥尼式立柱,
与佯作奔跑的后腿间,它们的锁子甲披风
几近溃烂,残破如视力损坏的渔网。
从它们鳕鱼似的小腹刺入
然后冷冰冰地,在既定的法则下
围着议会星空旋转的遥杆,看起来
就像是从骑手在风中解绑的心灵
由于战争来得太快,而来不及
与之达成共识的小天使手中抢来的。
而当木马停止了,它们也不肯
在你轻易踏出圆圈半步前失去亮度,
反而在冷风中,让四蹄的黝黑
消耗在激情远超其忍耐的空气里。
激情在这里是无意义的,像海滩的木马。
当习惯这种惊奇,它的感情
仿佛木马里的士兵流言般泻出,
趁夜晚占据你的身体,然后四散奔逃,
以至于许多年后,你走下来,
竟然还可以感到,你的双腿仍然
间或颠簸在它的感性不能持续的天真中。
在新城区
当我们心灵的针尖再次从立交桥
溃烂的肌肉下纫过,这海滩的一隅并未好转。
贫穷还在那儿,它的学生,
裹着烧焦的棕榈叶色头巾的
中年寡妇,蜷坐如一个雨中的谜语,
差点儿被五十欧分解开,几乎要说出“你不会———
被我吃掉,”而你,斜视的眼光如同
一片口香糖,黏在她下水管道般的结肠里。
海的无影灯在海面驱散影子,
灯塔将它的手术刀竖起,迎向漩涡的小腹
使游轮缓慢地,犹如夏加尔的巨婴
浮现在视野之中,她周围,黄狗吠叫着
给远方的拍卖品竞价,而风轮草推敲风的口气
故意拉长巴士的弦外之音,它粗哑,狭窄的喉咙
缓慢地吐出街道蠕动在我们身后的诗节,
每英尺的地砖都给面积同样大小的忧伤加覆。
尼斯的山脉,用阳光舔着它的齿龈,
而雨狂烈的麻药镇定排水厂的神经,
以地中海隼的灰色骨粉填滿帕勒永的河床,
对于那些充满好奇心的,在烟熏的风中
垂涎油光流溢的街区培根,把教堂的黑焦糖
洒在山丘布丁上的有神论者来说,
简易房是外省游民的龋齿,贪婪而必要,
不应该被观看,按照习俗我们将瞎眼。
在码头区
六月,乌云的秃鹫紧盯着
这座城市的河道下水泻出的部分。
雨伸长脖子的垂涎,让新刷过漆的
异国小帆船不由得感到恶心。
在橙色贝雷帽的沉默中,海浪
榔头般敲击海平线,弄弯它的两头
以将其维持在望远镜的辖域里。
有些日子足以说明,岛屿的图纸作废了。
一群鹮鸟用它们饱蘸的,钢笔尖般的
喙记录随沙冲散的事物,其中
仍然保持完整的,如蟹壳蛮横而对称。
但你时常怀疑,生活并不缺少
浪费的激情所赋予我们的权利。
梦难以把握,就像小数点的后几位,
雨的输入法缱绻船坞键盘,
企图仅靠一根雨丝,就把港口
和它的过去连在一起。
而那些孤零零的,决心翻阅
大海文献,以给你虚构的未来远景
做出注释的黑嘴鸥,知道自己
其实不存在于时间中,而是
相反地赘述了时间。
灰鹭
不止一次,我们看到
灰鹭匆忙闪过天空,
用它们电弧似的喙
不动声色地切割绿色的水面,
让桥的倒影加深。波浪
的黑色力量在水的
体内聚积,像鱼群被
某种惊惧驱赶在一起。
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是它们想要的。黑矿石中
被风的感觉威慑的一群,
完全来自外部:像我们
一样不知所措,像
养殖场待屠宰的牲口,
在污泥黑得发硬的
草棚下冲撞。眼球
仿佛好几个晚上没合眼,
被超出自身智慧的
野蛮的知识摆弄。
随后是自知无法解救,
那被误认为是狂喜的
足够穿透阴郁空气的下颌
比我们预想得更快,
让肉煤烟似的翻滚,
在细长的、火钳似的舌头上。
对自己的处境心里有数,
可对我们世界的崩溃
完全不感兴趣,我们消失
进入雾气蒸蔚的树林,它们中
不会有人类学家知道我们在哪里。
淮海路
冬日,再次回到公寓的床头,
我的手脚冰凉,舌头僵直,
像立柜一样竖在原地,
记忆如同旧衣服挂在里面,
等待房东清空,但一直没有来。
思念像靠枕伴我入睡,
让头深陷其中,而离身体很遥远。
仿佛后者处在不同的城市,
罢工者涌向街头,雨靴的拥挤
曾经使我的脚跟疼痛。
如今我再次走在淮海路,
手表提醒我时间远去,
但几块地砖通过其不再
严丝合缝的郊区风格,
接受时间在每个空间中的缺席。
我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
犹如一句格言了解事实上
什么都没有应验的生活;
我感到生命流逝,
像我的词语从墙上剥落,
有时别人又把它们重新写上去。
黑鱼
傍晚我们发现它死去了。
一艘失事的船,在狂风天
无目的地丢失它的残骸。
对于大海而言这微不足道,
我们的目光像海鸥盘旋其上,
很快就解散。我们哀叹道,
那些原本维系它生命的东西
现在填满了它,使腹部鼓起
如一张真正的帆,在它死去之后。
现在玻璃外没有任何事物
再使其不明智的眼球转动,
以得知那毫无智慧的爱的来源。
在北波士顿,这些没来得及发生
但是似乎确定无疑的事情
如何使广场的示威者感到不安,
当舷窗外的黄昏拼命变肿,
然后变黑,仿佛烧烬的煤
随着查尔斯河的渐冻症冷却?
刚钓上来时它腥味扑鼻,
就像某种突然的,并非我们
内心原来意识到的感情,
而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思念
这些天雨大得仿佛
能将日子的牢笼冲毁。
思念像马戏团的野兽退场,
踮脚穿过它尖酸而不熟悉的客厅。
出于对暖气的苍白脸色以及
其合乎礼仪地放弃热情的尊重,
冬天即将过去,但电灯泡的喷嚏
几乎再次让周围的事物变暗。
在比你更好理解的事实中,车站
如一片雪花一样站立,在两座小山间
把车窗的风度,洒在河流纵横的,
标记马场与积雨云灰色心碎的地图册上。
那些母马低着头,凭记忆的雷声打起响鼻。
两个月以来,遗忘朝这片土地逼近,
就像一个标注事宜的日期,
带着考古学家的谨慎,把过去分存在小方格里。
在对卧室被阴冷天气吞没的灰墙,
以及其白如海浪的窗帘杆
索取你似乎颠扑不破的知识后,
过堂风站在门口,如同理直气壮的
房东声称,我们准备好失去的
比已經失去的更多,像水电费账单。
和圆珠笔滔滔不绝的弹簧类似,
窗外的雨下了很久,但是仍无法
与它承认爱过的事物押韵,它说过的话
如幽灵掀翻脚下的泥块,让蚂蚁暴动,
让薄荷草衰败的气味清洗你周身,但并不认同。
海口站
滑轮尖叫如老鼠,行李箱
被蓝色手套推搡着向前,
远离你已经不在的候车区。
在充满最后时刻的大厅里,
人群骚动如烟,很快就散去,
因此证据似乎变得更少了。
几个穿制服的人小跑着走来,
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警告我“下次最好不要携带,
它很危险,”却心不在焉。
同一天,我们仿佛已到达
地图中出现的第一座海湾,
踏上随海浪颤动的胶囊小道,
头感到眩晕,有几次差点摔倒。
这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了,
風在我们中间保持平衡,
随船和潮水的紧握和推开
咬定目的,像每天往返
在两个世界之间的船员,
并非乐此不疲,等我来迟,
清点人数,直到确认无疑。
大英博物馆
大巴的灰色嗅觉摸索着经过黑灵顿,
其中的过渡点———很可能也被其他人
误认做旅途的终点,我几次错误地醒来,
像漫不经心的读者翻开新的纸页。
光的气味飘过你的脸,以完成一次快速的提喻,
街道的臭鼬在同样风格的天空下
摆弄公寓的郊区风度。周末我们缓过神,
在大英博物馆,两次回到原点,
看见我们追逐的,那些原始的
被种族隔离的方形玻璃放大恐惧
而敲击叫喊声的光柱的人偶,
在非洲皂石和埃及陶罐上的海浪
波纹间做出选择。我的头脑,
虽然错过了最佳机会,也随钟表那明亮的
模仿某种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运动的金属球打转———这么多长久的事物!
但值得爱的又太少。在它周围,
小怀表像我一样,把时间的蜡质
涂在世界地图平滑的纸层,
让鲱鱼般的名词穿过腓尼基人残破的,
如今已经被散文光谱修复的帆弦,
放任它们在和风中低语。尽管问题依然存在,
但作为一切次要感觉的起点,
在最初离开征服者的心灵,
把每个清晨的视线拉低到目光的门槛后,
这些耷拉着翅膀的,对知识毫无兴趣
却又趔趄地在门口觅食的海鸥,
就算被我们长时间观看,至少也是自由的。
搬家·其一
再也不会睡在相同的地方,
拥有角度相同的风景,和邻居,
连室内墙壁的白色也不会相同,
但这远非旅行。即使去海边,
或者城堡周围,也用不着
凭意志抛下所有,从一座城市
和自己的咳嗽飞到另一座城市,
并试着接纳新的交通规则,道路,
和以前几乎被你视作野蛮的
凌驾另一种语言之上的语气。
搬家用不着这样枉费心力,
没有什么东西跟踪你,那些杂物
全都没意愿进入你的生命,
尽管你曾经对它们消耗激情。
别去翻那本已然残破,像老奥登
沟渠纵横的脸的诗选,也不用
收起它旁边,撂下农活的打印机,
鲸鱼似的嘴张着,像波士顿
退休的观鲸船栓在码头上
疲惫而无所事事。每次我去海边,
像跛脚的海鸥,水蚊子般大小,
趔趄在风暴中,我都感到某种
在体内铁索般作响的
同样的疲惫,也许带着怀疑,
将自身置于风浪的中心,
如同码头清洁工,随时准备
弯腰撇清大海的白色浮沫。
我知道,下次冒雨出门的时候
如果我什么都不会带走,
这就相当于说,我没有完成工作,
待在原地,等没人注意我会搬去火星。
搬家·其二
晚饭后,初秋的湿手巾
还被英格兰中年的风紧攥着。
雨在眼前飘落,像是合同上面
房屋中介的落款慢条斯理。
有时搬家就像把自己词语般
放进一首新诗的繁文缛节里,
让原义和引申义的激素保持平衡。
我的创造力,像天然气
几乎肉眼可见地缩成一小团,
最后消失在厨房脏灰色的,
那匹胎盘似的小灶台上。
我的思想食物般变冷,
我饥饿的眼睛像被驱逐的
选民,看见却无力改变
今年树叶的真理又被一页页撕毁。
很难说这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总好过生活像时针
永远围绕一个轴转来转去,
像黄昏总是把蝙蝠群的
黑魔方扭得吱吱作响。
有时我确信搬家的好处是,
当我的百分之一走在大街上,
剩下的都会住在这里,
即使它们还未被拼成任何完整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