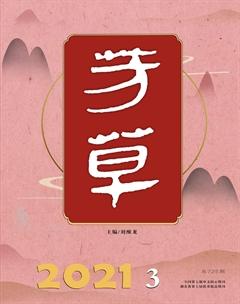亲人(三篇)
王慧敏
我的大娘
前不久我打听了一下,这位老人家,现今还活着呢!
老人家姓薛。她的内侄女告诉我,庚子年的腊月二十三,老人家刚刚过了九十九岁生日。
除了眼睛看不见、腿脚不灵便外,没有其他大毛病。尤其是脑子,灵光得很呢,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事,都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每天起床,她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利利索索,头发虽然稀疏了,但梳得纹丝不乱。
她,是我五服内的亲戚。听长辈讲,我该叫她大娘。小时候我们家下放的时候,我曾多次到过她家。那处四进的大院子解放初就被分了,只给她留了最尽头偏房的一间。
无论什么时候去,她的屋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方砖地面如同水洗过一般,一尘不染。那时候,她就已经失明了,在一张陈旧的紫檀八仙桌旁端坐着,右手放在左手上,十根长长的手指葱根一样白白净净。黑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发髻,一根银簪插在上面。
她喜欢穿黑平绒衣服,或对襟、或斜襟,用的是盘扣。这些,全是她自己手工做的。
她的脸色象牙般白净,端直的鼻梁,眼睛静静地平视着前方。如果不是事先得知她已经失明,你看不出她有什么异常。
她,一身的静气!小时候,我很淘气。可是一到这位大娘的屋里,我一下子就老老实实的了。
这位大娘,很有些来历:汉口大户人家的闺女。爷爷在前清当过翰林,父亲留洋回来后和德国人合开了一家医院。全家就她这么一棵独苗,心肝宝贝般供着:爷爷教她四书五经,父亲供她上了洋学堂。
我本家这个大爷在汉口念书时,不知施了什么“法术”,竟让姑娘着了魔似的爱上了他。
起初,大爷的父亲不同意:还在娘胎中,就和另外一家财东订了娃娃亲。
这可怎么向人家交代?老爷子派人把大爷从汉口找了回来,威胁说,你要再跟薛家姑娘来往,就不再供你上学。可大爷很犟,说你就是把儿打死,这辈子我非她不娶。
人家薛家也不同意。派人找到大爷,摊了牌:再敢胡骚情,打断你一条腿!
这一下,连大爷的父亲也不干了:这不是太不把老王家当回事了嘛!
不过,老爷子并没有硬着来:亲自到陕南置办了八船山珍,从汉江的后柳码头向汉口驶去——当面向薛家给儿子求婚呢。
老爺子那份洒脱和诚意,深深打动了薛家。薛翰林应允了亲事,还回赠了一船书籍。
婚事还没来得及办,抗战爆发了。大爷投笔从戎。
国难当头,谁都知道哪个先哪个后。
之后,大爷跟着国民革命军方先觉将军参加过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戎马倥偬,血雨腥风,死里逃生。
一九四八年腊月,官至副师长的大爷终于获准回乡完婚。可婚事正在操办中,传令兵飞马来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打过来了,上峰急令大爷迅速归队。
大爷安慰双亲和娇妻:放心,局势很快就能稳住,过几天他就会回来。
可是,这一走,大爷再无音讯……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沧桑巨变。大爷依然杳无音信。
周围的人,包括公婆,都劝大娘改嫁。可她,始终不为所动。
听老辈人讲,那位大爷确实招人喜欢!一表人才不说,还文武双全。我们这个地方尚武,大爷从小跟着一个老镖师习武,十五六岁时,武功方圆百里竟没碰到过对手。他曾为当地河防部队写的军歌,解放后还一直被人偷偷传唱。我还记得最后面这段:
倭尘未尽扫,绝不卸征袍。
抛颅洒血在今朝,血沃山河花更娆。
兄弟们,
生,我是英豪;
死,我是天骄;
好男儿何处不狂飙!
薛大娘天天坐在八仙桌旁垂泪,视力越来越差,几年后,她的眼睛看不见了。
大爷弟兄两个。弟弟也在汉口上过洋学堂。可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新四军。
一九四八年底,上级调他回家乡搞土改,被任命为区土改工作队队长。
一次,工作队捕获了几个地主还乡团分子,其中有一个人是他的发小。
小时候,二爷在江里玩水,差点溺亡。是发小的父亲救了他。在发小的恳求下,二爷竟丧失了革命立场,悄悄把人给放了。
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上级严令追究。幸亏二爷的老领导出面求情,才保住了一条命。
二爷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后,为了他的生计,经老领导斡旋,让他在镇中学当勤杂工。他的同事们这样评价:“这个人呢,好人。但是思想老是转不过弯,始终没有摆脱亲情的束缚……”
有一年冬天,盲嫂给街上的杨树刷石灰,他怕盲嫂摔跤,就拎着石灰桶帮她一起刷……于是,有人传了闲话,说他和嫂子明铺暗盖哩!
二爷有嘴也辩不清!
没想到,一向娴静如水的大娘站了出来,在一个赶集的日子,当着镇上熙来攘往的老少爷们,她拉着镇干部说:“俺嫁到王家,还没圆房他就不见了。到如今,俺还是黄花闺女!咱现在就可以去医院检查。如果不是,俺当场碰死在大家面前。如果检查后,说是,今天必须给俺和俺兄弟一个说法。俺守了一辈子寡,在俺眼里,名声,比命都金贵!”
此后,再没人敢拿这个来说事了。
再后来,武汉那边传来消息,抗战时大娘的父亲给新四军支持过大量的药材,还偷偷给许多新四军将士治过伤。于是,被追认为烈士。
当地有关部门劝她回去继承遗产。可她,谢绝了。人们知道,她还没有死心,她还在等那个人。
一九八六年,二爷患了绝症,走了。享年六十四岁。是孀居的寡嫂为他送的终。
听人说,大娘不允许任何人插手,自己摸索着为小叔子净了身,剪了指甲,还用指甲刀背面的小矬子认真把毛边挫平整。一针一线给小叔子缝了老衣。
我上大三那年,听说大爷从台湾回来了。
遗憾的是,大爷带回来了一个小自己近二十岁的夫人。
那是个大夏天,通往古镇的石板路晒得烫脚。大爷在镇外就下了车,一步一叩头,匍匐着向镇里挺进。陪同的当地统战部的干部劝他:“您恁大岁数了,别伤着了。”
他老泪纵横:“按咱老家的规矩,游子回家,无论当多大官、发多大财,在乡亲们面前,都要低一辈。”
他从镇外一直磕到祖坟,又从祖坟磕回老宅。膝盖都磨破了,鲜血淋漓。
进老宅那一幕,极有戏剧性:
大娘穿着当年新婚时穿的那套衣服——不知这套衣服是怎样躲过了解放后的风风雨雨。白发在脑后挽成了一个发髻,用一根银簪子插在上面。
她庄严地端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
大爷一进堂屋就要跪下:“我该死!我该死!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你……你一直……”
没等到大爷跪到地上,大娘哆哆嗦嗦、跌跌撞撞把他扶了起来:“不行!不行!在咱老家,没有掌柜的给媳妇跪的……我眼睛看不见,没办法给你行礼了。”
大娘很大度,说:“我不怨你,这是世事造成的。天杀的世事啊!怪我命苦……我了解你,你不是陈世美……”大爷早已泪流满面了。据说,大爷是在四十多岁后,才在老长官的强令下,和一个遗属结了婚。走前,大娘给他提了一个要求:“当年娶我,是三媒六证。旧社会没有结婚证一说,合的八字都还在呢。你要休我,只要把八字还我就可以了……”
“使不得!使不得!你没有做错什么,凭啥休你?!错的是我!错的是我!”
“新社会讲究一夫一妻。目前这状况,让人家回去咋说哩?你能不能出面办一桌酒席,当着街坊邻居的面,认下我这个干妹子?咱俩的事说清楚了,你和妹子回去也就不用背着思想包袱了。这样做,还有一个说道,按照咱老家的风俗,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嫁出去的闺女不能入祖坟。从辈分论,你现在是老王家的长门长孙,只要你出面拜过乡邻,也就是承认我是王家的闺女了。死后,我就能进王家祖坟了。将来,把我埋在咱爹娘脚下面的位置,我给他们暖脚……”
大爷走前,透露了如下情况:
一个是,就在他和大娘婚后的第六天,傍晚时分,他带着骑兵卫队回到了古镇外围。知道要南撤了,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他想回家见一下爹娘和新婚的妻子。
前哨摸了一下情况后告诉他,解放军的土改工作队已进了古镇。而队长就是他的弟弟。
如果贸然进镇,就很有可能和弟弟的队伍发生一场激战。凭自己的人马和武器,肯定能占上风。
可毕竟是自己的弟弟啊!
他在镇外树林里徘徊到了深夜。让卫队把马蹄用布裹了起来,牵着马在大街上走了一圈,嘱咐卫队:“不要惊扰了我的乡亲们!”然后,他来到家门口,跪在门口磕了三个响头……
大爷还说起了那边:一起过去的老乡们,逢年过节都会团聚。端午插艾,正月闹灯……一丝不苟恪守着老家的规矩。他嘱咐儿子:“‘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无论漂泊多久,一定要归葬故里!”
特殊年代的别样爱情
陶莲玉,是十多年前我在新疆工作时结识的朋友。如果还健在的话,老人该有九十岁了。
她住在乌鲁木齐天山区一个很有些年头的小区里。从穿着看,老人和乌鲁木齐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没有多大区别。不过,等摘了围巾、帽子,你会发现,活脱脱就是个外国人:高高的鼻梁,蓝蓝的眼珠。
认识她,缘于采访她的父亲陶喜陞。
陶老爷子原籍黑龙江宁安县西沟屯,当年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
在这里,有必要把义勇军的情况简略介绍一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奋起抗战,出现了多种群体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一度发展到三十多万人。日本关东军集中精锐,疯狂清剿。由于敌众我寡,为保存抗日力量,根据上级指示,部队转移到了苏联境内。
苏联远东一带人烟稀少,加之连年打仗,青壮年大批战死,许多村落只剩下了老人和孩子。苏联政府动员这批中国将士留下来。找到陶喜陞时,他拒绝了:“不行!我的母亲和弟弟都被小鬼子害死了。连这个仇都不报,还算爷们儿吗!我要回去抗日!”
就这样,陶喜陞和他的三万多名战友绕道西伯利亚从塔城巴克图口岸回到了祖国!
陶莲玉告诉我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父亲这批人留在新疆巩固西北边防。他被编入塔城边卡大队,任司务长。
作为司务长,父亲每天都要到附近的市场或菜园子里替部队采买生活用品。时间久了,姥爷一家引起了父亲的注意。
苏联“十月革命”后,沙俄贵族、地主、资本家纷纷逃往国外。有一部分逃到了塔城。姥爷一家,就属此列。
新疆地方政府在塔城一个叫克孜别提的地方把这批人安置了下来。划出一大块草原、河谷荒地,供他们放牧开垦。
姥爷是个知识分子,在沙俄时代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哪里会种什么地啊!所以,全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父亲很同情这一家人,去克孜别提买菜时,有时候便搭把手帮着干些农活。
一来二去,这家人都很喜欢这个勤快的中国小伙子。
有一天幫着干完农活后,姥爷一家硬要留父亲吃饭,姥爷装作很随意地问:“陶喜陞,你在老家有没有婆娘?”
“没有!”父亲没有领会这句话的意思。
“我的姑娘瓦莉亚怎么样?”姥爷单刀直入。
这可把父亲吓着了。在父亲眼里,瓦莉亚就是一尊神:袅袅婷婷,端庄娴雅,说话总是轻声细语,脸上永远带着微笑。她平时喜欢看书。只要有书在手,就会忘了周围的世界……
再说,父亲比她大将近二十岁呢。
那顿饭,父亲没有吃饱,慌慌张张离开了姥爷家。此后好多天,他再也没敢往姥爷家去——他不愿意让人家以为自己帮人,是有所企图。
见父亲不再过来,姥爷猜透了小伙子的心思。他把女儿找了来:“瓦莉亚,你觉得陶大哥怎么样?”
母亲低着头,揪着辫梢不出声……
“如果认为是个好小伙子,你就主动点!”姥爷给母亲支招。
在姥爷、姥姥的鼓励下,她便到边卡大队找父亲。谁知,小伙子不见了……
经姥爷、姥姥同意后,母亲开始在塔城打工,到处寻找心上的这个小伙子。可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一直没有小伙子的踪影。
母亲还在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找……
八年后的一天,有个小姐妹告诉母亲,城东头新开了一家理发铺,是个东北人开的。会不会就是你要找的那个陶大哥?
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急急忙忙找了过去,小跑着到了门口,可又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站住了:正是日思夜想的他!
她呆呆地看着小伙子,任凭眼泪哗哗地流。
父亲也呆住了: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姑娘还在找他。
真是个傻姑娘啊!那一刻,父亲心里一定翻江倒海一般:不知是喜还是悲?!
就这样,两人结了婚。
婚后,一溜儿生了五个孩子。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母亲,即使在生活最灰暗的时候,也保持着那份高贵和优雅:饭桌上什么时候都要铺台布——那块台布是姥爷陪嫁过来的,早洗得变了色;每个人面前要铺餐巾。她要求每个孩子都要有教养,不许讲脏话,饭前一定要洗手,不洗脚不许上炕。
每天晚饭后,她会就着昏黄的油灯,给我们读俄罗斯童话故事。父亲也端端正正坐在一边津津有味地听。
理发铺被她打理得井然有条:墙壁永远用石灰刷得雪白雪白;前一个理发的人刚走,她马上就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洗头的池子也从来都是一尘不染。父亲的围裙尽管有些旧,但没有一个污点……
人们都说:“陶喜陞好福气啊,找了个能干的洋婆子!”
“干净”成了父亲店铺的招牌,别人的理发铺冷冷清清的,而他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尽管如此,塔城毕竟是小城市,客流有限。所以,日子只能说勉强维持得下去。
随着孩子们年龄增大,饭量也在增加。打我记事起,就有这样一个印象:每到吃饭的时候,母亲很少上桌,独自一人躲在厨房里忙活。即使上了桌,碗里也盛得很少很少。
父亲问是怎么回事儿,她推说吃饱了。
小时候,我很羡慕母亲:如果什么时候也能像母亲那样,吃那么一点就能饱,该有多好啊!
懂事后我才知道,母亲这样做,都是为了自己的老汉和孩子啊!我在厨房窗外不止一次发现:等大家吃完了,母亲把锅底铲一铲,兑些水喝下。还把我们的一只只碗冲了水,一口一口喝掉。
有一次,我忍不住冲进去抱着她“哇哇”痛哭。她把我揽在怀里悄悄说:“乖女儿,千万不要告诉你爸爸。”
长年累月这样,谁受得了呀!五十年代中期,母亲的胃就开始出现问题:经常胃痛。
症状越来越严重。到了后来,痛的时候,她整个人蜷缩成一团,脸色煞白,豆大的汗珠沿着额角往下流。
看她病成这样,父亲急了,要带她到乌鲁木齐大医院看看。可母亲心疼钱,一直不肯去。直到后来,母亲的病情发展到吃点东西就吐,有时还会吐血,这才去了医院。
一检查,是胃癌晚期。
知道了母亲的病情,父亲哭得像个孩子:“你为啥要嫁给我啊!为啥要嫁给我啊!我早就知道自己命苦,怕拖累你,看我……看我都带给你了什么……瓦莉亚,你这个傻姑娘!”
母亲倒很镇定,攥着父亲的手,笑吟吟地看着他:“我乐意!我乐意!下辈子,还跟着你!永远跟着你,别想甩了我!”
她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有条不紊地干着手头的事:把父亲的毛衣拆了又织好;把哥哥陶莲海的衣服改小了给弟弟穿;把我手套上的洞也给补上了……
弥留之际,她拉着父亲的手说:“陶大哥,再困难,也要让咱们的娃娃都能念上书……”结婚后,母亲一直称父亲是陶大哥。
为了老汉和子女,我的母亲像没了油的灯芯一样,就这样熬干了自己。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家里没了能干的女主人,整个天似乎都塌了下来。父亲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人蔫了,眼神也没有以前活泛了。
一个男人要养五个娃娃,艰难可想而知。
那时候,大哥陶莲海正上初中。看父亲天天愁眉苦脸的,他要求退学回家帮助父亲。
父亲对哥哥发了火:“你要好好念书。念完初中,再念高中,将来还要念大学……我答应过你母亲的。”
哥哥遗传了母亲的长相和性格,身材修长,五官俊秀,彬彬有礼。在学校,一直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几乎年年都是全年级第一名。校长和老师们都很喜欢他。
母亲去世不久,开始公私合营。父亲积极响应,成了塔城公私合营的积极分子。为此,还受到了表揚。
每次发了工资,父亲都会认真做规划:何时该给孩子们添件衣服;菜金该留多少;每天家里买几个馕,大小孩子该怎么分……总是菜场就要关门了,他才去买一点最便宜的菜帮子。
经常是很长时间,家里都见不到一点荤腥。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政府要建设克拉玛依大油田,从塔城抽调工人前去支援,父亲第一批被选上了。
支援祖国大建设是好事,可女主人不在了,家里的娃娃都还小,这该怎么办?
父亲愁得吃不下睡不着。
这种情况,哥哥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擅自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退学。
当他拿着书包、凳子站在父亲面前时,父亲火冒三丈,上去就是一记耳光:“回去!马上给我回去!家里,还轮不到你操心!把书给我念好!”
父亲拉着哥哥就往外走。
哥哥挣脱了,平静地说:“爸,我已办完退学手续。莲玉、莲江他们需要照顾。在家里我最大,我回来了,他们就可以把书念完……”
父亲举起了巴掌。
“打吧!您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回学校了。”
这是哥哥生平第一次和父亲犟嘴。
“克拉玛依石油会战需要人,咱不能拖国家的后腿。家,您就交给我吧。”哥哥依然平静地看着父亲。
看着懂事的孩子,父亲扬起的巴掌终于放了下来,他搂着哥哥哭了起来:“我可咋跟你妈交待呀?!咋跟你妈交待呀?!都怪爸爸没本事……孩子,你是读书的料啊……”
就此,十五岁不到的大哥,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推剪和白大褂——担起了支撑家庭的重担。
他不但要料理我们的生活,每天还要挨个检查我们的作业。有些作业,他会在废日历的反面自己再重做一遍。我们明白,其实他很留恋学校的生活。
生活的重压,让这个曾经俊朗活泼的少年,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这时,一个女孩闯进了我们这个家庭,也闯进了哥哥的心扉。她就是我后来的嫂子妮娜。
妮娜也是从苏联逃难来塔城的白俄的后代。就住在我家的隔壁。
英俊潇洒、品德又好的哥哥早就赢得了姑娘的芳心。
俄罗斯姑娘发育得早,和哥哥同岁的妮娜,此时已经像个大姑娘了。
现在,看着隔壁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去世了,男主人又远去他乡,姑娘心里别提有多么着急,暗中不知抹了多少次泪。
两家隔着一堵篱笆墙,每天一有空,妮娜就会过来帮着哥哥照顾这个家庭。家里缝补浆洗这些活,她全包了。哥哥想搭一把手,她剜哥哥一眼:“去!去!去!这不是爷们儿该干的活。”
每天一大早,她就会过来帮哥哥烧饭。饭做好了,她会像家里的女主人一样把大家一个个吆喝起来:“陶莲江,太阳晒屁股了,快起来吃了饭上学去!”“陶莲玉,昨晚把你的衣服洗好了。晾在厨房呢。”
每逢她的家里做了好吃的,她就会借口过来聊天,端着饭碗来到我们家,把她的碗倾倒在我们的锅里。再和我们一起吃。
她看哥哥的眼神,就像秋日里成熟的野莓,蜜汁似乎就要沁出来了。尽管当时的环境是那样的肃杀,但两颗爱情的种子,顽强地突破坚冰发出了油绿绿的嫩芽。
过了四年,援建克拉玛依工程结束,父亲重新回到了塔城。
这时,妮娜和哥哥的爱情果实,也已经成熟了。正当俩人商量着准备结婚时,塔城又发生了另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事:
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唆使在中国生活的苏联侨民返乡。重点集中在新疆。正值国内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时期。有人乘机跳出来煽动:“苏联已把粮食和糖果运送到边境上了”“快过去吧,苏联那边有肉吃、有啤酒喝,苏联还要派飞机来接”……
这些言辞,在饱受饥饿的边民心中,有相当的蛊惑力。边境附近发生了边民零星越境逃苏现象,数日后,塔城地区所属的裕民、额敏两县边民也开始非法越境,并逐渐波及到托里、和布克赛尔、乌苏等县。
非法越境逃苏势头不断扩大,由零星非法越境发展为成批越境;由夜间秘密越境,发展为白天公开成群结队的大规模非法越境……
妮娜全家也准备走。她找到哥哥,央求他能一起过去。
一边是心爱的姑娘,一边是亲生父亲和骨肉同胞。哥哥为难了。
看着被生活重担压得过早衰老了的父亲和一个个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哥哥肝肠寸断。
那些日子里,他茶饭不思。给人理发时,推剪推着推着就停下来,望着远处发起了呆。夜里也是整夜整夜睡不着……
最终,他选择了留下。
这可能是哥哥一生作出的最艰难的选择!
妮娜和哥哥洒泪而别后,哥哥就像哈密瓜断了瓜秧。他满嘴是泡,一下班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
第三天半夜,哥哥突然离开了家。天要亮了才回来。一天都魂不守舍。
此后几天,他都是每天半夜出去,天要亮了才回来。回来,便一整天都沉默不语。
父亲经见的世面多了,一定洞悉了儿子内心的煎熬……
可他又能怎么办呢?!
我发现,父亲几次一个人躲在无人的角落里偷偷抹眼泪。
作为一个已经懂事的姑娘,我心很细。发现此后的几天,大哥似乎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没人的时候,一会儿摸摸桌子,一会儿摸摸凳子,一会儿摸摸那爿土炕,一会儿又进到厨房不停地摸着灶台……似乎家里的一切他都没有见过,都感到新奇,都要摸一摸。
摸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异样的光。
见了我们姊妹幾个,他都要抱在怀里,久久不愿放开。弄得我们莫名其妙。
白天忙完了店里的活,夜里他又接着忙家里的活:把菜园子的篱笆墙重新扎了一遍;房顶也上了新泥;把父亲的理发工具重新磨了几遍;把我们每个人的脏衣服都给洗了,破了的全给补好——自从母亲去世后,这些活,他都会干。
我很担心:是不是因为妮娜走了,他受到的打击太大了,魔怔了?
我想把这一情况悄悄报告给父亲。可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天清早,我们起床后,发现大哥不见了。
一开始,大家没有多想,以为他出去买菜了。可左等右等不见他,才觉得情况不对了。这时,弟弟陶莲江发现了一封信:
爸爸:
请您原谅我!我已随妮娜去苏联了。
前些天,妮娜跟着全家走了。她舍不得我,又一个人越边境回来躲在隔壁等了我好几天。她见了我就哭……说,没了我,她就活不下去了。
您年纪大了,弟妹们又都小,我有责任帮您操持这个家。可又不愿意伤她……这几天,儿子心都碎了。
炕角的一毛四分钱是今天买菜的菜金。
塔城天冷,我把棉衣、棉裤都留给弟弟了。袜子我也脱下来洗了,放在炉子边上烘烤,大小,估计莲江可以穿。您的那双劳保手套,右手拇指烂了个洞,我已经缝好,放在了理发铺的工具箱里。
那个铅笔盒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考了全年级第一,校长亲自奖给我的。这是我从小到大最珍爱的宝贝。我一直舍不得用。把它留给莲玉了。
妈让我们好好念书,我没有听话,没能做到。希望弟弟妹妹都能好好学习。
爸,原谅儿子的不孝!我一定惹您生气了,昨晚我在您的窗外跪了大半夜,真想让您好好打我一顿……
陶莲玉告诉我,从此,他的哥哥便没了踪影。
又是十多年过去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来越敞宽,对外交流越来越频繁,周边关系越来越和睦,不知道有没有陶莲海的下落……
阿仓姐弟
旧历年的最后一天,我给好友阿仓去了个电话,询问他眼下的生活状况。尽管他嘴里照例是“放心,放心。好着哩,好着哩。”但我并不踏实。
问起他姐仓雅文的近况,阿仓嗫嚅了半晌,没有正面回答。我的心,便跟着抽紧了。
阿仓是我高中时的同桌。我的小说《我的兄弟阿仓》就是以他为原型写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转学来到我们班上。阿仓的父亲原是省秦剧团的台柱子。阿仓的个子全班最高,人缘也最好,功课却差得出奇,每次考试都全班垫底。他告诉我,在农村上的是“复合班”——几个年级的孩子聚在一起上课。他动不动就被撵出教室。
阿仓的父亲是那种旧社会过来的艺人,吃尽了没有文化的亏,所以对阿仓的成绩看得很重。
阿仓后来还告诉我一个秘密:父亲想让他拼命念书考大学,是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想挽回一个男人的尊严。当年,阿仓的母亲之所以偷偷和剧团里的写头(编剧)好上,就是因为嫌他的父亲没有文化。
阿仓的母亲去世之前已经疯了,整天在城门洞里一遍一遍对着路人唱:“红豆豆,煮米米,我爹给我找女婿。不要房上溜瓦的,不要槽头拴马的,不要柜里盛金的,只要手里拿笔的……”
资料上说,解放前,她是名震三省的刀马旦。照片我见到过,真正的天生丽质!不像现在有些明星,脸上不知拉了多少刀。
其实,班上属阿仓学习最刻苦!他来得最早,走得也最晚。可是基础实在太差,成绩上得并不快。一旦考不好,他的父亲就会“动家法”。那可是真打。我在他家就撞见过一回,他父亲拿着练功用的枣阳槊没命地朝阿仓的背上、屁股上抡。只要哪天阿仓慢腾腾走进教室,我就知道他又挨打了,下课从凳子上起来后,凳面上会有血印子。
为使他免受皮肉之苦,每次考试,我都把考卷往他那边挪挪。可他,不为所动。我劝他先应付过去再说。他说,父亲叮嘱过他,无论啥时候,做人都要诚实。
其实,为了阿仓的学习,付出心血最多的是他的姐姐仓雅文。
阿仓说,在农村时,仓雅文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返城初期,父亲的工资还没有兑现,每月只发三十几元生活费。为了保证阿仓上学,仓雅文只好辍学了,在一家缝纫铺里给人打工。
他们家住在城郊接合部。临时栖身在这里。七八户人家混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吵架的,打麻将的,有时候大半夜都不能安生。
为了阿仓读书不受干扰,仓雅文每天晚上都陪着他到小巷的路灯下去看书。我们那座城市,挨着江,夏天蚊虫肆虐,仓雅文一边看书一边帮阿仓扇蚊子;冬天寒风凛冽,姐弟俩裹着大棉袄,手上、脸上都是冻疮。
為了弟弟,仓雅文什么都愿意做。
我们的班主任是教数学的陈老师。高二那年秋天,陈老师的爱人生下孩子不久去世了。为了让陈老师多关照阿仓,仓雅文经常到陈老师家帮着做家务,娃娃的衣服、尿布、红缎子虎头披风都是她做的……
我那时是班长,经常帮阿仓补习功课,仓雅文也给我做了条咖啡色涤卡裤子。在一切都凭票的年代,这条裤子价值可不菲啊!
阿仓给我讲过他和姐姐的往事:阿仓六岁的时候,父亲被遣送回原籍。大队里所有的重体力活,譬如修水库、挖大渠之类的父亲都得做。经常是十天半月回不了家。
所以,比他大三岁的仓雅文又当爹又当娘顽强地撑持着这个家。生产队挖的那口水井,离阿仓家有二里多地。幼小的姐弟俩都还挑不动水,就两个人合抬一桶。每次抬水,仓雅文都把水桶往自己这头放,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别把我家阿仓压得不长个了。”
绞水的辘轳是供成年人用的。两个娃娃一边一个绞动辘轳,当辘轳到了高点时,需要踮起脚尖才够得着。冬天,井台上结着厚厚的冰,人站都站不稳,两个娃娃绞水就更费劲了。
一次,大雪连着下了几天,井台上结的冰比任何时候都厚。辘轳到了最高点时,阿仓冻得实在受不了了,辘轳把脱了手,已经快到井口的水桶如同脱缰的野马向下急坠,带动辘轳飞速旋转起来。为了保护弟弟,仓雅文用瘦弱的手臂去挡辘轳,结果造成了左臂骨折……
“我有个天底下最好的姐姐。”阿仓曾这样对我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考前的几次模拟考试,阿仓的成绩已蹿升到了中游的水平。班主任陈老师很高兴,鼓励他说,只要再加把劲儿,考个大专应该没问题。
可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改变了阿仓的命运:总有几个社会上的浮浪子弟到学校袭扰女生。一次,竟追到了课堂上。班上的男生实在看不下去了,便一拥而上把这几个坏家伙揍了一顿,有个家伙受了点轻伤。
这些家伙很有背景,告到了省里。最后市教育局要求追究责任,阿仓站了出来,一个人把责任全揽下了。于是,他失去了高考的资格。
这,带来了连锁反应:那时候,还可以接班。如果阿仓考上大学,父亲退休时,仓雅文就可以顶上去。现在,可怎么办?
阿仓决定自己到火车站蹬三轮车,把机会让给姐姐。谁知有一天,姐姐突然不见了。二十多天后,仓雅文从深圳寄回了一封信,说自己在一家韩国人开的服装厂找到了工作,让阿仓踏踏实实上班。
阿仓先是在秦剧团拉大幕,可不久,秦剧团倒闭了。他下岗了。此后,他蹬过三轮车,摆过地摊,在建筑工地砌过墙……一直没有一个正经营生。
结婚后,他生了个女儿。不幸的是,女儿患有先天性耳聋。两口子天南地北地求医问药,欠下一屁股债。
阿仓属于那种“饿死不求人”的冷怂,全班同学中属他日子过得最孽障。可每次同学聚会,问起近况,他总是那句:“好着哩!好着哩!”
同学们想变着法儿帮阿仓一下,都被谢绝了。譬如,每年在春节或“六一”,你找个借口给他寄点钱,他又变换个花样寄回来,数额比你的还大。
一次,我在黄河“小浪底枢纽”采访,闲暇看了工地业余剧团的演出。听着稀稀落落的掌声,工程队的领导有些不好意思,说:“招不到像样的演员……你走南闯北的,有合适的帮着推荐一下。”
我便想到了阿仓。虽然他没有上过专门的戏曲学校,但毕竟是“门里”出身。一推荐,人家很高兴,邀请阿仓来试试。一曲《斩单童》,剧团领导脸上乐开了花。
可是不久,我听说阿仓死活不干了。打电话询问,他说,剧团还有一个唱秦腔的,他一来,人家就得下岗。“怎么着也不能戗人家的行。”
阿仓干得最久的营生是卖水果。在小区租了一个小小的门面,每天天不亮就蹬着三轮车去码头批发鲜果。阿仓的妻子偷偷告诉我:阿仓的腰肌劳损越来越严重,每天晚上都得给他热敷……
我从多方了解到,这些年,仓雅文也过得非常艰难。
她继承了母亲的基因,相貌比那些当红明星一点也不差,身高至少有一米七多。可是,屡屡遇人不淑:
先是厂里的主管看上了她,骗她说自己是单身,还说会好好帮着照顾她的父亲和弟弟。谁知同居不到半年,主管夫人打上了门。
之后,她找了个潮州人,两个人还生了个儿子。没想到这是个赌徒,债主拎刀上门讨债,潮州人跑路了。跑前把房子也抵押了出去。一跑,便没了踪影。母子二人被债主赶出了家门,只好到处租房子住。
再后来,她嫁了一个在深圳搞装修的江西老表。这个人倒是挺本分,可是,刚结婚两个月,他就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脊柱。从此,没能再站起来。
已经十多年了,仓雅文一直精心伺候着那个男人。打工挣下的钱,全花在为男人瞧病上了。
最令人操心的是她的儿子,为讨生活,倉雅文天天疲于奔命,对他疏于管教。这个孩子从十五六岁开始,就不走正道了,整天和一帮烂仔混在一起,打架、吸毒,三天两头进拘留所……
“雅文姐,到底怎样了?”我在电话那头紧着追问。
“去年闺女去深圳,我让她去看看她姑。我姐年龄大了,重体力活干不动了,找活越来越难,有时一年要换好几个工作。去年受疫情影响,大半年没有找到活干,秋天被推荐到一户有钱人家当保姆。可那家的老太太很坏,疑心病很重,一会儿说家里的首饰不见了,一会儿又说我姐和男主人眉来眼去了,老是用手拧我姐。我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也不敢吭声……这辈子,我欠我姐的太多了。对不起……对不起呀姐!可……可我没办法、没办法还啊……”
我呆呆地握着电话。
电话那头,早已泣不成声了……
(责任编辑:龙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