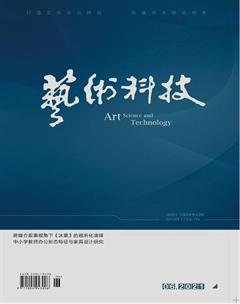凤冈吹打乐的法律保护探究
摘要:一种文化往往融合了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态度及精神,凤冈吹打乐对凤冈人民就是如此,凤冈吹打乐体现出了凤冈人民的生活态度及性格,已成为当地的文化特色。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进步,不断有外来文化进入当地,对凤冈吹打乐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必须加大保护与传承凤冈吹打乐的力度,尤其要从法律层面进行规制。本文从法律保护视角出发,旨在为凤冈吹打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借鉴。
关键词:凤冈吹打乐;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6-0-02
0 引言
凤冈吹打乐是贵州省人民政府于2007年5月29日公布的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音乐)之一,其发源地为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天桥乡,以音乐宏伟、热情及参与者众多而闻名。天桥乡因这一传统艺术荣获贵州省“唢呐之乡”的称号。
凤冈吹打乐的出现和发展与当地的人口迁移历史同步。根据周氏家谱的记载,凤冈吹打乐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初的周笑老先生,其祖籍为江西临江浦大桥高街沿。宋孝宗时期,周笑老先生高中武举,政府为了治理贵州,遂指派周笑老先生及其八兄弟从江西迁入贵州北部的六水口(现为平头溪)。周笑老先生具有出色的演奏技巧,并精通各种乐器制作技术。周氏家族第十三代周海棠在15岁那年,把所学的所有技巧整合在当地的民间音乐中,使“天生桥”吹打乐独树一帜、广为人知。
1 凤冈吹打乐法律保护的价值
1.1 凤冈吹打乐法律保护的文化价值
凤冈吹打乐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音乐为载体,在情感交流上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凤冈吹打乐出现在当地的各种酒宴上,红白喜事皆离不开它。喜宴上的吹打乐,一方面要表现出娘家人对闺女出嫁的开心与不舍,担心养育了多年的宝贝女儿离开家庭会受到委屈;另一方面要表现出新人終成眷属的喜悦之情。至于丧宴上的吹打乐,主要表现对逝去亲人的缅怀。当然凤冈吹打乐的应用场景不止红白喜事,但大多数时候用来表现喜悦。
1.2 凤冈吹打乐法律保护的经济价值
经济利益是衡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有社会价值的重要参考。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是文化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相反,文化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经济转型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实价值的实现。它不仅可以丰富文化产品的种类,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可以通过文化遗产的再生产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因此,当地政府可以以此为依托,大力发展旅游业,在凤冈吹打乐的起源地凤冈县天桥乡,修建吹打乐活动中心、吹打乐培训学校、吹打乐小镇等,助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可以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将当地的吹打乐乐曲发布到网上,在传播凤冈吹打乐的同时,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以上种种想法均建立在凤冈吹打乐能够得到有效保护的基础上。
2 凤冈吹打乐法律保护现存问题
2.1 法律的缺失
虽然我国早在2011年就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了非遗保护条例,但检索当下的法律可知,并没有与之匹配的实施细则及司法解释,因此我国的非遗保护法律体系极其粗糙[1]。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过程中,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施细则、审查规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人认定方法、认定程序等都比较模糊。此外,贵州省在非遗保护方面也略显不足,当下只有《民间文化保护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两部地方条例,且规定过于宽泛,微观层面的实施细则并未出台。而凤冈吹打乐的管辖地——遵义市,至今仍未出台相应的非遗保护条例,这使包括凤冈吹打乐在内的非遗文化的保护存在致命缺陷。
2.2 现存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足
一般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包含两个层面的目标,一是保护,二为发展。这两个目标共同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完整内涵。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视为一个过程,一种动态的知识表达方式。换句话说,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制定的任何法律规范都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是,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静态的角度出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保持不利,法律规范缺乏可操作性,降低了人们体验文化财产价值的可能性。贵州省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它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针对具体对象制定的地方法规,但将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条文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基本是照搬《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在具体规定上更是含糊其词、界限不清,大大降低了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以至于凤冈吹打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得到应有的保护[2]。
2.3 权利保护主体的界定存在争议
当下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以保护非遗代表人的利益为主导,但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可能为个人或团体的某些成员所有,甚至可能为该团体的所有成员所有。因此,需要确定真正的文化遗产所有者。以凤冈吹打乐为例,传承代表人究竟是一个人、多个人,还是凤冈天桥村集体?如果是特定的多人,如何定义“特定”的范围?指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权利主体(传承代表人),以使其成为具有明确范围的描述性对象,对非遗的保护至关重要[3]。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问题难以解决,因为非遗往往由一个地方独有,当地人或多或少均有所涉及,评选的代表人往往难以服众。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权利主体的非特定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最根本的区别,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化的最大障碍。
2.4 未建立损害赔偿机制及价值评估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五条和最高法颁布的《关于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均指出,在非遗的传承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始终以尊重为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应尊重其形式和内涵,不应扭曲或贬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上述法规和意见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让我们尊重文化遗产,但从反面解读,对“不尊重”的行为如何处理只字未提,因此我们需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害赔偿机制和价值评估体系。然而,凤冈吹打乐属于音乐作品,无任何实物载体,且时至今日未发表任何一张专辑,价值无法衡量。凤冈吹打乐受到侵害时,如何评价侵害程度,如何进行赔偿,能否仅赔偿金钱,以上问题法院无从下手,即使有相应判决,也并未达到保护凤冈吹打乐的预期[4]。
3 完善法律保护制度的构想
第一,关于缺乏立法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例如引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渠道,巩固依法行政的法律基础。还可结合我国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宝贵经验,特别是脱贫攻坚中,我国许多地方打造的“非遗+扶贫”的新模式[5],在传承非遗的同时,带动当地百姓脱贫。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出现了新变化和新趋势,即之前我们往往关注遗产名录,现在需要转变思想,把重心放在保护成效上,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贵州省虽然制定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但其条文内容大体照抄非遗法,并且在凤冈吹打乐所在地遵义市,仍未颁布相应的非遗保护条例,以至于当地的非遗缺乏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纵观贵州省其他州市,均有非遗保护条例。因此,要想更好地保护遵义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要紧的是出台非遗保护条例,让非遗保护落地。只有在国家与地方双重举措的支持下,包括凤冈吹打乐在内的非遗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6]。
第二,关于法律规范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除了要对贵州省非遗条例在遗产名录、保护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修订,将其变为具体可操作的非遗文化保护条款外,还应在制定遵义市非遗保护条例的同时,将包括凤冈吹打乐在内的一系列本土文化遗产纳入保护名录,并提供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对应分级分类保护原则,地方立法需要进一步增强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不同形态或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确定不同的保护层级、不同的补救技术、不同的保障方案。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风险时,可以出台地方专项保护性立法,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并建立体系化的专项保护制度,使地方非遗的保护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第三,关于非遗权利主体界定不清晰的问题,可以参考当下主流观点。首先要明确界定非遗文化的权利主体,突破原有学理框架中关于权利主体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方式,建立一套能够囊括非遗权利主体界定、非遗文化保护、非遗侵权救济等内容的系统的非遗文化法律保护机制[7]。同时,需厘清非遗代表人,让非遗代表人更好地、无后顾之忧地保护、传承非遗文化。当地政府需为其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不能让非遗代表人在进行文化传承的同时,考虑生计问题。当然,非遗代表人只是具有法定地位的传承主体,虽然要以立法的方式肯定非遗代表人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是唯一的传承主体。在传承过程中,可以通过倡导群众参与保护、传承的方式构建多元化的传承保护机制,从而更快地达到预期目的、取得预期效果。
第四,关于损害赔偿机制及价值评估制度的构建问题,首先各法律部门之间应做好协调与衔接,尤其要协调好与民商法、刑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诉讼法、知识产权法的关系。目前,我国主要采用以行政法保护为主、以知识产权法保护为辅的保护模式。出现关涉非遗保护问题的法律纠纷后,需要找到适用的法律条文依据。但非遗保护法只是在形式、意义上作出了保护性的规定,始终缺乏实质性意义,其具体模式和程序有待进一步完善。此时,遇到行为侵害非遗代表人权利、危害非遗文化传承工作的,应当依法追究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具体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8]。赋予权利时,应当预设该权利被侵害时的补救途径和补救方式,没有责任追究和权利救济条款的法律法规就是一只纸老虎,无法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在价值评估上,可以成立相应的评估机构,聘请当地的学者、非遗代表人等作为评估人员,毕竟非遗有其特有的属性、文化内涵,不能标准化,只有了解的人才能进行客观的评估,这为非遗侵权案件的判决提供了便利。当然,类似机构前期存续较为困难,政府需要大力支持,尤其要加大经济方面的支持,使包括凤冈吹打乐在内的非遗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
4 结语
凤冈吹打乐作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体现了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更体现了当地人民的乐观态度,以及音乐鼓舞士气的文化价值。当然,凤冈吹打乐也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其传承能够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但凤冈吹打乐在传承过程中,难免陷入法律困境,可以通过完善法律、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厘清非遗代表人、建立损害赔偿机制及价值评估制度等,克服传承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使包括凤冈吹打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焕发出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余志勇.让非遗之美更闪亮[N].遵义日报,2021-03-12(004).
[2] 赵莹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法律保护探究[J].岭南学刊,2021(01):103-110.
[3] 穆永强,蒋环.國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兰州鼓子的法律保护[N].民主与法制时报,2020-08-13(008).
[4] 梅贵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研究[J].汉字文化,2020(06):69-71.
[5] 王玉婷.浅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9,4(08):18-20.
[6] 白晓杨.论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J].福建茶叶,2019,41(08):210.
[7] 杨颖君.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9(20):27-28.
[8] 黎群.乡村振兴背景下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路径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05):190-197.
作者简介:赵军(1992—),男,贵州遵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商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