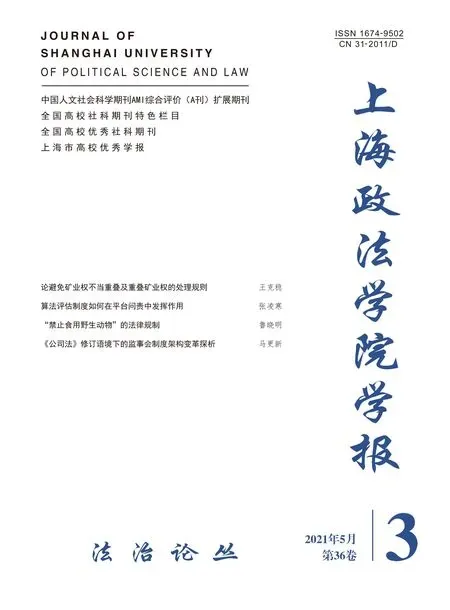“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规制
鲁晓明
接踵而至的SARS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大型公共疫情,引发公众对于滥食野生动物陋习(以下简称“滥食陋习”)之强烈愤慨。此种激愤情绪在立法层面发酵,使我国驶入了野生动物食用立法的快车道。①殊值一提的是,尽管这种情绪促成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决策的出台,但关于新冠病毒肺炎的溯源远没有完成。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传播机理等均有待流行病学查明。我国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决定,只是出于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基于科学常识所作出的决策,并不表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食用野生动物存在关联。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开启了就“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协同立法的大幕。作为因应突发公共疫情之重大决策,《决定》因时而生,对于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意义重大,但由于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系统论证,客观上也存在缺乏对多种利益进行平衡的问题,这为后续立法和修法工作留下了难题。笔者希望通过管窥蠡测,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助益对野生动物食用行为的科学规制。
一、“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之制度意蕴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积极老龄化的法治问题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ZDA157。
(一)“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意义
1.“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是“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必要手段
在《辞海》 中,“滥”指不加选择和节制。“食”在甲骨文中本指“饭食”,后逐渐引申出“吃”的意思。①参见彭晓燕:《“食”词群文化语言学研究》,湖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故所谓“滥食”,应是不加选择和节制地食用。人类饮食之合理性需要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安全性;二是人与自然之和谐关系。食用行为既不能带来安全隐患,又不能涸泽而渔。唯有加以选择,才能实现安全饮食;唯有节制饮食,才能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系统乃人的生存基础②参见张秀芹、王朝旭:《生态伦理视角下柏格森创造进化论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年第2期。,人作为生命活动“类”的存在,“我们甚至不能说,人类是整个进化的结果,因为进化是沿着好几条不同的路线进行的”③参见[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20页。。因此,饮食当“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④参见《墨子·节用中》。。引发安全危害或物种紧张关系的滥食行为既有违安全饮食,又有悖于生态伦理。
习俗是人类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作为社会活动和事务中的固化习惯,习俗覆盖团体、社群或社会成员⑤参见韦森:《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具有观念性、群体性和持续性。作为人后天形成的自动进行某种行动的心理倾向⑥参见张雄:《习俗与市场——从康芒斯等人对市场习俗的分析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习俗是“是一种不经由任何人在任何意义上‘要求’,个人遵从之而驻存的一种集体行动的方式”⑦See Max Weber,Economy and Society,Ed.by G.Roth & C.Wittich,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1968,p.315.。在社会交往中,人之不断重复的习惯向社会群体行为之重复的习俗不断转化。⑧参见韦森:《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正常饮食习俗应满足基本的安全性要求,即引发人类疾病的概率较低、引发之疾病烈度小,且风险可控。我国饮食习俗源远流长,但也存在不少与文明相悖的不合理风尚。⑨参见娜仁图雅:《民间陋习的法律规制研究》,《前沿》2012年第5期。就滥食陋习而言,主要有:(1)一味求鲜,视食珍奇动物为口福⑩参见赵荣光:《拒烹、拒售、拒食野生动物——我是怎样提出“三拒”倡议的》,《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置食物味道于安全性之上的习俗;(2)牺牲安全性,刻意贬低养殖食材的食用价值⑪参见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技委员会:《关于摒弃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树立文明健康饮食方式的建议》,《学会》2004年第1期。,渲染“土”“野”“天然”食材美食滋补功能的饮食习俗⑫参见夏明、管婧婧:《中国传统药膳文化科学发展问题的思考》,《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宋胜利:《中国药膳食疗发展诸问题刍议》,《时珍国医国药》2006年第4期。;(3)不遵循传统,以消费“新”“奇”食材为荣耀的猎奇性饮食习俗。⑬比如,古代习俗中“烹龙炮凤”的习俗,和为了追求奇珍异食而追捧熊掌、驼峰、猴脑、白腥唇等。参见鲍晶:《略谈饮食文化》,《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残忍、不文明的饮食习俗,虽也是陋习,但主要指食用方式有违饮食伦理,故不属于滥食陋习。
食用习俗和食用行为虽各有所指却又存在难以割舍的密切联系。食用习俗存在于观念层面,食用行为则是习俗在行为层面的自觉践行。习俗内化到人之自觉行动中,持续地影响人之消费心理,指导消费选择和消费行为,形成思维定势和心理强制。滥食陋习深植于群体置味觉于安全性之上的饮食偏好和传承经年的饮食习俗。革除滥食陋习应主要通过价值引导、革新饮食伦理、以移风易俗的方式实现,但这一过程漫长且必然遭遇食用者惯性、饮食文化、群体影响等多方面掣肘,若停留于道德自觉,革除陋习之目标很难短期内实现。唯有将节制饮食上升为法定义务,价值批判、思想引导与法律强制多管齐下,才能达到迅速革除滥食陋习之目的。“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即是滥食存在危及公共安全之虞时,通过设置法定强行性义务,运用法律强制力予以革除之必要手段。
2.“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是保障人之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举措
《决定》产生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演化为公共卫生事件,而野生动物食用行为引发疫情之揣测和传闻不绝于耳的特殊时期。其目的十分明确,即以限制公民饮食选择权为代价,通过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斩断致病微生物从动物传播到人的途径,实现饮食安全,以保障人之生命健康。
食用虽为个体行为,但又具群体影响。因此,饮食选择虽属个体权利,但节制饮食也是个体道德义务,且在事关公共安全时成为强制性法律义务。恣意放纵的食用行为极大地增加了致病微生物由动物传播到人的风险,不仅损害食用者自身健康①微生物通常包括寄生虫、细菌和病毒三种形态。三者形体上由大到小。随着医学和生物科技的进步,现代社会寄生虫和细菌引发的疾病虽仍对人类具有威胁性,但已难以构成大规模公共疫情。鉴于现代传染病疫情主要系由病毒传播造成这一事实,本文所称之微生物在无特别说明情况下,主要指病毒。,而且危及公共安全。尽管由于动物复杂多样,绝对的食用安全几不存在,但相对的安全性仍然可能且必要。“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即是对安全饮食这一强制性义务的确认。
生物学研究表明,野生动物是致病微生物传播到人的主要宿主。②参见王智勇:《浅析野生动物与人兽共患病(1)》,《特种经济动植物》2008年第7期。本文表1的研究显示,近年来造成人类重大损失的20种人畜共患流行病,除宿主不明的个别情况外,自然宿主均为野生动物。致病微生物跨物种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人的狩猎、屠宰和食用行为。③参见[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4-48页。尽管蚊虫叮咬和水也是微生物传播的有效途径,但狩猎、屠宰和食用行为对微生物的接触更加全方位。从表1可以看出,体液和接触传播占了人畜共患传染病传播的相当比例。狩猎、屠宰和食用行为犹如构建起微生物传播的高速公路,将不同物种之间的所有组织,连同栖息在物种上的微生物都连接起来,“让微生物以更直接、更便捷的方式跳到狩猎者身上”④同注③,第45页。。

表1:近年影响广泛的人畜共患疾病来源⑤本表类型系在参考医学分类基础上所做的分类。需说明的是,由于多在实践意义上使用,医学上的类型划分并不存在明确标准且难言符合逻辑,个别类型(比如出血热和黄热病)甚至是交叉或包容关系。

①参见薛庆於、于智勇:《马尔堡病毒研究进展》,《科技创新导报》2012年第2期;于双平等:《马尔堡出血热的研究进展》,《应用预防医学》2008年第2期。②参见刘丽娟、孙肖红:《尼帕病毒和尼帕病毒病》,《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2018年第6期。③参见孙雨等:《狂犬病毒流行病学特征与实验室诊断技术的研究进展》,《中国畜牧兽医杂志》2015年第2期;熊成龙等:《狂犬病毒生物学特征研究进展》,《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年第10期。④朊病毒严格来说不是病毒,而是一类不含核酸而仅由蛋白质构成、可自我复制并具有感染性的因子。参见张会侠等:《朊病毒疾病将如何发展?》,《科学通报》2017年第1期;杨建民等:《朊病毒致病机理研究进展》,《中国畜牧兽医》2004年第10期;高原等:《兔、犬、马抵御朊病毒疾病的研究进展》,《生命科学》2019年第11期。⑤参见张硕、李德新:《寨卡病毒和寨卡病毒病》,《病毒学报》2016年第1期。⑥参见张爱梅等:《人兽共患传染病的免疫保护策略》,《河南预防医学杂志》2004年第1期。⑦新冠病毒的宿主与传播途径尚处于研究之中,石正丽等专家虽认为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和呼吸道传播,但目前均没有最终的结论。⑧参见刘金玲、支海兵:《西尼罗河热》,《中国兽医杂志》2006年第9期。⑨H5N1、H7N9被俗称为禽流感,其实只是禽流感病毒的亚型。禽流感病毒包括16个H亚型和9个N亚型,只不过其他亚型一般不传染人,危害性较轻而已。参见陆家海等:《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毒研究进展》,《国际病毒学杂志》2007年第3期。⑩H1N1俗称猪流感,事实上是流感病毒的一种,可广泛感染家禽家畜并传染到人。参见王春丽、李子艳、毛艳艳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回顾》,《中国抗生素杂志》2021年第3期。⑪参见刘社兰等:《“中东呼吸综合征”流行现状与研究进展》,《浙江预防医学》2014年第7期。⑫参见王春丽、李子艳、毛艳艳等:《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回顾》,《中国抗生素杂志》2021年第3期。
毋庸置疑,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对于保持生物多样性,防止野生动物资源枯竭,维护生态平衡意义重大。但在新冠病毒肺炎演化为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时点,将滥食野生动物作为规制对象予以严厉打击,更主要是出于饮食安全的考量⑬参见王晨:《依法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中国人大》2020年第6期;孙佑海:《野生动物保护的重大制度创新》,《中国人大》2020年第5期。,既是基于致病微生物大多来自野生动物的客观实情,又是针对食用这一接触传播最重要途径的针对性策略。
(二)“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合适内涵
准确理解“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之含义,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作为禁食对象之野生动物具体指向哪些动物;其次需要明晰的是,全面禁止之内在涵义是什么?
1.禁止食用之野生动物对象
顾名思义,野生动物就是于野外环境繁殖生长的动物。“野生”是就动物的生长方式而言,与之对应的则是“家养”或“人工养殖”。野生动物和人工养殖动物具有集合性、可转化性和条件性。野生动物并不指向某类固定而明确的动物,世上并不存在名为“野生动物”的独立类型,而是所有于野外生存动物之集合。严格而言,动物只要满足野外繁育生长条件就是野生动物。反之,只要由人工繁育驯养就属于“家养”。事实上并不存在科学或规范意义上的野生动物概念,传统上野生动物与人工养殖动物的区分并非标准明确且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你中有我的复杂局面。一种动物即便经人工繁殖驯养,但只要养殖历史不长,就仍会被认为属野生动物;反之,猪、鸡等传统家养动物即便于野外繁育生长,仍会被看作人工养殖动物。实践中,野生动物几乎可在任何语境中使用,既没有明确指向,也没有确定内涵。只要不是猪、狗、牛、羊、鸡等传统家养动物,无论是否野外生长繁殖,均可能被称为野生动物。相反,江河湖海中的鱼类,通常不被看作野生动物。
在实践中,对于“野生动物”的随意使用使野生动物概念缺乏基本的确定性,作为法律概念将极大地损害法律的科学性。《野生动物保护法》服务于其立法目的,将作为保护对象的“野生动物”界定为“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是基于“具有保护必要”所作之限缩性界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若不能统摄至野外繁殖生长这一语境,难以达到针对性目的;若将其限缩至野外语境,则不仅与当下社会生活指向迥然有异,且在日常饮食中大量“野味”已是人工养殖动物的情况下②参见尹峰等:《中国食用野生动物状况调查》,《野生动物》2006年第6期。,还可能面临立法必要性质疑。
基于此,《决定》没有对野生动物作一刀切的统一界定,而是以“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育的动物”为基础,既有所扩大,又有所缩减。“野生动物”既不指所有野外生长繁育的动物,也不只是指野外生长繁育的动物。一方面,凡未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陆生脊椎动物,无论是否野外生长繁育,均被视为野生动物;另一方面,陆生无脊椎动物及水生野生动物均被排除在外,列入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动物无论是否野外生长繁殖,均不被视为野生。这一界定,正视了水生脊椎动物和陆生无脊椎动物与人类亲缘较远,列入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动物具有传承经年的饮食传统,两者食用安全性均较高之事实,但由于将野生与人工养殖动物混于一起,没能有效解决野生动物概念的确定性问题。
2.“全面禁止”之内在含义
尽管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是革除滥食陋习和保障人之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手段,但无论基于革除滥食陋习,还是保障人之生命健康安全,均难以得出禁止食用所有野生动物的结论。革除滥食陋习着重要解决“滥”食而非是否可“食”的问题,其手段应是“节”而非“绝”食。本文后半部分的论述充分证明,部分野生动物之食用安全性是有保障的。因此,基于减小社会成本及多法益平衡之考虑,不应对于“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做绝对化理解,而应理解为基于安全性考量之应禁尽禁的预防性策略。
(1)“全面禁止食用”体现以预防为主的思路
“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产生于怀疑食用野生动物具有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盖然性之特殊时期,是应对公共疫情诸多举措的组成部分。野生动物类型多样,人类对其认知仍囿于极有限之领域。动物食用的安全性尽管在科学上已有一定结论但并不都很清晰。SARS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说明,由食用野生动物引发的风险具有不可预知性,若不能提前加以预防,则当风险转化为现实危害时,极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待危害显而易见时再采取措施已显得太迟。为防患于未然,《决定》采取了事急从权,存疑从有的特殊处理方式。“全面禁止”意味着为确保饮食安全,凡安全性未经证明的陆生脊椎动物,一律禁止食用。
(2)“全面”反映对食用野生动物应禁尽禁的坚决态度
不同于重开发利用,仅在涉及生态安全等特殊情况时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的立法传统,《决定》将野生动物保护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决定》对于“食用”这一野生动物利用方式整体上采取了否定态度,从价值层面否定了食用野生动物行为的正当性。一方面,全面禁止意味着禁止食用之野生动物的广泛程度。任何野生陆生脊椎动物,只要其食用未证明不存在安全隐患或已证实不会引发生态紧张关系,且列入可以食用的种类清单,则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即便付出重大代价也要禁止食用。另一方面,全面禁止还意味着,饮食选择尽管系个体自由,但涉及野生动物时需受法律的严格限制,食用未列入可食范围的野生动物行为均涉嫌违法。
(3)对禁止举措之理解应符合比例原则
“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意味着为了公共利益而较大幅度地限制公民饮食选择权利,这必然牵涉到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问题。因而,禁止食用举措仍需经受比例原则的衡量。1)禁止食用举措需符合适当性原则。通过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应能达到饮食安全和解决生态紧张关系之公共利益目的。2)禁止食用举措需足够必要。在满足饮食安全和解决生态紧张关系的诸多手段之中,禁止食用应是对公民权利影响较小的手段。3)禁止食用举措需满足均衡性要求。克减饮食选择权利之手段应与公共利益目的保持均衡。
适应比例原则的需要,“全面禁止”不应理解为不分情况地一律禁止。某类动物是否禁止食用,仍需在安全性评估基础上进行必要性衡量。存在安全隐患和可能导致生态紧张关系的禁止食用;不存在前述问题的,则宜分类施策。故对于全面禁止食用,应通过限缩解释使其实质上指向分类区分基础上的甄别性禁止。①显然,相关立法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决定》通过的当天,全国人大法工委相关负责人答媒体问时也提出,对于具有较长养殖历史的动物应甄别情况。参见《全面禁食野生动物要把握好哪些界限?法工委相关负责人释疑》,《人民日报》2020年2月24日。
二、“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立法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一)清晰化总体的立法目的
为防挂一漏万,《决定》将“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足足七个立法目的汇聚于一起。
此种面面俱到的安排,体现了《决定》作为规范野生动物食用行为基本法律的特点,对于防止出现错漏,实现多重法的目标意义重大。但在学理上,某个目的是否合适作为立法目的,宜作为直接还是最终目的,不同目的之间是何种关系,则需进一步斟酌。其一,交易合法性与习俗合理性服务和服从于立法目的,但本身并非目的。故“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难以成立立法目的。其二,不同目的并非处于同一层面。比如,“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是直接立法目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以下简称“人之生命安全”)则是最终立法目标。其三,不同目的之关系也不相同。“革除滥食陋习”与“生态文明建设”是包容关系,“生命安全”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下简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平行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则是交叉关系。其四,从涉及层面来看,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是行为层面的刚性要求,主要应通过强行性规范中的禁止性规范调整;革除滥食陋习、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价值层面的要求,主要应通过任意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实现。②有关强行性规范、禁止性规范、任意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之区分,参见王轶:《论倡导性规范——以合同法为背景的分析》,《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王轶:《强行性规范及其法律适用》,《南都学坛》2010年第1期。
为明晰宗旨,宜对前述立法目的之层次关系进行梳理,使层次更分明,目的更明确。在前述七个立法目的中,“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均只是具体举措。“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虽可成立立法目的,但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重叠,可为后者所吸收。“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虽具有不同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处,但大抵可为后者所吸收。故而,《决定》之立法目的可整合为两个:一是“人之生命安全”;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一是要改变单纯基于人类立场所形成的物为人所用、万物可食之传统观念,通过倡导敬畏和尊重自然的思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节制饮食为核心内容重构饮食伦理,实现移风易俗;二是通过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实现饮食安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此两个立法目的,相互配合又各有所指。人之生命健康安全是每一个饮食行为都应予注意的,但单个食用行为通常不会危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平衡野生动物食用中的不同利益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之调节器①参见梁上上:《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始终面临着自由、安全、秩序、效率、公平和正义等多法益兼顾和平衡问题。②参见魏增产、段祥伟:《论经济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河北法学》2010年第1期。“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涉及生命安全法益与自然资源利用、个体自由权利与整体安全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合理平衡,建立一个含义相对明确、覆盖适中,既能满足安全饮食要求,又不过度牺牲其他利益的禁止食用之野生动物范围,不仅事关制度成本,而且直接影响实施效果。
1.个体饮食自由与群体生命健康、物种生态安全
个体与群体之关系历来是哲学上的重大命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史。现代社会基于个体主义立场,要求为个体划定一个不容侵犯的私人领域。③参见陈浩:《论共同体包容个体自由之限度——以黑格尔的“主观自由”概念为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基于个人嗜好的饮食选择,是个体的重要基本权利。基本权利具有排除国家干涉和侵害的功能。④参见张翔:《论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法学家》2005年第2期。国家非为必要不应该限制和克减公民选择饮食的基本权利,而应采取措施保障饮食自由。
基本权利不仅保障个体自由,还需在社会不同层面的自由之间进行价值均衡。⑤参见李忠夏:《基本权利的社会功能》,《法学家》2014年第5期。当国家面临重大公共安全危机、生物物种面临威胁时,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负责、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关系这一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家理当具有克减公民饮食选择权利的权力。⑥参见王晨光:《法治思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运用》,《法律适用》2020年第2期。但此种限制须符合比例原则,满足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的要求。⑦参见梅扬:《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所采取之手段需以满足公共利益目的为已足,且公共利益目的与限制饮食选择手段之间具有均衡性。
2.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
从自然界获取生存资料,繁育养殖动物为我所用,是人类发展之重要推动力。《周礼》有云:“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藩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⑧《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3页。当代社会随着人工繁殖技术的进步,相当种类具有食用价值的动物已实现人工养殖。相应地,动物养殖已形成庞大产业。以我国为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2018年养殖业总产值28 697亿元⑨参见国家统计局数据,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E5%85%BB%E6%AE%96%E4%B8%9A%E4%BA%A7%E5%80%BC,2020年3月4日访问。,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经济价值较高的特种养殖业。
尽管人工养殖动物实质上已属“家养”,但在公众和社会习惯均将其作为野生动物看待的情况下,既需考虑公众顾虑,又要有利于推动人类探索和利用自然的努力;既需通过禁食达到保障公众安全的目标,又要避免付出过于沉重的成本,防止使本已处于困境中的养殖业雪上加霜,避免使数量庞大的从业人员陷入困境。必要的野生动物利用自古就有,若不能服务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目的,为了禁止而禁止,则丧失了饮食传统、付出牺牲产业发展、使农民丧失通过从事相关养殖业脱贫机会之代价将过于巨大。
3.习惯传承与风俗现代化
饮食习俗内生于民族的世界观与文化自觉之中,指导人们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后辈的饮食习俗既体现文化传承,亦体现对于前辈情感和饮食偏好之追随。情感寄托、味觉偏好、文化习性、价值观念有机糅合于饮食习惯之中,指导人们自觉自愿的饮食活动。任何移风易俗的活动都应建立在对于传统文明的传承和肯定上,作为人类饮食文明发展的有机部分。但世易时移,饮食习俗的现代化无时无刻地进行着。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一切为我所用,解决食不果腹的现实困境成为压倒性的饮食观念,安全性让位于生存需要,生态伦理更无从谈起;而当生产力提高,温饱不再成为困扰人类的时候,选择饮食就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节制饮食,摈弃不合时宜、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饮食习惯就势在必然。
革除滥食陋习,既要兼顾人们对于传统的深厚情感,正视传统习俗中的合理内容;又要坚决摒弃置安全和生态伦理于不顾,与现代文明不相容的丑陋习俗,在二者之间求得合理平衡。
4.革除滥食决心与法治权威损害风险
法律只能规定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一点已为社会发展史中诸多事例如美国禁酒令的失败所充分证明。①在20世纪初,酒在美国被看成犯罪和贫穷的根源。1919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18条修正案,明确禁止酿造、出售、运送酒类行为。但事实表明这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法案。不仅非法贸易带来暴利,而且上百万人因违反禁酒令被捕,社会矛盾激化。1933年国会被迫予以废止。参见王晓光:《美国宪法禁酒令的立与废——兼谈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法制变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尤值一提的是,美国禁酒令的出台不仅得到了极高民意支持,还有深层次宗教信仰支撑。②清教徒敬畏上帝,有“酒即罪恶”的观念。这种宗教信仰对于禁酒令产生了直接推动作用。参见何军:《19世纪至20世纪美国禁酒运动失败原因探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通过革除滥食陋习维护饮食安全的决心可以理解,但革除滥食陋习与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毕竟不是直接对应的关系。革除滥食陋习并非一律要以禁止食用这一激烈方式进行。价值层面的问题整体上仍宜在价值层面解决。陋习之革除,更多地需通过移风易俗实现。禁止食用充其量是一种辅助和威慑的手段,仅在陋习危及公共安全及生态安全时采用。
革除滥食陋习针对的是不加节制地食用野生动物引发安全危机和生态紧张关系的行为,并非绝对排斥食用野生动物。若对于食用野生动物简单地一禁了之,则极可能因有悖于国情而出现违法行为泛滥的现象。同时,若野生动物禁食范围涵盖过广而致一些传统上可以食用且已经证实安全的动物被禁止食用,则会过度压制民众的饮食选择。当人们不再面临公共安全威胁时,选择遵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律禁食虽彰显革除滥食陋习之决心,但不仅于饮食安全未有增益,反而可能损害法治权威。
(三)合理确定禁止食用之“野生动物”合适范围
与既有法律重视多法益平衡不同,《决定》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放在优先位置。这一调整深刻地体现了即便牺牲一定经济利益也要维护饮食安全的决心,但为防止对相关产业及个体自由和法治权威造成伤害,禁止食用之“野生动物”仍宜明确在合适的范围。
1.不宜将人工养殖动物作为“野生”动物看待
(1)人工养殖动物已摆脱野外繁殖生长状态,应属于“家养”而非“野生”动物。将人工养殖动物列为禁止食用对象,将使“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名不副实,而成为“禁止食用陆生脊椎动物”,不仅严重损害野生动物概念的确定性,而且牺牲法律应有的严谨性。
(2)人工养殖动物的食用安全性有较高保障。生物学研究已经表明,人工繁殖饲养的动物长期与人共处,已与人形成共享的生态圈。“某种程度上,人类与狗、其他家畜的微生物库已经融为一体。狗在‘前家畜’时代携带的有可能传染给人类的微生物,在驯养活动后大部分已经进入人体了。而人类所携带微生物中能够在狗身上存活的,也都传染给狗了。没有成功传染给对方的微生物可能是受其能力所限。它们也许偶尔传染一两个个体,但却缺乏传播能力。”③[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家养动物虽然经常将致病微生物输送给人类,但其只是作为中间宿主扮演了致病微生物从野生动物传播到人类桥梁的角色。④因此,对于家养动物最应做的是通过规范养殖行为净化养殖环境,如减少野外接触,禁止滥用抗生素等,达到饮食安全的目的,而非禁止食用。
(3)禁止食用人工养殖动物将严重打击养殖产业。我国有悠久的养殖驯养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发展养殖业作为促进农业结构优化、破解农村发展难题的重要手段,国家和地方先后出台了系列文件支持畜牧业发展。⑤在中央层面,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在地方层面,河南、江西等多数省份均出台了本地关于大力发展畜牧业的决定。其中,经济价值高的特种养殖一直被寄予厚望。在一些地方,特种养殖俨然成为支柱产业,成为农民摆脱贫困之有效手段。一律禁止食用不仅将严重打击养殖业,而且可能使数量众多的从业农民丧失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人工养殖技术在挽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领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得益于人工养殖技术之突破,梅花鹿、麝、林蛙等种群才得以稳定。有些动物的主要价值就在于食用,将其列入禁止食用的范围,无异于釜底抽薪,将使养殖人彻底失去探索人工养殖技术的动力。
2.不同安全性的野生陆生脊椎动物宜分类施策
生物学研究业已证明,微生物跨物种传播遵循分类传播原则。①美国著名科普作家内森·沃尔夫在其名作《病毒来袭》中对于微生物跨物种传播的分类传播原则作了详细介绍。作为哈佛大学免疫学和传染病学博士,斯坦福大学人类生物学专业客座教授,内森·沃尔夫的著作向以专业严谨闻名。亲缘关系越近,微生物跨物种成功流动的可能性越大。②[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近亲物种由于存在相似的免疫系统、生理机能、细胞类型和行为,易受同样的感染源侵害。对人类而言,食用安全性以非脊椎动物为最高,水生动物高于两栖类动物和陆生动物,两栖动物高于陆生动物。在陆生动物中,冷血动物高于温血动物;在温血动物中,爬行动物高于哺乳动物。这也是尽管蛇的食用屡被攻击可致寄生虫病传播③参见刘树贤:《自然疫源性疾病基本概念》,《医学动物防制》1985年第12期;许炽熛:《食源性寄生虫病的防治》,《传染病信息》2007年第1期。,但迄今无任何危害严重的传染病确证源自蛇类的原因。而哺乳动物的安全性最低,哺乳动物中翼目类的蝙蝠携带的人畜共患病毒最多,其次是灵长类和啮齿类动物。④See Kevin J.Olival,Parviez R.Hosseini,Carlos Zambrana-Torrelio et al,Host and viral traitspredict zoonotic spillover from mammals,Nature,Published online 21 June 2017,doi:10.1038/nature22975.“用以下提及的每个动物群落所引发的人类主要疾病数,除以该群落物种数,我们获得了一个比率,来表达每一组动物群落在传染人类疾病方面的重要程度。数字令人印象深刻:猿类是0.2,其他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是0.017,非灵长类的哺乳动物是0.003,非脊椎动物的数值接近零。”⑤同注②,第58页。表2的统计清晰地显示,猩猩、猴、蝙蝠和鼠等哺乳动物扮演了传播致病微生物主力的角色。⑥蝙蝠和老鼠之所以成为致病微生物的重要宿主,除了其与人类同为哺乳类动物,具有相似的生物基因外,或许还与其潮湿阴暗的生存环境及活动能力极强的生物习性存在较大关联。在近年影响广泛的20种人畜共患疾病中,确定或疑似的自然宿主为哺乳动物者达17种,其中灵长类4种、翼目类7种、啮齿类3种,其他哺乳动物3种。

表2 近年影响广泛的人畜共患疾病的动物宿主

朊病毒病(疯牛病、羊瘙痒症、人的克雅氏病等)不明(疑似为羊、牛等病畜)哺乳动物寨卡病毒不明(疑似为猴子等灵长类动物)灵长类哺乳动物蚊子炭疽病食草性野生动物哺乳动物牛、马、羊等家畜新冠病毒肺炎不明(疑似为蝙蝠)翼目类哺乳动物不明西尼罗河热鸟卵生动物蚊子H5N1、H7N9水禽卵生动物鸡H1N1鸟类卵生动物猪MERS蝙蝠翼目类哺乳动物骆驼SARS中华菊头蝠翼目类哺乳动物果子狸
分类传播原则为分类施策提供了依据。甄别不同动物的安全性差异分类施策,更能达到均衡利用与安全法益的目的。从比较法看,在野生动物食用问题上分类施策也已成为主流。①比如,按照德国《捕猎法》的规定,法定大中型哺乳动物可以作为狩猎对象。猎人不仅是野生动物捕猎者,还是野生动物肉品的交易者和销售者;日本《鸟兽保护、管理和规范狩猎法》将野生鸟兽分为稀少鸟兽、指定管理鸟兽、狩猎鸟兽以及一般鸟兽,对前三者指定名录,实施差别化保护和管理;而美国则实施野生动物狩猎许可证制度,并制定濒危物种名录,禁止对于濒危物种进行狩猎。参见刘黄浦:《德国野生动物捕猎宰杀规范及其借鉴》,《铁道警察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刘兰秋:《日本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及启示》,《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3期;王昱、李媛辉:《美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制度探析》,《环境保护》2015年第2期。
第一,完全斩断物种之间的微生物交流不具有客观可能性。微生物间跨物种交流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其既不依人之意志而存在,又具有一定的客观必要性。微生物交流既带来病毒,亦创造了生命。②参见[美]卡尔·齐默:《病毒星球》,刘旸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6-148页。人类减少生物接触的自我净化之路导致病毒抵抗能力降低,已为科学所证明。③参见[美]内森·沃尔夫:《病毒来袭》,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62页。危害程度不高情况下的微生物跨物种交流,对人类是有益的。因此,在确有必要,安全性有保障又不危及动物物种的情况下,对动物的合理利用至少不应被全部禁止。
第二,野生动物因与人类亲缘关系各不相同,微生物跨物种传播的风险也不一样。亲缘关系较远、生活环境单纯的非疫源性动物即便偶有致病传播情况发生,烈度和规模也处于可控状态,相对于其利用价值成本低廉。在生物科学支持下,依据传播致病微生物的危险性程度列出疫源性动物和食源性动物清单,分类施策,严厉禁止食用疫源性动物而放开食源性动物的食用,显然更具针对性,也更有利于产业发展。此时,从严控制食用野生动物可以通过降低疫源性动物标准,扩大疫源性动物种类的方式实现,且更为灵活,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动态调整。
第三,禁止食用安全性较高的动物,存在必要性欠缺问题。当面临公共卫生事件重大威胁之时,出于公众健康目的,采取存疑从有原则④参见王岳:《论我国传染病疫情防控法律原则之完善》,《法律适用》2020年第5期。,通过克减公民权利维护公共安全⑤参见王晨光:《法治思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运用》,《法律适用》2020年第2期。,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具有充分的正当性。但权利克减和限制,以存在威胁国家安全的紧急状态和真实存在为前提,且存在一定的监督机制⑥参见滕宏庆:《论人权克减及其监督机制》,《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只能为了实现人的安全而实施有限的人权克减。⑦参见谢海燕:《人的安全视野下人权克减的正当性研究》,《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当前,我国列入畜禽遗传保护动物名录的种类非常少,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仅有猪、鸡、鸭、鹅、牛马驼、羊等大类之下159个品种,火鸡、鸵鸟、鸽、兔等都不在名录之列。⑧参见农业农村部:《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当公共安全处于可控状态后,将大量安全性较高的陆生脊椎动物列入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范围,存在不必要克减公民饮食选择权利的可能性。
3.安全性较高的两栖类脊椎动物不宜作为禁止食用对象
两栖类动物多在水中生育,水陆两地成长,属于水生到陆生过渡的状态。动物学界一般将其作为最原始的陆生脊椎动物而归入陆生动物范畴。①参见张文慧、高金伟等:《中国两栖类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探讨》,《天津农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目前,我国已知两栖动物398种,分隶64属11科3目②参见姚明灿:《中国两栖动物地理分布格局研究》,中南林业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其中不乏鳖、蛙等常用于食用的动物。一方面,从其卵生幼体只能生活在水中,繁殖和幼体发育离不开水,成年后虽可在陆地生活但多只可生活于湿润的陆地来看,这些动物对于水的依赖较之陆地要多;另一方面,其亲缘与人类关系遥远,所携带之微生物形态亦更具水生动物特征,导致致病微生物传播之风险极低。其食用宜比照水生脊椎动物对待。
三、“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协同规制
我国现行与“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相关的法律及法律性文件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生物安全法》《传染病防治法》《动物防疫法》及相关条例等,现均已实施。为全面落实《决定》精神,防止法律之间的抵牾,我国已启动“打包修法”的多法律一揽子修改,目前已完成《生物安全法》和《动物防疫法》的修订。这一路径无疑具有合适性③参见张文显:《依法治疫长治久安》,《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2期。,但在立法目的、基本法律选择等问题上,仍存在不少似是而非之处。
(一)应确立“人之生命安全”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二元统摄、各有侧重的立法目的
如前所述,“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之立法目的可整合为两个:一是“人之生命安全”;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关法律应在这两个立法目的中选择并有所侧重。
1.《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条例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立法目的
长期以来,公众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只保护珍贵濒危动物颇有微词。主张《野生动物保护法》增加“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立法目的④参见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课题组:《关于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吕忠梅、陈真亮:《〈野生动物保护法〉再修订:背景、争点与建议》,《生物多样性》2020年第5期。,将所有野生动物纳入保护范围的呼声不断。⑤参见宋蕾、秦天宝:《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制之完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李洪雷、戴杕:《我国野生动物立法的检视与完善》,《浙江学刊》2020年第3期。然而,法律保护的背后是国家财力的付出和自由受限。国家权力以社会财富为本源⑥参见朱孔武:《征税权、纳税人权利与代议政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1-43页。,动用公共资源保护所有野生动物违反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若均予保护将出现老鼠、蚊蝇也受保护的荒谬结果。当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直接关联时,野生动物不过是众多社会资源的一种,应任其自生自灭。唯在具有保护价值时,始有动用国家公器之必要。此种价值,一是物种处于濒危状态,若不保护将损害生物多样性;二是物种具有社会、生态和科研价值,若不保护将使社会、生态和科研价值受损。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法》以珍贵濒危动物为保护对象并无问题。
若《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为立法目的,则将带来下述问题:其一,导致立法视角由野生动物向人类中心回归,不仅达不到多元生态伦理目的,反而会导致伦理理论的倒退;其二,将混淆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卫生法之差异,模糊卫生法与野生动物保护法之边界,伤及法律之科学性;其三,尤应明确的是,食用仅是野生动物利用的一种而非全部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至为复杂,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动物驯化和利用的历史。即便对野生动物食用采取全面禁止的态度,也不意味着对于加工、使用等其他形式的利用行为持排斥态度。这些利用行为与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并无必然联系,若以“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为立法目的,则势必将食用以外的大量野生动物利用行为排除在外。
为体现对于公共安全的兼顾,《野生动物保护法》可在总则加入倡导安全饮食和文明饮食的内容,但可以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立法目的演绎而来。当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一是维护生态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二是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体现。因此,可以统合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立法目的。
2.《生物安全法》应以“人之生命安全”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双重目标为立法目的
生物安全最初仅在生物技术的角度使用,以后不断发展。时至今日,已形成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①参见刘长秋:《生物经济发展视野下的生物安全问题及其立法对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5期。狭义的生物安全仍未超出生物技术安全的范围,广义的生物安全则已扩展至人类不当活动干扰、侵害、损害、威胁生物种群正常发展而引起的问题,包括生物、生态系统、人体健康和公私财产受到污染、破坏、损害等广泛问题。②参见蔡守秋:《论生物安全法》,《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我国《生物安全法》确立了其生物安全领域的综合性、基础性法律的定位。从其作为生物安全基本法、一般法的视角来看,《生物安全法》无疑采用了广义生物安全的概念。广义生物安全的内涵虽然包罗万象,但基本可以归结于人类自身的生命安全和动植物物种安全两个方面。前者属于“人之生命安全”,后者属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物安全法》清晰地反映了这两个立法目的。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和应对生物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保护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定本法。”
3.《动物防疫法》和《传染病防治法》应以“人之生命安全”为立法目的
《动物防疫法》和《传染病防治法》作为疫病和传染病方面的基础法律,无论是预防、控制和消除动物疫病、人畜共患病还是人类传染病,均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维护公共安全。两者同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为目标。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不是其考虑的问题。
(二)宜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多法律协同规制
1.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基本法律的思路应予摒弃
由于滥食野生动物之危害尽人皆知,故每有重大公共疫情产生,则必有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打击滥食陋习的呼声。④相关观点参见阮向东、高明福:《滥食野生动物之立法思考》,《林业资源管理》2014年第3期;常纪文、常杰中:《科学准确建立禁食野生动物清单》,《中国环境报》2020年2月10日第3版;朱忠保:《依法禁食野生动物正当其时》,《人民法院报》2020年2月15日第2版;毛涛:《全链条管控食用野生动物行为》,《中国环境报》2020年2月6日第3版。在公众视野中,《野生动物保护法》俨然担负着维护食用安全,重构饮食伦理的最直接责任。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委员长会议提出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基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确立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制度,及自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地纷纷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修订工作来看⑤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2020年2-3月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改专项调研的省市就不下20个。广东、福建等省相继出台《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立法部门显然也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在维护食用安全方面责无旁贷。
然而,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作为规范野生动物食用行为的基本法律混淆了其立法目的,将对现行法律体系造成破坏,应予摒弃。(1)《野生动物保护法》以野生动物具有保护必要为基础。将《野生动物保护法》作为规范野生动物食用行为的基本法律,是基于食用行为将危及物种安全的假设。但在种群数量正常、并非处于濒危的情况下,这一假设并不存在。(2)任何法律保护举措均意味着立法、执法和公共资源的投入,及利益关联人权利的克减,故对保护对象有必要性要求。《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持物种多样性,其对动物加以保护的前提是物种面临威胁,如不予以保护将濒临灭绝,或造成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严重损失。而珍贵、濒危即为动物具有保护价值之标准,这与饮食安全并无直接联系。将《野生动物保护法》作为规范“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主体法律,将打破法律之间固有的分工,改变井然有序的法秩序,损害法律体系的科学性。(3)虽然出于维护饮食安全而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客观上也会导致野生动物获得保护之后果,但此种附带性后果与基于专门立法目的的针对性保护不可同日而语。(4)目前,真正进入食用环节的“野生动物”,绝大多数是养殖动物披上“野生”之名,这已超出野生动物范围。若仍将其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制对象,结果是严重的名实不副。
2.以《生物安全法》作为规范“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基本法律具有该当性
第一,在以《生物安全法》为生物安全领域基本法律的情况下,“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立法目标可以为《生物安全法》所包容。食用系动物利用之一种,滥食野生动物引发的人类健康和生物物种危机,均可归结于生物安全危机。“人之生命安全”理属生物安全当然之义。通过保持生物多样性,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同样属于生物安全范畴。
第二,将“人之生命安全”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融入生物安全之中,有利于从物种安全高度统筹规划,系统解决饮食安全和重构饮食伦理问题,既目标明确,又不会产生冲突和抵牾。
第三,从立法成本上来说,以《生物安全法》作为基础法律,亦优于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为基础法律的方案。《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定于1988年,配套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制定于1992年,虽经多次修改,但在基本原则、保护范围和手段等重要问题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于2016年底修订完成,仅经历3-4年左右的时间又要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过于频密,对已形成的法秩序亦是冲击。相反,《生物安全法》属全新立法,不存在冲击既有法秩序的风险。利用制定《生物安全法》之机,全面实现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立法目标,能够有效节省立法成本。
我国《生物安全法》分专章规定了防控重大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的举措,建立了包括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疫病信息采集、报告制度和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等一系列制度。该法第32条规定:“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加强动物防疫,防止动物源性传染病传播。”可见,《生物安全法》虽然没有直接规范野生动物食用行为,但从更高层面为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提供了法律依据,事实上充当了“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主体法律的作用。笔者认为,此种立法安排说明,立法者已认识到《生物安全法》在规范野生动物利用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是妥当的立法选择,不仅逻辑上合适,而且有利于厘清当前存在的理论误区。
3.契合不同法律特点、多法律协同的具体规制
(1)《传染病防治法》和《动物防疫法》宜重点规范疫源性动物食用行为。《传染病防治法》作为防控传染病的基础法律,可在如下方面对野生动物食用行为作出规范:一是在国家开展预防传染病健康教育条款中加入健康饮食教育的内容;二是确立未列入食用类型及未经证明安全性之野生动物不得食用原则;三是确立疫源性动物概念。在规范“与人畜共患传染病有关的动物之检验检疫”后,加入“国家建立疫源性动物清单,凡列入疫源性动物名单之中的动物,一律禁止食用”的内容,并明确违法食用疫源性动物致传染病传播的法律责任。①之所以只建议规定违法食用疫源性动物致传染病传播的责任,主要是考虑《传染病防治法》的性质、执法成本和传统习惯。我国长期有食用野生动物的传统,民众食用之野生动物很多虽无直接安全性证据,却已一定程度上得到实践证明。在民众习惯短期内难以改变、致传染病危险性不高及客观上没有导致传染病发生的情况下,若规定过于明确的责任,可能陷入违法者众而只能选择性执法的泥潭。
《动物防疫法》所指动物主要是家禽家畜和人工饲养、捕获的动物。不过,在合法捕获的野外和人工养殖陆生脊椎动物方面,与《决定》的禁食对象存在重叠。《动物防疫法》可从如下方面规范野生动物食用行为:一是将“防控人畜共患传染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作为立法目的。二是在《传染病防治法》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疫源性动物界定标准。可将疫源性动物界定为,经实践和科学证明易于造成传染性疾病的动物。其判定遵循三方面标准:首先是亲缘性标准,与人类亲缘关系近,易致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动物,如猩猩、猴等;其次是生存环境标准,在阴暗潮湿的恶劣环境中生长,易携带和传播致病微生物的动物,如蝙蝠、鼠等;再次是实践性标准,具有引发致病微生物跨物种传播较多经历的野生动物,如蝙蝠、猴等,除传统家畜之外,一律列为疫源性动物。②2021年1月22日修订的《动物防疫法》仍沿袭了只规定人畜共患传染病病种的做法,以笔者之见,这应该是一个立法遗憾。三是从防疫角度对于野生动物利用行为作出规范。食用是利用之一种,利用野生动物必须经过检验检疫,检疫合格方可利用。四是明确违法利用疫源性动物的法律责任。③此责任系单纯利用疫源性动物的责任,不以造成损害传染病传播后果为要件,故不同于《传染病防治法》上违法利用疫源性动物致传染病传播的责任。对于违法利用行为可以给予一定幅度的罚款;对于屡次非法利用疫源性动物,或利用疫源性动物引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严重后果的,除处罚款外,还可给予行政拘留;情节特别严重造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2)《野生动物保护法》重点规范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食用行为。其可在总则中确立“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原则”,对接《决定》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立法目的。尤需强调的是,保护珍贵濒危动物并非绝对排斥食用行为。有些受保护的濒危稀有动物,比如梅花鹿、新疆大头鱼等,野外种群稀少,人工养殖对种群存续意义重大且主要价值就是食用。若禁止食用不仅直接打击通过人工养殖扩大濒危生物种群的努力,还会加速物种灭绝。从可操作性来说,要求仅因数量稀少而进入保护名单的食源性动物之饲养人,将本可作为安全食材的动物躯体作为废弃物抛弃,不仅增大无害化处理成本,也根本不具操作性。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宜一概禁止食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应原则禁止,例外允许。换言之,我国实践中形成之依据人工养殖状况制定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并允其销售和利用的做法仍应坚持,但应根据新情况作出适当变化。不只聚焦于经济利用,更应着重于食用之生态后果。具体而言,应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基础上,依据种群情况及物种存续对人工养殖的依赖程度建立可食用珍稀动物名录,将野外种群稀少、物种存续与人工养殖依存度高、价值主要在于食用的动物列入可食用珍稀动物名录。凡未列入名录的珍贵濒危动物一律禁止食用。
(3)《畜牧法》重点规范畜禽遗传资源标准和程序。由于列入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的动物不在禁止食用之列,因此,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事实上发挥着通过动态调整实现分类施策的功能。为落实《决定》精神与弥补其缺陷,《畜牧法》既要严守安全性标准,又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充分发挥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在酌定畜禽遗传名录中的作用之同时,严防各地利用酌定畜禽遗传资源之机为滥食野生动物打开方便之门。具体而言,《畜牧法》可作如下具体规定:1)明确畜禽遗传资源酌定标准。畜禽遗传资源应满足三方面的条件:其一,安全性。此种安全性或者已为科学所证实,或者具有长久饮食传统,已为实践所证明。其二,传统性。该动物具有较长食用传统,其食用已成为饮食文化的内在部分,承载着民族之饮食传承和记忆。其三,经济性。该动物具有较大经济价值,其养殖已形成产业,相关从业人员众多。2)严格规范省级主管部门认定畜禽遗传资源的程序。省级主管部门确定和变动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应有不少于一个月的公示期。对于公示期间存在异议或群众反映较大的,应举行听证。新增畜禽遗传资源的,应经本地区遗传资源委员会鉴定,且书面征询疾病控制部门与动物检验检疫部门的意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进行鉴定时,鉴定专家中须有适当比例的生物医学与法律领域的专家,且生物医学专家不得少于2名;专家论证采取双重多数原则,既需专家组全体过半数同意,又要生物医学专家过半数同意;鉴定专家需实名出具鉴定意见;拟新增为畜禽遗传资源的动物物种,需报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备案;被否决的动物物种,除非有新的安全性证据,在2年内不得成为畜禽遗传资源新增审议对象。在一地被否决的动物物种,除非有新的安全性证据,在1年内不得成为其他地方新增畜禽遗传资源的审议对象。
(三)在坚守生态安全基础上,多法益兼顾地确定禁止食用之野生动物范围
历史经验表明,在存在多种法益情况下,锚定单一法益的立法安排,不仅法律成本过高,而且会产生顾此失彼的现实难题。因此,即便以一般条款的形式在重大法益之间作出选择,也会以其他形式进行补益,以回应复杂社会的现实需要。在这一点上,成文民法国家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之立法与实践就是鲜明的例子。出于受害者保护的需要,《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对民事权益采取开放式保护方式,任何民事权益,无论是民事权利还是民事法益,只要遭受损害,均可循此主张赔偿。由于保护范围过于广泛,由此引发限制行为自由、滥诉等诸多风险。于是采取法条竞合说优先适用合同责任,通过严格适用侵权责任构成等方式减少责任风险,以达致法益平衡目的。①参见鲁晓明:《论利益损害赔偿责任中的风险控制》,《法商研究》2012年第4期。与之相反,基于限制责任风险之考虑,《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仅将绝对权作为损害赔偿范围,而将民事法益排除在外,由此引发受害人保护不足的问题。在接连发生俾斯麦遗像案①二名记者偷偷进入存放俾斯麦遗体的教堂拍下其遗体照片,死者家属以人格权遭受侵害为由起诉,法院仅能通过适用不当得利的方式有限维护受害者遗属利益。See Vgl.RGZ45,170.、读者来信案②D公司在其周刊上发表一篇题为“Dr.Hjalmar Schacht和他的公司”,副标题为“值此Schacht银行建立之际的政治观察”的文章,称Dr.Schacht利用担任帝国要职的关系和在二战的影响力。M律师受Dr.Schacht之托致信D公司要求予以更正。D公司将律师函删减后登载于“读者来信”栏目,原告认为被告删减发表其律师函的形式侵害了其人格权。联邦德国高等法院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及《民法典》第823条1款后段,认为被告侵害了原告人格权。一般认为,这是德国司法界第一次承认一般人格权。See Karl Larenz,Das“allgemeine Persoenlichkeitsrecht”,im Recht der unerlaubten Handlungen,NJW 1955,pp.521-524.等明显于受害人不公的案件以后,乃通过特别法,扩容“其他权利”。索拉娅案③被告虚构原告接受采访的事实刊载有关原告的私生活报道,原告以侵害一般人格权为由主张15 000马克赔偿,法院支持了原告的主张。参见[德]提尔曼·雷普根著,胡剑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索拉娅案”:“创造性法律发现”的经典教案》,《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骑士案④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8页。等案件的判决使一般人格权、营业权等民事利益披上“权利”外衣⑤参见冉客平:《一般人格权理论的反思与我国人格权立法》,《法学》2009年第8期。,创造缔约过失责任⑥缔约过失责任由德国法学家耶林提出,目的是使尚没有形成合同关系的缔约人处于过错规则的保护之下。参见李昊:《德国缔约过失责任的成文化》,《清华法学》2010年第2期。、附保护第三人合同⑦附保护第三人合同理论系德国司法独创的一种理论,目的是使合同打破相对性规则限制,起到保护与合同当事人存在特定关系的第三人之作用。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2-595页。、附随义务、积极侵害债权⑧该理论由律师施道波于1902年在其论文《积极的损害合同及其法律后果》中提出,旨在给予加害给付的受害人以救济。参见齐晓琨:《德国新、旧债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8页。等众多理论。不断扩展的损害赔偿范围,达到了加强受害人保护之目的。⑨参见鲁晓明:《权利外利益损害的赔偿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7-104页。受上述立法例影响的其他国家,均采取了相似做法。
即便主张对动物实施普遍保护的学者也认为,在普遍保护模式下,仍需对各类野生动物进行区分,并根据野生动物生态功能和种群现状进行差异化保护,不能一概追求禁止利用野生动物。⑩参见冯子轩:《生态伦理视阈中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完善之道》,《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在遵循全面禁止食用总原则的基础上,还应在坚守生态安全基础上统筹兼顾,合理平衡,分类施策⑪参见杨朝霞:《关于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修法建议》,《中国生态文明》2020年第1期。,使对公民权利之限制符合比例原则,通过逐步增加可食用动物类型,达到均衡法益的目的。具体而言,可通过下述途径扩展可食用动物类型。
第一,充分利用相关部门在制定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上的酌定功能,在严格安全性评估基础上动态把握野生动物类型。人工养殖时间长、技术成熟,已形成饮食传统,产值较大,在脱贫攻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动物,比如鸽、兔、梅花鹿等,禁止食用不会于饮食安全有太多增益;相反,允许食用有利于实现多方利益平衡,应充分利用相关主管部门的酌定权利,将其列入畜禽遗传资源名录,作为家养动物而非野生动物看待。如前所述,为防止有关部门滥用畜禽遗传资源酌定功能形成新的安全风险,此种动态酌定的权力应限定于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对于省级有关部门的酌定权力则应严格限制。
第二,逐步限制“野生动物”概念的扩大适用,使之回归“野外生长繁育动物”之本来语境。人工养殖动物由于与人长期共处,微生物库已实现人畜混同,其食用安全性与野生动物已存在根本差异,禁止其食用更多出于对“人工”与“野生”难以区分、允其食用易给不法利用可乘之机的担忧。然而,一方面,动物生存状态之甄别和区分是一个执法问题,应通过提高执法水平实现,因存在执法难题而累及无辜即便于事急从权的特殊时期可以理解,在社会步入正轨之后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养殖动物都会陷入“人工”“野生”难以区分的窘境,对于野外种群已较为稀少及野生与养殖动物在外观上存在明显差异的动物而言,这一担忧并不存在,即便基于执法性担忧也应将这部分动物排除。将人工养殖动物归入家养动物,并不会降低饮食安全性要求,且既能够实现野生动物概念的实至名归,又不至于过度克减公民饮食的选择权利。
第三,以分类传播理论为基础,辅以动物生存环境衡量,针对不同动物之安全性分类施策。既然物种亲缘关系对于微生物跨物种传播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动物生存环境与所携带致病微生物情况存在直接关联,则是否禁止食用理当以这两个指标为考量基础。与人类亲缘关系较远、具有食用传统的动物引发失控性传染病的可能性较小,其安全性已得到实践证明,食用应逐步放开。按照安全性由高到低的原则,冷血陆生脊椎动物之食用安全性最高,其次为具有食用传统之温血爬行类动物,这两类动物之食用宜有序放开。①目前,部分爬行类动物(比如乌龟和鳄鱼)的食用限制事实上已经放开,只不过这些动物均被名不正言不顺地放在水生动物之中而已。参见《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而安全性未经实践证明的哺乳类动物则应严格禁止食用。以易于滋生致病微生物环境(如垃圾或黑臭水体)为主要栖息地的动物种类,即便属冷血或爬行动物类型,也应禁止食用。为免与《决议》产生过大差异和冲突,此举措可以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稳妥推进。
第四,对于允许食用的野生动物,建立野生动物食用安全制度。可借鉴比较法上的做法,规定国家基于最新研究制定野生动物利用指南的责任②日本参议院环境委员会在2014年修改《鸟首法》的附带决议中明确指出:“国家应基于最新知识制作指南,同时支持各都道府县制作手册,以彻底的卫生管理措施确保食用安全性。”,确定野生动物利用的专门机构,颁发交易证书,监管交易行为③德国《捕猎法》第36条规定,各州可以确定具体机构,负责监测野生动物肉品的贩卖、购买、交易以及加工,并监管野生动物交易证书的使用。,在交易的野生动物身上强制贴上“野生动物”标签并借鉴《烟草专卖法》的做法,注明野生动物食用风险。④德国勃兰登堡州《野生动物交易的监管和控制条例》规定,猎人宰杀野生动物后,应立即附上“野生动物标签”。之所以要注明食用野生动物风险,是由于我国民间存在追逐食用野生动物的不合理风俗。单纯标注“野生动物”反而可能引发对于“野生动物”的病态追逐。
第五,通过扩张解释、目的解释,将水生动物范围扩张至可食用两栖脊椎动物。既然“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之法目的乃在于维护饮食及生态安全,而两栖脊椎动物具有较高安全性,且通常仅鳖、大鲵等有限类型的两栖脊椎动物具有食用传统,克减公民两栖动物之饮食选择权自无必要。此时,从法规目的出发,遵循我国将可食用两栖动物解释为水生动物之既有传统⑤在《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中,鳖、大鲵等两栖动物赫然在列。,将水生动物范围扩张至可食用两栖动物,既不致与《决定》相冲突,又能合理解决两栖脊椎动物之食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