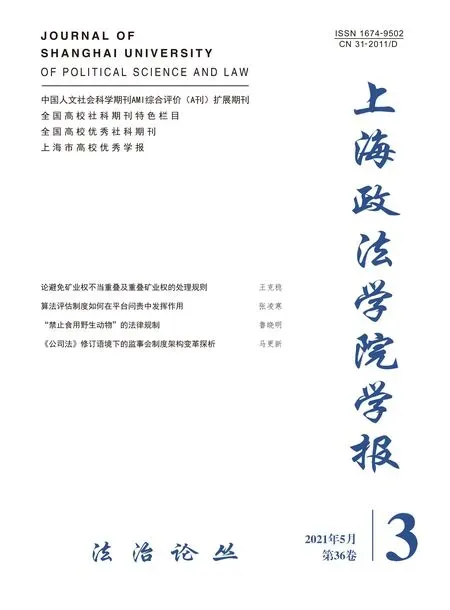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司法续造
傅 穹 虞雅曌
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实践中,控制股东虚假出资、操纵发行价格、进行内幕交易、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公司利益、侵占资金、违规担保等事件频频发生。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2020年度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十大纪律处分案例》为例①参见《2020年度上交所上市公司监管十大纪律处分案例》,https://mp.weixin.qq.com/s/LBGl2bc89PnqE_tiFSS57Q,载微信公众号“上交所发布”,2021年2月5日访问。,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涉及大额资金占用、公司违规担保、重大信批违规等行为,被施以纪律处分的案例,即占据三席。②三个案例分别为:“*ST鹏起:实际控制人占用资金,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案”(纪律处分决定书[2020]83号),“退市美都:违规为实际控制人提供巨额担保案”(纪律处分决定书[2020]77号),“*ST目药:实际控制人多次实施重大信批违规行为,公司内控严重失序案”(纪律处分决定书[2020]124号)。在我国有限公司的治理实践中,以“拒绝利润分配”“侵占公司财产”“夺取商业机会”“违规清算”“滥用表决权”途径,损害公司利益和非控制股东利益的滥用控制权行为,更为常见。可见,“作为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是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矛盾”①参见赵旭东:《公司治理中的控股股东及其法律规制》,《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了禁止股东滥用权利的原则性兜底条款,然而,该条款的抽象性与认定标准的缺失,驱使众多学者提出了引入美国判例法中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规则的主张。②参见朱大明:《美国公司法视角下的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本义与移植的可行性》,《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5期。控制股东的内涵界定与信义义务的引入固然重要③参见王建文:《论我国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1期。,但是,从程序公正与实质公平来判断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才可能最终弥补《公司法》第20条之法律适用的不足。本文从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合理性之争入手,经由观察美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司法审查标准,承认股东控制权的合理行使,针对我国控制股东滥用的司法实践,尝试搭建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规制路径。
一、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立法移植之争
在股权结构集中的我国,控制股东得以凭借其表决权优势或协议控制等方式,从法律层面或经营层面控制股东会④参见朱慈蕴:《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无论是经由股东会或董事会,公司经营均在控制股东的掌控之中。然而,除了《公司法》关于禁止股东滥用权利与董事信义义务的条款之外,能否将董事信义义务的约束扩张至控制股东之上?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立法移植,一直存在反对说与肯定说之争。
反对说认为,我国公司法不宜直接移植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继续完善禁止股东滥用权利条款,足以承担替代功能。道理在于:其一,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与传统公司法理论相冲突。所谓信义义务,源于信义关系,本质是一种利他义务。⑤参见范世乾:《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行为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控制股东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除此之外,无须对公司或其他股东承担出资以外的其他义务,更无须以他人利益为目的行事。其二,“股权平等原则”乃是公司法的基础性原则。在实施一股一权的公司假定场景下,按股东持股的多寡决定权利大小,进行股权配置,具有天然的经济合理性,控制股东基于持股量形成的控制权有其合理性,若对其施加信义义务,“将形成对有产者的歧视,进而损害整体公司秩序”⑥参见甘培忠:《公司控制权的正当行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其三,公司具有独立人格。控制股东并非直接参与公司经营,股东之间也无直接联系,股东意志均通过公司意思机关表达,若使股东承担信义义务,将无视公司独立人格⑦参见周淳、肖宇:《封闭公司控股股东对小股东信义义务的重新审视——以控股股东义务指向与边界为视角》,《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1期。,损害整体公司秩序。其四,从比较法观察,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判断规则存在分歧,事实上相关规则并未形成共识。例如,在美国封闭公司中,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安排,是股东压迫规则缺失的替代性需求。⑧See Robert B.Thompson,the Shareholder’s Cause of Action for Oppression,48 Business Law 609(1993).伴随信义法的发展热潮,美国司法相继引用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但是,在整个美国法律体系内,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判断规则并未统一形成。在实践中,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已实际成为包容所有诉讼请求的兜底性规则。这一结果,既混淆了信义义务的本来面貌,更导致了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肆意滥用①参见范世乾:《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行为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因此,无法成为我国移植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参考规则。其五,域内制度供给不足。美国各州主要以判例法方式确立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规则,而中国法律遵循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传统。美国判例法中的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并非独立存在的规则,还需有配套规则作为补充,如用以判断股东行为的合理期待原则、商业判断规则或实质公平原则。我国作为以成文法为传统的国家,贸然引进这一系列判例法规则,或许难以发挥制度移植的初衷。
笔者赞同支持说的主张,未来立法有必要移植控制股东信义义务。道理在于:其一,矫正控制股东滥权行为。控制股东因其所占多数股权而享有对公司的控制权,其可出于正当目的行使控制权,但若滥用控制权,则应对其予以限制,信义义务最核心的正当性则在于弥补控制权滥用所带来的损害。②See Tamar Frankel,Fiduciary Law,71California Law Review 795(1983).其二,权责相一致原理之所需。公司正义的基本目标要求股东权责一致,股东享有与其持股份额相应的股东权利,则应承担与其持股份额相应的责任,当控制股东因持有多数股而享有对公司的控制权时,其实际享有了类似于权力的“绝对权利”,此时为避免控制股东滥用权利,则需对其施加与控制权相对应的信义义务。其三,对弱势股东强制性救济的制度需求。控制股东与公司、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③参见王建文:《论我国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1期。,当控制股东实际控制公司,因其“理性经济人自利本性,靠其自觉守约绝不可期”④参见傅穹、王志鹏:《公司控制权滥用规制的法理基础与司法判断》,《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5期。,为使公司或中小股东免受不正当剥削,应使控制股东承担信义义务。其四,弥补标准合同文本缝隙。根据不完全合同理论,公司是公司成员所订立契约的集合,公司法向公司成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标准合同文本。⑤参见[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罗培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公司通过一系列关系契约持续存在,在持续过程中,必将发生标准文本无法预见的偶发性事件⑥同注⑤,第90页。,当控制股东行使控制权,则将产生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分歧与利益损害问题,若通过在两者间约定更加明确细致的合同条款,或额外监督控制股东行使控制权,将产生高昂成本。因此,出于效益考虑,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以阻吓作用替代了事先监督”,将更具效率。
二、美国司法裁判中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演进
在美国,最初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司法认定,是以马萨诸塞州为代表的裁判,其认为,股东信义义务仅适用于封闭公司,且所有股东均为义务主体,不对控制股东或中小股东进行区分;特拉华州法院则认为,股东信义义务适用于所有公司类型,且仅由控制股东承担信义义务。就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演进而言,美国经历了一个从适用于封闭公司到扩张至所有类型公司的过程,从信义义务的内涵解释到标准认定的个案审查过程,从关注形式审查到偏向实质公平认知过程。上述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司法续造,对我国公司治理中的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改革与司法解释,均具有借鉴价值。
(一)美国关于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经典判例
在美国,控制股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获取控制权私益,即一般经营行为与逐出式合并。①See Ronald J.Gilson、Jeffery N.Gordon,Doctrines and Markets:Controlling Controlling Shareholder,152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785(2003).一般经营行为指,控制股东获取与其股份份额不成比例之利益,以此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包括“掏空”、关联交易等行为。逐出式合并指,控制股东在公司合并时,以不公平价格强制驱逐中小股东的行为。针对控制股东的一般经营行为,因其仅影响其他股东的投资利益,属于公司商业判断范畴,法院仅作形式审查,不作实质判断;对于控制股东的逐出式合并行为,往往直接导致其他股东身份丧失,涉及股东身份利益,对此种行为,法院则以实质公平规则进行实质审查。②参见汤欣:《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收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笔者以美国特拉华州最高法院的四个相关裁判为样本,分析特拉华州法院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裁判的基本理念与裁判思路。案1为1971年Sinclair Oil Corp.v.Levine案,开启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程序审查的“门槛规则”(the threshold test)。③See Sinclair Oil Corp.v.Levine,280 A.2d 720(Del.1971).所谓门槛规则,是指法院需先行审查被诉控制股东是否实施了自我交易,是否存在以排斥方式,损害中小股东以牟取私利。若控制股东未实施自我交易,则以商业判断规则审查其行为,反之,则以实质公平规则做最终审查。当原告诉请控制股东为其“一般经营行为”承担责任之际,法院则以“门槛规则”审查控制股东是否违反信义义务,为直接适用实质公平规则设置了审查屏障。案2为1976年Weinberger v.UOP,Inc.案④See Weinberger v.UOP,Inc.,457 A.2d 701(Del.1983).,限定了“门槛规则”的适用范围。当原告诉请控制股东为其“逐出式合并行为”承担责任时,法院将直接以实质公平规则对控制股东行为进行实质性审查。本案较之Sinclair案,否定了“门槛规则”,区别在于控制股东滥权行为之性质,法院认为,对于控制股东逐出式合并行为,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足以使其承担证明交易实质公平之责任,无须求助于门槛规则。案3为1994年Kahn v.Lync案⑤See Kahn v.Lync,638 A.2d 1110(Del.1994).,开启了“控制股东逐出式合并”案中的“单一程序”同意规则。法院认为,若控制股东能够证明,交易经由独立董事委员会或其他股东多数、自由且未受压迫的“单一程序”同意,则可将举证责任倒置,由原告承担证明交易不公平之责任,但审查标准仍采用实质公平标准。案4为2014年Kahn v.M&F Worldwide Corp.案,开启了“控制股东逐出式合并”中的“双重程序”审查标准。法院认为,若控制股东能够证明,交易经由独立董事委员会与其他股东多数、自由且未受压迫的“双重程序”同意,则以商业判断规则取代实质公平规则对其进行审查,实际确立了控制股东“避风港规则”。⑥See Steven M.Haas,Toward a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Safe Harbor,90 Virginia Law Review 2245(2004).所谓控制股东“避风港规则”,指控制股东所实施的关联交易,若满足充分信披要求,并经独立董事委员会与其他股东多数、自由且未受胁迫通过,则向控制股东提供机会,适用商业判断规则抗辩原告指控,从而使该交易不公平性的举证责任转移至原告,且法院对该交易以形式标准进行审查。⑦参见蔡昌宪:《下市交易中利益冲突之净化机制:从美国Dell公司收购案谈起》,中国台湾地区《台大法学论丛》2015年第2期。在Kahn v.Lync案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触发条件为,交易经由独立委员会或其他股东的独立、无压迫性同意,为“单一程序保障”,且法院仍适用实质公平标准进行审查;而在Kahn v.M&F Worldwide Corp.案中,举证责任倒置的触发条件为,交易经由独立委员会与其他股东的独立、无压迫性同意,为“双层程序保障”,且法院审查规则将改为商业判断规则。Kahn v.M&F Worldwide Corp.案虽看似放松对控制股东关联交易的审查标准,实际上,法官立场在于以提供双层程序保障标准的方式,鼓励控制股东在进行关联交易过程中,以符合程序之行为行事,进而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正如Stephen Bainbridge教授所言,(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种状态,而非犯罪,若系争议冲突经由无利害关系且独立的董事与股东双重监督,则不应以最为严格的实质公平规则审查控制股东行为,否则,理性的控制股东将对提供“双层程序保护”毫无动力。
(二)美国关于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裁判的司法演变
从1971年Sinclair案“门槛规则”的确立,到1976年Weinberger案“门槛规则”的例外,显示了美国特拉华州法院对控制股东“一般经营行为”审查之宽松趋势(以商业判断规则审查),与对控制股东“逐出式合并行为”审查之严格(以实质公平规则审查)。对控制股东“逐出式合并行为”的审查,法院亦经历了从1994年Kahn v.Lync案的“单一程序保障”规则,到2014年Kahn v.M&F Worldwide案的“双层程序保障”规则,实际确认了控制股东“避风港规则”。
观察美国特拉华州法院对控制股东滥权行为的审查路径,可以总结出对控制股东行为审查的规制目的与裁判标准之态度。其一,就规制目的而言,法院对控制股东行为的审查方式,是根据控制股东的控制地位,根据控制股东不同类型控制行为对中小股东的危害程度,根据具体交易是否经由单一程序保障、双层程序保障等综合因素,考量以何种审判规则审查控制股东行为,以最终判断其是否违反“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因此,法院对控制股东行为规制的根本目的,并非在于泛泛地向控制股东施加“信义义务”,而在于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审查控制股东行为之违法性,解决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股东利益关系的实质公平。正如有学者向Ronald Gilson教授所确认,信义义务重点在于表彰“反形式主义”精神,即法院可借由审查信义义务是否被违反之名,以审查控制股东之行为是否符合实质公平。①参见章友馨:《美国控制股东“公平对待义务”之法制探源——兼论我国控制股东之滥权问题》,中国台湾地区《政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其二,就裁判标准而言,法院并未以信义义务的“利他性”标准要求控制股东,而是在认可其追求控制权利益的前提下,审查行为是否损害其他股东利益,是否符合“实质公平”。“门槛规则”存废标准之确定,并非建立在否认控制股东自利性权利之上,而是通过判断控制股东自利性行为是否属于“排斥并损害中小股东的方式牟取私利”的自我交易,进而确定以何种标准审查控制股东行为。亦有学者指出,公司法中的信义义务,不能以传统信义义务中的“利他性”标准进行解释,法官在审判中并不会要求控制股东必须依照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行事,因为控制股东自身利益也需获得保障②See Lawrence E.Mitchell,The Death of Fiduciary Duty in Close Corporations,13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75(1990).,法院审查案件时所追求的利益平衡,才是现代公司中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内涵。
但是,美国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审查态度并非形成于朝夕之间。在美国二战以前的早期判例中,法官倾向于从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概念出发,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本身进行理论解释。如在1903年Robotham v.Prudential案①See Robotham v.Prudential,64 N.J.Eq.673,689(1903).中,法院认为,虽控制股东有权任命公司董事,但董事本身为所有股东之受托人,若控制股东有控制公司董事的行为,则违反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在1939年Pepper v.Litton案②See Pepper v.Litton,308 U.S.295(1939).中,法院认为,控制股东享有控制权,则意味着其他股东将资产“信托”给控制股东,控制股东行事应从资产管理人的角度考虑,对全体股东承担信义义务。
综上可见,在美国司法裁判过程中,早期法官倾向于从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概念出发,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本身进行理论解释。③参见章友馨:《美国控制股东“公平对待义务”之法制探源——兼论我国控制股东之滥权问题》,中国台湾地区《政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法院在审查控制股东是否违反信义义务时,并不认可控制股东享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而是以控制股东行为是否存在“利己行为”,是否违背其作为受托人之“利他性”作为信义义务的裁判标准。早期法院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裁判标准道德要求过高,且仅对信义义务作出形式解释,缺乏恰当的审判标准④See Steven M.Haas,Toward a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Safe Harbor,90 Virginia Law Review 2255(2004).,也未结合实际需要作出实质审判。后来,法官的裁判理念实际发生了较大转变,即由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作概念解释,转变为要求控制股东交易公平,解决股东之间利益冲突⑤参见靳羽:《美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本原厘定与移植回应》,《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由早期信托法框架下,不认可控制股东私利行为,推崇控制股东“利他性”行为,转变为公司法解释框架中,在承认控制股东控制权的基础上平衡股东之间利益关系。
三、控制股东控制权的合理行使
控制股东享有控制权,是我国公司股权集中模式下的客观存在,不可回避。解决防范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行为,妥当之策并非否定或限定控制权的合理行使,而是设定合理的程序与实体的裁判尺度,将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行使置于合理的运行空间,并辅之以妥当的违规判断与救济机制。因此,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规制体系,需先行了解控制股东控制权之功能利弊,在此基础上,审查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行使边界⑥参见赵旭东:《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维护公司内部主体权益之平衡。
就控制股东控制权的潜在风险而言,包括如下方面:其一,削弱经由敌意收购而形成的外部治理激励。敌意收购形成典型的控制权市场,“敌意收购被视为监督公司管理层的手段,也是惩罚懈怠管理者的工具”⑦参见傅穹:《敌意收购的法律立场》,《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而控制股东的双重身份使其不存在“被敌意收购”的风险,亦不存在被替换的可能。虽有学者认为,在存在控制股东的公司中,控制权市场仍可对控制股东形成压力,因其必须将股价下跌所带来的成本内化以提高经营管理效率。⑧See Daniel P.Cipollone,Risky Business:A Review of Dual Class Share Strutures in Canada and A Proposal for Reform,21Dalhousi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62(2012).但是,当控制股东的控制私利超过控制权市场的监督管理功能时,控制股东为继续谋取控制私利,仍将会选择放任其运营管理的无效率状态。①参见郭富青:《论控制股东控制权的性质及其合理配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其二,股东利益异质化,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可能。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存在长期利益或短期利益、投资需求或管理需求的不同利益偏好,同时,控制股东通过多数表决权足以替换公司董事,进一步操纵公司董事会。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偏好的差异,加之控制股东客观上可实施的种种操作,均导致控制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时无所顾忌。其三,产生控制股东“代理”成本。传统代理成本理论搭建于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产生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之上。控制股东以多数表决权控制公司,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纯粹的代理关系被拟制为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关系”,控制股东为“代理人”,中小股东为“被代理人”,“无可争议的控制权给控制股东提供了剥削中小股东的机会,从而加剧控制代理问题”②参见[美]佐哈·戈申、阿瑟夫·哈姆达尼:《公司控制权与特质愿景》,林少伟、许瀛彪译,载黄红元、卢文道主编:《证券法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由此,在股权集中公司中,亦产生控制股东“代理”成本。
就控制股东控制权的结构优势而言,包含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有利于实现控制股东特质愿景,降低中小股东代理成本。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均珍视控制权,控制股东保持控制权为追求“特质愿景”,中小股东珍视控制权以降低代理成本。根据企业家特质愿景理论,应在两者之间搭建利益平衡的契约。③同注①。对控制股东而言,特质愿景指其所特有的经营理念与获得高于市场经济水平回报的期望。④See Bernard Black,ReinierKraakman,Delaware’s Takeover Law:the Uncertain Search for Hidden Value,96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521(2002).控制股东享有控制权,能使其在追求特质愿景的过程中,免受其他股东的事中质疑或反对。⑤同注①。对中小股东而言,将控制权赋予控制股东,将降低控制股东的剥削动机,进而减少中小股东对控制股东的监督成本。其二,有利于减少敌意收购,保持公司稳定。控制股东兼具股东与实际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其自己决定接受收购要约与否,从而减少敌意收购的发生概率。一方面,将使控制股东专注于公司长远发展,而非时刻警惕来自资本市场的敌意收购⑥参见朱慈蕴、神作裕之、段磊:《差异化表决制度的引入与控制权约束机制的创新——以中日差异化表决权实践为视角》,《清华法学》2019年第2期。;另一方面,控制股东控制权的保持与稳定,也使公司不易易主,避免出现入侵者通过压榨公司员工,消耗公司的信用与稳定。其三,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激励控制股东、全体股东共享收益。当控制股东控制权得以有效利用,加之控制股东与公司的密切联系、信息成本低等因素,将使控制股东控制的公司获取最大利益。赋予控制股东控制权将发挥其在最大限度激励下的潜藏动力,作出最有利于公司且全体股东共享之收益。
在公司制度发展历程中,控制股东控制权合法形成并经久不衰,受到各方讨论关注,自有其自身存在的正当利益,但同时也有其自身弊端。因此,既要对控制股东控制权予以约束,又要充分利用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其违背现实地剥夺控制股东对公司治理的控制权,不如通过法律正面认可并加以限制”⑦参见赵旭东:《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直接将控制股东视为公司治理的行为主体,使其对自身控制权行使导致的损害行为承担责任,从而达到规制控制股东控制权行使的目的。
四、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司法现状
《公司法》第20条“禁止股东滥用权利条款”的规定,在规制控制股东的规制体系中,具有一般性条款的指引价值,通常作为控制股东对中小股东承担信义义务的法律依据。①参见朱慈蕴:《对股东诚信义务的再思考》,《中国法律》2007年第4期。然而,缺失控制股东的具体义务范围与审查标准的条款,难免出现司法的判断分歧。对于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规制完善,不应止步于概念引进与内涵解读,更需要具体的适用范围与裁判标尺。“信义义务”作为一种标准策略的立法技术,无论是成文法或判例法,均须求助于个案的司法审查,审查的成败在于“法官通过何种方法切入复杂的商事交易”。②参见潘林:《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实践表明,以现有损害股东或公司利益的侵权路径,难以解决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的防范问题。
(一)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司法实证观察
首先,关于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范围,司法呈现不同的认知。一方面,借注意义务之名,以司法审判代替商业判断,如在“陕西西厦电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刘明星,伊茂泽,刘刚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③参见“陕西西厦电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刘明星、伊茂泽、刘刚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初1040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被告作为持股65%的控制股东,本应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召集股东会、董事会等义务,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进行表决,但因被告怠于履行前述职责,对公司重大经营和投资计划持放任态度,导致涉案项目未能有效开发,给公司造成损失,故依据《公司法》第20条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法院实际以控制股东“怠于履行”对公司的注意义务之名,要求控制股东对经营决策事项承担责任,恐有以司法介入代替公司商业决策之嫌。
另一方面,借公司自治之名,实际否认股东义务,如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第10号“李建军案”④参见“李建军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436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股东李建军诉请撤销免除其总经理职务的公司董事会决议,指导案例文件在本案的“裁判要点”中指出,案件应审查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决议内容是否违反公司章程,在未违反上述规定的前提下,解聘总经理职务的决议所依据的事实是否属实,不属于司法审查范围⑤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三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2〕227号)。,由此,法院依据《公司法》第22条第2款驳回原告撤销董事会决议的诉请。但是,若进一步挖掘本案将会发现,本案实际属于股东压迫问题。在本案中,涉诉公司共3名股东,原告李建军为持股46%的股东,另2名股东合计持股54%,本案争议所涉及的董事会决议事项,实际是持股合计54%的股东联合罢免持股46%股东总经理职务的股东压迫事件,是大股东挤出(squeeze out)小股东的手段,属于股东滥权与信义义务范畴,而非董事会召集程序履行与否的公司自治范畴。因此,法院应解决本案争议背后的股东义务与滥权问题,考虑以《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判断股东是否违反股东义务,实施滥权行为,而非机械地适用《公司法》第22条第2款,看似维持公司自治,实则并未根本解决问题。①参见彭冰:《理解有限公司中的股东压迫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0号评析》,《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其次,关于控制股东滥权行为的审查标准存在分歧。法院在适用《公司法》第20条审查控制股东滥权行为时,实际并无配套的审查标准与方法,实践中往往以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判断控制股东是否存在滥权行为。例如,在“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诉董服龙、苏玲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②参见“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诉董服龙、苏玲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再1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为公司控制股东,法院认为,被告将案涉资金从公司资本公积金中转出的行为,属于对公司的侵权行为,应适用《公司法》第20条主张损害赔偿责任。又如,在“上海钰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顾晴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③参见“上海钰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诉顾晴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10267号民事判决书。中,公司以被告股东违反注意义务,并存在违约行为为由,诉请被告承担损害公司利益责任,法院认为,公司的请求权基础实际是对财产权益之侵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通常包含过错、行为、结果和因果关系,案件的争议焦点则主要集中于对过错责任及损害结果的认定。
法院以侵权行为审查控制股东滥权行为时,往往直接采用一般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司法》第20条审查标准的缺失问题,但也使中小股东面临举证责任不能之困境。在“济南鲍德彩板有限公司等与济南永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④参见“济南鲍德彩板有限公司等诉济南永君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1民终5792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原告诉求实质为侵权之诉,应按照《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及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分配举证责任。即使被告控制经营公司,但原告股份价值缩水是因为被告违法违规经营导致,还是正常的公司经营风险,均需要原告举证证明,对此原告举证不足,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在控制股东控制下的公司,中小股东本身即难以调取控制股东侵权行为的证据,加上公司经营本就难以预料并存在未知风险,若要求中小股东证明控制股东侵权行为与公司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将使中小股东陷入两难境地。
(二)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改进路径
从解释论角度,为推动控制股东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控制权,必须明确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范围与审查标准。从功能上划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分为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忠实义务是对控制股东的道德要求,常表现为“禁止”类的否定性规定,是消极义务。注意义务是对控制股东的能力要求,是为防止其对公司经营事务注意不足,造成公司损失,表现为“应当”等积极性规定,是积极义务。“基于品德的忠实义务和基于能力的注意义务的划分,不过是为了理论或表述上的清晰”⑤参见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3页。,在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审查规则上,不妨考虑借鉴美国司法审查所采用的商业判断规则与实质公平规则。
首先,就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范围而言,须明确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的各自边界。一方面,控制股东忠实义务区别于董事忠实义务,董事的忠实义务源于公司对其之委托,应承担绝对的忠实义务。但控制股东的忠实义务源于对利益冲突之化解,因此,无法要求其绝对忠实,只能要求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控制股东忠实义务的消极属性,要求其不得利用控制权实施以下行为:其一,欺诈行为。控制股东利用其在公司中掌握信息优势,违反信息披露要求实施的欺诈行为不在少数,如虚假出资、操纵股价、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公司利润分配、操纵公司信息披露等。其二,侵占公司财产,包括直接占用公司大额资金、利用公司清偿债务、拖欠公司大额资金不归还、利用公司资金为自己提供无法偿还之担保等。其三,不正当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包括生产性关联交易与非生产性关联交易,生产性关联交易包括产品销售、资金拆借等,非生产性关联交易包括资产重组、股权转让等。关联交易实际本是中性交易,但是,当控制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则被法律所禁止。其四,其他无视并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基于控制股东在公司的控制地位,其实际可操纵的并不止于前三种典型行为,对于任何控制股东压榨中小股东利益之行为,均为法律所禁止。另一方面,控制股东的注意义务,是对控制股东影响公司经营事务的行为要求,实际上,控制股东应以忠实义务为主,注意义务为辅。①参见朱慈蕴:《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法学研究》2004年第4期。与董事注意义务相区别的是,董事是直接履行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而控制股东并无直接履行职能的职权与身份,更谈不上“积极审慎”地履行义务。对控制股东注意义务的要求,若能“跳出理性人的界定迷局”②参见潘林:《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意味着对其行为的事后审查将倾向于程序审查,为控制股东正当行使控制权提供有效激励。美国特州司法实践亦表明,控制股东注意义务的违反多发生在敌意收购式的掠夺案件,在掠夺案件以外,控制股东违反注意义务的案件则极为少见。③参见苏怡慈:《论并购交易中之控制股东受任人义务——兼论特别委员会之功能》,《东吴法律学报》2015年第3期。
其次,就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审查标尺而言,美国公司诉讼实践中的商业判断规则与实质公平规则的运用,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象,笔者将以其中所涉及的具体规则,判断我国审查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规则供给与不足。一方面,避风港规则的使用与否,将决定控制股东交易行为公平性的举证责任分配,决定审查控制股东行为之宽严程度,能使交易审查具备实质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1条规定,被告以关联交易已履行信批义务、股东(大)会同意为由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在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看来,即使关联交易经过股东会决议批准,且关联股东按规定回避,仍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我国关联交易的司法裁判,虽然呈现了从程序公正转向实质公平的审判路径,但是,片面强调所谓“公平”,否认程序公正的正当性,却无法提供与商事审判相契合的“实质公平”审查方式,反而将增加商事审查的自由裁判可能,无益于对交易审查的“实质公平”。反之,只有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基础上,方可达到实质审查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强调交易公平性的司法审查。美国特拉华州法院通过实质公平规则审查控制股东交易行为,包括对交易公平与价格公平的审查。所谓交易公平审查,即审查控制股东交易过程的公平性,包括交易的发起、谈判、架构与达成,是否经信息披露与内部审核,具体表现为控制股东需向中小股东履行完全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得对中小股东实施压迫行为、不得隔离中小股东同等条件下的公司机会、不得利用控制权转移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①参见章友馨:《美国控制股东“公平对待义务”之法制探源——兼论我国控制股东之滥权问题》,中国台湾地区《政大法律评论》2012年第4期。我国《公司法》第20条规定了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赔偿责任,然而,该条“宣示性”与“概括性”的归责条款,不同于实质公平规则中的交易公平与价格公平认定。对于如何界定控制股东“损害”公司利益,如何判断“公司利益”,甚至如何判断公司“损失”,损失源于股东作出决策时的主观损害动机,还是源于决策后无法预见的商业风险,我国法律均未作出进一步解释。商事裁判的复杂性在客观上要求司法审查具有立体性,《公司法》第20条显然难以提供足够的审查需求,该规则并未提供“利益冲突交易司法审查的分析框架”②参见潘林:《优先股与普通股的利益分配——基于信义义务的制度方法》,《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亦可见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1条之规定,在对程序性审查否定的同时,却未进一步提供可操作的实质审查标准之弊端。因此,我国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具有审查功能的相关条款,存在片面理解实质公平之嫌,在否认程序性审查规则之余,却无法提供实质审查条款与有效的实质公平审查路径。
五、结论
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结构背景下,控制股东行为规制本应是我国公司治理的重要课题。从立法规制体系观察,除了我国《公司法》第20条与第216条关于“禁止股东滥用权利”“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界定之外,《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63条与《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39条规定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堪称我国引入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初步法律尝试。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63条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39条规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及公司社会公众股东负有诚信义务。”立法实质上已经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理论一定程度上制度化,借法律解释方法及类推适用成为裁判依据。④参见王建文:《论我国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1期。然而,在我国相关司法裁判中,仅仅采纳《公司法》第20条的一般性条款,导致法官往往倾向于求助一般侵权行为的认定标准,不仅造成非控制股东侵权赔偿的举证责任难题,而且难以实现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规制的初衷。面对控制股东的持股优势或控制董事会优势,单一求助于控股股东的认定或董事高管忠实勤勉义务,均难以独当规制控制股东滥用权利的重任。值此,在我国营商环境与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背景下,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司法判断与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已经成为迫切的立法需求与司法使命。我国公司法改革要合理对待控制股东控制权的正当行使,回应司法审判需求,厘清信义义务范围,同时,不妨借鉴美国法上对控制股东信义义务审查的商业判断规则与实质公平规则,经由其中的避风港规则与交易公平性审查规则,明确我国现有审查规则供给之不足。应在尊重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审查控制股东行为的实质公平,实现控制股东信义义务规制的根本目的,从而完成公司治理中控制股东行为认定的司法续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