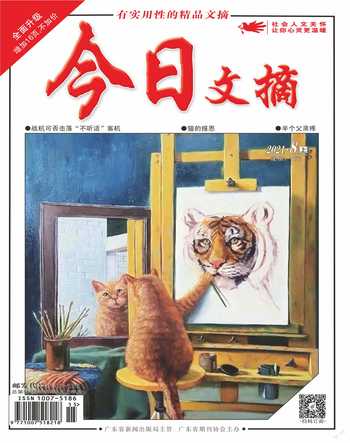母亲的红烧肉
2021-05-30 13:25王红山
今日文摘 2021年15期
王红山

舊年月吃都吃不饱,平常更吃不到肉;后来生活好,不缺肉了,母亲却已吃素——但她决意学做红烧肉:“你们长身体的时候吃不上东西,苦了你们了!你们大概不记得了,邻居刘姨吃红烧肉,你们眼巴巴望着,嗓子里都要伸出手了。”
不久,我们就尝到了母亲做的红烧肉。满满一大盆,我们三个吃得满头大汗。我说:“妈,你也吃啊!”母亲只是紧盯着我们说:“怎么样?好吃吗?”我们边嚼边答:“好吃,好吃!”母亲的脸霎时盛开成一朵花。
父亲诉苦:“你妈已悄悄练了三回了,苦了我,吃了那么多实验品,现在我看见红烧肉就害怕。”哈哈哈,一家人笑得东倒西歪。
转眼间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孩子都进了城,成了家。我们的孩子也一天天长大,母亲在一天天衰老,偶尔全家赶回老家,也是姐姐和妹妹进厨房,年迈的母亲已没精力给一大家人做那么大一锅红烧肉了。
前几天,母亲兴冲冲要来城里,非要给每个儿女家做一顿红烧肉。她说:“现在好歹能动弹!说不定哪天我走了,你们想吃也吃不上了。”
一早,母亲就去了菜市,转了三家肉铺,挑选肥三瘦七细皮薄膘的五花肉,选好各种调料,手脚迟缓的母亲,忙碌了整整一上午。餐桌上,妻子女儿不碰红烧肉,一个怕吃胖,一个在减肥。母亲望定我,我把一大块夹进嘴里,妻子轻踩一下我的脚说:“妈——”我忙截口道:“妈,香,真香!”
母亲顿时开心起来:“快,多吃点。”说着话,她又夹给我几块,我又往嘴里塞了一块。妻子嗔怪的眼神飘来,我微微摇头。妻子看过我的体检报告,血脂高得厉害。红烧肉终究剩下许多,我小心翼翼放进冰箱里。
第二天,母亲去妹妹家,继续她的红烧肉巡演。
两周过去了,红烧肉在冰箱里终没吃完。妻子说,红烧肉有味儿了,得扔掉。妻子把红烧肉倒进垃圾桶时,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妻子却说:“不就是斤把肉,至于吗?”
(陈峰荐自《今晚报》)
猜你喜欢
家庭科学·新健康(2023年9期)2023-10-01
华人时刊(2023年9期)2023-06-20
保健与生活(2022年9期)2022-05-06
食品安全导刊(2021年7期)2021-09-05
意林(2021年13期)2021-07-29
桃之夭夭B(2019年10期)2019-12-14
意林(2019年22期)2019-11-27
初中生世界·八年级(2019年6期)2019-08-13
妇女之友(2016年8期)2016-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