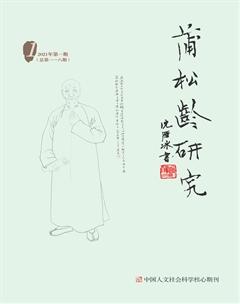天山阁本《琴瑟乐曲》伪托蒲松龄俚曲考
摘要:题署“蒲松龄遗作”的天山阁本《琴瑟乐曲》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传,但1923年天津《大公报》连载的《闺艳秦声》题作“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批”,与其内容大致相同。本文考辨天山阁本《琴瑟乐曲》后附的“高念东跋”为改窜《闺艳秦声》后附《评》而成,《琴瑟乐曲》文本亦出自后人伪托,作伪者即天山阁本《琴瑟乐曲》的钞录者王丰之其人。
关键词:闺艳秦声;琴瑟乐曲;天山阁本;高念东跋;后人伪托;王丰之
中图分类号:I207.3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由来
清雍正三年(1725)二月二十三日为清明佳节,奉祀子孙蒲箬等人齐集蒲家庄东原的蒲氏墓地,为十年前去世的其父、祖、曾祖蒲松龄立碑。碑的阳面镌刻同邑后学张元撰文的《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镌刻的是蒲松龄与其妻刘氏的生卒年月日时、蒲松龄著述与奉祀子孙的名衔。
《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镌刻的蒲松龄著述有“通俗俚曲”一项:
通俗俚曲十四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各一册;《禳妒咒》《富贵神仙曲》后变《磨难曲》《增补幸云曲》各二册。[1]3437
按墓表碑阴的排名顺序,所载通俗俚曲第六种为“《琴瑟乐》”。碑阴镌刻的文字表明,蒲松龄创作的《琴瑟乐》,与《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十种俚曲装订形式相同,它们都是以“一册”的样式存传于世的。
蒲松龄创作的聊斋俚曲中有《琴瑟乐》一种,凡一册,并曾为蒲松龄的后人蒲箬等所目见,题名被镌刻于《柳泉蒲先生墓表》的碑阴,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然而,蒲松龄创作的《琴瑟乐》是一种什么面目的俚曲作品?有着怎样的人物、情节和故事?虽然这一俚曲作品的名称被镌刻于《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但在蒲松龄去世之后三百馀年的时间里,除了为乃父立碑的蒲箬等人外,没有人能有幸一睹它的庐山真面目,更没有人言及它的流传情况,这同样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直到1958年,蒲松龄故居的管理干部蒲玉水先生经过多方搜求,认为已经找到了包括“《琴瑟乐》”在内的《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记载的全部十五种聊斋俚曲 ①。蒲玉水先生哲嗣蒲泽后来回忆此事说:
1958年,对于蒲松龄故居来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蒲玉水先生的努力下,蒲松龄的15种俚曲全部搜集齐备,弥补了《蒲松龄全集》的缺漏之憾。与此同时,为了展出的需要,他还组织力量完成了俚曲新抄本的抄写工作。1962年,路大荒先生在整理出版《蒲松龄集》时,补进了蒲松龄故居收藏的《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等3种俚曲。《琴瑟乐》中亵语偏多,路老感到“内容黄色”,而弃置不收,殊为憾事。[2]103
路大荒先生没有把蒲松龄故居搜集到的、他自己此时也有收藏的“《琴瑟乐》”收入其整理出版的《蒲松龄集》,除了“内容黄色”外,其实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路先生在《蒲松龄集》的《编订后记》中说:
通俗俚曲……只有《琴瑟乐》一种没见到。(另有一种《闺艳秦声》,据说就是《琴瑟乐》,但无依据,难以考定是否蒲氏作品,且内容黄色,故不列入。) [3]1828
路大荒先生当时所见钞本,其实就叫《闺艳秦声》。他因此对这一作品的作者问题采取了审慎待考的科学态度,没有将其视为蒲松龄的作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大都认为蒲松龄纪念馆收藏有一个题名《闺艳秦声》的俚曲钞本,但路大荒先生所说的实为他自己收藏的原润生藏《闺艳秦声》钞本。由于此钞本未被路先生收入《蒲松龄集》,也没有单独发表,所以长期未见流传。
1984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著名聊斋学家藤田祐贤教授访问了山东大学蒲松龄研究室。记得藤田先生来访的那天晚上,蒲松龄研究室在经五路济南宾馆设宴招待,藤田先生在席间拿出了一个题名为《琴瑟乐曲》的钞本复印件,向在座的袁世硕先生、马瑞芳先生和笔者询问其中有关名物和方言的解释。其中有一句是“你看乖了我的纂” ① ,藤田先生不明白“乖了”和“纂”的意思,我告诉他说,“乖了”是淄博方言“碰触到、触到了”的意思;这个“纂”字,指的是已婚妇女在脑后挽起发髻,再将发网罩上之后的形状,淄川方言称这种形状的发髻为“纂”。记得藤田先生当时十分高兴,说这个解释消除了他心中积存多年的疑问。席间袁世硕先生问可不可以复印此件,藤田先生表示可以。自此以后,这个由平井雅尾携至日本,又渡海归来的《琴瑟乐曲》的复印件开始进入中国大陆研究者的视野。
藤田祐贤教授此前写过《聊斋俗曲考》,认为这个《琴瑟乐曲》是蒲松龄的作品 ② ;《琴瑟乐曲》中又有较多的山东淄博一带的方言语词,所以当时没有人怀疑它不是蒲松龄所作。《琴瑟乐曲》的复印件经藤田先生携来中国之后,大大促进了《琴瑟乐》整理工作的开展。1986年1月,蒲松龄纪念馆编、盛伟先生辑注的《聊斋佚文辑注》由齐鲁书社出版,其中收录的《闺艳琴声》(又名《琴瑟乐》)删去所谓“内容黄色”的七百七十馀字,但却是该文本的第一次公开发表。[4]57-671989年第1期的《蒲松龄研究》,发表了刘宣先生依此复印件整理的《琴瑟乐》文本和盛伟先生的《〈琴瑟乐〉国内藏本与日本藏本校释》;1997年第4期的《蒲松龄研究》,发表了盛伟先生的《闺艳琴(秦)声》(又名《琴瑟乐》)整理本。此后,因为未见有人对此文本的作者问题提出异议,先后出版的盛伟先生编校的《蒲松龄全集》本《聊斋俚曲集》 [1]2681-2692,蒲先明先生整理、笔者校注的《聊斋俚曲集》 [5]344-360,蒲松龄纪念馆编、齐鲁书社出版的《聊斋俚曲集》 [6]246-258,张泰先生校注的《〈聊斋俚曲集〉校注》 [7]757-770,無不将此《琴瑟乐》文本视为蒲松龄的俚曲作品而收入其中。
然而,随着聊斋俚曲研究的深入和影响的扩大,质疑与否定此《琴瑟乐》文本为蒲松龄作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上世纪90年代,长春师范学院的郭长海教授应邀参加吉林文史出版社计划出版的《中国艳歌大观》的编选工作,他所分担的编选任务即为已经出版的聊斋俚曲《琴瑟乐》。在编选期间,郭长海先生发现了天津《大公报》1923年连载的《闺艳秦声》及其《后序》,与《琴瑟乐》正文及后附的“高念东跋”内容相同,但作者与批评者则署作“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批”。经过对文本的校勘与考察,郭长海先生于2001年撰文指出,《琴瑟乐》与《闺艳秦声》内容有同有异,而《闺艳秦声》后附的《自序》和《后序》,可以说明它的作者不是蒲松龄,而是一个名叫“阿蒙”的人。郭先生由此推测,大概是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有一个名叫阿蒙的山东人,将他儿时读过的曲词唱本《两头忙·恨媒人》(或称《两头忙·闺女思嫁》)改编成了有说有唱的说唱体曲本《闺艳秦声》。蒲松龄大概是见过《闺艳秦声》流传的本子,所以他钞录了一本,并改题为《琴瑟乐》,和自己创作的文稿放在了一起。蒲松龄去世之后,儿孙们见到了他的钞录本,误以为《琴瑟乐》是自己先人的作品,于是将其归入《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镌刻的蒲松龄俚曲题名之中。[8]42-46总之,《大公报》刊载的《闺艳秦声》文本的发现,对于今本《琴瑟乐》的作者是蒲松龄的说法提出了挑战。
复旦大学黄霖教授对《闺艳秦声》与《琴瑟乐》的认知与郭长海先生存在较大差异。他于2004年发表《〈闺艳秦声〉与“易性文学”——兼辨〈琴瑟乐〉非蒲松龄所作》一文考辨此事,考订了与《闺艳秦声》和《琴瑟乐》两种文本相关的许多重要史实。如郭长海先生在《中国艳歌大观》所收的《闺艳琴声》(笔者按,即据《聊斋佚文辑注》收录的今本《琴瑟乐》)之前加编者按语云:
清代初期,坊间还流传着另外一种刻本,名《闺艳秦声》,署名“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批”,其《自序》中说,是根据《闺艳·两头忙》改写的。[9]111
如果“清代初期”真有《闺艳秦声》的刻本流传,并且是“根据《闺艳·两头忙》改写的”,那么清初流传的《闺艳秦声》或许真的与蒲松龄有关。为了证实此说的准确性与真实性,黄霖先生曾以电话咨询的方式向郭长海先生求证,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人见过所谓清初流传的刻本,也没有相关的版本著录,郭长海先生所见最早的《闺艳秦声》文本即1923年《大公报》的连载本。黄霖先生还发现,《闺艳秦声》不仅连载于1923年8、9月份的天津《大公报》,而且被姚灵犀编入他校订的《未刻珍本丛传》,于1936年1月自印出版。
关于《闺艳秦声》的创作时间,《大公报》刊载的《闺艳秦声》作者《自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亥(客)夏阴雨匝旬,经(径)绝屐齿。日抱膝坐败辟(壁)中,郁闷欲死。偶忆儿时所记,有《艳情·两头忙》一册,遣意摛词,颇有可观,微嫌其调不谐时,句多杂凑;儿女情事,未能描写尽致。遂捉笔补成,变古意作新兹(声),用以破除烦愁,消磨永日。计旧词止二十馀阕,补者十之五;插白则皆新增者。[10]
郭长海先生以为,“亥夏”的“亥”字之前应有一字缺失。从这一推论出发,他在《〈琴瑟乐〉作者与源流考证》文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自序》中,“□亥夏”所缺的一个字。按之庆应大学本与《大公报》最为相近的关系,庆应大学本后有“康熙乙亥抄”的字样,那么,这个缺字,也就是“乙”字。“乙亥夏”,即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8]44
黄霖先生考辨说,所谓“乙亥夏”,《大公报》本作“亥夏”,而且“亥”字之前没有表示缺字的空围号“□”,说明这个“亥”字本是“客”字之误排,在姚灵犀校印的《未刻珍本叢传》中,“亥”即被校订为“客”字。“客夏”指的是去年夏天,与干支“乙亥”无关。由于《闺艳秦声》的清初刻本并不存在,将“客夏”推论为“乙亥夏”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缺少确凿证据。黄霖先生的结论是,《闺艳秦声》并不是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作品,其创作时间应在乾隆朝后期,甚至是此后的嘉庆年间。[11]119-132
郭长海先生认为《闺艳秦声》不是蒲松龄的作品,但在蒲松龄生前已经存在,今本《琴瑟乐》系蒲松龄据之钞录而成;黄霖先生则认为《闺艳秦声》的创作时间在蒲松龄去世之后,今本《琴瑟乐》系后人据《闺艳秦声》伪托而出现在今人的视野之中。为了弄清今本《琴瑟乐》的作者问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镜源流,搞清楚今本《琴瑟乐》版本的来龙去脉和渊源关系问题。可以这样说,厘清了今本《琴瑟乐》版本的来源,其作者是不是蒲松龄也就真相大白了。
二、《琴瑟乐》的版本情况
《琴瑟乐》今存四个不同版本,其面貌与来源也各不相同。
题名为蒲松龄著作的《琴瑟乐》,在文本校订整理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三个版本,即盛伟先生在《〈琴瑟乐〉国内藏本与日本藏本校释》中使用的蒲松龄纪念馆藏本《琴瑟乐》(正文首叶题《闺艳琴声》,以下简称“蒲馆本”)、博山田庆顺原藏复钞本《志异外书闰(闺)艳秦声》(以下简称“田氏本”)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收藏的淄川王丰之天山阁钞本《琴瑟乐曲》(以下简称“天山阁本”)。
蒲馆本和田氏本的情况,杨海儒先生在《聊斋俚曲及其研究》一文中曾予著录:
《琴瑟乐》又名《闺艳琴声》。蒲松龄纪念馆存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新抄本:一为朱丝格十行稿纸(书口上印“聊斋遗著整理稿笺”字样),用毛笔竖抄,封面竖题“琴瑟乐”(下书:聊斋俚曲),但首叶书题却为“闺艳琴声”,第二行紧接正文。一为方格稿纸用钢笔横抄,封面横题“志异外书闰(闺)艳秦声”,“淄川蒲留仙著,一九八一年六月据田庆顺本重抄(闰艳秦声,琴瑟乐全传)”。从内容看,除毛笔抄本加了词语注释外,两抄本基本相同,似同出于一源。最近,笔者曾拜访过其收藏者田庆顺先生,通过交谈,证实了二者皆抄自于其家藏本。[12]135
杨海儒先生的调查,证明蒲松龄纪念馆今藏的这两个钞本同出一源,皆为田庆顺家藏本的复钞本。其不同之处在于蒲馆本钞于上世纪50年代末,田氏本则钞于80年代初。杨海儒先生告诉笔者,80年代初,蒲松龄纪念馆征得了田庆顺藏本的复钞件,馆里先后有数人据之誊写,故蒲松龄纪念馆藏有几个不同钞写者誊录的田氏本,其中之一为已故前馆长鲁童先生手钞,馆里的老人能清楚地辨认出他的笔迹。
天山閣本的《琴瑟乐曲》,即1984年藤田祐贤先生携来中国的庆应义塾大学藏本的复印本。因为此本封面“琴瑟乐曲”的题名之前有“蒲松龄遗作”五字,其下钤有长方形阳文篆体“天山阁藏”之印;题名之后又有钞录者王丰之题写的“在淄川城内文化街天山阁家藏 依命平井院长 王丰之手抄”三行文字,说明此本所依据的原件本是由淄川王氏天山阁收藏的,所以我们称这个依据王氏天山阁藏本过录的钞本为“天山阁本”。
《蒲松龄研究》1989年第1期发表的刘宣先生据天山阁本《琴瑟乐曲》整理的《琴瑟乐》,仅将其中的几段抄自《金瓶梅》的文字删除,反映了天山阁本的基本面貌。
笔者注意到,盛伟先生在其辑注的《聊斋佚文辑注》收录《闺艳琴声》(又名《琴瑟乐》)时,还提到过另一个“淄川王氏的天山阁藏抄本”。他在《聊斋佚文辑注》本《闺艳琴声》文后的“说明”中写道:
我这次辑录,是依据淄川王氏的天山阁藏抄本题名《闺艳琴声》(又名《琴瑟乐》)的俚曲清抄本整理……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珍藏本《琴瑟乐》,其封面亦题依淄川天山阁藏本抄录……我怀疑,藤田祐贤先生所挟海而西之《琴瑟乐》,可能是蒲氏之初稿,抑或是与我所依据之天山阁本为两种不同的本子。[4]66-67
笔者以为,盛先生所说的“清抄本”,即与庆应义塾大学藏本(天山阁本)不同的另一个“淄川王氏的天山阁藏抄本”,其实是并不存在的。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笔者在盛伟先生后来整理的《蒲松龄全集》本《琴瑟乐》的校勘记中,看到盛先生又一次提到了《聊斋佚文辑注》本《闺艳琴声》的底本来源。盛先生说:
拙篇(编)《聊斋佚文辑注》,已收录(该文,是据蒲松龄纪念馆所藏《闺艳琴声》抄本收录,故以下简称:蒲馆抄本)。[1]2690
盛先生这段话,进一步明确了《聊斋佚文辑注》所收《闺艳琴声》(又名《琴瑟乐》)的底本就是蒲馆本。蒲馆本的情况,前面曾引杨海儒先生《聊斋俚曲及其研究》一文的著录。杨先生介绍得很清楚,它是钞录在印有“聊斋遗著整理稿笺”字样的朱色竖行钞写纸上的,其钞写时间在蒲玉水先生觅得此钞本的1958年之后,怎么可能会是“天山阁藏抄本”,而且还是“清抄本”呢?
这样,我们可以确认,天山阁本只有一种钞本存传,就是题名为《琴瑟乐曲》的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藏本。
在天山阁本、蒲馆本、田氏本之外,还存在一个人们所知不多的版本,即路大荒先生收藏的原“润生藏抄本”。
《蒲松龄研究》2001年第3期发表过蒲松龄纪念馆孙巍巍女士《路士湘先生向蒲松龄纪念馆捐赠文献资料》的报道,文中写道:
日前,路大荒先生之子、年已八旬的路士湘先生又把家藏的部分珍贵文献资料及其文稿无偿捐赠给蒲松龄纪念馆,其中包括《志异外书·闺艳秦声》(一名《琴瑟乐》)(润生藏旧抄本)……《志异外书·闺艳秦声》旧抄本的出现说明了该作品当时就已经被路大荒先生挖掘整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收到《蒲松龄集》中,致使我们无法从《蒲松龄集》中看到聊斋俚曲的全貌。[13]9
这里,我们称路大荒先生收藏的原润生藏本为“路藏本”。经询问杨海儒先生得知,路藏本为64开本,一册,纸色陈旧,文字与天山阁本差异较大。
天山阁本《琴瑟乐曲》与蒲馆本、田氏本、路藏本虽然内容大致相同,但从版本校勘的情况看,它们之间的文字差异较为明显,天山阁本与蒲馆本、田氏本、路藏本应该各有其来源,从性质上说分属不同的版本系统。
笔者首先要感谢盛伟先生,他的《〈琴瑟乐〉国内藏本与日本藏本校释》一文,通过校勘将天山阁本和蒲馆本、田氏本的文字异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依据盛伟先生的《〈琴瑟乐〉国内藏本与日本藏本校释》,我做了如下几项统计:
(一)通过盛先生的校释文字,笔者共发现天山阁本、蒲馆本、田氏本三本的异文578处。这里所作的统计,是以盛伟先生所列文本的一句为一处,不再细数这一句中一个还是两三个字的不同。如果去除天山阁本单独存在的、明显是后人增补的来自《金瓶梅》一书的文字,今本《琴瑟乐》全文在6000字以下。如果不计数标点,只算字数,全文约5500馀字。如此篇幅,而三本的异文之多,竟然达到了1/10以上。
存在着如此多的异文,说明天山阁本、蒲馆本、田氏本三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它们极有可能不是出于同一个源头。
(二)文本中同一句话,蒲馆本与田氏本文字全同,而蒲馆本、田氏本两种钞本与天山阁本存在异文,这种性质的异文多达414处。
有一种版本现象笔者未予统计,那就是版本的现代特征。《琴瑟乐》现存的三个版本,都存在大量的现代钞写者在钞写过程中随意改字的情况。以蒲馆本和田氏本中出现的异文为例:年程—年成、惹的—惹得、恨恨—狠狠、妆羞—装羞、合—和、随心—遂心、恨不的—恨不得,等等等等,笔者以为诸如此类的异文都是钞写者随意改字的例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钞写者缺少版本常识,不了解古代白话作品常用字的使用情况,于是把一些古人用字当成了别字,钞写时随意改动,使得文本不断地现代化了。所以,随着钞写者不自觉地改用现代通行的文字,钞本的现代特征也就显露了出来。
即使我们不把因这样的版本现象而出现的异文计数在内,蒲馆本、田氏本和天山阁本之间存在的414处异文同样可以说明,蒲馆本与田氏本的关系较为密切,而这两种钞本与天山阁本则存在着较大的文字差异。本节前面介绍的杨海儒先生关于蒲馆本和田氏本同出一源的版本调查,更进一步地说明了蒲馆本和田氏本之间的密切关系。
既然来源相同,蒲馆本和田氏本自应纳入同一个系统。而与这两个钞本存在大量异文的天山阁本和路藏本,则属于另外的版本系统。
现在所知的天山阁本、蒲馆本、田氏本、路藏本分属不同的版本系统,其来源也应该各不相同。由于研究者多认为天山阁本《琴瑟乐曲》是今本《琴瑟乐》最为可靠的版本,下面我们先来考察天山阁本的源头问题。
三、天山阁本后附的“高念东跋”出自后人伪托
因为是将天山阁本《琴瑟乐曲》与《闺艳秦声》进行比勘考辨,我们先介绍一下《闺艳秦声》的情况。
《闺艳秦声》题作“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批”,其《后序》则称作者为“阿蒙”。黄霖先生据“坚誓狮子座下人”所作的《题〈闺艳〉卷尾》称作者为“单居士”,认为作者单姓。
查检相关著录与介绍,国家图书馆藏有《闺艳秦声》的清代钞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民国初年的晒印本,一部题名为《艳桃记》的清代小说也附录了《闺艳秦声》。降至民国年间,《闺艳秦声》又先后出现过两种版本,即天津《大公报》四处钞录了《金瓶梅》第四回、第八回、第七回和第九回、第六回的文字,而在结尾的[对玉环]带[清江引]两个曲牌之间,则插入了《金瓶梅》第四回的《男子物》与《女子物》两首打油诗。与天山阁本正文情况相同,其后附的“高念东跋”,同样存在着依照《金瓶梅》抄袭改窜的痕迹。
清张竹坡批评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筆者曾见据清康熙年间刻本翻刻的玩花书屋本。此刻本卷首,有署名“秦中觉天者谢颐”题写的《序》,该《序》凡三叶,每半叶五行,每行十二字。其叶三下,钤有“谢颐”“敬题”二印,而印章之前的题署,就是“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
清明中浣,是清明之月的中旬。康熙三十四年(1695)乙亥,二月二十一日为清明节,故谢颐所说的“清明中浣”,指的是这一年的二月中旬。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想像一下古人笔下出现了“雷同卷”的画面:同样是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仲春二月的中旬,有一个叫谢颐的人和蒲松龄的乡前辈高珩,两个人同时异地,正在为张竹坡批评的《金瓶梅》和蒲松龄创作的《琴瑟乐曲》题写序跋。序跋写完,二人分别署名,这时候“雷同卷”出现了: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写下了“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十一个完全相同的墨书大字,而且又都在自己的名号之后加上了一个“者”字。试问有这样的可能吗?
显然,“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般阳高念东者题于栖云阁”的题署文字,是作伪者蹈袭了《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的题署。前面所说的天山阁本抄袭《金瓶梅》的五处文字塞进《琴瑟乐曲》正文的事实,则为这一抄袭行为提供了佐证。
所以,与相信“高念东跋”出自高珩之手的研究者不同,笔者相信,题署为“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般阳高念东者题于栖云阁”的“高念东跋”,百分之百出自后来的作伪者之手。
三是天山阁本后附的这个“高念东跋”,透露出了十分明显的作伪痕迹。
最为明显的作伪痕迹,是“高念东跋”中竟然出现了“阿蒙”的名字。“高念东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有怪此词剥尽女儿面皮者,此弗思之甚也。天上下样事,只见人说,不见人做;天下极下等事,人都肯做,坚不许说。伊虽不说,谁其不知?肯说肯做之人还是天真烂熳,况女儿须嫁夫归之间。人之大欲,纵复急于结缡,亦自无伤风化,非终不可告人者也。请问词中情事,那回女子能尽摆脱?第不许人说耳。女不许说,而忽一男子代吐其肚膈,正如犀炬一燃,水怪毕现,正恐天下红妆心爱此郎君解事,亦恨其饶舌伤人,将有群起而以香唾唾何郎之面。所奈何我知,知阿蒙善学古人,必能令其自干也。一笑,一笑。
这段文字钞自《闺艳秦声》后附《评》,但因数处出现文字脱漏,令人难以卒读。其中所说的“阿蒙”其人,正是《闺艳秦声》所附《后序》所揭出的这篇曲文的作者。阿蒙之名,在《闺艳秦声·后序》中凡五见:
阿蒙兴之所触,偶为秦声。以诙谐之词,写幽艳之意,丧(舍)我以求,摹拟入神……余戏谓阿蒙:“红颜易老,绿鬓星星。过时不来,而复谈朱愤(幩)说郊。百两(辆)迎门,即安知不为东家妇窃笑哉?”……而或有以调寄于委琐,情拟于鄙屑,为阿蒙病。余谓《离骚》辞托美人,《南华》意寓胠箧,比物之心,何所不可?……是奚足病阿蒙?但恐摹写幽情,刻划太甚,慧业文人,又添一重公案耳。阿蒙以为何如?[14]
我们且不论《闺艳秦声》所附《后序》作者与《评》的作者是不是同一个人,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知道《闺艳秦声》是阿蒙依据《闺艳·两头忙》改写而成的曲本。正因为如此,《评》的作者在《闺艳秦声》的评论中再一次提到了阿蒙其人。可惜的是,天山阁本《琴瑟乐曲》的托伪者在将《评》改窜为“高念东跋”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疏漏,竟然把原作者阿蒙的名字也钞在了改窜之后的“高念东跋”里。可笑这位作伪者,有心作伪却不会掩藏其作伪痕迹,画虎不成反类犬,何其不慎也哉!
既然“善学古人”的阿蒙之名都现身于改窜之后的“高念东跋”里,《闺艳秦声》与天山阁本《琴瑟乐曲》究竟孰先孰后,孰真孰假,不是已经昭然若揭了吗?
“阿蒙”二字出现在“高念东跋”里,清楚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的“高念东跋”脱胎自《闺艳秦声》后附《评》证据凿然,铁定无疑;二是这位作伪者就是一个“文钞公”而已,他不是心思缜密的作伪者,实在是缺少作伪的专业水准,改窜之间偶有不慎,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
为了更为明确地说明“高念东跋”钞改《闺艳秦声》后附《评》的铁定事实,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下面两段文字:
《闺艳秦声》后附《评》有这样一段话:
文字论神理,不论皮毛。即如此卷新词,固皆家人儿女于(之)常谈,若论其搆造之法,有步骤,有深浅,有开阖起伏,有照应关锁。慧思绮语,时时点注;渲染补衬,处处钩连。时而闲冷传神,时而艳极含态。波委云属,穿经度纬,一气宕折中章法精严,色浓味永,骨秀韵圆。此是昔人作赋之才小试于香奁一派,必传何疑![15]
下面是天山阁本“高念东跋”中相类的文字:
文字论神理,不论皮毛。即如此卷《琴瑟乐曲》,固皆家人儿女常谈,若论其结构之法,有步骤,有起伏,有照应关销(锁)。慧思绮语,时时点注;渲染陪衬,处处勾连。时而冷□传神,时而妍热合态。波委云屡(属),穿经度纬,一气宕折中,章法精[严],色浓味永,骨秀韵圆。此是松龄作赋之才小试于香奁一脉,必传何疑!
以上两段文字,分别见于《闺艳秦声》后附《评》和“高念东跋”的第一段。
《评》中的“闲冷传神”一语,是说在《闺艳秦声》文本的闲散疏冷之处时见传神之笔,评语切中肯綮;但因改窜者不明其意,于是随笔改作“冷□传神”。“冷□”为何?是冷笔,还是冷艳?实在是不知所云。
“艳极含态”是说原作者将那些“艳极”的段落写得情态真切,摇曳多姿;而改窜者同样不明其意,改作“妍热合态”。“妍热”究竟为何意?费人疑猜而不着,因为此词为作伪者生造,本来就不通。而且,这里的“合”字,分明就是“含”字之误。
“波委云属”一语,“波委”是言水波聚积,“云属”是说云彩接连不断。“波委云属”与“穿经度纬”合用,表达的是赞扬《闺艳秦声》主线贯穿,针线细密之意。但因改窜者同样不明其意,改“属”为“屡”,语意又入不通之境。这个“屡”字,同样也是一个误字。
再下面,改窜者将“章法精严”的“严”字钞漏,让排比的意韵荡然无存。
由这一段文字的比勘可以发现,《闺艳秦声》后附《评》语中肯綮,文字水准也高;天山阁本对《评》加以改窜,不时出现错漏,大大降低了这篇《评》的艺术价值与文字水平。
也就是说,如果是“高念东跋”先出,那么它只是一篇识见与表达都很平庸的文字。这样的文字不会出现在翰林院出身的高珩笔下,也不会被别人“拔高”到《闺艳秦声》后《评》的高度;而如果《闺艳秦声》后附《评》在先,经过一位识见与表达都很平庸的改窜者的点窜之后,形成所谓的“高念东跋”,则于情于理尽皆符合。
《闺艳秦声》正文之后,附有《后序》《自序》《评》与《题〈闺艳〉卷尾》四篇文字,其中的《评》约1900馀字。天山阁本《琴瑟乐曲》后附的《高念东跋》其实没有钞录全部评语,而是钞录到“《牡丹亭》出”一段就停止了,然后草草结尾。笔者查验的结果是,未经其改窜的评语尚馀约500字。《评》语的前半部分经其改窜,成为《高念东跋》的部分约1400字,中间经过改窜者的增补,写成的《高念东跋》约在1700字上下。
下面,附带谈一谈李尧臣“诗跋”的托伪问题。
天山阁本后附的李尧臣“诗跋”,由三首七言诗组成,这三首诗其实都不是李尧臣本人的诗作。三首诗的出处,盛伟先生在1989年发表的《〈琴瑟乐〉国内藏本与日本藏本校释》中就已经指出:“李希梅摘抄《金瓶梅》第五回的首引诗,第七回的结尾诗及第七回的首引诗,但抄录时,有几个字稍异,并加上‘题媒婆诗五字(笔者按,‘题媒婆诗为四字)。” [16]260
不是李尧臣的诗,又怎么能说成是李尧臣的“诗跋”呢?这是因作伪者考虑不周而形成的漏洞之一。
关于李尧臣“诗跋”同样是伪作的问题,我们看一看这位“李尧臣”的题署就明白了,此“诗跋”之后的题署,为“康熙甲戌中秋后四日 淄川希梅李尧臣跋诗于松阴书屋”。
这个题跋,其实是为呼应假冒的“高念东跋”的题署而伪造出来的。“高念东跋”署作“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般阳高念东者题于栖云阁”,乙亥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而甲戌是乙亥的前一年,康熙三十三年(1694)。
看得出来,作伪者先是通过改窜《闺艳秦声》后附《评》伪造了“高念东跋”,并顺手从《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拈来一个“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者”的题署例句,照猫画虎伪造出了高珩“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般阳高念东者题于栖云阁”的题署,之后又打蛇顺竿上,伪造了“康熙甲戌中秋后四日 淄川希梅李尧臣跋诗于松阴书屋”的题署,从而给读者造成先是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李尧臣题诗,然后是康熙三十四年乙亥高珩题跋的假象。
所谓的李尧臣“诗跋”,是从《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里钞来的诗,题署是在先有伪“高念东跋”的前提之下伪造出来的,“诗跋”的所有内容都与蒲松龄挚友李尧臣无关。
也就是说,无论是“高念东跋”还是李尧臣的“诗跋”,其实都是后人托伪的假货。
本来笔者打算另立一节,通过《闺艳秦声》和天山阁本《琴瑟乐曲》文字的比勘来揭示后者钞录前者的种种痕迹的,现在看这一论证过程可以省略了,因为天山阁本后附的“高念东跋”和李尧臣“诗跋”作伪的痕迹太过明显了。“高念东跋”是由《闺艳秦声》后附《评》改窜而来的,此事可以说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所谓一假俱假,作伪者是不可能手中握有《琴瑟乐》真品,还要画蛇添足、费力不讨好地去伪造这样一篇漏洞百出的“高念东跋”的。
我们通过相关事实的考察说明了“高念东跋”、李尧臣“诗跋”和天山阁本《琴瑟乐曲》皆为后人的托伪之作,也就可以订正上文中郭长海先生作出的两个推论了。
一是关于《闺艳秦声》的创作时间的。《闺艳秦声》作者《自序》有云:“亥(客)夏陰雨匝旬,经(径)绝屐齿。”郭长海先生说:“《自序》中,‘□亥夏所缺的一个字,按之庆应大学本与《大公报》最为相近的关系,庆应大学本后有‘康熙乙亥抄的字样,那么,这个缺字,也就是‘乙字。‘乙亥夏,即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
既然郭先生依据的天山阁本“高念东跋”之后“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般阳高念东者题于栖云阁”的题署出自后人伪托,高珩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为蒲松龄的《琴瑟乐》题辞纯属子虚乌有之事,而且《闺艳秦声》的清初刻本同样并不存在,那么,关于《闺艳秦声》在康熙年间已经出现的说法也就销解于无形,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个曲本当时已经存在。
二是郭长海先生推断,蒲松龄见过清初人阿蒙改编的《闺艳秦声》,他于是钞录此曲并改题为《琴瑟乐》,后来这一钞录本被其子孙看到,误以为《琴瑟乐》为蒲松龄作,于是将其镌刻在《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聊斋俚曲的题名之中。
郭先生这一推论的前提,是《闺艳秦声》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蒲松龄在世的时候已经出现。既然康熙三十四年(1695)《闺艳秦声》出现的证据至此全无,也就不能说蒲松龄钞录过阿蒙创作改编的《闺艳秦声》,更不能说镌刻于《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的《琴瑟乐》不是蒲松龄本人创作的俚曲作品。
天山阁本《琴瑟乐曲》是后人的托伪之作,那么这个作伪者会是谁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四、天山阁本的作伪者是淄川人王丰之
天山阁本《琴瑟乐曲》的封面,有“在淄川城内文化街天山阁家藏 依命平井院长 王丰之手抄”三行文字,其第三行之下钤有阳文篆体“丰之”之印;扉页有“本稿我传之元抄,小心留意写之 王丰之”的题署;封底又有“依命淄川鲁大公司医院平井院长 琴瑟乐曲终 淄川城里王丰之抄于酌月轩”三行文字,第三行之下同样钤有“丰之”之印。以上文字俱可以说明,此天山阁本的钞录者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世的淄川人王丰之其人。
关于王丰之与其家族,因在淄川一带搜罗、购藏聊斋学文献而与王丰之发生交往的日人平井雅尾,在其所著《聊斋研究》一书中有过简单介绍:
原稿在各处素封之家乃至文人墨客之后裔家内,反较蒲家庄所藏为多,似因经久远之时日后,被转卖流失所致。闻淄川县城内天山阁主人王沧佩及张店耿家等处,颇有相当之收藏。而王沧佩氏之父君王敬铸(号子陶)与张店耿士伟,皆清末之举人进士,在世之日,收集聊斋遗稿最多……王沧佩氏现已七十馀岁,为淄川县署县志编纂委员,系该地屈指之聊斋遗稿爱藏家。笔者虽未一度晤面,但其侄王丰之君,曾将传家之遗稿,费数年之时日细心留意的转抄与余。王家所藏者,殆已抄写完毕。虽非尽属定稿,但其中亦有难得之珍稿。[17]20
由平井雅尾的介绍和王丰之天山阁藏本的题署可知,王丰之乃清宣统三年(1911)第三次续修《淄川县志》的淄川人王敬铸之孙,天山阁主人王沧佩之侄。
据平井雅尾《聊斋研究》介绍,王丰之先后为其钞录过《未刊聊斋志异稿》四册、《聊斋诗赋词曲》二册、《荆钗记曲》二册、《农桑经》一册、《续农桑经捕蝗法要诀》一册。其所钞各本,皆称作“聊斋蒲松龄之遗著”。笔者考察认为,除其中的《农桑经》一册外,其他各种皆为托伪之作,而钞录者王丰之其人,则实在难脱假他人之作品,伪托为蒲松龄遗著之干系。
下面我们以王丰之钞录、平井雅尾原藏的《未刊聊斋志异稿》为例,来看一看他以他人著作冒充蒲松龄遗著,托名为蒲松龄作的相关事实。
平井雅尾《聊斋研究》之“墓碑所载以外有考证者”一类,有关于《未刊聊斋志异稿》钞本的著录:
未刊聊斋志异稿 四卷全四册(天山阁所传抄)
右系天山阁王家所传者,為珍稿中之珍稿。
卷之一(所载五十一题)
王再来 天台道士 孽镜 吴冷
血怪 丰都润城隍 三绝 张方海
飞鱼 原襄敏 李明珍 犬婿
义婢 黄孝子 大蝎 李翘之
护军女 朱外委 双蝶 白云岫
吕英秋 王奇 秋水小姐 邵春萝
桂芳华 凉燠珠 阿萧 王不留
沂州案 刘车夫 空空儿 冷生
念袂三则 念袂二 念袂三 翠芳
那刹 两铜菩萨 封采烟 解巧璇
乔莺 摩霄 丐者 胡元素
胡岱华 陈世伦 粉蝶 王寿星
神针 甸隐 蝴蝶精 [17]48-49
其卷二、卷三、卷四目录今略。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此只介绍经笔者考察所知的《未刊聊斋志异稿》卷一诸篇的来源情况。笔者经多方考察,发现上举卷一目录所列的五十一篇中,有三十七篇又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由几部书中的作品打乱卷次混编在一起冒充“未刊聊斋志异稿”的。
首先是目录中的《大蝎》和《念袂三则》两篇,平井雅尾在其篇名右侧划有竖线,并在全书目录之后注云:“以上右侧注有直线者,系已登载于赵荷村本乃至王金范本及《聊斋拾遗》者,有七、八题之多。盖《志异》所述,多属鬼狐妖异,千变万化,奇奇怪怪,故《志异》之初稿题名为《鬼狐传》或《鬼狐遗草》,后改为《志异》。是则《鬼狐传》草稿,《志异》为清稿也。” [17]51
我们知道,《大蝎》与《念秧》两篇作品确为蒲松龄作,故“念袂”实为“念秧”的形近之误。《大蝎》与蒲松龄所作的《念秧》,见于当时通行的《聊斋志异》青柯亭刻本,并不在所谓“未刊聊斋志异稿”的范围之内。
《聊斋志异》中的《念秧》篇,系由两个不逞之徒设计骗人的故事组合在一起。由此可知,被王丰之钞录于《未刊聊斋志异稿》卷一的《念秧三则》,其中一则已经是与真品混合为一的假的聊斋故事。而排列于其后的《念秧二》《念秧三》两篇,则应该是王丰之从别人著作中钞来的两个性质相同的设计骗人的故事。因为蒲松龄创作的《念秧》只有两个故事,可以肯定的是,《念秧三则》与《念秧二》《念秧三》中,有三个故事的文字是王丰之从别人的书中钞来冒充“未刊聊斋志异稿”的。
其次是目录中的《李明珍》《犬婿》《义婢》《双蝶》《白云岫》《邵春萝》《桂芳华》《凉燠珠》《阿萧》《王不留》《沂州案》《封采烟》《解巧璇》《乔莺》《摩霄》《丐者》《胡元素》《胡岱华》等十八篇,经查证,这十八篇作品均出自1913年上海图书公司铅字排印出版的《聊斋志异拾遗》。此《聊斋志异拾遗》全一册,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附录《近世坊间蒲氏伪书》曾揭露其为伪作:“《聊斋志异拾遗》。民国二年(一九一三)上海图书公司出版一册《聊斋志异拾遗》石印本,收有篇文计有二十七篇:《傅于槃》《乔莺》《王秋英》《解巧璇》《白云岫》《李明珍》《封采岫》《双蝶》《邵春萝》《桂芝华》《凉燠珠》《赵谷》《王鹿儿》《沂州案》《张红桥》《陈天籁》《陈世伦》《胡岱华》《胡元素》《犬婿》《义婢》《丐者》《东六珈》《梁铁锤》《摩霄》《阿箫》《王不留》。” [18]212
笔者所见的《聊斋志异拾遗》为1913年铅字排印本,非刘阶平所云为石印出版。版权页题“民国二年一月付印 民国二年二月出版 著者:蒲松龄 分售处:中华图书馆 中华书局 鸿文书局 广益书局 商务印书馆 出版所:上海民国(以下残缺) 全一册 价洋三角”。无序跋。首目录,次正文。此《聊斋志异拾遗》中,《阿萧》,目录、正文俱作《阿箫》;《解巧璇》,目录、正文俱作“《解巧璇》”;《封采岫》,目录、正文俱作“《封采烟》”。从文字的异同看,王丰之钞书所用底本即此铅印本,只是在钞录时将《阿箫》的“箫”字错钞成了“萧”字。
托名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拾遗》中的另九篇作品,篇目为《傅于槃》《王秋英》《赵谷》《王鹿儿》《张红桥》《陈天籁》《陈世伦》《东六珈》《梁铁锤》,被王丰之将其分别钞在了《未刊聊斋志异稿》其他三卷之中,有几篇被改易篇名。
王丰之为什么不依照《聊斋志异拾遗》的原貌,将这二十七篇作品统录为一卷呢?如果统录为一卷,甚至可以表明王丰之首肯《聊斋志异拾遗》一书,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些作品是假托蒲松龄之名的赝品。
笔者以为,王丰之之所以要打乱《聊斋志异拾遗》一书的编次,将此二十七篇赝品分钞于四卷之中,原因就在于他同样知道这部《聊斋志异拾遗》是假货,不是已经刊刻的《聊斋志异》之外的遗篇。如这部《聊斋志异拾遗》首篇《傅于槃》,所记为清开科状元聊城傅以渐事。傅以渐字于磐,此书则误“磐”为“槃”,是《聊斋志异拾遗》的作伪者实不知“槃”字为蒲松龄之父蒲槃的名讳一事。但王丰之的祖父王敬铸是以整理蒲松龄著述而闻名的清末大家,他所整理的蒲松齡著作应该就收藏在他们家的天山阁,身为王敬铸之孙,又喜欢舞文弄墨的王丰之对于蒲松龄之父名槃当不会陌生。笔者以为,王丰之将伪作《聊斋志异拾遗》打乱顺序钞入其《未刊聊斋志异稿》,说明他对《聊斋志异拾遗》属他人伪托一事,同样是心知肚明的。
再次是《王再来》《天台道士》《秋水小姐》《孽镜》《吴冷》《血怪》《丰都润城隍》《三绝》《张方海》《那刹》《两铜菩萨》《翠芳》《王寿星》《飞鱼》《原襄敏》《神针》《句隐》等十七篇,出自清人徐昆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柳崖外编》之卷一、卷二、卷三、卷六诸卷。其中《吴冷》原题《吴伶》,“伶”误作“冷”;《丰都润城隍》原题《丰润城隍》,误衍一“都”字;《两铜菩萨》原题《两铜菩》,误衍一“萨”字;《句隐》原题《丐隐》,“丐”误作“句”字。
徐昆字后山,号啸仙,又号柳崖子、柳崖居士等,山西临汾人。因《柳崖外编》卷首王友亮、李金枝二序皆言其为“蒲留仙后身”,后人多云其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2001年占骁勇《〈柳崖外编〉作者徐昆生平考》始确认其乾隆十二年(1747)生于山东济南。徐昆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成进士,乾隆五十七年撰成文言短篇小说集《柳崖外编》,其家刻本贮书楼刻本于同一年付梓。[19]197-202
《柳崖外编》原书十六卷,后来的坊刻本所刊仅原书之半,或题《真正后聊斋志异》,或题《聊斋志异外集》,但其卷首皆题“平阳徐昆后山撰”。王丰之将徐昆所著《柳崖外编》打乱原来各卷编次,钞入其所谓《未刊聊斋志异稿》,其以他人著作冒充蒲松龄遗著的做法同样是十分明显的。
此外,《未刊聊斋志异稿》卷一所录《黄孝子》《李翘之》《护军女》《朱外委》《吕英秋》《王奇》《刘车夫》《空空儿》《冷生》《陈世伦》《粉蝶》《蝴蝶精》十二篇,笔者一时未检得其出处,然由其人名和人物关系可知,这十二篇并无一篇属于“未刊聊斋志异稿”。
王丰之钞录的《未刊聊斋志异稿》,既然以伪作《聊斋志异拾遗》和徐昆《柳崖外编》等别人的小说冒充未曾刊行的《聊斋志异》篇什,这一事实可以说明他确曾有过以别人的作品冒充蒲松龄著作的前科,此事事实俱在,不容否定。
从钞录别人撰作的《未刊聊斋志异稿》《聊斋诗赋词曲》《荆钗记曲》《续农桑经捕蝗法要诀》冒充蒲松龄遗作的事实,可知伪造蒲松龄著作是王丰之其人惯用的手段。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王丰之钞录了题署为“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批”的《闺艳秦声》。因为王丰之作伪的事实俱在,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就是王丰之其人把自己钞录的《闺艳秦声》题署为“蒲松龄遗作”,同时又将《闺艳秦声》正文之后的《评》改窜为“高念东跋”,将钞自《金瓶梅》的三首诗伪造为李尧臣“诗跋”。至于这一作伪的具体经过,笔者前面的论证已经通过他对“高念东跋”的改窜列出了证据与事实。
五、结 语
(一)蒲松龄创作的聊斋俚曲中有《琴瑟乐》一册,并曾为蒲松龄的后人蒲箬等所目见,题名被镌刻于《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这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二)蒲松龄去世之后三百馀年的时间里,除为乃父立碑的蒲箬等人外,没有人能得睹《琴瑟乐》的庐山真面目,更没有人言及它的流传情况,这同样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三)笔者考察发现,天山阁本《琴瑟乐曲》后附的“高念东跋”系改窜《闺艳秦声》后附《评》而成,其题署“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般阳高念东者题于栖云阁”则是改窜《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的题署而成。“高念东跋”不是蒲松龄乡前辈高珩所作的跋语,而是出自后人伪托。
(四)天山阁本后附的李尧臣“诗跋”,三首七言诗钞自《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康熙甲戌中秋后四日 淄川希梅李尧臣跋诗于松阴书屋”的题署是在先有偽“高念东跋”的前提之下伪造出来的,“诗跋”的所有内容都与蒲松龄挚友李尧臣无关。
(五)1923年天津《大公报》连载的《闺艳秦声》题作“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批”,与20世纪30年代传世的《琴瑟乐》内容相同。“高念东跋”与李尧臣“诗跋”出自后人伪托,可证天山阁本《琴瑟乐曲》同样是后人据《闺艳秦声》伪托的赝品。作伪者不可能在持有《琴瑟乐》真品的情况下,还要画蛇添足、费力不讨好地去伪造漏洞百出的“高念东跋”和李尧臣“诗跋”。
(六)天山阁本“高念东跋”和李尧臣“诗跋”出自后人伪托,而且《闺艳秦声》的清初刻本同样并不存在,可证蒲松龄见过清初人阿蒙改编的《闺艳秦声》,钞录此曲并改题为《琴瑟乐》,其子孙误以为《琴瑟乐》为蒲松龄作,将其镌刻于《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的说法不能成立。
(七)20世纪30年代在世的淄川人王丰之,先后为日人平井雅尾钞录过《未刊聊斋志异稿》四册、《聊斋诗赋词曲》二册、《荆钗记曲》二册、《农桑经》一册、《续农桑经捕蝗法要诀》一册。其所钞各本,皆称“聊斋蒲松龄之遗著”。由《未刊聊斋志异稿》乃钞自托名蒲松龄作《聊斋志异拾遗》、徐昆《柳崖外编》并冒称蒲松龄作的事实,可证将自己钞录的《闺艳秦声》题署为“蒲松龄遗作”,同时将《闺艳秦声》正文之后的《评》改窜为“高念东跋”,将钞自《金瓶梅》的三首诗伪造为李尧臣“诗跋”的作伪者就是王丰之其人。
(八)蒲松龄不是由《闺艳秦声》改窜而来的《琴瑟乐曲》(今名《琴瑟乐》)的作者,他创作的聊斋俚曲《琴瑟乐》真本在其去世之初尚存于世,但迄今未见流传,现在到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2]蒲泽.传唱俚曲,怀念故人[J].蒲松龄研究,2007,(4).
[3]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盛伟,辑注.聊斋佚文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
[5]蒲松龄.聊斋俚曲集[M].蒲先明,整理;邹宗良,校注.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
[6]蒲松龄.聊斋俚曲集[M].蒲松龄纪念馆,编.济南:齐鲁书社,2018.
[7]张泰,校注.《聊斋俚曲集》校注[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
[8]郭长海.《琴瑟乐》作者与源流考证[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1,(1).
[9]巩武威.聊斋俚曲《琴瑟乐》两辨[J].蒲松龄研究,1997,(2).
[10]古高阳西山樵子.闺艳秦声·自序[N].大公报,1923-09-04.
[11]黄霖.《闺艳秦声》与“易性文学”——兼辨《琴瑟乐》非蒲松龄所作[J].文学遗产,2004,(1).
[12]杨海儒.聊斋俚曲及其研究[J].文学遗产,1991,(3).
[13]孙巍巍.路士湘先生向蒲松龄纪念馆捐赠文献资料[J].蒲松龄研究,2001,(3).
[14]无名氏.闺艳秦声·后序[N].大公报,1923-09-03.
[15]齐长城外饼伧氏.闺艳秦声·评[N].大公报,1923-09-05.
[16]盛伟.《琴瑟乐》国内藏本与日本藏本校释[J].蒲松龄研究,1989,(1).
[17]平井雅尾.聊斋研究[M].釜山:上田印刷所,1940.
[18]刘阶平.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
[19]占骁勇.《柳崖外编》作者徐昆生平考[J].明清小说研究,2001,(2).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fact that Tianshan Pavilion vision of
Qin Se musical compositions belong to the popular music
written by Pu Songling in disguise
——one of the discriminations about Qin Se Musics author
ZOU Zong-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ianshan Pavilion version of Qin Se musical compositions that claim?蛳ed it was a missing literary work by Pu Songling,started prevailing among the world since 1930s. However,Guiyan Qinsheng published in the Tianjin Dagong Newspaper in the year of 1923 contains the same content with a topic “composed by a woodcutter lived in ancient Gaoyang Mountain Xi,commented by Bingcang Shi lived in outside Qi Greatwall” as Qin Se musical compositions. This present text distinguishes that the attachment at end of the Qin Se musical compositions were rewritten by the postscripts written by Gao Niandong at the end of Guiyan Qinsheng. Moreover,the one who forged the text Qin Se musical compositions as a piece of Pu songs literary work is the copier of Qin Se musical compositions——Wang Fengzhi.
Key words: Guiyan Qinsheng;Qin Se musical composition;Tianshan Pavilion version;postscripts of Gao Niandong;Forged ancient literary work by future generations;Wang Fengzhi
(责任编辑:朱 峰)
收稿日期:2020-08-04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大学2018年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聊斋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RWZD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邹宗良(1958- ),男,山东淄博人。山東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聊斋学会(筹)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与聊斋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