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挪亚方舟”(外两篇)
陈家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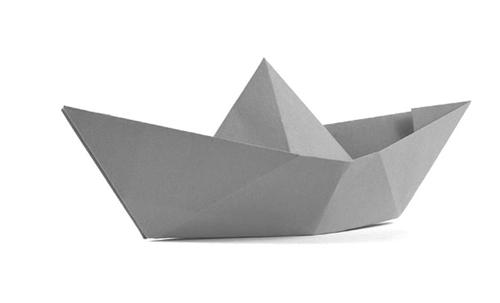
已经很久没有推母亲出去了。原定今天用轮椅推她出去,可是不行,因为我要去大洋镇和同安镇参加首届耕读文化艺术节启动仪式。真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啊。
说实话,有名无实的诸节之于我,如同喧嚣一时的烟花之于我,向来不感兴趣。节,《说文》解释为:约,缠束。以竹节引申出节制、管束。节日,就是自我节制、管束、停顿的日子。目的在于回归道统,永续不竭。那么,在村庄如此凋敝的当下,诸如此类的节,今年办了,明年还能办吗?明年办了,后年还能办吗?节日如果不能像竹子一样根植于大地,亦即缺少百姓的广泛参与(作为主角),它能够接连不断吗?如果不能,那还叫节吗?
每当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早在150多年前,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的这些忧思,都会像春草一样冒出来:“古代的诗歌和神话起码让我们看到,农事曾经是一门神圣的艺术,却被我们的不敬、匆忙和草率弄得面目全非……没有节庆日,没有列队游行,没有庆典仪式,就是我们的耕牛展示大会也不例外,所谓的感恩节也不例外。农夫本来是通过这些仪式表示其职业的神圣意义,或者以此来想一想农事的神圣起源的。现在引诱他的却只是收获的奖金和宴席了。”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种古训由于失去了它的语境,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劝导功效。正如农耕时代的生活状态已经发生了颠覆性变化,锄头、犁铧、镰刀和耕牛已经退出了日常生活,就像上了年纪的老农蜷缩于老屋偶尔举目远眺荒芜的农田,如同躬身探望罹患绝症的至亲,除了惆怅,除了叹息,便是茫然不知所措。如今的中年人曾经依赖于田园生活,他们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结下了不解之缘,山村巨变而衍生的乡愁,召唤他们回望,甚至萌生了挽救故乡的使命,比如邻村盘富的一批中年人便是如此。我敬佩他们的情怀,更敬佩他们的举动——自发成立村庄复兴基金,复垦荒芜近20年的稻田,引入传统稻种,进行传统耕作,试图还原童年印象——村庄的原初模样——最亲切的景观莫过于金色的稻浪,最宏大的叙事莫过于馨香的米饭!十几二十年前,他们背离老家与至亲,仿佛一粒带着羽翅的种子,各自御风而行,撒落于都市的某个角落,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拼搏,终于拥有一片比老农田园更光鲜更肥沃的小天地,因而也具备了反哺家乡的能力或智慧——舍得拿出比金钱更珍贵的時间,或驾小车,或乘飞机,洄游似的返回始发地,重拾已被父辈或同龄人撂下的农田与农事。他们的肩膀一头挑着城里的事业,一头挑着老家的期待,累并快活(兴许存在)着。而村庄的症结更在于,除了这些中年人,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与村庄建立感情,并且乐于蛰居村庄过着晴耕雨读的传统生活?村庄如果没有年轻劳动力,生产力何以重建,传统的接力棒交给谁?
今天的仪式由专业公司策划。搭于稻田的舞台,有肥狮表演,有非遗服饰展示,有儿童合唱……看热闹的很多,既有不再耕作的农民,又有不谙农事的城市看客,还有小飞机似的航拍器。人头攒动,车水马龙,堪比过年。在大洋镇,与彩色稻田相对的一丘长满野草的田地里,一头羊,一头牛,它们可能仍在反刍或酣睡,却被人早早地拉出来,钉在田里。它们仿佛成了明星,许多人簇拥着,又是抚摩,又是抓拍。陷于都市情调包围之中,它们焦灼地转圈,终究不能挣脱开来。稻田里摆着若干农产品,被称为市集,观看寥寥,买者更是无几,唯独一位老农面前摆放的五六只金毛狗——像狗,像猫,又像黄鼠狼,最为打眼;但是,不少猎奇者询问一番,拿起手机矫情地摁一下,便像流水驮着落叶过去了。
耕也好,读也罢,过程都是缓慢的,内容都是质朴的,如同番薯一般的农家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而又芜杂,琐碎实则精细,滋润并非功利。然而,不能不说,匆忙和草率,已是这个时代的“重症”之一。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多少有识之士致力于“药方”的寻找,而且从未停止过。
“谁找到故乡,谁就是胜利。”无论世情如何变幻,故乡酷似硕大的石榴,储满了田园、溪流、粮食、野果、农具、风习、乡党……只要找到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能获得俄国诗人叶赛宁所断言的“胜利”——物质的,精神的,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那么,乡愁也就不至于加剧为“乡痛”(语出澳大利亚哲学家阿尔布雷克特)。
我坚信,在中国,村庄才是我们的“挪亚方舟”——不论是已经盘踞都市的,还是依然困守村庄的,终究是个命运共同体。
采 柿 红
现在是采柿红的黄金期,这也是城里人去乡下最乐意的趣事。亦非随身带方凳和盛器。儿子拿着竹叉——随手揭竿而已,并非从前专用的那种柿叉。我空手尾随。柿树就在水井附近的园地里,从家里出发,绕过一个小小的转角,即可遇见。我小时候管园地叫后头坪。那是我们家最大的一块自留地;但它并不肥沃,土壤是黄褐的,固执的,好像不大愿意开化。每一季耕作,我们都寄予厚望,但它从来没有奉献过丰盛的果蔬,抑或番薯,乃至于改作田地的水稻。它的存在,俨然法国作家大仲马代表作《基度山伯爵》结尾的那几个字:等待和希望。每一次前往那里,我都一如既往,满怀希望。这一回更甚。
儿子走前头,倏地爬上布置于埂壁的乱石阶。在石阶顶端,别人的番薯地边沿,亦即小径的草丛,他瞥见一朵淡紫色的小花。儿子当即被吸引住了,蹲下观察。如此纤细,居然托起一朵那么漂亮的花,瞬间使他讶异。它细若衣线,长一小拃,小叶四片,除了盛开的一朵花,还有两个待放的蓓蕾。他直呼它喇叭花。亦非不赞同。乍看颇像番薯花,毕竟它的旁边确实蜿蜒着几条番薯藤。眼下正是薯藤着花的季节。仔细观察,它与番薯藤又毫无关联,纯属独立的生命个体。我拿出手机,利用辨识软件“形色”,拍摄一下,名曰:五裂叶薯。儿子端详一番,狐疑地说,从它的叶片上看,看不出所谓的五裂,倒像小小的心脏呢。他打开手机里的QQ浏览器,读取的结果是:小心叶薯。很显然,这一雅称更接近它的外貌特征,也更接近儿子的浪漫想象。该词条同时告诉我们:这种野花,至今未有人工培育。
再上几个台阶,就是我们的园地。严格地说,如今的它,更像一个苗圃,布满杂七杂八的树木,有红豆杉,有罗汉松,有板栗树,有青梅,有桂花,枇杷,还有青花梨树、柿树。这些都是大哥亲手所植,像是有心栽花,更像无意插柳,缺乏主题。至于柿树,也是矮化的外来品种,它和板栗相似。矮化似乎成了潮流。嫁接或杂交技术已经演进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高矮胖瘦悉听尊便。我多年未曾涉足园地,虽然每年清明节,都去给祖父和二哥祭墓,但从未顺路拐上几步,浑然不知道那里的新世界,竟有柿树,而且如此之大。
柿红不少,站在地上,拽下一枝,即可摘取数个,凳子用不着,叉子也用不着。这些低垂之果,是丰稔之果,是谦逊之果,更是奉献之果。一个家庭需要这种角色,一个民族需要这种角色,一个国家同样需要这种角色。不过,那几个诱惑于树梢的柿红,委实难奈其何,唯有望之兴叹的恳切。无处觅食的红嘴蓝鹊,它们兴许正在远处窃喜呢。我抓住树干,既像尾生抱柱,又像螳螂捕蝉,试图攀爬,但被他们拽住了——认为此时此刻的我,好像是刚刚从树上来到地面的树懒,已经笨拙得不行了。我向他们述说当年的骁勇——在你们这样的年龄,所有的树,即便是比这高大几十倍的柿树,我也像猿猴一样如履平地,摘得星辰般的柿红——他们将信将疑,依然认定我年纪不轻,手脚也已退化——给我的直觉反而是:他们自己不会爬树,就以为我也不能。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他们矫捷如猿!爬树与游泳同样重要,前者使人跃升,后者使人沉潜,它们都可以使人成为佼佼者。它们应当纳入学校的体育科目。凌空和戏水是孩子的天性,学校要有可以攀爬的大树,可以畅游的场所。1998年长江流域暴发特大洪水,平原上的人们,不少幸存者,就是爬到树上,让树成为自己的挪亚方舟。毫无疑问,爬树是一件美妙的事,说不定有时也会产生类似梭罗在《远行》里的那种感慨:“我们经常在大地上留下自己的脚印,却很少涉足山峦。我想如果山的高大让我们望而生畏,我们可以通过爬树以弥补高度上的不足。”
柿红采够了,顺便拔些鬼针草。儿子仍然惦着那朵小花,返回时,他又停下,用竹叉的尖端挖掘。过于纤弱,不忍细看,移植恐怕难以成活。我劝他放弃,他偏要。小心翼翼地挖起,择片柿叶折成漏斗,把花放入其中,揸了两把母土培上,又折了一茎草芯扎好,带回,浇了水,安顿于纸杯。儿子向来喜欢花草虫鱼,上学途中,邂逅一朵小花,或者一只小虫,他就会流连忘返!
父亲依次察看了所有的房间。临走时,他凭栏俯瞰,发现天井花坛的山茶花被杂草围困,他欲去拔除,被我制止了。他又嫌阳台的花钵长了野草。所谓的野草,已然经年,只是未被正视罢了。我用“形色”辨识其中的一种,鉴定结果居然是稻。荒唐!软件竟也忽悠。我叫儿子来辨识,结果却是鼠尾粟。我当然相信后者,毕竟它形神兼备。同时辨识了另一种:落地生根。父亲终于知晓这两种看似熟稔的杂草的高姓大名。
来到水沟边,父亲猛然发觉那棵树长得奇快。我以为是杜仲。父亲则不以为然。经“形色”坐实,是杜仲。父亲笑着说,原来是宝贝啊,应当保留。我说,凡是树,最好都保留,人和树过不去,最终都是和自己过不去。
阿禄见我持宝似的捧着柿红,不屑地说,唉,你那柿红有点涩,不好吃,白摘了,仁庚那兜是朱柿,是老品种,它的柿红才好吃呢,你们去摘。
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我们不敢。
仁庚不想摘了,他都叫我去摘呢,你們大胆去。今天,他也不在家。我刚去摘过,确实好吃。
但是,仁庚没有叫我们去摘。多谢你告诉我那兜是朱柿。原来还有老品种。
老品种就剩这一兜了。朱柿不仅柿红最好吃,柿饼也最好吃。
嫁接可以吧?
当然可以。谁会去嫁接?再不嫁接,真的要绝种了。即使嫁接了,长到以前那么大的,也要四五十年,你我恐怕都见不到了。
我们的后代总可以享受到吧?
当然可以。
这时,不远处的柿树上突然射出几枚尖锐的蝉鸣,同时射出一羽椋鸟。随着椋鸟的远去,蝉鸣在我们诧异的注视中渐渐消失了。对于鸟,我素来敏感,参加工作之前,在老家的日子里从未见过椋鸟。
今夜清光似往年
不知何故,最近两三个晚上,和太太散步,总要找星星,而且从月亮旁边找起,目力不逮,也不罢休,还要央求她帮我继续找。毫无疑问,她找的结果与我的不相吻合。于是,我不时仰望璀璨的星空——寻思,神情兴许颇似年轻人面对手机屏幕——只是,我的嘴唇并不像他们那样变幻多端——仿佛发情的羊牯觊觎近处的羊母,一脸傻相,薄薄的嘴唇噘得千奇百怪。今晚,自然要多看几眼月亮,纵使我的想象超不出古人咏月诗词里的丰赡的比方,竟也把自己遣回童年。小时虽识月,未曾“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但是,终究没有将遥远的月亮与馋人的月饼联系起来。
散步返回,我独自拐去住处楼下的姐妹便利店取了月饼——太太通过网络,在一家微店订制,快递而来的冰皮月饼。是的,月饼,但它的确不一般——前缀如此之多,又是如此之新:网络、微店、订制、快递、冰皮。真是孤陋寡闻,这种月饼,我是头一回见识的。它活像一枚枚退役的玉玺,小巧玲珑,如白璧,如玛瑙,如琥珀,却糯软。
二嫂被女婿接来——头一回在县城过中秋。家庭小聚之后,个个像采蜜归来的蜜蜂,朝着同一方向——母亲住处聚集。
母亲的晚饭是二嫂喂的,但吃得不多。征得母亲同意,我接着喂了一枚冰皮月饼——拿箸搛起,一点,一点,又一点,如同明月临近拂晓,渐次食去。大家各尝些许。尝罢,所有记忆的角落似乎都被它照亮了。我说,小时候,我们家的中秋,只有月亮,没有月饼,好在总有半番(一种菜鸭,多杂色)煮粉干,有早米粿;我吃到月饼,是从长庆乡人民政府考到县委办公室的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的中秋。秀珠说,我头一回见识月饼,是1990年在梧桐中学念初一的时候,班主任自主动用班费,给每个学生分发一块月饼(全校唯一);许多人当场独享,我舍不得吃,撕了几张作业纸,把它包得严严实实,带回家交给娭媪;她因此见识了月饼,把它切了,一人沾一点,我们胜似采蜜。阿六说,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也就是1994年在城峰中学教书,中秋那天,抱了一头很大的全番(一种菜鸭,多纯白,体形比半番大得多,类似中等的家鹅)回家,娭媪煮了一大鼎粉干,全家吃得很开心。秀珠说,我也记得那一回,特别好吃,后来再也没有尝到那种滋味了!
母亲问,你今晚吃什么?我说,一般的饭菜。有掼肉吧?无。为什么?不稀罕。最近猪肉大涨价,是吗?正是。涨了多少?现在城关肉价大体是:每斤瘦肉23块,排骨32块,猪肚45块,猪脚23块,五花肉25块,均比年初高了四成左右。少见的。有个屠夫告诉我,最近肉价是20年来最高的,可以算天价了。什么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去年8月份,许多地方爆发非洲猪瘟,猪死了很多,同时造成有猪的地方猪运不出,缺猪的地方猪进不来,市场无法正常调节;第二,许多地方为了保护环境,关了很多养猪场;第三,许多地方大搞所谓的美丽乡村,不让农户养猪,散养猪大大减少,肉价自然就蹿上去了。富不离书,穷不离猪,怎能不让农户养猪呢?被她这么一点拨,我不仅想起了“家”的结构及其寓意,而且复述了拙著《将心比心》中《掌控》一文的相关阐释。养猪是件大事。确实是,1959年,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头版出现了“猪为六畜之首”六个大字;农村许多门联也经常出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是农民最朴实最基本的愿望。不过啊,猪也是韭菜命,好运总是不长,猪肉价涨涨跌跌,无从摸索,不像海水,几时涨,几时退,有定律。普遍认为:养败不养兴(这是农民总结的养猪经验:肉价大降——淘汰母猪——生猪减少——肉价大升——纷纷补栏——母猪大增——生猪过多——肉价大降)。农村不像城市,它有自己的规律,不该折腾,一折腾,百姓就受苦了。是的,不该折腾,任何事都不该折腾,都要听民意,顺民心。老话早就讲过,宁可犯天条,不可犯众怒。
“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父亲虽已驾鹤西游,但我依然为他留了一份冰皮月饼。父亲会回来品尝吗?他若不回来,冰皮月饼滋味再好,它在我的味蕾中也显得寡淡;他若不回来,今夜月亮再圆,它在我的心目中也觉得亏食。
曾有智者预言,善人寿终,皆化星辰。对此,我深信不疑,尽管我不是唯心主义者。“三五夜中新月色,一千里外故人思。”呜呼,今夜,父亲,今夜的父亲,您究竟是浩瀚天宇中的哪一颗星星呢?
责任编辑林 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