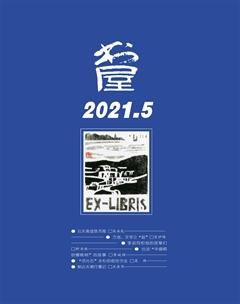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
秦行国
广辉先生的大作《新经学讲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终于问世了,这对我们这些尚在门墙之外的学生来说,是一件盛事。如若记忆不误,先生在文字或是演讲不同的场合中,都曾提到“新经学”这一尖新的观念,强调中华文化的“根”在“六经”,“魂”在“六经”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观,可谓三复斯言。《汉书·薛宣传》言“经术文雅,足以谋王体、断国论”,经学本身是经世致用之学,如何在獭祭般的文献中勾稽、抽绎出一套成型的观念或思想并资于世用,这也许是经学研究一个比较重要的面向。明代陈子龙曾在《皇明经世文编》的序中表达对遗文散佚无人加以总结的隐忧,他认为此种情形会造成三患,“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世无实学”,经学遗献至今日亦面临这一问题,《新经学讲演录》隐约带着“经世文编”的影子,并以世之“实学”的面目示人,给人以相当大的启发。
经学讲演性质的著作,在新旧激烈交锋的近代可以说是相当璀璨。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章太炎的《国学概论》、范文澜和周予同的《群经概论》等都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大体上皆在经学与经学史之间徘徊,或固守经学的老传统,如皮锡瑞、刘师培、章太炎,或将经学剥离、瓦解成历史,如范文澜、周予同。在另一方面,近代对经学的批判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五四时期,胡适发动“整理国故”运动,顾颉刚兴起“古史辨”运动,都试图将经学从中国历史中抽离出来,彻底否定其价值。《新经学讲演录》反思这一股风气,不株守以往之研究路数,明确肯定经学的价值、意义,同时亦主张因应时代,为世所用,可谓是守先待后。“新经学”新在何处?诚如书中所言,“新经学”的“新”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理论视域新,可以从价值观、诠释学、“文化记忆”的理论研究经学;其二,时代意识新,“经以载道”,研究经学的目的在于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并服务于时代需要,使得经学中的智慧和经验融入今日的时代意识中;其三,破译思路新,经学研究中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今人可以继承前人进行突破;其四,研究取舍新,抓大放小,抓住经典的主旨大义,舍弃一些琐碎的考证;其五,治学工具新,善用“E考证”的方法去搜集资料。这些新颖之处,在新与旧、中与西、今与古方面进行了较好地融通,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新经学讲演录》在内容的爬梳上亦是颇见层次的,其分为综论、分论、补论三个部分,综论部分分别对经与经数的流衍、中国经学发生的历史背景、六经的基本内容与价值、先秦儒家对经典的诠释加以考辨、论述,分论部分分别对《尚书》、《礼记》、《诗经》、《周易》、《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的主要内容以及其所展现的思想进行了总结,补论部分讨论“新经学”与“人文信仰”的重建问题。
《新经学讲演录》中的文字体要而深峻,《文心雕龙》说“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如果用此句中的“雅义”与“清文”来概括其风格,还是很合适的。一则,《新经学讲演录》皆是以中国传统重要的经典为根基,赓续朴学的气息,提炼出其中蕴藏的价值与意义,并能与现实世界相参酌,此乃“雅义”;二则,《新经学讲演录》以讲演的形式,将许多艰深的问题讲出来,而不是写出来,摆脱了如今干枯的论文格套约束,使得整个文章文辞活泛,气脉浑然,此乃“清文”。我们可以将“雅义”与卡西尔的“符号宇宙”对照起来理解。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其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人实际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而非一个简单的物理宇宙,语言、神话、艺术、宗教、历史等乃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而已,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如此看来,人书写的历史并非属于“物理宇宙”,而属于“符号宇宙”,经学实际上亦是“符号宇宙”,在其广大的网络之中,充溢、附带着各种符号、意义。梁启超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批评清儒时说:“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疼,结果还是提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钱穆在《中国思想学术史论丛》中亦说:“乾嘉以下,清儒治经,自标以为汉儒之经学,然于古经籍大义乃及汉儒通经致用之精神,渺不相涉,既已漫失其纲宗,徒于散末处枝节分别,以考以辨,用力虽勤,而所得实觳。”梁氏、钱氏之所以对清儒治经有“玩弄光景之具”“所得实觳”的感受,在我看来,清儒完全将经学视为质朴的“物理宇宙”,而非有意义的“符号宇宙”,重视经学中的史实,而忽视经学中的价值。《新经学讲演录》实乃论经,而非解经、注经、治经,十分注重经学的价值与意义的阐发与挖掘,强调“经学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考证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握经典的主旨大义”,在讲解诸经时,特别对其中文化精神进行了总结,并与现实关联在一起。譬如《尚书》中的“禅让”、“协和万邦”、“敬畏”、“德治”理念,可以作为现实政治制度与国际关系一种启发性思想资源;礼学中的礼仪教化功能,可以吸纳进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礼仪规范;《诗经》中的审美功能,可以熏陶人的情志,培养人的审美情趣;《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对于身处“忧患”之中时,可以当成考验和磨炼,没有“忧患”时,亦当居安思危;《论语》中的“孝悌”、“仁爱”、“和谐”观念,可以借鉴到如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等,皆可以运用到现代人的身上。这种凝练地勾勒,使得经典中的思想图景一下子清楚起来,经学的“符号宇宙”即显现出来。
《新经学讲演录》亦在诸多方面具有“清文”的格调。如前所述,《新经学讲演录》是讲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作为讲义,其不必拘于各种僵硬的形式,读起来让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先生就在眼前“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最近这几十年来,人文领域的研究逐渐被自然科学研究的指标带着走,越来越程式化、单一化,谈到文章,即是鳞次栉比的学术论文,这当然说明学术走向了规范,但反过来看,实则形成了牢笼。我们看以往能立言的学者,并不都是以洋洋洒洒的文字名世,或一通信札,或一阕诗文,或一则短小的随笔,譬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一条简短的小故事即能让后世反复沉吟、玩味,张岱的《陶庵梦忆》,一些零碎的故国景致,读起来兴味盎然,《尚书》说“辞尚体要,弗惟好异”,即是如此。《新经学讲演录》另行他途,并不按照学术论文的单一规范来行文,这在文章体裁上亦是一个典范。其次,从内容上看,《新经学讲演录》中插入若干历史故事,使得厚实的研究文字变得轻灵了许多。譬如在讨论春秋时期,时人利用《诗经》“赋詩断章”的问题时,举出鲁文公在郑国国君宴会上赋诗而巧妙化解外交尴尬情形的故事。譬如在讨论《大学》中“静而后能定”的问题时,举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而魏国统帅司马懿坚守要塞不出,最后迫使诸葛亮退兵回蜀的故事。又譬如在讨论孝道的问题时,举出范滂因陷党锢之祸而主动投案,其母为他送行的故事。除此,《新经学讲演录》亦加入了许多先生的生活经历。譬如在讨论《论语》时,先生回忆起跟他的老师邱汉生先生求教的经历。又譬如在讨论“新经学”与人文信仰时,先生忆及1978年考入社科院读研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下,而等到二十多年以后,先生做社科院思想史研究室主任时,人均收入翻番,而心底产生了社会将会出现人文信仰危机的隐忧。梁启超尝自谓“笔锋常带着感情”,《新经学讲演录》中若干的回忆文字亦使得整篇文章富有感情。
《新经学讲演录》在历史的层峦叠嶂中展示出纷繁的棱角,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之多,并不是此处寥寥数语所能囊括的,读者自可美酒自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