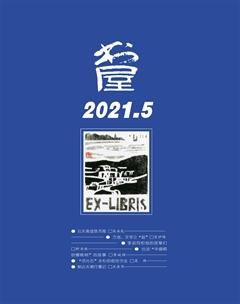汤姆·琼斯:一个私生子的逆袭之路
沈瑞欣
1749年二三月间,伦敦接连遭受了两场地震。英国教会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究竟是何等弥天大罪招致了上帝的怒火?只不过,精明的教士是绝不会把矛头对准自己的。一番思量后,红衣主教托马斯·谢尔克散发了四万份《告教友书》,疾言厉色地声称,伦敦地震的罪魁祸首是一本“邪书”,信徒如不立即停止阅读,第三次灾难还会降临。《老英国》杂志见状也敲起边鼓,怂恿政府明令禁止此书的发行。然而,笃信宗教的先生们虽熟读《圣经》,对人性的了解却不够透彻——禁忌总是甜美的。仅在1749年这一年里,书就重印了四次,手忙脚乱的出版商不得不请求购书者自行装订。那么,到底是怎样一本“邪书”,让教会如临大敌、普通读者趋之若鹜呢?
私生子的逆袭
“邪书”名叫《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亨利·菲尔丁的代表作。这位菲尔丁先生的头衔很是唬人,“英国小说之父”、“英国现代小说三大奠基人之一”、“十八世纪英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照理说,菲尔丁完全可以像他的同时代作家一样,写一写高门大户的绅士淑女,可是不,他选择了一个弃儿、一个私生子作为自己小说的主人公。
“私生子”这个词如今似乎少有提及,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可是个上不得台面的敏感词。尽管自文艺复兴以来,市民文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夫、城市平民开始逐渐取代神和英雄,成为作家着力描写的对象,但以私生子为主人公的故事毕竟是极少数。如果看过这几年大热的美剧《权力的游戏》,我们就会发现,门阀制和父权制背景下的私生子,社会地位极其尴尬。在这部影视剧中,私生子即便知道父亲是谁,也不得使用父亲的姓氏,而是有一个私生子专用姓氏追随一生。出生在北境的私生子全都姓雪诺,就像天上落下的雪花,没有来处,没有归宿,没有荣誉可以捍卫,也没有家产可以继承。所以,当全家人都在大厅欢宴的时候,主人公琼恩·雪诺只能独自缩在阴暗的角落,羡慕着不属于自己的热闹。甚至是作为质子的席恩·葛雷乔伊,也总是嘲笑欺负琼恩。眼看拥有婚生子女地位的兄弟罗柏即将当上城主,姐妹珊莎和艾莉亚也会成为名媛贵妇,没有立足之地的琼恩只能弃绝身份、亲情、欲望,投奔守夜人军团,在绝境长城之上熬过苦寒,全力抵抗北方蛮族和怪物的进攻。
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主人公汤姆·琼斯的处境比琼恩还要尴尬。琼恩至少被城主认领为自己的私生子,但说到汤姆的父亲,有的只是些不无恶意的揣测。婴儿汤姆是在乡绅奥尔华绥的床上被发现的,有人说他是奥尔华绥本人的私生子,也有人说他是女仆珍妮·琼斯和塾师巴特里奇苟合的产物。虽然,汤姆在奥尔华绥的教养下成长为一个好心肠的漂亮青年,但他始终洗不脱出身的污点。庄园主魏斯顿本来把他当成一同宴饮游乐的知心伙伴,可一发现他竟敢肖想自己的女儿苏菲亚,马上对他破口大骂。女仆昂诺尔大姐也敢对他表示轻蔑:“论出身他可比不上我——我的父母还正式结婚的呢,我是诚实人家的孩子。”
对保守的批评家来说,汤姆的存在本身已是“败德”的明证,这样的人是不配有什么好結局的。偏偏到了菲尔丁笔下,汤姆硬是走上了一条逆袭之路。养父奥尔华绥疼爱他,美丽善良的富家小姐苏菲亚爱慕他,就连奥尔华绥嫡亲的外甥布利非也嫉妒他的好运。当然,因为布利非的恶意中伤,奥尔华绥一时糊涂,把汤姆撵出了家门,让他在外面颇吃了一些苦头。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收获大团圆结局:原来,汤姆竟然是奥尔华绥的外甥、布利非同母异父的哥哥。奥尔华绥查明了汤姆的身世,也顺带拆穿了布利非的诡计。于是,汤姆欢欢喜喜地和苏菲亚结了婚,还成了奥尔华绥和魏斯顿两家田产的唯一继承人。不体面的私生子到头来却成了富甲一方的体面绅士,这种情节显然对劝人修身节欲毫无助益,也难怪道德家们要对此书嗤之以鼻了。
毒舌大师的风俗盛宴
触怒道德家们的不只是汤姆的逆袭,还有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无情嘲弄。与后辈巴尔扎克相同,菲尔丁以呈现整个社会的风俗史为己任。在这部长达六十二万字的巨著中,活跃着不下五十个人物:地主、贵族、流氓、士兵、伪善的神学家、戴了绿帽子的丈夫……这些人物轮番登台表演,以自己的言行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丑恶,讽刺了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虚伪与贪婪,下层人民的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就像菲尔丁自己在第一卷开篇所说的那样,“一个作家不应以宴会的东道主或舍饭的慈善家自居,他宁可把自己看作一个饭铺的老板,只要出钱来吃,一律欢迎”,他力求为读者献上一道社会风俗史的盛宴,向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不过,对于菲尔丁来说,当代流行的“零度写作”是无法满足他招徕读者的热情的。所谓“零度写作”,是指作者在文章中不掺杂任何个人想法,将澎湃饱满的感情降至冰点,人物的功过是非任由读者自己去评说。以饭铺老板自况的菲尔丁生怕读者错过了真正的美味,情节进行到刺激处,他总是忍不住跳出来介绍菜品的妙处。为了刺激读者的味蕾,他还不时贡献几句毒舌金句,让这道盛宴更加辛辣爽口。
写到奥尔华绥妹妹的假正经,他吐槽说白丽洁小姐“尽管并不漂亮,可她一举一动还是小心谨慎,处处留神,仿佛自己随时都面临着堕入为所有女性设下的各种陷阱的危险”,而谨慎往往抛下那些男人倾心渴慕的美貌女子,“却经常守卫那些德行更高的女人——也就是说,那些男人敬而远之(想必因为没有成功的希望),从来不敢追求的女人”。他也讽刺了布利非生父的处心积虑:此君追求白丽洁小姐,是为了跟对方的房屋地产联姻,只要能得到奥尔华绥的遗产,“不管是亲近只猫还是亲近一位白丽洁小姐,在他看来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魏斯顿的老糊涂:他逼女儿嫁给布利非,对女儿的痛苦视若无睹,“他感到的不安也就相当于一个看见自己骗到手的可怜的黄花姑娘初次听到接客而惊慌失措时的老鸨”,“只是老鸨逼姑娘接客是有利可图的,而做父亲的逼女儿去干这种和卖淫相差无几的勾当(尽管他也许糊里糊涂地以为并非如此),实际上却什么好处也捞不到”。类似的金句在全书中比比皆是,菲尔丁将英式嘲讽运用得炉火纯青,每句吐槽都能搔到读者的痒处,小说也因为这些热辣辣的讽刺变得更加好读。
西方文学史的重要一环
挑战世俗道德也好,金句频出也罢,都只能够让一本书流行一时,不足以成其伟大。《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主要还是因为它继承了西方文学的传统,同时也为后来的写实作品提供了新的范式。如果说西方文学史是一条长长的链条,那么此书就是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在书名中用到“历史”二字,足见其野心,也揭示了此书对西方史诗传统的继承。小说借鉴荷马史诗,插入了祷词、颂词、奇异的比喻,文中几次冲突都因琐事而起,描写却气势磅礴,与史诗中的英雄战斗相仿。例如巴特里奇夫妇之间因为出轨问题的血战;身怀六甲的毛丽化身亚马逊女杰,大战觊觎她长衫的泼妇;汤姆和毛丽被布利非撞破私情后,在小树林里发生的争斗。菲尔丁借此糅合了史诗的悲壮色彩与市民文学的喜剧色彩,使得古老的史诗传统与方兴未艾的写实思潮相映生辉,焕发出一种新奇的审美效果。
除了史诗传统,菲尔丁还充分吸收了“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模式。“流浪汉小说”诞生于十六世纪中叶,在这类小说中,主人公往往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离家外出,在漫游中历经各种奇遇,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命运有起也有伏,最终功成名就。这与汤姆的经历丝丝入扣。但菲尔丁并没有止步于模仿,还在“流浪汉小说”体例之外加入了“突转”与“发现”的戏剧因素。在《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无巧不成书的“突转”与“发现”总是出现得很及时:当初恋情人毛丽成为汤姆和苏菲亚爱情道路上的绊脚石时,汤姆便凑巧地发现她在与别人私通;当汤姆因为刺伤费兹帕特利入狱时,又凑巧地发现费兹帕特利的情婦是他传闻中的“生母”,他的身世也因此水落石出。有了这些“突转”与“发现”,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急转直下,小说也变得更加烂漫和轻盈,不再像需要一定阅读门槛的严肃文学,更像可以为普通读者消闲解闷的通俗小说。
当然,就像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样,《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也是说不尽的。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你可以享受到酣畅淋漓的乐趣,也可以与整部西方文学史悄然邂逅,你甚至可以从其中找出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影踪。关于这本书,另一位英国文学大师萨克雷的评价是极为恰切的(他的《名利场》或许也从中吸收过养料):“每一情节都有前因后果,不带偶然性,它们对故事进程都起了推动作用,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卓绝的(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字眼的话)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