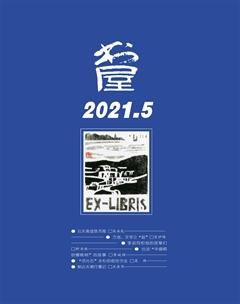无可逃遁的思考邀请
朱奇莹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是在《单读》杂志的主编吴琦与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之间展开的一场两代学人的对话。通过北京访谈、牛津访谈、温州访谈三次访谈,吴琦向项飙述说了一些当前青年的迷思与对一些具有社会性普遍意义的问题的见解,而项飙教授则从自己的个人生活经验出发,向读者陈述出他对于人文社科工作者、学者的一些思考。吴琦和项飙的谈话,就像许知远在序言中用以描述《为了以色列的未来》的感觉一样,“提问朴素却精确,回答高度个人化又极富延展性”,“它既镶嵌进具体历史情境又随时会通向一个意外的方向。它将个人思想、时代精神、众多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这是一种对话形式的示范,也可以说,它创造了一种对话形式的例外。项飙的种种言谈,与其敏锐的思想相携而行,将自我经历问题化,是认真的自我总结,也是深刻的自我反思,是对小世界的精准描述与切身观察,也是对个体如何与他者、与社会、与大世界盘根连接的真诚思考。
项飙意识中的谈话对象和期待中的读者自始至终都非常明确,他希望自己面向那些更具体、更实在的具有多元社会身份的“知识人”,面向那些一直保持着读书和思考习惯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是“针对青年”、“回应青年”的。这种谈话意识,我想首先来源于他自身作为一名社会研究者的自觉。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做思考工具的孵化器,不是给读者什么结论,不是做宏观而抽象的判断,而是通过很小的分析,去激发读者、提醒读者,帮助读者思考如何找到介入社会的具体方法。因此,谈话的线索之一始终是知识如何更有效地介入社会,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成为有效的工具去帮助年轻人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项飙强调理解世界必须从自身的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来理解。通向世界的途径就在自己的“身边”和生活世界之中。如果跟周边的人、生活的世界关系不清楚,人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其他人都成了利用工具。在具体的理解方法上,项飙把乡绅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引入自己的实践。他指出乡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扎根之地的情况摸得很熟,能够形成一个实证的、系统的、内在的叙述,不是靠外来的逻辑推演,而是行动者自己对生活的描述。
这种方法的提出当然首先呼应着项飙对自己身处的当下知识环境的反思和对现代职业化知识分子的某种现实批判,即在学校整体呈现公司化、专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学者们的学术话语也呈现着某种分裂的“自足”的悖论,一方面缺乏着对自己身边的观察兴趣,另一方面又继续着自知空洞和功利性的学术生产。当知识分子自身已然“脱嵌”于与周边现实世界的内在连接,不接地气,不能从非常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讲事情,而只钻营于无机且缥缈的专业话语体系生产,理想意义上的社会动员的工作自然无人承担也无法承担。在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进程中,“悬浮”心态下的人们都显现出群体性的症候式的或保守或激进的人生态度。
然而,站在自己专业的立场上,项飙并不希望年轻人把社会科学当作寻找答案和解决方案的一个路程,他提醒年轻人,社会科学是给普通人提供观察世界、为人处世的办法,不是通过简单的道德教化,不是期待规律的发现和依从,而是需要通过分析,去找到自己理解世界的角度和位置,形成对世界充分理解的图景,由此进一步去创造新的现实,去改变世界。在項飙看来,整个社会科学就是学习培养主体性。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特殊”,而是说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只有由内而外地切入其中,把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想透,学会由点及面地分析社会生活中的那些复杂性、多面性,才会形成具有冲击力的内容,才可显现出社会科学的“深刻性”所在。这也是项飙所谓的“进入历史的方法”,进入历史不是将历史和当下的事实本质化,而是从当下的矛盾中出发进入历史关系之中,形成对当下和自身的历史性的理解。
把自己作为方法,把个人的经历问题化,怎样从经历到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这场谈话向读者发出了无可逃遁的思考邀请。从自身出发的沟通,不是对外的封闭,不是向内的自恋,而是每个位置都成为一个小的中心,是汇集的地方,像一个穴位,贯通着全身又塑造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