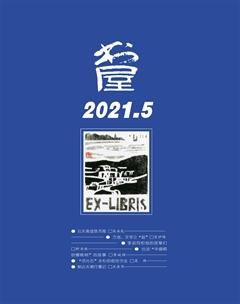李叔同和他的侄辈们
钟书林
李叔同(弘一大师)是一位很注重亲情的人。无论是在家,还是出家,都能一以贯之。这对于出家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李叔同青年时代,虽然因为母亲的丧葬一事与仲兄李桐冈有过一点矛盾,但此后兄弟间的书信往来还是不少的。从这些书信中,完全可以映照出他们的手足之情。他们的后辈李孟娟说过:“虽然大家庭老一辈的嫡、庶间会有些矛盾,他们兄弟间一直是同多异少。”李孟娟以一封书信为例,见证了他们兄弟之间的深情。1927年8月间,李叔同拟回天津老家,仲兄李桐冈接到信后,非常高兴,随即给李叔同回信说:
三弟如晤:获晤手书,得悉弟有意返津,欣慰之至,兹特由邮(局)汇去大洋一百元,望查收后趁此天气平和,交通无阻,即刻起身回家,不必游移,是为至要。至居住日期及衣服、谢绝亲友等项事,悉听弟便。(李孟娟《弘一法师的俗家》)
从“悉听弟便”中,即饱含着仲兄李桐冈的一片恺悌与慈爱。紧接着,李桐冈又叙说全家人得知弘一大师即将返津的消息而兴奋不已。
这次的返津计划,初衷是为仲兄李桐冈的七十寿诞诵经。姜丹书《追忆大师》对此事也略有记载说:“上人本为多情之艺术家,佛教又以慈爱为宗旨,故于民十四五间计及兄七十岁时,犹发宏愿赴天津为之诵经。惜津浦路以时局关系中断,不果行。”终成遗憾。
一
李叔同仲兄李桐冈共有三子三女,长子李圣章(名麟玉),次子李相章(名麟符),三子李晋章(名麟玺)。在侄儿辈中,李叔同与李圣章、李晋章默契较深,关系较密。
李孟娟说,李晋章是和弘一大师晚年联系最多的一个晚辈,替弘一大师办事和向各方面介绍弘一大师的近况,代为购物、寻物、转信和代刻图章等。李晋章与弘一大师有着颇多相同的兴趣。换言之,弘一大师的艺术造诣与人格魅力对李晋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据李叔同儿子李端《家事琐记》记载,李叔同离家后,他原在天津老宅的“洋书房”,主要由大侄儿李晋章使用。李叔同从日本回国后,经常在这间“洋书房”里工作和接待宾客。“洋书房”早年挂过李叔同留学日本时画的日姬裸体油画,到李端长大以后,“洋书房”的书橱中还摆有李叔同贴来信的册子、用过的碑帖等,李叔同出家后,“洋书房”仍保持旧状,没有改建。居住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李晋章的成长不免受到叔父的熏陶。他们叔侄的共同兴趣表现在多个方面。
其一是话剧。李叔同是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他组建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上演第一部话剧《茶花女》。李晋章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南开新剧团活动,曾和周恩来等一同演过话剧,在《恩怨缘》一剧中,李晋章扮演算命先生,并做了大量后台剧务工作,可见他对此事的热衷。
其二是篆刻。李叔同篆刻独树一帜,技艺精湛,他亲自发起成立继“西泠印社”之后的又一印学团體——乐石社,定期雅集,并编印印社作品集和史料汇编,开近代篆刻风气之先。李晋章一生都在天津银行界服务,业余之暇,在故居“意园”和“洋书房”内书画刻石、养鸽养花。李叔同出家后所用印章,多出自李晋章之手。现存的有限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们有关印石切磋和交往的片段。如1934年冬,弘一大师给李晋章写信,信中请李晋章为他刻印二三方;1935年2月,收到印石,弘一大师给李晋章回信,称赞“篆刻甚佳”。
其三是佛教。李叔同皈依佛门,成为著名高僧。李晋章受其影响,也曾自取禅号“雄河居士”,弘一大师1935年以后的书信,不再称其“晋章居士”,而是称“雄河居士”。李晋章还经常遵弘一大师的吩咐,为一些居士转赠物件,往来穿梭于大师与居士之间。如1931年5月8日,弘一大师给李晋章书信说:“晋章居士,寄上写经一包,乞收入。其中《梵网经》多二册,乞转赠幼樵、品侯二居士为祷。”1932年11月10日,弘一大师给李晋章书信说:“前属为姚仲矩居士哲嗣书佛号,乞示其名字。附一纸乞交徐居士。”
终其一生,李晋章对叔父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很注重搜集和珍藏叔父的很多文物,如在小摊上购得李叔同早年画的扇面,李叔同早年送他的在南方定烧并写有“叔同”两字的一对白瓷茶杯,他视为珍藏永久保存。他将搜集到的李叔同文物全都单放在一个樟木箱中,足见李晋章对这些文物的珍视(李孟娟《弘一法师的俗家》)。
1927年8月间,李叔同拟回天津老家一趟,家中因一时经济紧张,难以筹措,但李晋章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兴奋,并主动请缨,很快筹集了钱款。仲兄李桐冈在给李叔同的回信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彼时收弟信时,适麟玺儿、叔谦女在座,余云汝叔有意回家事极可快,惜需款甚巨,余一时手拮据,奈何奈何。家中经准侄喜事,已借贷千余元尚未弥补,一时无款。麟玺闻而雀跃曰:“儿愿筹此款。”……此等小事,本不必令弟知之,但儿女辈体亲之心,盼叔返津相见之切,聊表孝心,亦可爱也。录之以博一粲。
后因爆发战争,交通中断,李叔同返津之愿未能成行,但透过书信,他们叔侄间的浓浓深情却跃然纸上,动人心弦。
殊为可惜的是,李晋章与弘一大师的来往书信,今多散佚不存。《弘一大师全集》仅收录有1931年5月到1935年3月大约共四年的信件七通。其中1932年11月28日,弘一大师写信给李晋章说:
数年前上海报已载余圆寂之事,今为第二次。记载失实,报中常常有之,无足异也。厦门天气甚暖,余唯着一件布小衫,一件夏布大衫,出门须执伞,与津地八月底天气相似。榴花、桂花、白兰花、菊花、山茶花、水仙花,同时盛开。星命家言,余之寿命与尊公相似,亦在六十岁或六十一岁之数。寿命修短,本不足道,姑妄言之可耳。“洗心人读经室”额纸后方,拟留空白尺余,由仁者自跋一段,说明此事之因缘。
面对一再的传闻,弘一大师让李晋章代之出面澄清,可见弘一大师对他的倚重。
弘一大师圆寂后,李晋章收到妙莲法师寄送的讣告和弘一大师圆寂时的相片,李晋章将这一噩耗转告亲友,并寄赠挽联悼念,其文曰:
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
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象真堪痛绝乎。
所有这些,都能够看出李晋章、李叔同叔侄之间的密切交往深厚感情。
二
至于二侄儿李圣章,李叔同与他关系更是显得特殊。一是叔侄两人从小一起玩大,素有佛教的情缘,他们亦师亦友,感情非同寻常。李叔同比李圣章只大九岁,他们叔侄幼时是同玩的小伙伴。李圣章回忆说,他们幼时一起常学和尚念经玩,李叔同扮作“大帽”和尚在那里念念有词,李圣章当小和尚听从调遣。两人用夹被或床单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李圣章上家塾时,李叔同还教过他英语。1927年,李圣章在赴法视察的回国途中,绕道上海、杭州,去看望弘一大师,曾试图劝他还俗回家,叔侄俩在庙内共住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一个多星期里,他们如同幼时大和尚与小和尚的关系那样,李圣章不但没有劝服弘一大师,反而受到他的熏陶和影響。李圣章回天津时,还带回了一些弘一大师手写的经书、对联,以及弘一大师穿过的旧僧袍。
这些举动,引起了李圣章父亲的警觉,他让儿子在北京安心教书,少操心家里的事。对于祖父这样的安排,李孟娟解释说:“事实上,我祖父是深怕我父亲受弘一法师的影响,再出第二个和尚。”从幼时学和尚念经的游戏,到杭州庙内共住一个多星期的佛教体验,可见李圣章父亲的警觉也并不是多余的。不过,通过这件事情,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李叔同与李圣章的关系之近,以及李叔同对李圣章的多方面熏陶与影响。
二是叔侄俩都有极高的爱国热忱。李叔同早年积极投身思想启蒙运动,加入同盟会文学团体“南社”,出家后也一直秉持“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理念,并且提出名论:“我们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释迦如来张些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子守门,吾人一无所能,而犹腼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李圣章也颇富爱国热忱,他在1919年留学法国期间,当时作为中国留学生“国际和平促进会”的秘书之一,积极参与爱国运动,与国内学生运动互通声气,成功阻止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当时,他被推选为同学代表,面见陆徵祥和顾维钧,他甚至预先向同学借得手枪一支,以备一拼,可见他的豪侠之气。1921年李圣章回国任教后,又参与“三·一八”反段祺瑞的学生运动,创办《猛进》周刊,遭到通缉,鲁迅文章都曾记载其事。这样共同的爱国豪情,加上幼时之谊,使他们叔侄俩的关系走得更近。
即使李叔同出家以后,也难以隔断他们叔侄的俗世之情。1922年4月6日,出家已有四年的弘一大师与李圣章尽叙俗怀,情真意挚:
二十年来,音问疏绝。昨获长简,环诵数四,欢慰何如。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以四阅月力料理公私诸事:凡油画、美术、图籍,寄赠北京美术学校(尔欲阅者可往探询之),音乐书赠刘质平,一切杂书零物赠丰子恺(二子皆在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布置既毕,乃于五月下旬入大慈山(学校夏季考试,提前为之),七月十三日剃发出家,九月在灵隐受戒,始终安顺,未值障缘,诚佛菩萨之慈力加被也。出家既竟,学行未充,不能利物;因发愿掩关办道,暂谢俗缘。(由戊午十二月至庚申六月,住玉泉清涟寺时较多。)庚申七月,至新城贝山(距富阳六十里)居月余,值障缘,乃决意他适。于是流浪于衢、严二州者半载。辛酉正月,返杭居清涟。三月如温州,忽忽年余,诸事安适;倘无意外之阻障,将不它往。当来道业有成,或来北地与家人相聚也。音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比年以来,此土佛法昌盛,有一日千里之势。各省相较,当以浙江为第一。附写初学阅览之佛书数种,可向卧佛寺佛经流通处请来,以备阅览。拉杂写复,不尽欲言。
这封书信,是李叔同出家后少见的长札。他向李圣章回顾了自己十多年来的人生经历。所谓“二十年来,音问疏绝”是指自1898年李叔同离开天津南下后,叔侄两人从此就聚少散多,各自或求学,或留学,难得相聚。李叔同虽然分别于1905年(护柩回津)、1910年(留日回津)返津小住,但李圣章多半求学在外,直到1921年从法国学成归国,故才有1922年叔侄之间的长札往来。弘一大师信中说自己在杭州任教六年,门人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又说自己“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这些肺腑之言的倾诉,足见他和李圣章之间虽然“二十年来,音问疏绝”,但一如既往饱蘸着难以割舍的深情。
1924年6月21日,弘一大师给李圣章书信说患病,“谢客养疴”,但在信末却格外提及说:“掩室已后,仁者及其他至友数处,仍可通信,惟希仁者勿向他人道及。以此次返温,知之者希,欲免其酬应之劳也。”这份叮嘱,叔侄浓浓的旧情悄然流淌其间。
弘一大师与李圣章往来书信,迄今发现的仅有十七通,主要是身在菲律宾的传贯法师向陈慧剑先生提供的材料,时间集中于1924—1927年间。从现存这些书信来看,李圣章在这段时期主动承担起弘一大师的物质供养。如1924年3月11日弘一大师给李圣章书信说:“今犹有余资,他日须者,当以奉闻。”1924年4月17日书信:“圣章居士慧览:居衢已来,忽忽半载。温州诸人士屡来函,敦促朽人返彼继续掩室,情谊殷挚,未可固辞。不久即拟启程,行旅之费,已向莲花寺住持借用三十元。尊处如便,希为代偿,由邮局汇兑此数,以汇券装入函内,双挂号寄交衢州莲花村莲花寺德渊大和尚手收为祷。”请李圣章代偿他赴温州时向莲花寺住持借用的行旅之费三十元。1924年6月21日:“荷施资致返莲华,感谢无尽。”回信表示感谢。1925年1月28日,拟离开温州时,他再次致书李圣章说:“近以迁徙事,预计颇有所须,希仁者斟酌资助为感。来书乞寄温州南门内谢池里周孟由居士收下,转交朽人手收。汇款由邮局为善。”1925年2月15日收到资助,回信说:“圣章居士:顷诵惠书,并承施金三十元,感谢无尽。是中拟以八元为添换衣被等费,以二十二元为行旅之资及旅中所需也。此数已可敷用,他日万一尚有他种需要,再当奉闻。”
弘一大师持律甚严,不随意接受布施。譬如他离开青岛湛山时,向住持倓虚法师辞行时,弘一大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字条,上面开出了五个条件:第一,不许预备盘川钱;第二,不许备斋饯行;第三,不许派人去送;第四,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第五,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福建高僧释广义称赞弘一大师:“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了无余物。精持律行,迈于常伦,皎若冰雪,举世所知。此次沪上刘传声居士,探悉闽南丛林,粮荒异常,深恐一公道粮不足,未能完成南山律丛书,特奉千元供养。信由广义转呈,而一公慨然辞之。谓:‘吾自民国七年出家,一向不受人施;即挚友及信心弟子供养净资,亦悉付印书,分毫不取。素不管钱,亦不收钱,汝当璧还。广义谓:‘上海交通断绝,未能寄去。师乃谓:‘开元寺因太平洋战事,经济来源告绝,僧多粥少,道粮奇荒,可由此款拨充,经柯司令证明,余不复信,并不写信与彼,由开元寺函复鸣谢可耳。又谓民二十年间,挚友夏丏尊居士赠余美国真白金水晶眼镜一架,因太漂亮,余不戴,今亦送开元寺常住为斋粮,约计价值五百余元。该寺遵命后,闻已议决公开拍卖购充斋粮云。”确如其言,弘一大师出家后,一向不受人施,所以他每次辞行时,都是向挚友及亲近弟子自行设法筹备盘缠。从上述书信来看,1924—1927年间,弘一大师往返盘缠主要是由李圣章设法筹供的,可见两人的亲近之情。1927年以后,因史料阙如,无从得知他们的往来详情。
据李孟娟回忆,李圣章晚年仍然还珍藏着一方青洋緅绣白花、四边缝有小狗牙的小手绢。这是李圣章生母卢氏亲手缝制、送给李叔同的,而李叔同后来又交还给李圣章(李孟娟推测转交这方手绢的时间大约在1910年1月4日,即李圣章留学法国之前,李叔同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因叔侄又将离别,故有此赠,留作纪念),并告诉李圣章说:“这是你母亲当年绣给我的,她生你后就殁了,现在还给你,留着当个念想吧!”李孟娟说,他的父亲(李圣章)将一方小手绢一直珍藏了多年,一方面是纪念他的生母,同时也是忆念李叔同。
——《李叔同—弘一大师年谱长编》评介
——《李叔同——弘一大师行踪图典》评介
——《李叔同——弘一大师影像》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