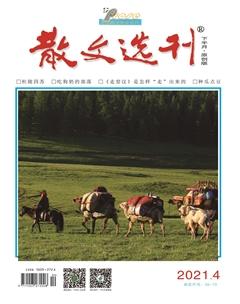老家的土炕
万有文
我的老家是一个处在祁连山下的小村庄。说起老家,让我倍感温暖和记忆犹新的就属老家的那方土炕了。
那一方土炕,曾承载了一代又一代老家人的愿望和夢想。无论是人生的畅想,还是生活的欢娱。
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从那里诞生,然后在土炕上一天天长大,像大地上的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着。有了土炕的保护,有了土炕提供的温暖,幼小的生命便成长得特别快。土炕似摇篮,在梦乡里我们听到母亲的摇篮曲,看到母亲那张慈祥的脸一次次浮现。就在那方土炕上,我们第一次笑,第一次做梦,第一次尿遗,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温暖的怀抱。
土炕似懂人情。夏天它让自己变得清凉宜人,有了疲惫则可以整个地将身心放松,躺在它坚实而平硬的后背上,疲惫顿时消散,不一会儿便可进入梦乡。而冬天,在麦草和些许的煤炭灰的熏烧下,土炕便一点点儿地温暖起来,进而整个土炕都透着人间的大暖。从小我们都有赖床的毛病,就是有土炕娇惯着,像我们的长辈一样宠爱着我们。我们当然更不想过早地从那温暖中脱离出来。因为乡村的冬天有着刺骨的寒冷,土炕成为我们躲避和防御这些寒冷的唯一去处。我们趴在被窝里,整个身体都被土炕的热量拱着,热得整个脸都红彤彤的。看着地下忙碌的母亲,为我们做饭、打扫房屋。
而在冬天,老人们也在这里找到了最终的归宿,几乎一整个冬天,他们都将自己的身体和命门交予土炕,似乎土炕可以给予他们生命的力量。在生命一天天垂危的状况下,土炕让他们减轻了日渐感觉到的冷。一整个冬天,老人们不是在暖墙弯下,就是在土炕上度过着他们惨淡的剩余时光。
而年轻人在土炕上找到的却是更多的欢乐。新婚宴尔,一场酣畅淋漓的人生大战和爱语、纠缠,与人生的瞩望,直到数月后,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落在那方土炕上,那人生的幸福和欢乐才真正地打开门。多好!添丁的热望被土炕的温暖包裹着,从此一家三口在土炕上升起的月光下幸福着。也许欢乐的极致就是幸福,而土炕正是这幸福诞生的摇篮。
两筐纹子、一筐麦草就可以保持一夜的温暖。为了让温暖更长久一些,再热烈一些,母亲还要将炉子里没有着败的煤灰,或和泥煤留下的碎块扔进炕洞里。这样,直到第二天,再填坑时,炕都是热的。那时候冬天太冷了,又没有更多的煤加热取暖,将整个房屋都烧得热火朝天。而大地上,那些麦草秸秆是富裕物,拿来填炕。在炕上的被窝里取暖,要比在房屋的火炉旁取暖更加惬意一些。因为在炕上当身体暖洋洋的舒服劲儿升起的时候,眼帘会不由自主地合在一起。那便乘着土炕的温暖,睡上一觉吧。这种自由、天性、自然、舒服的举动,是对当时乡村生活的一种诠释。在土炕上什么也不想,就那样睡着,直睡得天昏地暗。连睡梦中都能感觉到土炕丝丝的暖流正一点点儿地浸入身体,富裕权贵又如何?王侯将相又如何?那不过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还不如在这土炕上一梦长起,梦柯南山。
这多少有点儿像希腊斯多葛主义者的想法了,我想,那个时代的农村人大多都是斯多葛主义者吧。
岁月静幽。乡村生活已离我们渐渐远去,土炕仍沉静在故乡一隅,但它给我们的记忆是美好的,也是长久的。当我们拖着疲乏的身体,每天奔波于生活当中时,我们便想起了它;当更多的病痛纠缠于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起它;当人生失意落败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找到一方土炕,能躺下去,就像我们刚出生不久,在父母和土炕的怀抱里一样再撒一回娇。
只是,只是啊,时光已不再了,我们只能将记忆埋在心灵深处,一点点儿地品尝、回味、感慨,那一方土坑给予我们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