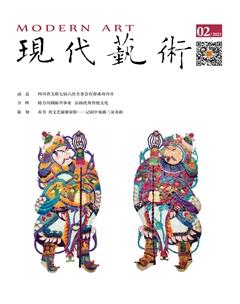春潮暗涌慢流无言
代宜纳

现就职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电视学院。
电影《春潮》自上映以后,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该片也作为2019年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的开幕影片,与众多观众探讨女性问题。影片导演杨荔纳以其真实犀利的女性叙事视角,结合多重视听语言的艺术元素将女性主义进行了创新的表达和符号性建构,引发当代人的反思。
一、“反”女性主义的创新表达
影片中,无论是郭建波所认为的父亲,还是母亲纪明岚新的老伴,都体现出男性的温柔和体贴。在郭建波的成长环境中,母亲是冷漠的,她强势地控制着家里的一切;而父亲是温柔的。当她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母亲只是冷漠地说“怎么来这个了”,是父亲教她叠纸巾,接热水给她泡脚。母亲在女儿和孙女的面前不断地诋毁自己丈夫,即使丈夫已经离世多年。她在女儿和自己的丈夫之间建立了一条鸿沟,彻底切断女儿通向幸福的可能。郭建波曾说:“我渴望躺在母亲的怀里,却只能躺在男人的身边。”由于母亲所建立的畸形的夫妻关系、母女关系,以及女儿和孙女之间的关系,都让每一个人在家庭中拼命逃离。她烧掉了她的日记,一次次地提醒女儿在她看来丈夫的种种“罪行”。越是这样,郭建波越怀念自己的父亲,当母亲躺在病床上时,郭建波以一段长达8分钟的内心独白,向母亲诉说着自己崩溃的内心,诉说着自己心里对于父亲的想念。
在这里,男性的形象反而是正面的,并不像其他影片一样将女性的悲剧命运归结为男性,而是女性之间的彼此伤害。从母亲纪明岚和女儿郭建波之间的关系,可以感受到母亲对于女儿的控制欲,以及女儿为了打破这种控制不惜毁掉自己的生活。郭建波既是女儿,也是母亲。她同时面临着父亲与丈夫的缺席,那个在她眼里完美的父亲,却是母亲口中的变态狂。而那个在他人眼中柔弱善良的母亲,却是将仇恨的心态延伸到家庭中,把家庭当作战场,对他人进行精神控制的人。影片中没有清楚地交代郭建波的父亲究竟做了什么、是什么样的人,在男性角色略显刻意的缺席中,女性角色被放大了,也体现出了导演的女性主义创作视角。
二、活在母親阴影下
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和美国女剧作家玛莎·诺曼的《晚安,妈妈》中都反映了父亲的缺席造就的变态母亲,以及扭曲的母女关系导致了女儿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女人的价值通过其母性角色以及女性气质而不断累加。但事实上这种女性气质是男性系统强加于女人的一类角色,一种形象。在这种女性气质的面具下,女人失去了自我。”在《春潮》里,郭建波有着强烈的反叛性格,但在家庭内部,对来自长辈的专断独行,她在迷茫中隐忍长大。她每一次面对母亲都是一种无声的反抗,比如影片开始,当看到母亲将社区合唱团的人带到自己家逼仄的客厅练习唱《我和我的祖国》,她先是将烟头按灭在母亲擀好的饺子皮上,接着拔掉家中刚接好的水管,来造成水漫厨房,让母亲不得已停下排练。
金燕玲所扮演的母亲形象,是父亲身份缺失的家庭中,唯一的家长,在公有领域里如鱼得水,但因个体经历的创伤,导致其在处理家庭关系时,显得无所适从,更多的是采用专权的手段。而郭建波在母亲的专权下,故意用手狠狠地抓仙人球刺伤自己,犹如生活的利刺刺痛自己一样;在母亲跟给自己介绍的对象聊天时,不断给对方发出的反抗信息,无声地向外界也表明自己对母亲的反抗;甚至连自己在工作中作为记者本能的伸张正义都要受到母亲的指责和质疑。郭建波在母亲的阴影下无论怎样逃离,而内心永远都逃脱不了原生家庭本身所带来的困境。
三、意识流书写与符号建构
影片中运用了几处符号化的隐喻,比如“水”“动物”“红衣女子”。这些都是导演杨荔纳通过符号化的建构和意识流对于女性不同的方式表达。
“水”在中西文学作品中都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传统隐喻意象,往往与女性的柔软、灵动、多变甚至年华易逝等特征形成互文关系。在电影艺术中,“水”作为女性形象的审美载体和文化联想,参与影片的叙事。影片中几次出现的“水”,都是导演赋予其更深层的意味。比如一开篇当郭建波拔掉水龙头的水管,任其水在厨房蔓延,表现出郭建波对母亲无声的指控,溢满厨房的水象征着缓慢渗出子宫的“羊水”,预示着孩子与母体的脱离,也寓意着祖孙三代盘根错节的命运羁绊。“水”在影像艺术中也可以作为爱欲的表达,以其充满诱惑性的符号语言传递男女间的亲密关系。在郭建波与男友浴室缠绵的场景中,溅起的水花,升腾的水雾,都将此时的欲望无限放大。这种符号化的建构,将郭建波的人物角色赋予了纵欲、本我和迷乱的潜意识色彩。在影片结尾,导演用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意识流表现方式,让水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漫出,按照既定的轨道分流并汇聚,最终以婉婷和英子寻找到“水”的源头,当婉婷在河水中拍起水花将影片中女性隐忍又澎湃的内心情感推向高潮,春潮暗涌,漫流无言,当冰雪融化成水汇入河海,这种顺势而流的心境犹如影片中三代女性敢于超脱男性社会与原生家庭的束缚,建构出女性精神力量的生命之潮。
在电影语言中,“动物”可以表露人类的兽性和攻击性。比如母亲纪明岚化身为“黑山羊”几次出现在郭建波的梦境中,这种符号化的建构是对郭建波儿时创伤记忆的解读,内心对母亲既厌恶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理。“鸽子”象征着纯洁和和平,郭婉婷长久生活在姥姥和妈妈的撕扯中,当她看到英子一家和谐的氛围,内心充满了无限向往。她将鸽子的羽毛刷成粉色,并放在至高无上的“女王”宝座,表现出婉婷内心深处压抑的愿望。“长颈鹿”是一种没有声带的动物,因此长颈鹿不会发声,看来很安静,而郭建波和女儿都很喜欢温和的长颈鹿。透过动物园的玻璃围栏,婉婷指着问:“妈,我特喜欢长颈鹿,你看他们像不像咱俩和姥姥?”这句指向性的提问是导演赋予这个家庭最佳的解说。面对强势的母亲,郭建波就如一只没有声带的长颈鹿,失去了发声权,无论何时都无法沟通。包括年久未调过音的钢琴发出不和谐音,也隐喻着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影片中,郭建波与盲人技师的拥抱,也隐喻着郭建波一直发出的心声:“希望你看不到我现在的样子。”影片结尾处流水的特别设计,也隐喻着流水永远经过着你不曾发现的地方,细水长流的日子,有缓、有急,最终都会汇入江河大海,找到它应有的样子。
电影《春潮》通过三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和难以沟通的境况,表现出纪明岚、郭建波和郭婉婷三个女性在原生家庭撕扯的关系中期盼精神自由的解放。看似是影片中的故事,实则化作人们日常生活中每天似曾相识的经历。就如影片海报中该片的宣传语:“你和你母亲的关系,决定着你和世界的关系。”写实的纪录,真实的表演,让观众深入其中,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