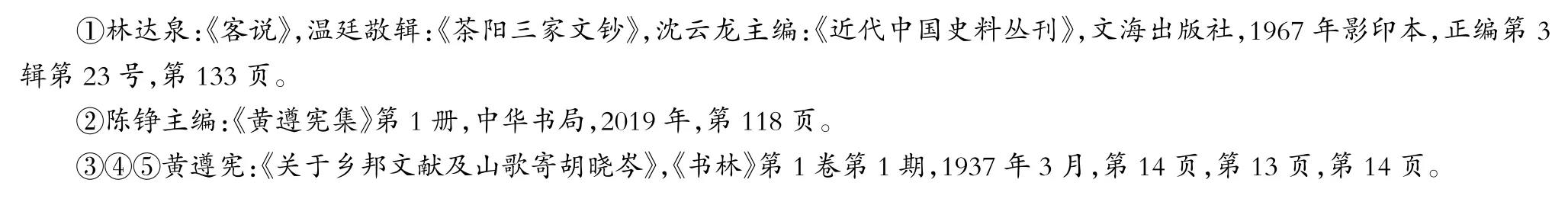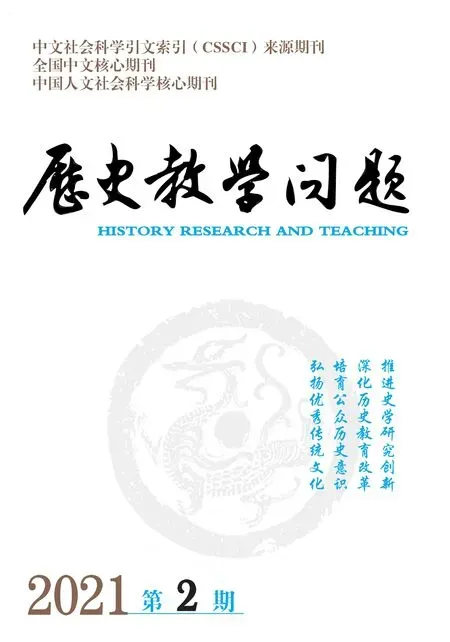传教士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
杨 扬
一、引 言
有学者在回顾现代客家研究史时强调,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专题性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是客家研究深化的一个表征。①在这些专题性研究成果中,客家妇女研究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人类学家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和历史学家谢重光的《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12—20 世纪客家妇女研究》是常被提及的两部力作。这两部力作有一共同目的,即探究客家妇女与客家文化的关系。本文所涉及的对象即传教士欧德理(E. J. Eitel,1838—1908)的客家妇女研究,也有同样的旨趣,不过却是上述两书出现疏失或未置一词的。前书虽然提到“英国人爱得尔(E. J. Eitel)在其所出版的《中日访问记录》(1870)一书谈到:‘……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越的妇女典型’”,②但是复核此话,国籍、文献形态与出版时间、引文均存在问题。后书虽然指出客家妇女“清末已引起……外国传教士的注意”,③但是翻遍全书,未见欧德理的身影。有鉴于此,本文将对传教士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做系统深入的讨论,以为当今客家妇女研究者提供一个较早且准确的学术史参考系。
上文提到,有学者在涉及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时出现疏失,故而有必要在正式讨论前做一纠正。欧德理不是英国人而是德意志人。他受巴色会派遣于1862 年来到香港,由于巴色会的传教对象是客家方言群,故而他一开始便到邻近香港的新安县客家社区传教,虽然到1865 年时因为结婚问题被迫离开巴色会加入伦敦会,但是由于他掌握的客家方言正是伦敦会的传教对象博罗县客家人所说的语言,故而他又前往博罗县客家社区传教,直到1870 年才离开此地。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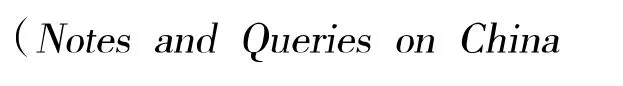
检视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相关文章,笔者并未发现“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越的妇女典型”一言。既然没有此言,那么欧德理关于客家妇女说了什么?他的目光聚焦在客家妇女与三种客家文化现象的关系上。
二、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之内容
客家风习是第一种客家文化现象。在欧德理笔下,风,即风俗(custom),习,为习惯(manner)。他在谈论客家风俗时,一上来就指出,客家人、本地人、福老人③在风俗上“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妇女”,④由此可知,他把客家妇女当作客家风俗特色的例证者。接着,他从五个方面比较了客家妇女和本地妇女、福老妇女的不同。其一,劳动分工。客家妇女是主外的,她们像男人一样负担大部分的户外工作:把重货带去市场、把干草带去炉灶、整地、挑水、到远处割草、带着农产品赴墟等。本地妇女和福老妇女则是主内的,她们除了做针线活之外,主要工作是操持家务。其二,对外态度。如果村落有洋人到访,客家妇女不害怕他,本地妇女和福老妇女则会躲在房屋门后。其三,身体形态。客家妇女即使家庭有钱也很少缠足,本地妇女则家庭小康就会缠足,福老妇女也会缠足但是没有本地妇女普遍。其四,婚姻情况。一夫多妻的现象在本地人中常见,贩卖妇女的现象则常现于富裕的福老人中,客家人较少有这两种恶习。其五,女婴命运。杀女婴普遍存在于福老人和客家人中,本地人则少有此种恶习。⑤就前四点来说,由于客家妇女自食其力、对外友好、身体少受摧残、婚姻较为简单,故而欧德理得出客家风俗“最值得赞赏”的结论,⑥反过来说,客家妇女是客家风俗美善这面的化身。但是,就第四点而言,由于客家妇女也有悲惨境遇,故而欧德理觉察到客家风俗恐怖的一面,反过来说,客家妇女也是客家风俗丑恶那面的载体。
客家妇女除了是客家风俗特色的例证者,她们也是客家习惯特点的例证者。欧德理在讲到习惯之一的打扮时指出,客家人和本地人、福老人在男性打扮上差别细微,但是在女性打扮上差别“相当明显”。⑦概言之,欧德理认为,本地妇女和福老妇女的品味完全相同,客家妇女则展现与前两者不同的原创性。⑧具说之,欧德理作了从头到脚的摹写:客家妇女用一银环把头发束紧在头的正上方,夏天时戴上一顶凉帽,凉帽中间有让发髻穿过的圆洞,发髻和圆洞配合可以把凉帽牢牢固定住,冬天时则把一块蓝布披在头上然后用棉条固定住,本地妇女和福老妇女讨厌这种头部打扮,觉得它像兽角或茶壶,她们会把头发编起来;客家妇女的肩上会垂下一片方形、扁平的小银饰,这是她们特有的配件;客家妇女外衣的袖子比本地妇女和福老妇女的窄;客家妇女会系腰带,这也是他们特有的配件;客家妇女的鞋子是圆头的且向上弯曲,本地妇女和福老妇女的鞋子则是尖头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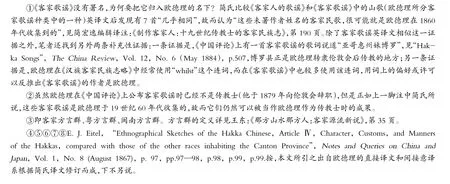
客家歌谣是第二种客家文化现象。欧德理将客家歌谣分成6 个种类,根据他给出的这6 种客家歌谣的定义或举出的对应文本,可知客家妇女是其中至少4 种客家歌谣即山歌、和歌、采茶歌、小儿歌的创作者。由于欧德理提供的和歌、采茶歌、小儿歌的文本无汉文歌词,②而山歌的文本多有汉文歌词,故而以下以山歌为例展开讨论。从山歌汉文歌词来看,欧德理呈现的客家妇女创作之客家歌谣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连情、送别、求友。
连情,指客家妇女在婚姻出现问题时口吐苦水。列三首歌谣如下:“更深深时夜又寒;苧蔴绩尽油点干。男人冇句真说话,害咱一夜门唔闩。”③“亚妹生成凤凰身:朝日担柴受苦辛。早知今日穷难过,何不当初嫁好人。”④“亚哥说话不公平。世间由命不由人。官人都系男人做:亚哥何不做官人?”⑤送别,指客家妇女因为丈夫外出谋生而心生不舍。也列三首歌谣如下:“送郎送到十里亭,再送十里难舍情:再送十里情难舍:十分难舍有情人。”⑥“送郎送到屋檐下,眼泪流来把袖遮。手中捉竟郎衫袂,问郎何日转回家。”⑦“送郎送到伯公亭:洗手烧香拜神明。烧香拜神无别意,保佑咱郎早回身。”⑧求友,指客家妇女热切希冀结识如意郎君。亦列三首歌谣如下:“日头一出炳怱怱,小妹门边种坜葱。日里愁来冇葱摘,夜里愁来冇老公。”⑨“有好日头冇好天,有好花木冇好园,有好禾苗冇好谷;有好女子冇人连。”⑩“日头一出凹里黄。那介亚姑唔想郎?枕冷衿寒犹且可,蠔情一发正难当。”①
为何连情、送别、求友成为客家妇女创作之客家歌谣的主要内容?欧德理未予解释。罗香林在客家歌谣研究的经典性专著《粤东之风》中,从普遍的人类心理与特殊的客家社会环境之结合的角度提出解释。笔者大体同意罗氏的解释,故而引用该论以供读者参考:“性的爱,是人类所同有的。有了性爱,便有欲求”,“不幸了,欲求横被障碍竟达不到,那么‘愤愤于心’,‘神志沮丧’,嗟叹哪,呻吟哪”,客家“青年男女所具有底性爱的强度,自然也是不消说的。可是一不幸受了旧礼教和旧宗法的压迫”,“夫妇间若有了不融洽的地方,也只好抱恨在心,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家长前说话”,“因此许多青年男女的性受(笔者按,应为爱),都不能于正当的地方发泄,然而又不能压迫地消灭,而且还要依物理学上弹力的定律,发出他们和她们的反抗力来,所以一片‘连情’的呼声便直破礼教的纲维而出”。“不幸受了地理上的影响,许多青年夫妻,因为要维持各人的生计,不能不频唱骊歌,住在山谷的女同胞们,更是因为常常任过苦的劳作,觉得生活枯燥,恰巧家里要叫她们上那礼纲不到的山岗上去采樵,而她们的性爱的冲动,也就使她们自然而然的发表她们求友的唱声”。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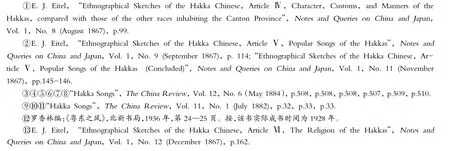
客家宗教是第三种客家文化现象。在欧德理笔下,客家妇女是客家宗教的参与者。虽然多数时候欧德理是用客家人这个不分性别的称谓来论述客家宗教的参与者,但是他还是提供了五段特别标明客家妇女是客家宗教的参与者之论述。第一段论述与佛教神祇观音有关。欧德理认为,观音在客家人中难说流行,例外是客家妇女农历每年两次去观音庙享用以观音之名奉献的施食。⑬第二段论述与客家人的迷信有关。欧德理指出,客家人的迷信起因于他们对于恶魔的持续性恐惧,为了降低这种持续性恐惧,他们倚赖宗教专家的服务,客家妇女扮演的仙婆(仙姑)就是宗教专家之一。①第三段论述与社公社母的崇拜仪式有关。欧德理看到,客家人的社公坛位于村落旁边,是露天的。农历每年仲秋和仲春,每个村落的长者会派一位信使去按家庭收钱用来买相当数量的猪肉,然后在社公坛旁边煮,如果钱是自愿捐献的就还会置些酒。当万事齐备后会敲锣打鼓以为信号,所有村民,男人、妇女和小孩,就从自家房屋赶来社公坛。他们各带碗筷,围坐在社公坛周边的草地上,如果草地潮湿,他们还会带席子给小孩坐。然后村民在一位拿着交钱名单的长者的指挥下分发猪肉、粥和酒,食物分配原则是看人数而非钱数。分到食物后,他们平静地分散到草地或围绕社公坛的树下享用它们,从吸奶的婴儿到银发的老妇女都有份,会餐通常在傍晚举行,伴着余晖,景象美妙。②
第四段论述与冥婚仪式有关。欧德理说道,客家人深信灵魂不灭和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故而如果小男孩在父母为他找到妻子之前就去世,父母会向邻居和朋友询问他们有无同龄的夭折女孩,如果有,两位夭折小孩的父母会为小孩举行庄严的订婚仪式,所有细节都仿照活人的婚礼,就像新娘和新郎都还活着一样,客家人相信这样可以结合两个小孩的灵魂,让他们不管在哪里都像有真正的婚姻生活一样。③
第五段论述与使受惊小孩康复的仪式有关。欧德理提到,如果有小孩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就突然生病,通常客家人会认为小孩受惊了,这时小孩的母亲或祖母会拿一个蛋、一碗米饭、一件这位小孩的外衣,仔细地卷起来,接着把这些东西摆在灶前属于司命灶君的神圣空间,然后她点燃乳香,重复念数次:“什么惊着小孩?求司命灶君指点保佑!”。之后,她大喊三声小孩的名字,每次都在名字后面加上“快回卧室与你父母睡”的话,在重复念着这句话的同时,她把那颗蛋、那碗米饭和那件外衣拿到卧室,然后放在靠近枕头的床架上,那里是床头亚公和床头亚婆的神圣空间,她再次点燃乳香。上述仪式会在接下来两天重复进行。第三天,在床头亚公和床头亚婆前点燃乳香后,她把盛米饭的碗和蛋打碎,碗的碎片和蛋清蛋黄被仔细地检查,然后在她的眼中显示出惊到小孩的狗或水牛或马或其他动物的形象,依照每种情况的结果,她会去拿相应动物的毛绑在小孩的身上,她相信这样会让小孩马上康复。④
三、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之价值
在欧德理之后,还有其他传教士关注过客家妇女。第一位是毕安(Ch. Piton,1835—1905)。他是法国人,为巴色会成员,于1864 年来华传教,在客家社区待了20 年。⑤他于1874 年在《中国评论》上发表《论客家人的起源与历史》一文。在文中毕安提及欧德理的《汉族客家民族志略》。该文透过客家妇女看到客家风俗的美善一面,说她们为了“下地干活和搬运重货”而“抛弃了荒谬的缠足风俗”。⑥
第二位是黎力基(R. Lechler,1824—1908)。他是德意志人,也是巴色会成员,于1847 年抵达中国,先是对闽南方言群传教,失败后转对客家方言群传教。⑦他于1878 年发表《汉族客家》一文,登载在《教务杂志》上。在文中黎力基也提及欧德理的《汉族客家民族志略》。此文留意到客家妇女反映的客家风俗的美善这面,讲她们“赴墟”“背负重货”“从山上割草以作燃料,养猪以为买卖,为全家煮饭,整地”;“不缠足”;“一夫多妻的现象”不常见。⑧此文也留意到毕安未看到的客家妇女反映的客家风俗的丑恶那面,发现“杀女婴的现象相当常见”。⑨此文还留意到毕安未看到的客家妇女参与客家宗教的情形,提及客家妇女扮演的仙婆可以帮助客家人与阴间沟通,并且以一位客家妇女“不认为此生有罪,却因为前世的行为,有些东西碍着她”的言论说明客家人相信轮回。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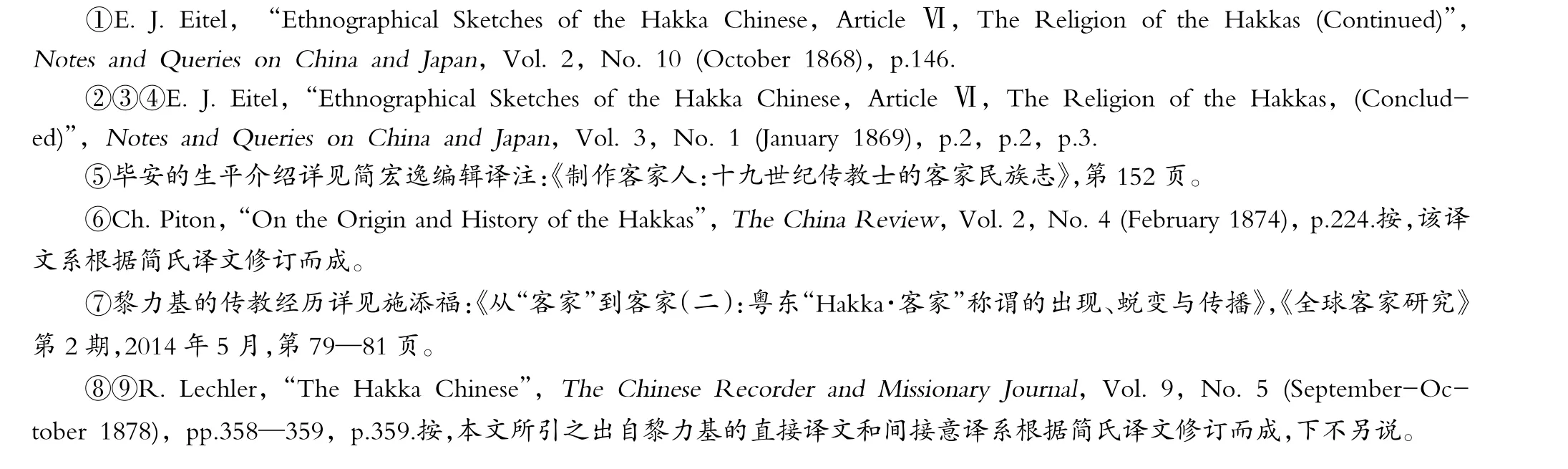
第三位是何必烈(F. Hubrig,1840—1892)。他也是德意志人,于1866 年来华传教时隶属巴陵会,到了1872 年由于巴陵会中止在华传教就转入巴勉会,在这两个会中他都是向客家方言群传教。1879年3 月,他在柏林人类、民族、史前学会例行月会上宣读《论汉族客家》一德文文章。②有学者经过对查,认为这篇文章的题材和内容类似欧德理的《汉族客家民族志略》。③在论述客家妇女与客家风俗的关系时,与毕安和黎力基的文章点到为止不同,该文详细得多。就客家妇女体现的客家风俗美善这面,他写到:“客家妇女从不抽烟与游戏,她们与丈夫一起在田里工作,把作物带到市场贩卖,在男人的社会里也行动自由。在秋冬两季,她们从山上割下干草作为燃料,一部分自用,一部分拿去卖。在没有水运的地方,你会看到一大群客家妇女扛著最重的货物走很远的路横跨山岭”;“即使是家里最有钱、身分最尊贵的客家妇女,都保持天然足,因此可以比本地人和福老人的妇女更自由地活动”,“虽然工作得比较辛苦,客家妇女作为妻子,看起来比本地人妇女更快乐,因为后者常常要跟其他的小妾、情妇、奴隶等人分享她的权利。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客家人之中比本地人来得少。有钱的客家人只有在第一个妻子没有为他生下儿子时才会娶第二个妻子,而且必须取得第一个妻子的同意,且第二位会成为第一位的侍女”。④就客家妇女体现的客家风俗丑恶那面,他说道:“很少有客家妇女会养育超过一两个女儿,其他的都在出生时就杀掉了。由此可说,几乎所有的客家妇女都可以被视为杀婴凶手。许多杀了四五个女婴,甚至有杀到十名以上的案例。杀婴通常由祖母执行。女孩也经常因为贫穷而被杀,由于父母付不起教养她们所需的花费。有时女孩则因为迷信被杀,由于父母相信可以因此招来男孩。当有越多的女孩出生,杀婴的方法也就越残酷,因为他们相信被杀死的婴儿会转世成为下一个孩子,所以越残酷的杀法能够让灵魂不希望变成女孩的样子被生下来。”⑤另外,该文也论述了客家妇女与客家习惯的关系,这是毕安和黎力基未提及的。他将客家妇女的打扮摹写如下:“发型简单,就是往后梳起来,结成球状,插上银簪”,“都会戴上银制的粗耳环”,“外衫比较长,袖子窄,领口也窄”。客家妇女这样的打扮,彰显客家人与本地人、福老人在习惯上的不同。⑥再有,该文认为客家妇女是客家歌谣的创作者,⑦这也是毕安和黎力基没发现的,不过未能给出佐证文本。又有,该文和黎力基一样给出客家妇女是客家宗教的参与者之论述,即客家人仰仗客家妇女扮演的仙姑,因为她们可以带来灵界消息、叫回逃离的灵魂(例如生病小孩的灵魂)。⑧
第四位是艾希勒(R. Eichler,生卒年不详)。他同样是德意志人,先前是巴勉会成员,其后改隶伦敦会,接替欧德理在博罗县的传教工作。⑨他于1883年发表《几首客家歌谣》(Some Hakka-Songs)一文,登载在《中国评论》上。在文中艾希勒以汉英对照的形式写出客家歌谣,这和欧德理在《中国评论》上写出客家歌谣的形式相同。此文弥补了何必烈未给出客家妇女是客家歌谣的创作者之佐证文本的遗憾,公布了内容为连情的歌谣,例如“三年唔嫁红粉女,嫁郎一朝打身体,头发松松毛又脱;啀郎追旧又贪新”,⑩也公布了内容为送别的歌谣,例如“大船拉起三张巾里;小船架桨两边摇。船上水下番娘屋,嘱咐啀连心莫憔”。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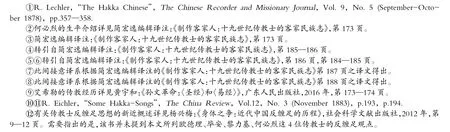
如果将这四位传教士的客家妇女研究成果合观,可以发现,他们的意图与欧德理的旨趣相同,都注目于客家妇女与客家文化的关系;他们举出的事例也多和欧德理提及的事例重合,像是户外工作、不缠足、⑫一夫多妻的现象少见、杀女婴普遍存在、外衣袖子较窄、连情歌词、送别歌词、仙婆等等;他们得出的结论亦与欧德理的三点论断一样,即客家妇女是客家风习特征的例证者、客家妇女是客家歌谣的创作者、客家妇女是客家宗教的参与者。考虑到他们都曾阅读过欧德理的客家研究文章,我们有理由认为是欧德理触发了传教士毕安、黎力基、何必烈、艾希勒的客家妇女研究,前者建构的客家妇女形象成为后者的认知模版,由此,若想明了传教士客家妇女研究的学术脉络,就必须熟悉作为起点的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
在19 世纪60 年代,欧德理不是唯一一位客家妇女研究者,因为客家知识精英也讨论过客家妇女。一位是林达泉(字海岩,1830—1878)。他在《客说》一文中以“男女皆耕织”为据证明客家风俗“勤”的一面。①另一位是黄遵宪(字公度,1848—1905)。他在《送女弟》这一组诗中一方面从“鸡鸣起汲水,日落犹负薪”等客家妇女从事户外工作的情形中得出“尤见”客家“风俗纯”的结论,另一方面也以“盛妆始脂粉,常饰惟綦巾”的客家妇女打扮让读者感知到客家习惯特点。②除了对客家妇女与客家风习的关系着墨外,他也留心采集整理客家妇女创作的客家歌谣,并在多年后将它们书之纸上,其中既有内容为连情的歌谣,例如“见郎消瘦可人怜,劝郎莫贪欢喜缘。花房蝴蝶抱花睡,可能安睡到明年”,③也有内容为送别的歌谣,例如“送郎送到牛角山,隔山不见侬自还。今朝重到山头望,牛角依然弯复弯”,④亦有内容为求友的歌谣,例如“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声声铜鼓门前打,打到心中只说郎”。⑤
将上述两位客家知识精英的客家妇女研究成果合观并与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文章比较,可以发现,后者要比前者更全面且丰富。就全面性来说,在欧德理的论述中,既论及客家知识精英提到的客家妇女与客家风习、客家歌谣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关系,也述及客家知识精英未提到的客家妇女与客家宗教这种文化现象的关系。就丰富性而言,在双方都有的客家妇女与客家风习的关系之论述中,欧德理既举出客家知识精英讲到的户外工作和打扮这两个事例,还举出客家知识精英未讲到的对外友好、不缠足、一夫多妻的现象和贩卖妇女的现象少见、杀女婴普遍存在等事例。由此,要想对19 世纪中期客家妇女的形象有清晰的认知,只知道同时期客家知识精英的客家妇女研究而不了解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我们将无法实现此目标。
在与他人成果的比较中成一家之言是学术进步的通则,故而轻视传教士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这一事实上存在的学术史参考系,当今客家妇女研究者便失去一种可供比较以彰显创新的资源,这不能不令人惋惜。希望借由本文的宣介,当今客家妇女研究者能重视传教士欧德理的客家妇女研究,通过与之比较,进而找到自己的客家妇女研究之合适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