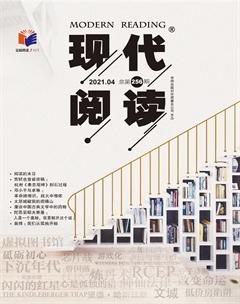阅读的末日
“为什么现在还要盖图书馆去摆书呢?”最近在一场图书馆大会,有一年轻的未来学家含笑问了这问题。
为什么还要浪费宝贵的空间去收藏无以计数的纸本印刷品呢?这些简简单单就可以贮存在一片小之又小、历久弥坚的芯片里了。硬是要读者出门走远路到图书馆,先是要等,看看要的书在不在,要是在就还要自己扛回家,借阅期限还不长,何必呢?有成千上万本书,离家最近的图书馆未必找得到,何必就此害得读者看不到呢?既然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都可以尽数收纳在指尖之下,任你随地随时选取,那又何必非要面对酸雨腐蚀、装帧破损、墨水褪色、虫蛀、盗窃、水火等威胁呢?其实,我们所知的阅读如今已经不再是普遍的需求了,图书馆应该扔掉那些娇贵但过时的文本载体,也就是大家叫作“书”的东西,一口气全部改用电子文本,就像先前扔掉了泥版、羊皮纸卷而改用册子本。大势所趋,就应该坦然接受:古腾堡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了。
该说不幸,还是该说大幸,我转述的这一段发言,是建立在误解之上。无论读者身在何处,零落星散的天下图书无不可以重现在读者面前,无所遗漏。可是,书籍相较于电子记忆库,就像电子记忆库相较于人脑记忆库,即使负载的是一字不差的文本,却是不同的东西,各有不同的特性。我在《圣奥古斯丁的计算机》一书提过,这些工具不属于同一种类,各自的特性在供我们认识世界时发挥不同的效用。所以,任何逼我们消灭其中一种的反对声音,都比错误还糟糕。如今,拜电子科技之赐,弹指便找得到只记得半句的斯塔提乌斯的名句,转眼也找得到柏拉图深奥的信笺一读,这些事几乎没有谁做不到,还完全不需要像圣哲罗姆一样满腹经纶。只是,拿起有折角做记号的书上床,重拾已经读得滚瓜烂熟的旧书,在页缘的旧批旁添加新解——这些兴味,便有赖书册至今阴魂不散,几乎所有人尚得以寻觅。每一类技术皆有利弊,所以,放下以电子文本消灭印刷纸页的变革大旗,深入探讨各类技术各自的利弊得失,恐怕更为有益。
传统的图书馆依其本性,恐怕就不同于人脑,载体比不上内容的野心。科学研究说人脑的神经元能够贮存的知识,不管怎么塞,空处始终多到数之不尽。人类脑叶的迷宫里,一列又一列無法丈量的长串书架沿着秘密的走廊延伸,其中许多书架在我们一生中都是空的——害得图书管理员失去了他们众所周知的沉着,燃起了一肚子理所当然的嫉妒。我们从生到死不断累积字句与影像、情绪与感觉、直觉知识与理念,不断汇集我们对世界的记忆。然而,不论我们自认在脑中强塞了多少经验,人脑始终还有余地再作填塞,恍若那一种叫重写本的羊皮纸卷,新的文本可以复写在旧的上面,如此重复不断。波德莱尔于1869年便问过:“人脑若非漫无边际的天然重写本,又是什么?”人脑图书馆便像波德莱尔几乎看不到尽头的重写本,找不到边界。然而,砖石、玻璃盖成的图书馆内,社会记忆的贮藏室始终不够大,纵使官僚钳制,精心挑选,经费又短缺,还有意或无意毁损,众人希望流传后世的图书却始终不够地方放。为了解除这一层束缚,我们拜科技所赐,创立虚拟图书馆,贮存空间因之扩展至近乎无限。可是,连这样的电子方舟为后世抢救的文本,也不过区区几类形式。在这般幽灵似的图书馆内,文本的具体化身被扔下不管,文字的血肉因之荡然无存。
虚拟图书馆有其优势,但这不表示实体图书馆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不管电子产业如何致力于说服我们相信相反的观点,不管谷歌等一众数据科技企业如何费尽力气表示他们在做慈善而非剥削智慧遗产,都无法抹杀这一点。世界数字图书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及其他国家图书馆多方合力支持的国际机构,进行的工程极其庞大、艰巨,虽然部分资金出自谷歌,(目前)尚未沾染商业利益的纠葛。只是,即使如此卓越的虚拟图书馆当真建成,传统图书馆依然不可或缺。电子文本是一回事,内容完全相同的纸质印刷书又是另一回事,二者无法相互替换,一如一句诗行的录音无法取代深植个人脑海的同一句诗行。一份文本的背景脉络、物质支持、具体历史和经历,一如文本的语汇、音乐性,都属于文本的一部分。紧扣字面意义而言,物质并非无关紧要。
在任何以有文化自居的社会,传统图书馆的问题——存偏见的选书、带主观色彩的分类、层层分级的编目及隐含的审查工作,还有存档和流通的责任——都依然是重要问题。我们的心灵图书馆的困扰,是知道所有没有读过的书,我们都没有权利说是我们的书;而集体记忆的图书馆的困扰,则来自图书管理员们未曾青眼有加的所有图书:被排斥、被丢弃、被限制、被轻视、被查禁、没人爱、没人理的书。
我们的知识活动便由这样的钟摆运动在主宰,而且,还有问题好像在随钟摆滴答不断回响,既问感叹时间太少的读者,也问感叹空间太小的读者所属的社会:世人读书,所为何来?为何总想知道更多,知识的探索不断朝永在后移的天际线推进?探索得来的战利品,又为什么要收藏在砖石盖的图书馆库房和电子记忆库中?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前述未来学家急切提出来的问题,可以再往下深挖,而且,不是再问阅读何以走到穷途末日(这是自证的假设),而是要改问何谓阅读的末日穷途。
于此,以我个人为例,说不定有助于我们检视这个问题。
2008年圣诞节前两周,我忽然被告知说我需要动紧急手术,而且,紧急到没有时间让我收拾住院所需的东西。我就这样躺在陈设简单的急诊室,又别扭,又紧张,手边除了那天早上正在读的书,没有别的。那是塞斯·诺特博姆写的怡人小说《荷兰群山》,在接下来的几小时内,就被我读完了。之后,一连14天都要待在医院养病;没有东西可读,对我可是天大的折磨。所以,当我那另一半提议从家里的书房挑几本书带给我,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也很感激。只是,该挑哪几本好呢?
《传道书》的作者,还有皮特·西格,都告诉过我们:万事万物各有其时。同理,我不妨再加一句,天下之书一样各有其时。人生走到某一当口,我们挑来作伴的书为什么是这一本,而不是那一本呢?王尔德在雷丁监狱开出的书单,有斯蒂文森的《金银岛》和一本法语—意大利语会话入门书。亚历山大大帝四处远征,行囊里有荷马的《伊利亚特》。杀害约翰·列侬的凶手预谋行凶的时候,认为随身带着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相当适合。而航天员进行太空探险,会带雷·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编年史》呢,还是觉得纪德写的《地粮》反而更好?伯纳德·麦道夫先生入监服刑,会向狱方索阅狄更斯写的《小杜丽》吗?《小杜丽》中的莫多尔先生侵吞公款东窗事发之后,无地自容,可是拿借来的刀片刎颈自杀的呢。教皇本笃十三世可会带着夏尔-路易·菲利普写的《蒙帕纳斯的蒲蒲》回到他在圣天使堡的书房,去研究何以少了保险套会害得巴黎在19世纪惨遭梅毒肆虐?讲究实际的切斯特顿也想过万一流落荒岛他要带什么书:简单一本造船手册便好。同样的状况,要是教儒勒·列那尔碰上了,他可就没那么讲究实际,他选的是伏尔泰的《憨第德》和席勒的《强盗》。
那我呢?在我流落医院斗室期间,我认为哪几本书最适合与我为伴?
我虽然认为虚拟图书馆有其明显可见的大用,但我自己不用亚述泥版在现代的化身——电子书,也不用小人国的iPods,更不用怀古风的掌上型游戏机。我的看法和雷·布拉德伯里的说法一样:“因特网是玩物丧志的玩意。”我习惯的是书页的空间、纸、墨的“血肉之躯”。我在心里盘点了一下家里堆在床头的书,我需要的不过是相当于“安慰餐”的书:以前就很爱读,可以轻松地多次重读,可以只为得到乐趣而读,同时又能点亮心中的明灯,维持大脑灵活运转。所以,我便要我那另一半为我带上下两册的《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正是忍受痛苦的完美典范——枯等别人来在我身上又戳、又扎、又下药的时候,随手翻开《堂吉诃德》,不管哪一页,都找得到那位博学的西班牙老兵,以亲切的嗓音安慰我,要我放心,不管什么事,最后都会转危为安。由于从少年时我便不断回头重读《堂吉诃德》,所以,我知道《堂吉诃德》曲折离奇的情节不会绊倒我。也由于《堂吉诃德》单单是看情节想象之妙,单单是看故事如何推进,便趣味无穷,不用去钻研、分析其中的谜团和离题的枝节,因而可以安心随叙事的流动漂移,追随高贵的骑士和他忠心的仆从桑丘而去。
卡雷尔·恰佩克在他谈花园的精彩著作当中,说园艺这一件事的奥妙,可以归结为一条规则:耕耘要大于收获。藏书的规则,亦复如是。
实体世界的每一座图书馆内的藏书,都取决于前人的阅读。追根究底,这种“创造性诠释”——随读者个人的经验、好恶、直觉、知识去了解一本书——便是读者无上权柄的所在。读者的权柄无法遗传,只能学习。虽然人生在世就是要在万事万物当中找寻意义,在姿态、声音、色彩、形状当中解读意义,不过,破解社会通行的沟通密码,依然是要学习才能掌握的技巧。用字、语法、意義的层次、文本的摘要和比较,诸如此类,都是要别人教才学得会的本领;这样,进入社会大家庭的人才能拥有完整的阅读力。不过,练就阅读力的最后一步,也就是在书册里发现对自己人生经验的记录,却只能靠自己单独来练。
只是,一般人却不太重视这样的本事。从远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士精英学校到西方中世纪的修道院、大学,深入极致的阅读始终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后来到古腾堡活字印刷的年代乃至网络时代,文本不断流传扩散,但阅读的情形亦无甚改观。没错,在我们这时代,世人绝大多数都说不上是文盲,都还看得懂广告,订契约时也会签自己的名字。只是,单单如此未足以成为读者。阅读这样的能力,指的是钻进文本当中,以个人才具的极致,在字里行间深入探索,再于重建的过程当中,重新将文本纳为己有。不过,练就这本事,路上的障碍可是形形色色多得很。正因为阅读赋予读者权柄,诸多主宰我们的政治、经济、宗教体制,最怕我们拥有这类想象的自由。最佳的阅读,会导向反省和质疑,反省和质疑又会再导向反对和改变。不管哪一社会,这可还真是危险。
如今,图书管理员愈来愈多地遇到一个棘手问题:现在进图书馆的人,阅读能力都嫌不足,尤以年轻一辈为然。他们找得到电子文本,看得懂电子文本,也有办法拿几份网络文本剪贴重组成另一份文本。但是,对于一张印刷纸页上表达的意思,他们好像没办法作品评、批判、注解,也记不下来。电子文本唾手可得,太过容易,导致使用者产生错觉,以为不需要渡过学习的难关便可以据为己有。阅读的宗旨,他们浑然不知,所剩者,搜集信息而已,有需要时再加以运用。
阅读绝非取得文本便告了事。电子文本吹嘘的包容力,反而害得电子文本难以让人充分理解特定的意思,难以透彻探索特定的页面。面对电子屏幕上的文本,读者的工作不像实体书的文本那般明确,毕竟,实体书的文本有页缘和装帧划出的界线。
“无不唾手可得。”这是一款手机打出的广告词。这款手机可以照相、录音、上网、传送文本文件和图片文件、收发短信,当然,还有打电话。不过,所谓的“无不”在此却岌岌可危,因为“无不”和“无一”只有一步之隔。所谓“习得”一样东西(而非任何东西),向来需要挑选,不能单靠无限量供应。观察、判断、选择,需要练习才做得好;责任感,甚至道德立场也是如此。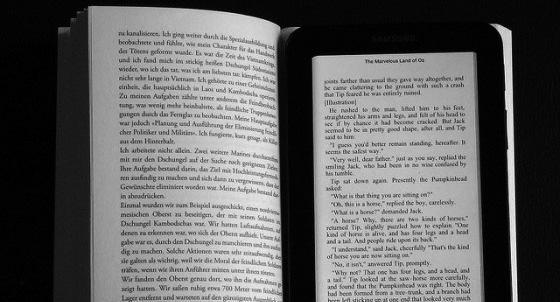
人类于其历史的某个点,在发明出一套符号供共同读写之后,有一天发现,由一位或许隔着遥远时空的作者写在泥版或是莎草纸上的文字,传达的不仅仅是通用符号中所表明的事。当初这一段文字所指,出于某人的意志和智慧,后人已经看不见了,所见者,换成读者经验中熟悉或揣测的。在那一刻,读者发觉社会选择用来沟通的工具,也就是语言所用的文字,并不确定,也不清楚,而且模棱;不过,文字的威力,就在于不确定、不清楚、很模棱,就在于文字有魔法赋予名状,却又不以名状作囿限。远古有人写下“山羊”或是“作战”,心里要的意思必然十分明确,然而,如今的读者会在文字明确的意涵之上,添加千百万头山羊的映像,添加可能出现的和平回响。每一份文本既然是由文字构成,除了说出作者原本要说的意思,也说出了作者从没想过的意思,连篇累牍。日后还会再有读者继续连篇累牍地汇编、搜罗。有的具体形诸明文而再衍生其他文本,有的则写于半梦半醒之间,流变不定,替换不休,汇聚于心灵的图书馆。
我对我的《堂吉诃德》感激不尽。住院两周,上下两册始终在我床边守候。我需要解闷时,它们便对我讲话,逗我开心;不然就静静地等在我的床边,凝神伺候。它们从来不会不耐烦,也不会唠叨说教,或是颐指气使。两册《堂吉诃德》的对话起自好几世代之前,它们对时间仿佛无动于衷,仿佛笃定眼下这一刻也会过去,它们这位读者的不适、焦躁会过去,而且笃定这位读者的书架只会保留他记得的书页以之自况,以之描述切身幽暗的心灵角落、无法自剖的角落。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的读者》作者:[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译者:宋伟航)